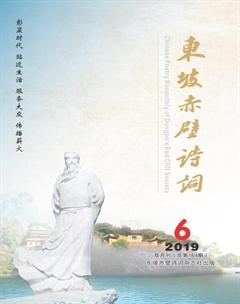張其俊教授的詩學特色
張其俊同志是位大學教授,博古通今,識兼中外,可謂學富五車、胸藏萬卷。他不僅擅于學術研究,而且長于詩文創作。張教授主要從事教育工作,在職時,創作只能作為業余愛好;退休后,則全力投入詩文寫作,飽享寫書出書之樂。唐代白居易晚年有詩道:“新篇日日成,不是愛聲名。”(《詩解》)張教授致力于詩論研究,沉迷于詩文創作,雖然碩果累累,卻都不是為了求取聲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重利輕文。即使佳作連連,也不大可能聲名鵲起、一夜走紅。恰如詩圣杜甫詩說:“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即然如此,那就不能奢望寫作能給自己帶來什么更大聲譽。借用兩句古詩:“如今不重文章士,莫把文章夸向人。”
然而,張教授仍然樂此不疲。難道寫作會有利可圖嗎?非也。詩仙李白也有詩說:“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現代社會有所進步,詩文偶爾或有稿酬,盡管微不足道,倒也聊勝于無。但如依此為生,那就難免陷入凍餓;倘若賴以發財致富,則更是緣木求魚,南其轅而北其轍了。唐代司空圖說:“自古詩人少顯榮,逃名何用更愛名。”(《白菊三首》)顯赫榮耀,輪不到詩人;尊崇富貴,數不上論者。縱然著作等身、汗牛充棟,也照樣窮困潦倒,貧寒相伴,即所謂“千首富,不救一生貧”(宋戴復古《望江南》)宋代陸游詩說:“詩家事業君休問,不獨窮人亦瘦人。”(《對鏡》)由于勤奮筆耕,累得形銷骨立、體瘦如柴,詩人文伯多半只能困厄終生。
顯而易見,張教授沉于寫作,既不是為著求名,也不是希圖謀利,而是因為他熱愛教育事業,鐘情詩文藝術,為了傳播知識,宣揚真理。退休之后,他雖然不再教書,但是育人工作從未稍停,只是方式略有改變:不在教室里授課,而在研討班講座,或在報刊上發表高論;傳授對象也有不同,不再限于莘莘學子,而擴大到了蕓蕓眾生,詩詞老人、普通作者居多。
文人愛文,猶如戰士愛槍。農民愛地,順理成章,天經地義。更何況張教授愛詩成癖,為文入迷,已經到了如醉如癡、欲罷不能的地步。而且寫作雖然苦不堪言,卻也樂在其中、妙不可言。尤其是人到老年,依然能夠文思似水、佳作如泉,所謂“不堪歲月如流水,賴有文章似涌泉”,實在是種幸福,自然讓人甘之如飴、樂不可支。古人都有這種體驗:“相門相客應相笑,得句勝于得好官。”(唐鄭谷《靜吟》)“詩萬首,酒千觴,何曾著眼看侯王。”(南宋朱敦儒《鷓鴣天》)“高聲味一篇,悅若與神遇。”(白居易《山中獨吟》……有此樂趣,誰肯棄之?!
如今,張教授已年過八十,卻照舊身強筆健,詩興還濃,文思尚酣,仍處于“身處無余事,唯應筆研勞”(唐張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之際,時不時地便有論發于心中。文成筆下,吐納珠玉之聲;動天動地就會吟出肺腑,詩凝紙上,舒卷風云之聲。現在,張教授將其詩文匯編成集,真可謂窮畢生之力,極筆墨之初,建詩文之廈,為美麗之觀。盡管其學術范圍廣泛、研究內容豐富、創作詩詞眾多,還是其詩學理論。文章超過千篇,心血耗盡半生。其文,說理透徹、深刻,見解新穎、獨到,既有學術性,又有實踐性,堪稱鏘金鏗玉,能夠震聾發聵,可以醫愚啟智、雅俗共賞。
張教授的詩學理論,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微宏兼備、古今結合、中外交融。所謂微宏兼備,即他談詩論藝,往往能從微觀分析入手,引申至宏觀闡述;也就是將具體議題的微觀層面,升華為理論闡述的宏觀把握。如他賞析具體詩歌作品的一趣一味和一技一藝,由此論說詩學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把作品剖析與理論闡釋聯系起來,讓人以小見大,由微知宏。如同觀賞一雕欄、一畫礎的細部,從而領略一大廈、一高閣的全貌。所謂古今結合,即他善于將古典詩論和當代詩學結合起來。我國歷代詩話、詞話、曲話、藝話等等多不勝數,論詩談藝,遺產豐富,只是大都屬于片言只語,零縑散珠,不成系統。張其俊教授十分重視繼承開拙這份寶貴資源,能夠運用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辨證思維,對之進行認真研究,汲取古典之精髓,熔為現代之詩學;也就是將我國的古典詩說予以當代化。所謂中外交融,即他努力學習、借鑒外國詩論、文論的優長,并與我國古今詩論對比考量,去偽存真,刪繁就簡,批判借鑒,取長補短,引進外國之精華,鑄成中國之詩學;也就是把外國的詩歌理論加以中國化。可以說,張教授在微宏兼備,古今結合、中外交融方面,為中華民族詩學理論的健康發展做了有益探討,取得了可喜成果和重要創獲,能夠自成一家之說。
總而言之,張其俊教授的詩學研究富于理論勇氣和學術價值,令人欽佩,應予重視!
2019年4月21日至28日于浙江杭州創作之家
(丁國成,原任中國作家協會五、六屆全委委員,《詩刊》常務副主編,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常務副主編,《詩國》主編。現為中國作協九屆名譽委員、中華詩詞學會顧問,編審,享有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