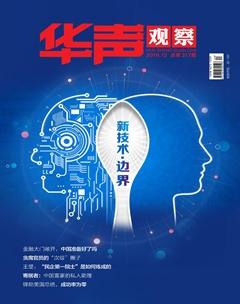歷史中的“首級文化”令人瞠目結(jié)舌
夏安

“推出去斬了”這句經(jīng)典臺詞,一直是大眾對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典型印象。就中國而言,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下,對于頭顱的用法和象征各不相同。有的頭顱被奉為國寶,有的頭顱被當(dāng)作“計數(shù)器”,有的頭顱作為珍貴的盛酒器皿,有的頭顱作為征戰(zhàn)殺伐的象征……可以說頭顱在歷史長河中逐漸變成一種人類獨特的符號文化。
王莽的“國寶腦袋”
西晉時期,洛陽武庫的一場大火引起了三件累世之寶的覆滅——孔子的草鞋,劉邦的銹劍,王莽的頭。
王莽篡漢后,建立新朝,沒過幾年就在他失敗的改革中覆滅了。而王莽也死于亂軍之中,當(dāng)時他身上的兩件寶貝獻給了勝利者,一件是秦始皇的傳國玉璽,另一件就是他的腦袋。
傳國玉璽象征著正統(tǒng),在之后的亂世中,誰搶到此物,誰就象征著天命所歸。但王莽的這顆腦袋,起初傳給人民展示觀看,起到警示作用。以為是一時之用,但沒想到統(tǒng)治者將這顆腦袋煮洗腌臘保存了起來,在亂世的傳遞中,漸漸也變成了政權(quán)傳遞的正統(tǒng)象征。
東漢光武帝保留這顆頭,本意是為了告誡朝臣宗親謀逆者的下場,并以此為戒,永葆漢王朝流傳下去。誰知在之后,傳著傳著此物竟成為東漢王朝的傳世國寶。王莽的頭顱從劉玄、劉盆子、赤眉綠林、劉秀、曹丕再傳到司馬家族,不管是漢室皇親還是亂臣賊子,都以繼承此物為榮。這顆頭從王莽的腦袋上摘下來后,逐漸符號化,一代又一代的人賦予它意義,這不免充滿了諷刺意味。
一顆被砍下的頭顱可以代表很多東西,如樊於期的頭是通行證,關(guān)羽的頭是政治禮物;宋理宗的頭是宗教信物;智伯的頭是值得炫耀的戰(zhàn)利品。不同時代、不同地點、不同階級,頭所代表的意義與頭主人密切相關(guān),是頭主人生前影響力的延續(xù),間接反映了勝利者對死亡的態(tài)度。
羞辱的“尿盆腦袋”
春秋末期三家分晉之前,一場晉陽之戰(zhàn)奠定了趙、魏、韓的歷史地位。當(dāng)時晉國最大的勢力智家,以智伯為核心,脅迫韓、魏兩股勢力一起攻擊趙家。趙家在艱苦奮戰(zhàn)后,策反了韓、魏兩家,反擊打敗了智伯,并瓜分了智家的領(lǐng)土,滅了智家滿門。
但在智家的門客中,有位叫作豫讓的人,決心為智伯報仇,刺殺趙國之主趙襄子。豫讓隱姓埋名,自我閹割,凈身進入趙家,成為了趙家內(nèi)院的雜役。費了這么大勁兒,他卻主動選擇去做了趙家的廁所清潔工,行刺地點也選擇在廁所。
但刺殺終究還是被趙襄子發(fā)現(xiàn)了,不過,趙襄子念他是個義士,為故主舍命行刺,錚錚鐵骨,便放了他,將他驅(qū)逐出趙府。之后豫讓屢次刺殺趙襄子,都未能成功。最后已經(jīng)厭倦的趙襄子讓豫讓在他的衣袍上刺了三劍,象征性地協(xié)助豫讓完成了使命,讓他為智伯報了仇,豫讓在感慨中自刎,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史記·刺客列傳》中司馬遷著重描寫了這段有情有義的故事。
豫讓費了這么大的勁兒,為什么要選擇在廁所下手?一來,廁所不好得手,地方狹小躲藏的空間不大,還有侍衛(wèi)跟隨;二來,他作為被閹割的趙家內(nèi)侍,本可以爭取更貼身的職位,非要當(dāng)廁所清潔工,不免讓人覺得蹊蹺。
司馬遷在《史記》中交代了這么一句:“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選擇在廁所的關(guān)鍵點,回到了頭顱上。以仇敵的頭顱作為盛酒容器,在野蠻的民族中盛行,一些古籍記載中也證實此事。但對于智伯的頭顱的記載并非只有一個版本,在有些版本中,智伯的頭并不是用來當(dāng)作酒器,而是當(dāng)作溲器,也就是尿壺。趙家長期與匈奴人打交道,之后的趙武靈王還掀起了“胡服騎射”的改革,所以在風(fēng)土習(xí)氣、宗教文化等方面和匈奴長期互動交流,互相學(xué)習(xí),互相影響。
在曾為趙國國都邯鄲的澗溝村夏家店下層時期(前2000年至前1500年)遺址中,通過考古在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被斬首、剝皮后的四個頭骨,可見在趙國早已有這種對頭顱殘忍的處置方法。所以,也很難去說究竟是誰影響了誰。但可以肯定的是,趙襄子和智伯結(jié)怨已久,無論從身份還是實力上,趙襄子一直被智伯欺壓。當(dāng)智伯被打敗后,趙襄子的一腔怒火全發(fā)泄在了智伯的這顆頭上。
當(dāng)腦袋成了“計數(shù)器”
當(dāng)統(tǒng)治者將頭顱賦予貨幣一樣計數(shù)的功能時,“首級”一詞便誕生了。
商鞅變法前,秦國就已有在戰(zhàn)場上割頭的習(xí)俗。變法后,秦國則第一次用規(guī)章制度將割首與計量、榮譽、官爵、財富等聯(lián)系起來。首級拆開來,“首”就是人頭,“級”就是爵位級別。隨著戰(zhàn)爭規(guī)模的擴大,在戰(zhàn)場上人頭成為最方便的、最有效的戰(zhàn)功計量單位,財富與血腥直接刺激了士兵們的殺戮欲。
秦國的爵位在商鞅的改革下,與軍功、首級牢牢掛鉤,嚴(yán)格規(guī)定斬首數(shù)量與所獲爵位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甚至還有最低斬首數(shù)量的要求,沒砍夠腦袋還要受罰。“其戰(zhàn)也,五人束簿為伍;一人死,而剄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fù)。”如果有人一場戰(zhàn)斗一顆腦袋都拿不回來,便與其捆綁的其他下級軍官一并斬首。
在商鞅的改革下,秦國顛覆了傳統(tǒng)的貴族政治,一時之間改變了秦國的面貌,戰(zhàn)斗力激增,成為其他六國所懼怕的“虎狼之師”。在這個制度之下,將士為了邀功,往往會濫殺平民,所過之處就像蝗蟲過境,沒有人能保留個全尸。在嚴(yán)苛的秦法下騙財騙爵猖獗,為了冒領(lǐng)功績而互相殘殺,秦國為后世開了個頭兒,之后的發(fā)展更是出乎人們的意料。
宋代,經(jīng)濟高度發(fā)展,銀錢流通頻繁,出現(xiàn)了“銀行”。人頭和軍功這門“生意”在發(fā)展后,也出現(xiàn)了“人頭銀行”這種奇怪的產(chǎn)物。
宋神宗時開西北邊境,主持軍事的王韶為了虛報戰(zhàn)功濫殺藩民。為了照顧投靠自己的親友老鄉(xiāng),他讓下屬四處抓羌人藩民,將他們像牲口一樣養(yǎng)起來。平時攢著,在上級需要人頭立功的時候,再拿出取頭使用。
在首級與軍功的關(guān)系中越來越功利,充當(dāng)沒有感情的計數(shù)單位和通往富貴之路的鋪地磚。
千百年來,頭顱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文明還是野蠻,地位一直是尊貴且重要的。在古代各種嚴(yán)刑峻法層出不窮,但是砍頭這個懲罰方式卻極為牢固,存在了有千年之久。除了實施方法簡單、便捷外,頭顱所代表的社會符號和在個體中所占的地位一直是有著廣泛的共識,是死亡與恐懼最具代表的象征。正是這個矛盾沖突最為明顯、表現(xiàn)最極端的事情,橫貫了整個中國歷史,在人類史中,直到現(xiàn)在的文明社會砍頭、殺頭也會被一些野蠻的組織所使用。這背后的傳承性和與人類對自我認知的巨大共性值得深思。
摘編自《北京晚報》2019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