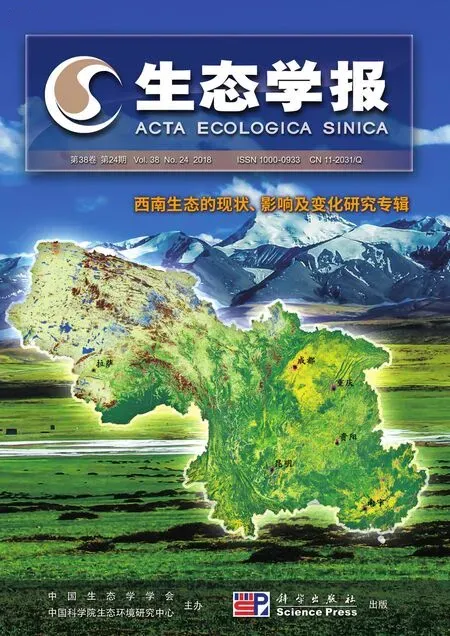基于多風險源脅迫的西南地區生態風險評價
王慧芳,饒恩明,肖 燚,*,嚴 巖,盧慧婷,朱捷緣,
1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5 2 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049 3 四川師范大學地理與資源科學學院,成都 610000 4 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城市環境與健康重點實驗室,廈門 361021
生態風險是指一定區域內自然災害和人類活動形成的多種脅迫因子對復合生態系統造成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包括生態系統內部某種因素或整體的健康、生產力、遺傳結構、經濟價值和美學價值的減少[1-2]。生態風險評價是運用生態學、地理學、環境學等多學科知識,采用數學、GIS等技術手段來預測和評估風險源對生態系統造成損害的概率和程度,是根據有限已有資料預測未知后果的過程,對區域生態安全建設、資源管理具有重要的指示意義[3-5]。
20世紀末期生態風險評價由化學污染物風險評價、人體健康風險評價轉向區域生態風險評價,并與景觀生態學與流域生態學結合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評價對象從單一的個體、種群擴展為區域,評價內容由最初的單因子單風險評價、多因子單風險評價逐步向多因子多風險評價演化[6-7]。目前,國內外學者運用相對生態風險模型(RRM)、USEPA模型、遙感和GIS空間分析等技術對區域生態風險進行研究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如Angela M和Suzanne M運用相對風險模型[8-10],通過分析風險源與風險受體之間的關系,對科多羅斯河流域及俄勒岡朗德河流域進行了生態風險評價。盧亞靈運用USEPA模型,采用風險受體分析—風險源分析—生態系統易損性分析—風險表征的思路對渤海五省進行風險評價[1]。許妍、張雅洲、許工學等利用遙感與GIS技術對太湖流域、南四湖、遼河三角洲進行了生態風險評價[11-13]。但由于區域尺度大且生態系統復雜,評價過程中風險源危險性及各指標的計算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西南地區位于我國三大災害帶中沿江災害帶與山前災害帶的交匯部位,特殊的地形和多變的氣候以及快速的城鎮化使生態系統面臨著多種風險源的脅迫。本文以西南地區為研究對象,從風險源危險性、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度、生態系統易損性3個方面分別建立單一風險評價模型,利用GIS空間疊加分析對區域綜合生態風險進行計算。研究結果可為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和環境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西南地區包括四川、云南、貴州、廣西、重慶五省以及青海和西藏的部分縣市,總面積217.8萬km2。該地區處于我國第一階梯和第三階梯的過渡帶,以高原、山地和丘陵為主,地貌類型多樣,地形高差懸殊,是我國地形最復雜的地區[14]。境內有雅魯藏布江、金沙江、怒江、瀾滄江及長江等重要水系,氣候類型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和高原山地氣候,年均降雨量20—2100 mm,降水時空分異較大,主要集中在5—9月。生物種類和生態系統類型豐富,約有20000多種高等植物和2000余種脊椎動物生活在此,北半球主要生態系統均可以在這里找到(圖1),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和生態脆弱區。

圖1 研究區生態系統類型 Fig.1 Ecosystem types in the study area
1.2 數據來源
生態系統類型數據(30 m)來自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氣象數據來源于中國氣象局氣象中心;DEM(30 m)來自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土壤數據來源于基于世界土壤數據庫(HWSD)的中國土壤數據集(http://westdc.westgis.ac.cn);地震頻率數據來源于中國地震網;氣象災害數據來自中國氣象災害大典;人口數據和GDP數據來自2015年各省統計年鑒。所以空間數據分析前統一投影方式為WGS_1984_Albers,數據精度均重采樣為250 m×250 m。
2 研究方法
基于西南地區的本底特征,將風險源分為自然災害風險源和人類活動風險源,選擇森林、灌叢、草地、濕地、農田、裸地、城鎮7類生態系統為風險受體,從風險源危險性、生態系統易損性、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度三個層面構建風險評價模型[1,15]。其中風險源危險性通過相關影響因子進行定量評估所得,生態系統易損性由環境脆弱性和景觀結構脆弱性構成,生態系統潛在損失用生態系統質量表征。風險計算公式為:
Ri=Di×Vu×Va
式中,Ri為第i種風險的風險值,Di為第i種風險源的危險性,Vu為生態系統易損性,Va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先對單一風險進行評價,把各風險評價結果分為少風險、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4個等級,通過GIS空間分析得到西南地區綜合生態風險等級。
2.1 風險源危險性(Di)
風險源指可能對生態系統造成不利影響的一種或多種風險來源,包括自然災害和人類活動兩大類。本文選取干旱、洪澇、地震、滑坡、泥石流、石漠化、水土流失為自然災害風險源,其中干旱、洪水、地震危險性用近50年來災害發生的頻率表示,滑坡[16-17]、泥石流[18-21]、水土流失[22-27]、石漠化[28-31]危險性用敏感性評價結果表征。人類活動風險源選擇人口壓力、經濟壓力、水污染、土壤污染四類,人口壓力和經濟壓力危險性用人口密度和GDP密度表示,水污染、土壤污染危險性通過相關影響因子定量評估所得[32](表1)。

2.2 生態系統易損性(Vu)
生態系統易損性表示風險源脅迫下生態系統表現出的易損程度,易損性值越大,生態系統穩定性和抵抗外界干擾的能力越弱。本文從環境脆弱性和景觀結構脆弱性兩面入手,環境脆弱性考慮地貌、地表、氣候和人口4類指標[1],其中地貌因子包括高程、坡度、起伏度,地表因子用植被覆蓋度表示,氣象因子以干燥度指數表征,人口因子用人口密度表示,首先將高程、坡度、相對高度進行加權疊加,得到地貌環境脆弱性。再將地貌、地表、氣候、人類影響因子進行加權疊加得到環境脆弱性結果[33]。景觀結構脆弱性選擇斑塊密度、景觀分離度、景觀干擾度3個指標,計算各類生態系統3個景觀指數后,分別對所獲得景觀指數標準化,計算其平均值[34-35],然后將結果賦給各個生態系統類型得到西南地區景觀結構脆弱性結果,環境脆弱性與景觀結構脆弱性值進行疊加得到生態系統易損性指數(表1)。
2.3 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度(Va)
風險源脅迫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可能受到損害,從而導致物質遷移、能量流動、信息傳遞等生態過程發生改變,進而使生態系統面臨不同程度的損失。生態系統質量指一定時間、空間范圍內生態系統的整體或部分組分的質量,是反映生態環境質量和服務功能的重要指標[36-38],本文用其表示風險源脅迫下生態系統的潛在損失度。主要以生物量數據和植被覆蓋度數據為基礎,結合植被區劃數據,對西南地區生態系統質量進行計算[30],通過研究區實地調查,將結果劃分為5個等級(表1)。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風險源危險性分析
(1)自然災害風險源
地震危險性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西藏東南部、云南西部以及川西高原,這些地區分布在龍門山、鮮水河、龍陵-瀾滄等斷裂帶附近,地質活動頻繁,地震災害頻發。干旱危險性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貴州省的東北部,廣西省的南部,重慶和云南省的大部,這與近年來全球氣候變暖導致這些地區溫度升高、降雨量減少有關。洪澇危險性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廣西的西部,云貴高原和重慶市的大部,主要原因是西南地區降雨時空分布差異較大,汛期這些地方降雨量大且易出現暴雨。滑坡泥石流在西藏的東南部、四川中西部、云南省南部、廣西北部危險性較高,原因是這些地區地質構造不穩定,山高坡陡,降雨量大,孕育了極敏感的受災環境。石漠化危險性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貴州的西部和南部、云南東部、廣西西北部,這些地區是我國典型的喀斯特地區,碳酸鹽巖分布廣且極易淋溶,在降雨和人類活動的作用下易發生石漠化。水土流失危險性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川滇黔交界、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部,這些地區生態環境復雜,石灰巖、紅壤、黃壤、紫色土、黃棕壤所占比例比較大,土壤可蝕性高,在降雨的作用下易發生水土流失(圖2)。

圖2 研究區自然災害風險源危險性Fig.2 Risk sources of natural disaster in the study area
(2)人類活動風險源
西南地區人口和GDP空間分布極為不均勻,大多集中在東部地勢平緩的山間盆地,其中成都、重慶兩個城市的人口平均密度高達萬人/平方公里以上,GDP位于全國前列,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壓力尤為突出。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危險性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貴州西部山地、重慶市西部、南寧、昆明及周邊城市,原因是這些地方農業較為發達、工業規模較大、人口高度聚集,對周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圖3)。

圖3 研究區人類活動風險源危險性Fig.3 Risk sources of human activity in the study area
3.2 生態系統易損性分析
西南環境脆弱性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貴州、廣西、云南大部分地區生態環境良好,脆弱性較低。景觀結構脆弱性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人為活動較為劇烈的東部地區,原因是城市化的作用下,自然景觀被不斷分割分散,斑塊間距不斷增加,導致景觀格局指數較高。生態系統易損性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北部、川西北山區、三江源地區、西藏山南和林芝地區東部及南部(圖4)。

圖4 研究區生態系統易損性Fig.4 Ecosystem vulnerability in the study area
3.3 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度分析
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度較高的區域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三江源、念青唐古拉山及云南的無量山和哀牢山等地,這些地區植被生長良好,生物量和植被覆蓋度較高,生態系統質量較好(圖5)。西藏和青海的北部地區主要分布著草原和裸地生態系統,生態環境惡劣,植被覆蓋度較低,生態系統質量較差,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度較低。

圖5 西南地區生態系統質量Fig.5 Ecosystem quality in Southwest China
3.4 生態風險結果分析
結果表明,西南地區高風險面積為17.02萬km2,占研究區總面積7.4%,主要分布在四川的邛崍山、岷山、大渡河流域,云南的無量山和哀牢山及西藏念青唐古拉峰以南地區,這些地區地勢起伏懸殊、降水充沛、生態環境復雜,自然災害易發,再加上生態系統易損性較大,生態系統質量較高,所以生態風險較高;成都、重慶、昆明、貴陽、南寧等城市及其周邊由于人類活動頻繁、人地作用強烈,生態風險也較高。中風險區分布較廣,面積為48.24 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20.6%,除西部高寒荒漠、中部和東部的山間盆地外,大部分區域均有中風險區分布。低風險和少風險區面積為162.3 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69%,主要分布在西藏和青海的北部地區(圖6)。

圖6 西南地區綜合生態風險Fig.6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isk in Southwest China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針對西南地區面臨的多種風險, 從風險源危險性、生態系統易損性、生態系潛在損失度三個方面構建了生態風險評價模型。結果表明:
(1)西南地區高生態風險區主要沿著念青唐古拉山、橫斷山脈、邛崍山、哀牢山、無量山、金沙江、怒江、瀾滄江、大渡河等山脈和水系分布,這些地區生態環境復雜,自然災害易發,應加強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防控與監測,盡量降低災害造成的損失,繼續推進天保工程、退耕還林工程,降低生態系統脆弱性,提高抗風險能力。
(2)成都、重慶、昆明、南寧等城市及周邊地區是西南地區人口高聚集地,人類活動頻繁,人地作用強烈,生態風險也較高,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人類過度開發,優化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推廣有機農業,降低人口和經濟壓力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3)藏北和青海北部的草原、荒漠地區生態風險等級較低,但是由于環境脆弱性較高,一旦受到風險源脅迫,難以得到恢復和重建。因此應該加強生態環境建設,預防本來脆弱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防患于未然。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用環境脆弱性和景觀結構脆弱性表征易損性,用生態系統質量表征潛在損失,詮釋了生態系統結構與過程的互饋關系,有利于在基理層面上理解風險受體受到風險源脅迫時的狀態變化。然而,由于區域生態系統的復雜性,本研究仍存在不足:風險源危險性評價過程中指標分級和取值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需結合專家、當地居民和政府部門意見進行修正;從理論上講,不同風險源脅迫下生態系統的受損程度是不同的,但是目前區域多風險源和多生態系統相互作用背景下,生態系統受損程度的差異仍然較難甄別,今后研究應重點關注風險源脅迫下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互作關系,進一步探討生態系統受損程度的差異;生態系統潛在損失度方面,單用生態系統質量表征生態系統潛在損失顯得不夠全面,如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損失考慮較少,需進一步完善;由于風險間相互作用的復雜性,綜合風險分析過程中各風險的權重設定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應結合野外調查進一步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