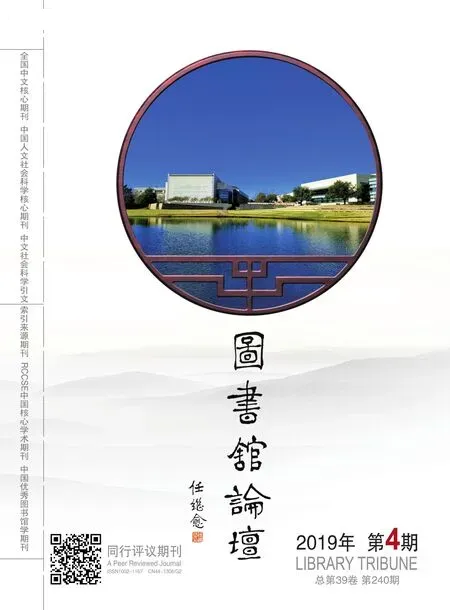袁同禮致王重民四通書信淺疏*
顧曉光
2019年是國家圖書館建館110 周年。在國家圖書館歷史上出現了眾多出色的管理者和業界專家,袁同禮和王重民即為其中代表。
袁同禮(1895-1965),字守和,191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自1929年任主持館務的副館長至1948年離館赴美,主政國立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長達20年。其貢獻已多有論述,再多贊譽亦不為過。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曾用名王鑒,1929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1928年入職于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1934-1939年,受袁同禮委派,王重民作為交換館員至法國國家圖書館工作,1939-1947年又前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在袁同禮1948年底離開國立北平圖書館后,王重民被袁氏指派為代理館長。
兩位先輩亦師亦友,沒有袁同禮的提攜,王重民難有此后的成就;沒有王重民多年海外孜孜不倦地輯錄散佚中文典籍,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及學界研究便失色不少。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藏有部分王重民資料,其中包括四通之前從未示人的袁同禮致王重民的信件。這些書信對于兩位先生的研究較有價值,特整理并進行釋讀,也請方家指正。個別字跡難辨,以○替代。
1 第一通:1927年9月23日,袁同禮致信王重民
重民吾兄:
茲奉上致嚴館長信一件,赴津時可攜交之,《老子通》購到者系明本(缺第一本,共四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北京圖書館所缺者系第二十五葉,以前者如能照樣影鈔,其鈔寫費當由北京圖書館奉上也。
此致
時安
袁同禮頓首
九.二十三
(一)此信未具年份,約寫于1927年,這是目前發現的兩人最早的通信。因“北京圖書館”之名在袁同禮任職時代僅存在于1927年1月16日開館(1926年3月1日正式成立)[1]至1928年7月更名(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京改名為北平,易名為北平圖書館,幾個月后改為北平北海圖書館)[2]。
(二)彼時王重民還在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就讀(1923年9月-1929年6月)。袁同禮在校任兼課教師,對青年王重民厚愛有加,并邀請他為當時的北海圖書館編制《國學論文索引》。李劍雄評論說,這“對他一生治學道路,有著幾乎是決定性的影響”[3]。1940年1月2日,通過王重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期間致袁同禮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袁氏對學生時代貧苦的王重民之幫助:“生猶憶在師大肄業時,曾以《史記版本和參考書》(刊載于1926年12月出版的《圖書館學季刊》第1 卷第4 期)一文呈閱,蒙賜二十元,以作鼓勵,從此以后,生始專力于學問,得有今日,十余年來,此恩未忘。”①王重民并未辱沒眾多老師的賞識,不僅于1927年7月出版專著《老子考》,而且畢業成績位列14 位國文系畢業生第一名,80.8 分②。
(三)此信應是王重民在《老子考》發表后所寫,因書中所輯版本并未提到《老子通》。此信顯示袁同禮介紹王重民前去天津查閱一本有關老子的古籍,并且產生的費用由館方負責。彼時王重民亦入學術之門,不僅著書立說,也同時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兼職做事,以補貼學費。1927年,他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里發現被全毀的圖書九種的提要,輯錄并編成了《四庫抽毀書提要稿》[4]。
《老子考》是王重民最早的一部專著,也是受袁同禮所授目錄學課程所影響之作[5]。袁氏為之寫序,序中對王重民多鼓勵之語:“王君重民從余治目錄學,近輯《老子考》一書,其書其志均足繼朱謝二氏之后。雖資力方有限,未能著錄無遺,然其博訪窮搜之功,于治斯學者貢獻多矣。故樂而為之序。”[5]
(四)嚴館長,可能是嚴臺蓀(孫)館長,時任直隸省立第一圖書館館長(1918年9月-1933年8月)[6]。此館是今天津圖書館之前身,于1908年6月9日開館,館名直隸圖書館,為中國長江以北最早的近代公共圖書館。成立之初,嚴臺蓀堂兄“南開校父”嚴范孫便捐贈了大量藏書[7]。
曾與王重民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的謝國楨在《江浙訪書記》中對嚴臺蓀有過記錄:“當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曾到天津河北公園直隸省立圖書館去閱讀書籍,認識了館長嚴臺蓀先生。臺蓀是天津南開學校的創始者嚴修字范孫的堂弟,是一位長于目錄之學、潛修自學的學者,他借給我看館藏管庭芬手寫自編的《花近樓叢書》《銷夏錄舊》等書,鈔得謹慎精美,所收輯的都是有關史料和文藝價值的書籍,讀起來真是愛不忍釋,現藏于天津圖書館。”[8]
直隸圖書館建館之初便藏有近20 萬卷(冊)圖書。1921年4月顧頡剛曾到此查閱《楝亭全集》(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文集),便手書老師胡適。正在研究《紅樓夢》的胡適便趕往天津,并拜訪了嚴范孫[9]。
2 第二通:1934年11月12日,袁同禮致信王重民
有三吾弟:
在羅馬時奉到三日來書,詳悉種種,內中述及留學計劃,尤佩卓見。惟卻意法文極不易學,亟應用全副精神先在最短期內將其學好,能懂能說能寫缺一不可。至關于東方學書目極不易作,必須先懂拉丁文及德、俄、意、西班牙諸文,因天主教士之書札及報告多用此種文字為之。李小緣君編此書目已有十年,尚未完成,明年擬設法使之至國外考察,順便完成輕而易舉,吾人不必作重復工作也。茲有一事在法時可編成之,即將1934 及1935 法國出版之東方學書籍及論文編一簡目,愈完備愈好。可先查此二年之通報及Journal ○東方美術雜志、里昂大學雜志等。(安南遠東學院二刊,之學報介紹)并請他同學隨見隨告,(且常至書店訪求),將來可在國內發表以后,再作1933 及1932 者,為此逐年進行,輕而易舉且可多得經驗也。
今晚于埃及余談 續告 順行
拜安
同禮頓首
十一月十二
(外二片請分轉林君及于君)
(一)此信未具年份,應為1934年,因根據內容推測應在1934-1935年間,而1935年袁氏并未在意大利,且1934年11月10日從意大利乘船回國[10],故撰寫時間為1934年11月12日于埃及。
(二)1934年,袁同禮大部分時間都在歐美各國參訪和開會,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潘梅的博士論文《袁同禮與中國圖書館事業》有較為詳細的記錄,不再贅言。他的海外訪問收獲頗豐,京津學術界知其歸國后,爭先約請演講。他特別看到了中美兩國圖書館發展的差距,認為“中國圖書館事業與美國相比先后相差百年”[11]。經過半年多的奔波,他體重竟減少20 磅[12],足可見袁同禮之辛勞。
(三)彼時,王重民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工作不到兩個月時間。通過給伯希和的信得知,王重民于1934年9月28日抵達巴黎,暫時居住在13 rue des écoles (巴黎第五區學校街)[13]。王重民在法國工作至1939年8月“二戰”爆發前,而后至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工作。對于初在異國生活和工作的王重民來說,一切也許并不容易,但他不忘袁同禮的期望,在法期間成績卓然,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蒙曦(Nathalie Monnet)有一篇專文較為詳細地記述了王重民巴黎的工作情況[14]。
(四)正信的旁邊有行小字:外二片請分轉林君及于君。林君應為林藜光。在1936年王重民給劉修業的信中,他幾次提到了林藜光。林藜光(1902-1945),佛學家,精通梵語。曾于法國漢學家戴密微的舉薦下,在愛沙尼亞漢學家、梵語專家鋼和泰手下工作四年。后于1933年底來到巴黎,潛心進行佛學研究。胡適在1949年7月25日給陳受頤的信中曾言:“吾國學者之中,治梵文與佛典最精最有成績者莫如林藜光先生。”于君應為于道泉。于道泉(1901-1992),藏學家、語言學家。于氏同為袁同禮推薦至國立北平圖書館任職。1934年5月,他留學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在給伯希和的信中,王重民提到了于道泉,“晉謁時,偕王海鏡,于道泉,王靜如三先生同往”。
3 第三通:1935年4月13日,袁同禮致信王重民
汪長炳已由教部委為在西班牙舉行圖書館大會代表,茲有論文一篇,請轉交,可先寄一信至倫敦中國使館,轉并告其在巴黎之住址,如汪君不到倫敦,或可先至巴黎。如見不著,即將此稿徑寄西班牙中國使館(Madrid)留交,為○該會五月二十開會也。
此上 有三吾兄
袁同禮頓首
四、十三
(一)此信未具年份,應為1935年。從第四通1935年5月2日袁同禮致王重民的信可以推測出。
(二)袁同禮提到圖書館大會為現在的國際圖聯(IFLA)大會前身,當時名為“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brarianship and Bibliography”。1935年第二屆大會和第八屆工作組會議聯合舉行,會期很長,從5月19日在馬德里開幕,然后轉到塞維利亞,再回到馬德里,最后于5月30日在巴塞羅那閉幕。共有來自26 個國家的550 多名代表參加此次會議,并有150 多篇大會宣讀論文。在會議上,大會主席還宣讀了來自中國和印度的電報,邀請國際圖聯將來到中國和印度舉辦會議。除了日本參會代表外,其他國家的代表都表示不現實,因為很難解決參會的經費。但美國代表CarlMilam 則評論說,國際圖聯不要老聚焦于歐洲,也應在將來放眼國際[15]。
(三)汪長炳(1904-1988),1926年畢業于武昌文華大學圖書館學專業,后任職于國立北平圖書館。1932年袁同禮派汪長炳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交換館員,形式也是半工半讀,兼管該校中文圖書[16]。193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后任南京圖書館館長一職[17]。他參加此次大會雖是以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身份,但彼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因袁同禮安排汪長炳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后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這段經歷在1934年5月22日袁同禮致裘開明的一封信[18]和一則新聞“汪長炳,文煥,參加國際會議后,又返美就國會圖書館職務”[19]可知。
4 第四通:1935年5月2日,袁同禮致信王重民
有三仁弟為晤連接,來書欣悉。旅居巴黎,一切順適,至以為慰。上月離平共三星期,返后又忙,久未作復。伯希和在滬晤面數次,不日來平。(交換昭陵碑○與之一談)交換及延長事當可決定。杜女士極愿延長一年,(惟法方愿來華者總大有人在)法使館總為之幫忙,想法庚款方面無問題。本館有二條件(一)執事在法總延長一年(二)杜女士在華多留一年,本館不負任何經濟上之責任,但如同時要求,執事在法總受九千元之待遇,或較現在之四千元為多,均不易實現,蓋法方增加預算較難而我庚款法國之部份由法使館可完全作主也。(國立圖書館或受外交部之補助),(此外并有中國部分及共同部分)現在只可作退一步想,能在巴黎多延長一年,總比自費為上算也。又法使館增加之五千元,伯希和認為太多,且旅費總在內。《海外希見錄》已登《圖書副刊》,以后寄敝處,總可徑寄王庸或賀昌群,此可因向君擬秋間赴英影照敦煌卷子,進行順利極佳,下年度清華仍可出資志以在執事未離巴黎以前,將其重要者完全照完為要,(擬由清華及本校再各認二千元)太平天國文件不論有若干,或東方語言學校有多種也。關于天主教之書,聞徐家匯有全份,故不必照,但作一有系統之目録,則藏有用。茲寄上在羅馬所鈔一部分,其余然則因○○停止將來可繼續完成之。李樂知托照南艾二先生行述,總○早日攝出寄與。
專此 順頌福安
同禮頓首
五月二日
汪君長炳已赴西班牙,前寄之論文,可寄使館轉交。
(一)此信未具年份,應為1935年。《海外希見錄》刊登于《圖書副刊》1935年第2 卷第1 期,且信中提到的向君(向達)是1935年秋(10月20日)搭船赴英[20]。
(二)《海外希見錄》是王重民受袁同禮教誨所寫,袁氏曾對他說:“海外保存吾國史料頗多,善本書之流出者亦不少;君于圖書館稍窺門徑,盍記之,可以海外希見錄命編也。”[21]在1935年7月23日,王重民又撰寫了《海外希見錄》(二),這是根據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康熙三十九年閔明我等奏疏》所寫提要而成,文章刊登于1936年2月27日第190 期《圖書副刊》。
(三)杜女士為杜乃揚(Roberte Dolléans,1911-1972)。1934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簽訂互換館員協定,為期一年,法方派出的館員即為杜乃揚。信中披露了原本一年的互換為何延長。杜乃揚非常喜歡在北平的生活,通過蒙曦的文章[14]可以看出,伯希和兩次幫助她延長在華的工作時間,使得她1938年才離開。現法國寫本部存有王重民在倫敦寫給杜乃揚的四封信,對他在法國的工作情況作了說明。杜乃揚也對王重民的工作贊賞有加,1955年杜乃揚在總結王重民巴黎工作時說他“鑒定了所有的敦煌中文寫本”[14]。她愿意延長在華時間與其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愉快的工作很有關系。法國寫本部的一份卷宗里藏有她的記錄:“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袁同禮就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建立了只有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圖書館才具有的先進服務。”[14]
(四)袁同禮提到的太平天國和天主教文件也是王重民在歐洲的重要成就。1936年,王重民發表《太平天國官書補編》。為了尋求明清間天主教士華文著述,他于1936年10月2日來到梵蒂岡圖書館查閱明清間來華天主教士的華文著作,一直至15日上午,閱畢館中所藏全部華文書籍,并且于次日還去了意大利國立圖書館,因袁同禮曾對他說:“欲稍致力于此,羅馬不可不游也。”在《羅馬訪書記》[22]中,王重民有較為詳細的旅行記錄。
王重民,字有三。不知何時“有三”被解讀為王重民有“三寶”,即“敦煌遺書,太平天國史料和明清間天主教士華文著述”。根據先生之前的同事對筆者說,他對這個解讀也頗認同。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有三”的原意并非如此,因這“三寶”均是1934年以后在歐洲工作和訪學所得,而筆者目前所收集的信件中,1929年即有人稱其為“有三”。李劍雄認為“有三”取義于國家三寶(土地、人民、社稷)[3]。根據本文第一通1927年9月23日袁同禮致王重民的信可以推測,“有三”可能是在1928年左右才有的字。這種大膽的假設只能等以后小心的求證了。
注釋
①國家圖書館館藏手稿。
②北京師范大學檔案館館藏成績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