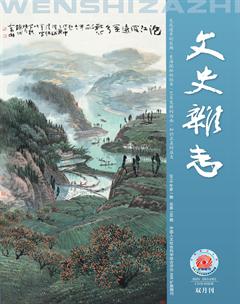為什么會叫《風》《雅》《頌》(上)
聞衷
《風》《雅》《頌》是組成《詩經》的三大部分,而關于它的定義,最早則是由《毛詩序》作出的。不過,進入南宋以后,漸有學者對《詩序》定義予以質疑,直至當代,仍連牽不絕。其間的問題,已不僅在于《風》《雅》《頌》這所謂“三體”的含義,還包括十五《國風》各自的內涵、時代與地域分布等。弄清楚這些問題,對于正確解讀《詩經》應該具有重要意義。
《風》《雅》《頌》之稱是由《周禮·春官·大師》提出的,原本屬于周代大師(樂官)所教“六詩”中的三項內容。《毛詩序·大序》改“六詩”為“六義”,指出其中的《風》《雅》《頌》是先王用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三類詩篇,并對《風》《雅》《頌》的含義作了定義性的解釋。稍后東漢鄭玄的《周禮注》《毛詩傳箋》以及《詩譜》等對《風》《雅》《頌》的注釋與編排,則不過是對《毛詩序》(簡稱《詩序》)的附和以及在《毛詩詁訓傳》基礎上的發揮罷了。
入宋以后,由于疑古思潮以及與此相應的反《詩序》論爭的興起,不少學者也對《詩序》關于《風》《雅》《頌》的定義提出批評或修正。在這之中,對《雅》《頌》的詰難要相對少些,而對《風》因為還牽涉到《十五國風》,則矛盾要復雜得多,形成眾說紛紜,各抒己見的局面。因此下面遂采取首易次難的順序,先介紹《雅》《頌》,再介紹《風》的問題。
一、秦聲烏烏大小《雅》
現存《詩經》有《小雅》74篇,《大雅》31篇,計105篇,合稱“二雅”。其中《小雅》在《毛詩》號稱“八十篇”,但有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只存篇目而無文辭)。這六篇即所謂《六笙詩》,其題目分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儀禮·鄉飲酒》等說,在周代“鄉飲酒禮”及“燕禮”上皆以笙演奏此六詩,故名《笙詩》或《六笙詩》。
關于《雅》,《毛詩序·大序》說:“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這里的意思是說:用本國的事情來勸戒王者的叫做《風》,用天下各國的事情來勸戒王者的叫做《雅》。《雅》就是正,即政治,是講王政的盛衰敗亡及其原因的;也可說是“正得失”的意思(鄭玄《周禮注》說,《雅》是“言今之正者為后世法”)。王政有大小,所以又分出《小雅》《大雅》來。按夏傳才的理解,《詩序》所說的《小雅》“大多說個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感受”,《大雅》則“說朝政大事”。(夏傳才:《詩經語言藝術》,語文出版社1985年版)

詩經地理圖(選自向熹著《詩經詞典》)
對“雅”字,清人王引之曾有過訓詁。他在《讀書雜志·荀子》里說:
雅讀為夏,夏謂之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
近人梁啟超根據王引之的考釋,在《釋四詩名義》里論證《詩序》之小《雅》、大《雅》說:
《偽毛序》說:“雅者正也。”這個解釋大致不錯。……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樂,當時謂之正聲,故名曰《雅》。……然則正聲為什么叫做“雅”呢?“雅”與“夏”古字相通。……雅音即夏音,猶言中原正聲云爾。
今人陸侃如、馮沅君按云:“所謂中原正聲,其實即是西都土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說:‘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中國詩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蔣伯潛、蔣祖怡在《經與經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里評論梁啟超關于雅音“猶言中原正聲”之說時又不忘順帶批評《詩序》道:
舊說訓“雅”為正,又訓“正”為政,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實曲解。梁氏之說,遠勝舊解。梁氏又謂《儀禮》所記樂工以歌詩與“笙歌”同時合奏,相依而節,正如今西樂的伴奏。……不過所謂“雅”者,我覺得還有意思可以補充。“雅”和“雅言”“方言”之“雅”一樣,是對于帶有地方色彩的樂歌(如采自各國之“風”、起自南方之“南”)而言的。所謂“雅言”,和我們現在講普遍話標準國語,讀標準國音一般。《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這是說孔子讀《詩》、讀《書》和執禮(即今司儀贊禮之類)時,是用普通話的。因為大《雅》、小《雅》是周代國定的標準音樂,所以謂之“正樂”,名之曰“雅”。
對蔣伯潛、蔣祖怡所引《論語·述而》“子所雅言……”句,楊伯峻曾有過注釋:“雅言——當時中國所通行的語言。春秋時代各國語言不能統一,不但可以想象得到,即從古書中也可找到證明。當時較為通行的語言便是‘雅言。”(《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梁啟超、蔣伯潛、蔣祖怡、楊伯峻等對“雅言”的理解,將王引之的研究往前大大推進了一步。
與梁啟超同時的章炳麟則在《大疋小疋說》里從音樂的角度去解釋“雅”:
凡樂之言疋(筆者按,《說文解字》有云:“疋,足也。……古文以為《詩·大疋》字,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者有二焉,一曰大小雅,再曰舂牘、應、雅(打擊樂器)。雅亦疋也。……鄭司農注《笙師》曰:“雅狀如漆筒而弇口(指口小),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熟羊皮)挽之,有兩紐,疏畫(器體上畫著稀疏的花紋)。”……《大小疋》者,其初秦聲烏烏,雖文以節族,不變其名。……頌與風得函數義。疋之為足跡,聲近雅故為烏烏,聲近夏故為夏聲,一言而函數義可也。
對章炳麟之言,陳子展疏云:“這是說,雅是近似鼛鼓的一種樂器名,又是一種曲調名。”(《詩經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陸侃如、馮沅君也極贊同章炳麟在《大疋小疋說》里對“雅”的考釋,稱其“最為完善”。他倆認為《雅》就是樂歌(“夏聲”或“秦聲”),“就內容言為記事,就地點言為西周。至于現存雅詩中有東遷以后的作品,那也無害于其發源之地”(《中國詩史》)。

《詩》之《小雅》與《周頌》(宋本朱集傳)
在此基礎上,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指出:
雅詩為什么有大小之分,從前說詩者有許多爭論。清代惠士奇《詩說》謂大小雅當以音樂來區別它們,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其意義并不在“大”“小”上。我們認為風、雅、頌既是根據音樂來分類,雅詩之分大小,當然與音樂有關。
梁啟超、章炳麟、陸侃如、馮沅君、蔣伯潛、蔣祖怡、游國恩等學者的觀點已被《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所吸收。
不過,今人高亨對于《小雅》《大雅》的由來則有與之不同的說法。他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里寫道:
雅有《小雅》《大雅》,合稱二《雅》,共一百零五篇,都是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域——“王畿”的詩歌,多數為朝廷官吏(公卿大夫士)的作品。雅是借為夏字,《小雅》《大雅》就是《小夏》《大夏》。因為西周王畿,周人也稱為夏,所以《詩經》的編輯者用夏字來標西周王畿的詩。
在這里,高亨頗贊同“雅”通“夏”的說法,但他筆鋒一轉,卻將《小雅》《大雅》說成按地域劃分的《小夏》《大夏》了,這首先是針對《詩序》“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發難的,因為《詩序》是按《詩經》所述政事內容的大小來分大《雅》、小《雅》的。其次是針對梁啟超、章炳麟等的“樂歌”說而予以補充。高亨認為:西周王畿以后歸秦國所有,“從而這個地域的詩篇就是《秦風》了。春秋時人尚稱《秦風》為‘夏聲。……《詩經》三百篇都是以地域分編,用地域名稱加標題的。十五國風的十五國(《王風》的王代表東周王朝的統治區),《周頌》《魯頌》《商頌》的周、魯、商,都是代表地域,可見二雅的雅也是代表地域,即借為夏字。如果不是這樣,二雅是哪個地域的詩歌就表示不出來。雅詩為什么有大小的區別呢?古說都不圓通,現在還得不出確解。”
劉惠孫則在《中國文化史述》(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版)里提出:“《雅》的一些作者正是管仲所定‘四民之中的‘坐而論道,文質彬彬的士階層。”“《大雅》《小雅》之分,從內容來看可能又是卿、大夫階層與士的階層的不同。”
又有黎子耀在《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發表題為《毛詩秘義》緒言(節錄)一文,從周代天文歷法學的角度來辨析《雅》,認為“雅”為月朔之隱語。他指出:“朔望正時,為歷法中之大政,象征王政。”他又引《說文》“雅,楚烏也”具體解釋說:
日月合朔,無光,日如烏鴉。月本無光,亦如烏鴉。日為小鴉,月為大鴉。此小雅、大雅得名之由來。日月相會,積日成月,積月成歲,《詩經》大小雅之詩即是一歲之日數。小雅八什,詩八十篇。大雅詩三十一篇。大雅詩為一月之數,以三十日計,多一日以示閏。30×8=240日,此為八個月之日數。隱去四個月之日數為120日,隱顯兩者之日數合計為360日。十二月各加閏數1,得12日。360+12=372日,一歲日數為365又1/4,故小雅詩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詩本無辭,意在減少六篇,以示減少六日之數,并非本來有辭而后亡佚。辭字其義有二:一為言辭,另一為辭別。射箭如人有言辭,箭發如人之辭別。天干地支如同弓箭,相配一次,如射一箭,故以箭計數。相傳隸首作數,隸首即箭鏃之隱數。弓為主,箭為奴。弓中有箭則為弩。372-6=366日,接近周天之日數。
二、舞曲融融歌三《頌》
現存《詩經》有《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計50篇,合稱《三頌》。
關于《頌》,《毛詩序·大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意思是說:《頌》是贊美王者的功德業績的(鄭玄《周禮注》說,頌即歌頌,是“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并將他們的功績通過祭祀報告給神明。總之,《頌》是歌頌王者的祭祀詩。
應該指出的是,《大序》這里是以“頌”的引申義來為《頌》下定義的。而“頌”的本義則是“容”,籀文作“”。《漢書·儒林傳》說:“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史記·儒林列傳》則說:“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可見,在上古時代,“頌”與“容”是相通的;而這里引的《史記》《漢書》的“容”則系“禮容”“儀容”之義。《漢書》顏師古注引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后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清人阮元注意到上述情況,而對《詩序》用“頌”的引申義而忽略其本義表示不滿。他指出:
《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后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揅經室一集·釋頌》)
在這里,阮氏認為應當重視從“容”的層面上去探討《詩經》之《三頌》的含義。他認為,“容”就是樣子,是踏著音樂節拍唱歌跳舞的舞姿。因此,“頌”實際是一種與祭祀有關的歌舞曲。梁啟超也不贊成《詩序》定義而支持阮元之說。他在《詩經解題》里說,“頌”是“歌而兼舞”;“舞則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類詩曰‘頌”。近人張西堂還在《詩經六論·說頌》中指出,古字“頌”與“庸”“鏞”音相通,鏞是樂器大鐘,因此《頌》應是用大鐘伴奏,聲調緩慢,用于宗廟祭祀的樂歌。張西堂之說,可以視做對阮元“舞曲”說的一種補充。

《詩·商頌·殷武》(宋·朱集傳)
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里評論說,雖則阮元之說被“公認為對于‘頌解釋得最為完善的”,“然而若據此而說《三頌》四十篇無一非舞曲,那未免固執不通了。因為這四十篇之不全是舞曲,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最明顯的證據是魯、商二頌,無論就它們本身說,或就古代文獻看,都難附會到舞容上去。即時代較早的《周頌》三十一篇,也難勉強一律比附。而且如果我們說現存頌詩中有一部分祭歌,那也不算出于舞容的本義之外,因為舞曲與祭歌本是有密切關連的。……故《三頌》中有不少的祭歌。”
陳子展亦在《詩經直解》里說:“大較言之,《詩》三百皆可誦、弦、歌舞。自《二南》以下《風》詩,多屬里巷歌謠之言,本為徒歌,而亦可以入樂。《雅》作為政治詩,合樂而不必配舞,略與《風》詩不同也。《頌》作為宗廟祭祀之樂章演出,當是采用載歌載舞、有聲有色、美先人之盛德而形容之形式。”在這里,陳子展實際已對《詩序》以下關于《頌》定義的諸說兼采并蓄,綜合歸納之。而作為對《頌》的內涵最凝煉的總結,還當推《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
頌的意思是形容,也含有贊美之義,是祭祀所用的樂歌,部分是舞曲。
但發明“雅”為月朔之隱語的黎子耀,在前舉《毛詩秘義》緒言(節錄)里則認為,“頌”為月望之隱語。他引《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句而說道:“月望之月即是盛德。”他指出:
魯頌、商頌象月之五行循環,而為九疇。周頌之數象征一月之日數。商頌按五行相克順序,周頌按五行相生順序。《孟子·萬章篇》比喻五行相克為傳賢之制,五行相生為傳子之制。
黎子耀之言雖有刻意比附之嫌,但卻又具別開生面之象,似可備為一說。
在三《頌》之中,誰個生成時代最早?一般認為是《周頌》,它而且還遙居《風》《雅》《頌》三體之首。詳細的論證可參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至于具體的時代,《辭海》歸納歷代研究者的考釋,認為“多為周初的作品,是西周統治者用于祭祀的詩歌”。高亨《詩經今注》還進一步指出說:“從它們的內容和藝術性觀察,多數是昭王、穆王以前的詩篇。”
過去有認為《商頌》時代最早者,認為生成于商代,屬商詩。一般而言,持此論者為古文經學派,最初見載于《毛詩序·小序》。其在《商頌·那》題下說:“《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按微子為周代宋國的始祖,商紂王的庶兄。周公旦攻滅武庚后,封他于宋。宋戴公于公元前799~公元前766年當政。《毛詩序·小序》在這里的交代盡管不甚清楚,但指《商頌》為商代作品的意圖卻是很明白的。
不過,早出于《詩序》的《國語·魯語下》卻說:“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又據《史記·宋世家》及《后漢書·曹褒列傳》李賢等注,此正考甫(父)為宋襄公時代(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的大夫(陸侃如、馮沅君說:“或者有兩個正考父),“孔子之先也”。這三條資料,則將《商頌》的時代降至春秋早期。高亨在《詩經今注》里贊同這一意見,認為《商頌》“不是商代的作品,而是周代宋國的作品。宋國疆土在今河南東部及江蘇西北部。”至于為什么要稱《商頌》?高亨解釋說:“宋國是商湯的舊地,也稱為商,宋君又是商王的后代,所以宋詩稱為《商頌》。原有十二篇,只剩下五篇。”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里說,現存《商頌》五篇可分作兩類,“前一類的時代似乎較早,不妨假定為公元前8世紀的詩;后一類似較晚出,或者是公元前7世紀的詩。”這大致也是近代以來大多數研究者的共同看法。
至于《魯頌》,一般認為是公元前7世紀魯國(在今山東省西南部,開國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都城為曲阜)的作品。理由是根據《魯頌·閟宮》以及在《魯頌·駟》下之《小序》里提到的兩位作者奚斯與史克的活動時代——前者約當公元前7世紀中葉,后者則處在公元前7世紀末至公元前6世紀初。由于《魯頌》四詩前的《小序》都具有“頌僖公”等文字,所以《辭海》也予以了認可,稱《魯頌》“歌頌貴族統治者魯僖公”。
研究者還注意到《魯頌》風格與《風》《雅》的某些接近處。誠如宋人王柏在《詩疑》中所言:“《魯頌》四篇有《風》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也。”(待續)
(注:上期第58頁—61頁《“四家詩”是如何爭得官學地位的》屬“詩經懸案”之五,漏排眉題,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