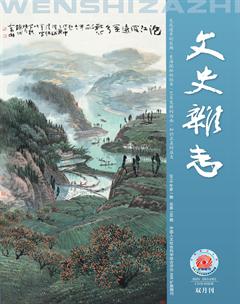漫談古代帝王及太子身邊的訓導
慧繪
古代帝王跟正常人一樣,并非生下來就具有治國理政的才能,必須通過后天學習與實踐獲得知識與經驗。為此,皇室十分重視對皇子、特別是太子的教育與培養。即便太子(或其他皇子)做了皇帝,也需要繼續學習,繼續接受教育和幫助,以豐富或提高自己的道德政治素養、思想文化品位、軍事斗爭才干以及治民馭臣的權謀,甚至深入到具體而繁瑣的禮儀涵養,包括政務程序、朝會儀節、文書程式等等的修為。為此,皇帝在身邊聚集了一些德高望重、具有豐富知識及實踐經驗的訓導人員,以便隨時問事咨詢,解疑釋惑,并接受教導(或輔導、開導)及告誡。這樣的職能,部分類似于今天的政府參事,但地位更高,權力更大,責任更重。
三公三孤
先秦君王身邊常見的訓導人員是三公、三孤。三公指太師、太傅、太保(一說指司徒、司馬、司空),是針對君王而設,為君王的老師。三孤亦稱“三少”,即少師、少傅、少保,針對太子而設,是太子及其他王子的老師。《北堂書鈔》卷五十引許慎《五經異義》:“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宋元之際的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職官考二》里釋“孤”說:“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
三公三孤統稱“公孤”,或稱“師保”。按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二》里的說法,所謂師,指天子所師法,傅為傅相天下,保即保安天子于德義者。三公之責,在于“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在先,東漢班固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里也指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傳說遠古虞舜時代就設有師保。《禮記·文王世子》說:“虞、夏、商、周有師保。”這情況,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易·系辭下》云:“無有師保,如臨父母。”這里把師保等同于父母,其教誨亦視同父母之教。
上古文獻往往將君王的老師與太子的老師混為一談,即有時師保專指君王之師,有時則指太子之師,有時又兩者之師兼顧。我們或可這樣理解:因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所以當太子當上君王后,他昔日的老師——師保也跟著成了皇帝的老師。須要說明的是,先秦時期的師保——三公三孤,既是君王的老師,又是他的顧問或高級參謀,還往往進入治國理政的角色,甚至成為執政。《文獻通考·職官二》引朱熹語指出:“惟天子方有三公、三孤、六卿。……公、孤以師道輔君,是為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兼相職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遞修本)
先秦君王的師保,因為是君王的訓導之師,理所當然地被君王委以輔弼重任,成為握有實權的重臣乃至宰相,如朱熹所舉周初的周公、召公。或者倒過來:重臣因為輔弼君王有力,而成為后者的先生。商湯(成湯)時代(商早期)的伊尹、仲虺,武丁(?——公元前1192)時期(商后期)的傅說可謂當時的名相,又分別是商湯和武丁的導師和高參。商湯時代的伊尹最為歷害,他連湯王算起,輔佐過四代君王(即成湯、卜丙、仲壬、太甲)。他輔佐太甲時,由于后者不遵湯法,不理國政,被他放逐于桐宮(在今河南偃師)逼其悔過,自己則代為施政。三年后,伊尹見太甲能痛改前非,才將他迎回京城,還政于他。太甲見到伊尹——他的賢相兼導師、高參后,痛哭流涕,行跪拜禮。《尚書·商書·太甲中》記錄了他對伊尹所講的、后來被廣為征引的一段話: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的檢討大意是說,上天帶來的災禍還可以避開;自己造成的災禍,卻難以逃脫。以往違背師保您的教誨,一開始就沒管住好自己;還希望憑借您匡救的恩德,給我一個好的結果。在這里,太甲終于認識到他的師保——伊尹訓導、懲戒自己的良苦用心,發誓今后永遠聽師保的話,做一個好君王。
聽從師保的訓導,按照師保指引的去做——大致是虞舜以來歷代君王相沿以襲的好傳統,不能輕易更改;但凡更改或違背,便會犯錯誤,沒有好下場。夏代太康失國、夏桀敗走鳴條而亡國,商代武乙田獵河渭被雷劈死,紂王(帝辛)牧野兵敗自殺,走的都是這條不歸路。特別是紂王后期“淫亂不止”,他的師保們“數諫不聽”,氣得一個個棄他而去,“持其祭器奔周”。剩下繼續苦諫的箕子(太師)與比干(少師),一個被紂王囚禁起來,不準發聲,另一個則被掏了心,永遠閉上了嘴。唐人司馬貞讀到這段歷史時嘆道:“帝辛淫亂,拒諫賊賢。”[l]“賊”是虐害、殺害的意思;“賢”,這里不僅指賢人、賢臣,更重要的是賢師。虐殺賢師,天理不容,所以紂王最終亦不可活,“赴火而死”。
《尚書·仲虺之誥》說,商朝開國之初,湯王的導師仲虺對湯王提出的第一條要求乃是“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就是說要尊師尚賢,重用忠良。他還借他人的話告誡湯王: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2]
這段話大意講,我聽說:“能夠自己找到老師的人,就會成為君王;認為別人都不如自己的人,就是自取滅亡。謙虛好問,得到的就多;剛愎自用,得到的則少。
與此相應,成湯立國之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廣發布告尋求一位或數位好老師來輔佐自己,成湯將他們稱為“元圣”。成湯這是吸取了夏桀腐敗禍國的教訓。《史記·殷本紀》說,成湯很有運氣,找到了伊尹,還有仲虺為師,委以他們重任,在他們的幫助下,終于滅了夏,得以“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先秦師保對君王明顯具有監督、督問性質,這就是說師保不僅是君王的老師、顧問或高參,還是監護人,如前舉商代伊尹對商王太甲,周代周公對成王,召公對康王。這對君王實在不太好受;故而多有抵觸,甚至反抗。《竹書紀年》卷上記載了太甲與伊尹關系的另一個版本:太甲被伊尹長期放逐(不止三年),七年后,太甲潛回京城,將伊尹殺死,強行奪回了政權。這個對具有監護人意義的師保進行叛逆的傳說,說明號稱天子的人君在本質上是不會容忍被人凌駕的。《易辭·系辭下》里將師保視作父母的話,乃是一種理想境界。其間隱藏著多少類似太甲弒師的故事,不得而知。

經筵進講(選自《大明衣冠圖志》)
入秦以后,具有監護君王意義的師保制度便逐漸淡化于歷史深處。秦始皇嬴政本人曾長期糾結于相國兼“仲父”的呂不韋的監護,故對一切監護及監護人深惡痛絕。據《史記·呂不韋列傳》,嬴政在他宣布“朕為始皇帝”的第十二個年頭,即公元前235年,便剝奪了呂不韋的一切職務,將其放逐到邊遠的蜀郡,使之“恐誅,乃飲酖而死”。秦始皇在擺脫了呂不韋的監護后,又在此前基礎上大量設置博士,以代替師保的部分功能。畢竟,皇帝不是萬能的,并非無事不曉。但博士只類似于今天的參事,只備皇帝咨詢、問事,最多起個高參作用,主意還是由皇帝來拿。
入漢后,所謂三公,完全成了宰相,失去了君王導師、高參兼監護人的職能。到了三國兩晉及南朝、北魏、北齊的三公,則多為大臣的加官、贈官,或備皇帝顧問。兩宋時的三公一度復為真宰相,但終還為加官。元、明、清三代,三公僅為勛戚大臣加官、贈官的最高榮銜,連顧問也不是了。
經筵講官
經筵就是給皇帝講授經史的講座,或者說是皇帝學習經史的課堂,打個不恰當的比方——類似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讀書班。讀書班的講師是各路專家學者(包括政府參事、文史館館員),而古代皇帝經筵的講官則是博士、侍讀、侍講學士等。
漢武帝時,用丞相公孫弘之議,特設五經博士,專掌經學傳授,除面向皇帝、皇室及大臣子弟外,也向太學生授課。《后漢書·張酺列傳》載有尚書博士張酺給皇帝經筵講經事。據《后漢書》本傳及唐李賢等注,張酺的祖父張充可能就是尚書博士(因張酺從充受《尚書》),少時與劉秀曾同在京城長安學《尚書》。后者即帝位后,欲“求問充”,惜“充已死”。張酺給明帝、章帝、和帝三代的經筵長期當講官,張酺的兒子張蕃亦侍講于和帝,曾孫張濟則侍講于靈帝……《后漢書》本傳稱“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該本傳關于他為漢明帝、章帝父子兩代明確講經的史實主要有兩條:
永平九年(公元66年),顯宗(明帝)為四姓小侯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于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自酺出后,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訚訚惻惻,出于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公元85年),東狩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并會庭中。帝(章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禮。賞賜殊待,莫不沾洽。
從《后漢書·張酺列傳》的這兩條記載并及本傳的其他文字,可以看出古代經筵及皇帝學習的一般情況:
1.古代皇帝大多重視學習,重視繼續教育,以豐富自己的知識,擴大自己的眼界。
2.古代經筵(皇帝的讀書班)制度,應該自漢明帝始。[3]經筵的地點不拘泥于京城皇宮;隨皇帝巡行,也可移至地方。在地方開設的經筵,可以吸收當地經生與官吏旁聽。
3.皇帝帶頭尊師重教,以此推動皇室子弟及臣子乃至百姓的讀書熱潮。
4.漢武帝之后的皇帝確實是以儒學作為自己的統治思想,或核心統治思想。所謂“獨尊儒術”,當不是虛言。
5.經筵講官多有正氣,往往借講經之際古為今用或借題發揮,向皇帝諫失指弊,建言獻策;而皇帝也欣然接受,未有抵觸。這情形,有些類似于今天政府參事與政府首長的關系。
據《文獻通考·職官考八》的記載,唐玄宗時專設集賢殿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入內侍讀,待以師傅之禮”,入宋后延續此制。宋仁宗時又設崇政殿說書,三者皆掌講讀史書,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宋神宗初,《資治通鑒》編成。神宗此后常開經筵,令編者、翰林學士司馬光講讀。司馬光在神宗為其序后寫有一段話:“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圣旨讀《資治通鑒》。”這說明神宗迫切希望盡快了解歷史上興亡衰替的歷史經驗,故令司馬光充任講官,及時講讀。《文獻通考·職官考八》引葉夢得《石林燕語》介紹了宋代經筵講讀對講官的禮遇: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后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后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沖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日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這段記載表明,自宋仁宗乾興(1022年)以來,經筵講官除專職者外,還有他官兼者,故對講官不再以師道論之;但畢竟是為皇帝提供知識,“考釋義理”的顧問,仍待以較高禮遇,未有怠慢。宋神宗元豐(1078—1085年)改制后,更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而以侍從以上兼侍讀、侍講,至南宋則多以臺諫官兼任,使經筵講官純以他官充任,不設專職。元朝承宋制,亦開經筵,至元泰定帝(1323年—1328年在位)大盛,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皆令聽講。至元末順帝(1333年—1368年在位)時期卻廢除了經筵,入明后又以恢復。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詔定經筵為制度,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定期于京城文華殿專為皇帝講經,朝中眾大臣陪聽。講讀官先講“四書”,后講“五經”,或讀史。這叫“日講”,又稱為“小經筵”。楊慎(升庵)在嘉靖初曾任經筵講官給皇帝授課。到了明中葉以后,經筵時斷時續,逐漸式微。入清后,朝廷重開經筵,設經筵講官滿漢各八人,講官滿漢各二人,由高級官員及翰林充任。順治十二年(1655年)規定,每年春、秋兩季經筵之后,按日進經,春講至夏至日止,秋講至冬至日止。順治帝、康熙帝甚至還請湯若望等外國傳教士講授西洋知識,特賜其“通玄教師”(后改稱通微教師)稱號。到了乾隆以后,皇帝日惰,經筵也很少開了。而乾隆以后,中國封建王朝便進入衰落期。其成因固然很多,但皇帝自身不注重學習,或許也算是一條原因吧!

太子屬官
古代皇帝大多既重視自身學習,更重視對皇子特別是太子的教育與培養。因太子是儲君,其能否健康成長、全面發展,關系到血脈的傳承,社稷的安危。為此,皇帝也在太子身邊安置了一大批文人武士,授以各種官職,以為太子保駕護航,總稱太子屬官或東宮官(因太子居東宮)。其中輔翼、訓諭太子,相當于太子導師、顧問及高參的人,多是德高望重的飽學之士。他們分別是太子六傅、太子賓客、太子詹事、太子庶子。
太子六傅:前述《北堂書鈔》卷五十引許慎《五經異義》中的“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即是“太子六傅”中的“三傅”。先秦之時,太子身邊的訓導官兼監護人就是這三傅。《史記·商君列傳》記秦孝公時任用商鞅變法,令行禁止,威震國中。時太子犯法,商鞅仍堅持用法律繩之。但“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商鞅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聞之,拍手稱快,心悅誠服。商鞅施刑的對象公子虔,即是太子少傅,公孫賈乃太子少師。少師、少傅、少保是先秦時太子身邊的最高師傅。商鞅不能加刑于犯法的太子,就移刑于太子的師傅,道理就在于“弟子不教,師之過錯”。漢高祖劉邦又以博士叔孫通為太子太傅,張良為太子少傅。西漢的疏廣、疏受、韋玄成、丙吉、匡衡、王丹都當過太傅或少傅。《晉書·愍懷太子列傳》載,西晉末,晉惠帝為愍懷太子“盛選德望以為師傅”,乃置東宮六傅,即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但因避景帝(司馬師)諱,又改太師為太帥。東晉東宮只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南朝宋齊梁陳大體因之。北朝則六傅齊備。北魏稱太師、太傅、太保為“東宮三太”,少師、少傅、少保為“東宮三少”。唐宋以后至明代,六傅不常備。個中原因,如《舊唐書·職官志二》所言:“三師,訓導之官,天子所師法,大抵無所統職。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舊唐書·職官志三》亦說:“三師三少之職,掌教諭太子。無其人,則闕之。”清代自康熙以后因不立太子,自然無太子屬官。需要指出的是,唐以后,太子六傅多為兼官、加官、贈官,與輔導太子無關。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言:“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清代雖無東宮屬官,卻明文規定從太師至太子少保的十二個官銜“為大臣加銜”,以前代太子六傅的加銜謂之“宮銜”。光緒二年至光緒十二年(1876—1886年)的四川總督丁寶楨就被朝廷加銜為太子少保,民間昵稱“丁宮保”。今天川菜中的名肴“宮保肉丁”“宮保雞丁”,據說就是由丁寶楨在成都的府邸——宮保府傳入尋常百姓家。
太子賓客:省稱賓客,在東宮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文獻通考·職官考十四》載:“晉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愍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遹(太子名)幼蒙,今出止東宮,雖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兒子)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華虞息恒,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侍儲皇。其后無聞。唐顯慶元年(公元656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仆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并為皇太子賓客,遂為官員,定置四人。”唐玄宗時立李亨(即后來的唐肅宗)為皇太子,以著名文士、詩人、書法家賀知章為賓客,并授秘書監(秘書省長官,相當于政府秘書長)。天寶三載(公元744年),賀知章“請為道士”,告老還鄉。皇太子李亨及百官餞送,惜別依依。唐玄宗念其德行高尚,輔佑太子勤勉有加,遂賦詩贈別,其中有云:“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群臣讀之,皆感嘆不已。宋天禧四年(1020年),宋真宗以參知政事(副宰相)任中正、王曾及樞密副使(副宰相)錢惟演兼太子賓客,《文獻通考·職官考十四》說:“執政兼東宮自此始。”
太子詹事:相當于東宮總管或總務長,秦時即設,后代因之,清末廢。宋乾道元年(1165年),宋孝宗為莊文太子置詹事二人;一個月后,又詔令太子詹事遇東宮講讀日,須前往陪侍。后莊文太子去世,乾道七年(1171年),孝宗又立其第三子趙惇(后來的宋光宗)為太子,以當時大學者、著名文學家、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及敷文閣待制陳良翰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可見皇帝對教育、培養繼承人的一片苦心。
太子庶子:始自周代,《周禮》謂之諸子,其時職掌管理教喻諸侯,漢以后方為太子侍從官之一種,南北朝時稱中庶子。唐代于太子官屬中設左、右春坊,以左、右庶子領銜,以比皇帝的侍中、中書令。歷代相沿。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詔定左、右春坊各置大學士一員,掌太子奏請、文書及講讀之事。其左、右庶子職在陳古義,申典制,規鑒太子,不常置。清代以左、右春坊為翰林升遷之所,清末廢。
注釋:
[1]漢·司馬遷:《史記》卷三《殷本紀》附司馬貞《索隱述贊》。
[2]《尚書·商書·仲虺之誥》。
[3]《大辭海·中國古代史卷》說:“西漢成帝曾召儒臣講說《尚書》等。”(《大辭海·中國古代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頁)。但正史似乎未記成帝以后至明帝之前數代皇帝百年間有關經筵的事;或有,也是斷斷續續,尚未形成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