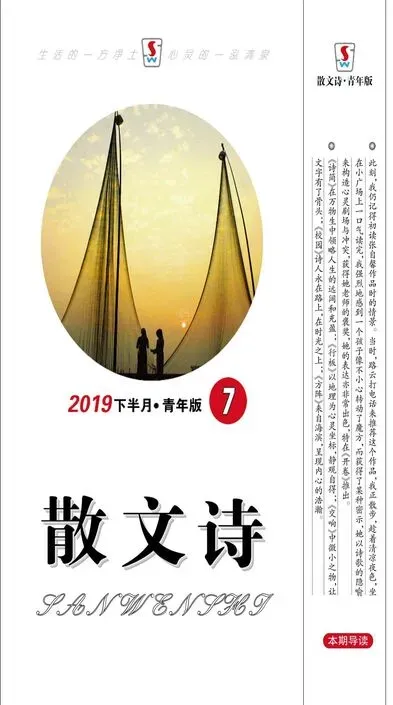泥巴也是有骨頭的(外二篇)
云南/鄭賢奎

徐紅暉/圖
傳承是什么?是一門技藝,是一種審美,是一種智慧。或者這些都不是!傳承是一縷游絲,她是一位母親,有著古老的面孔,花發斑白,深邃的雙眼,蒼涼的身軀,能說話的巧手,能夠洞穿一根根歷史經緯,串起一條條文明的項鏈,織成一襲長袍,她有青銅冷清的質地,也不失葵花奔放的熱烈。
這是一幅長卷,往后一翻,泥塑的肉身,水做的魂。這是一次完美的演繹,方寸之間,賦予她一生的品格。傣族土陶,她的一生,是粗獷、古樸、自然的。她讓我記起我的童年,我的童年生活在鄉村度過,我的童年是玩泥巴的童年,她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住在南高原大江纏繞的村莊,江水自古以來就未曾停止過大江東去。山自不必說了,充滿詩意的小涼山,她貧瘠而頑強,生長苦蕎,洋芋,豬膘肉,詩歌,充滿神話象征意義的塔爾波忍山,白牛廠挖出銀牛,究竟是“賣仙桃”還是“賣先逃”的傳說,茶馬古道的趕路之人。這些經久不息的歌聲在九曲十八彎上婉轉悠揚。
傳承一直在延續,在那片情深意長的土地上。多年以后,子孫們會在來時的路上仰望祖先曾抵達的村莊,那里有炊煙升起,蒼鷹掠過天際。
小時候,在我的故鄉,泥巴,它是一座城堡、一片大海、一個萬物賴以生長的溫床。我是那里小小的主人,我有自己的奇思妙想。
詩人阿信說:到不了的是遠方,回不去的是故鄉。
如今,鋼筋,混凝土,推土機,工廠……隨著工業文明的急速推進。我們的生活改善了,回頭看,滿目瘡痍的土地讓人心驚,以前看余秋雨的《廢墟》、于堅的《昆明記》,你或許真能從里面發現一點什么,這算是一種快與慢的較量吧。生活,頓時在這里給我們出了一個大命題。這命題讓人質疑,讓人無法反駁。
一城里小孩回鄉下外婆家,在自家門前玩泥巴,泥做的土路,矮小的房屋,幽深的水井。大人見狀,立刻上前制止并大喝。
這泥巴這么臟,你還玩兒?
由他玩兒,這里自有一番天地。我覺得這泥巴比人干凈,難道你不這么覺得?父親笑著朝田野大步走去。
泥巴,更多的時候,在我心里是一條回鄉的路,一條逃離后又無法安放的路,如江水不能回頭,看夕陽西下,斷腸之人,也須學會自救。泥巴,她在我心中的意義遠不止這些。
更多的時候,我甚至以為,泥巴比人更干凈,更高貴了!
泥巴也是有骨頭的,這,就是我眼中的傳承。
傣族銀飾
歷經千年,還薪火相傳,哪怕缺一道工序,都不能成全她。那是銀在火中的鳳凰涅槃,那是突然之間的力迸發出的花朵,她太古老,古老得令人肅然起敬,她還年輕,年輕得令人不加思索地微笑。
輕輕揭開她神秘的面紗,我不知道要經過多少道工序才能這樣唯美,但我知道,她傾注了匠人無數的心血。傣族銀飾,每一次的鍛打、抽絲、扭絲、焊接、拋光、鍍金,都在考驗著一個銀匠。
時間是個好東西,總是會給人以答案,它有時出其不意,有時卻在情理之中。紐扣、胸花、頭飾……這些出自匠人之手的作品,是時間的杰作,佩戴成了日子原本的模樣,詩意也在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中發生著,儀式感讓你知道你每天是在活著,或者說是生活著,不然怎么會有“人充滿勞績,卻還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
如秋葉靜美的不止是一個季節的輪回,一次浴火重生也是一種輪回。她豈止是你看見的靜態美,看她的美,要用仰望星空的姿勢,她是一條瀑布,在匠人的巧手下,她千鈞一發,奔瀉而下,她是夜空下的一條小溪,傣家竹樓前,有人曾等候,她是風雪夜歸人的一抹眉間雪。
傣族銀飾,她只是一件飾品、一種技藝、一件藝術品嗎?
恐怕不是!她有自己的出處,也自會有歸處,與其說每一次的鍛打,不如說是一個少數民族在邊疆的摔打,多少年,不僅沒有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而是喊出一聲疼,帶著傳承,一路走來,眼瞼上的睫毛撥開了歷史的風塵。
傣族銀飾,你是火中疼出來的美,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
人生如鐵
引子:人生如鐵,放久了會生銹,染上鐵銹,這鐵也就廢了。在我的老家寧蒗,鐵是樸素的,鐵匠也是。
鐵匠這個古老的職業世襲著祖先們無窮無盡的智慧結晶。穿越時空隧道,鐵不僅僅只是用于生產生活、戰爭物件等的鑄造。更多的時候,它是一個時代文明進步的象征,是一代人無法抹去的記憶,更是一種精神標桿。
在我有限的記憶里,鐵是一把小小的鋤頭,我曾用它下地干活。小小的人兒,大大的土地,人的氣力全使在一塊苞谷地里,偶爾手上起泡,身上流汗。鐵與人,人與泥土,泥土與莊稼,這三者之間的聯系像是母親與孩子之間那根永遠也剪不斷的臍帶。一方水土喂養一方人,一方人的生活習性也是隨流水賦形般順從大山的高、江水的長。
鐵是彎彎的鐮刀,鐮刀像月亮,指認過月亮的孩子,要保護好耳朵;鐵是一個個舂臼,舂出舌尖上的酸甜苦辣;鐵是不被時光淘洗褪色的那一抹灰塵,稍微撣一下,祖母臉上的皺紋里露出春天的酒窩;鐵是一個游子,父母在,年輕時遠游,年老也要歸家,只有真正的鐵,才能鑄造真正的游子。游子是無悔的、近鄉情怯的、令人思索的。
鐵也是可以拿一個童年來回憶的,只是這回憶有時換來的是哭泣。夕陽徐徐落下,背著柴火的老爺爺邁著吃力的步子,一頭青牛沉默著走在回家的路上,孩子們仍然還在路上快活地打泥巴仗。就在村口不遠處,母親吆喝著自家孩子回家吃飯。不是不愿回家,是舍不得那些泥巴和小伙伴,喊了不聽的,那就吃條子(鞭子)了。也不是真的打,就是那種看起來挺嚇人的樣子。
那時候,我非常想擁有一個鐵環。不用太大,也不能太小。只要和小伙伴們一起出去滾鐵環時有,我就萬分滿足。在那個年代,這樣的情形歷歷在目,小伙伴們三五成群在田埂上滾著鐵環,大家的技術很好,好到一種什么程度?這恐怕科學都沒法子解釋。童年的鐵環是天邊的那輪夕陽,生怕它天黑了,總是小心翼翼地滾動著金色的童年,歡愉的笑聲一浪高過一浪,直到天邊那顆啟明星在天際升起,每一盞忽明忽暗的燈光點亮整個村莊。
鐵也是一個人的名字,一個人的名字帶了鐵,他是頑強堅毅的。秋天很美好,北海的菊花又開了,歷史的車輪卻不會再倒退,該遺憾的終歸是遺憾,該懷念的也只是懷念。一個作家讓人敬佩,除了他的作品,應該就是他的人格了吧?
史鐵生,《我和地壇》怎么樣?《病隙碎筆》又如何?我認為都很好,更好的是他在面對身體上的疾病折磨時的那股子精神,真是有鋼鐵的意志、樂觀豁達的胸襟。命數給他開了一個玩笑,上帝為他開了另外一扇窗。他渴望有健康人的身體,他羨慕能跑能跳的運動員,但他絕不自卑,他睿智博學,對于體育運動比賽,他懂得更多。“痛楚難以避免,而磨難可以選擇。”村上春樹在《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中也不只是說到了跑步,更多的是一種堅持,他是一個作家,他也在一如既往地做一件事。他是史鐵生筆下那種健康的人,他更是一個跑馬拉松的作家。一個有著鐵一般意志的作家是可敬的,一個堅持跑步的作家是少有的。
七彩云南,高原之上,三江并流,鐵一樣的漢子撐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每一個故鄉都會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定居在某個集鎮,他們卑微但并不渺小,他們與鐵是不可分割的。古代的萬里長城,今天的黃河長江,并沒有在浩瀚星河中淹沒那關于鐵的記憶。好男兒鐵骨錚錚,手握鋼槍,駐守邊防,保家衛國。
鐵,遠離了銹,離活也就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