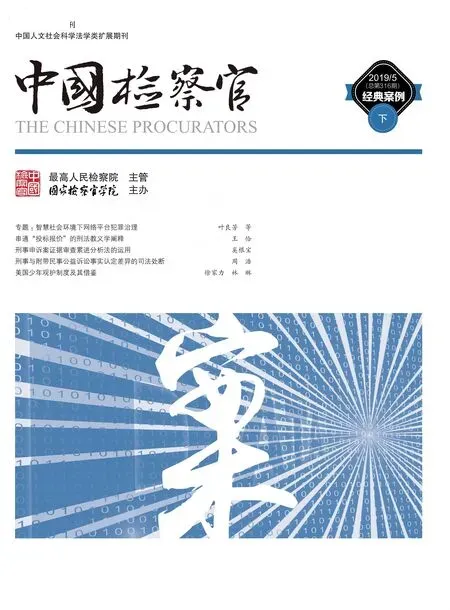聚眾斗毆罪犯罪構成的全局性考量
● /文
[基本案情]2016年12月23日,祁某、李某等人與李某甲等人發生矛盾,雙方約定在遼陽市第十六中學門前見面解決此事。當天雙方到達遼陽市第十六中學門前,因警察在學校附近巡邏,雙方決定改天再約便離開。隨后被告人祁某、李某等看見李某甲等人乘車離開,遂追趕李某甲等人至遼陽市白塔區政和旅店門前,李某甲下車后,被告人祁某、李某對李某甲進行毆打,造成李某甲輕傷二級。2018年4月,遼陽市白塔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祁某、李某(其余人因刑事責任能力等原因未起訴)犯聚眾斗毆罪起訴到遼陽市白塔區人民法院,遼陽市白塔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1]
一、爭議焦點
本案主要的爭議焦點在于檢、法兩機關對于被告人祁某、李某所觸犯的具體罪名有不同看法。檢察院認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構成聚眾斗毆罪,而法院則認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法院認定行為人成立尋釁滋事罪的主要觀點是,被告人祁某、李某系雙方已經放棄當天毆斗的情況下,臨時起意去追趕對方的少數人,其主觀故意是無事生非毆打他人,而不是成幫結伙互相毆斗,客觀上被告人祁某、李某等人追趕上落在最后的被害人后,對被害人李某甲實施了不到一分鐘的毆打后離開,其行為更符合尋釁滋事罪。那么,對于該案中準備聚眾斗毆的雙方在已經完成糾集眾人的“聚眾”行為后,因為警察巡邏或其他意外因素導致雙方決定改日再約離開后,一方乘機追趕另一方并最終實施毆打行為如何認定,需要深入討論。
二、案件分析
法院主要觀點認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系雙方已經放棄當天毆斗的情況下,臨時起意去追趕對方的少數人,其主觀故意是無事生非毆打他人,而不是成幫結伙互相毆斗,客觀上被告人祁某、李某等人追趕上落在最后的被害人后對被害人實施了不到一分鐘的毆打后離開,其行為更符合尋釁滋事罪。這種觀點沒有從全局的視角來考量判斷聚眾斗毆罪的入罪標準和成立條件,而是以局部的、孤立的視角來分別認定行為人每個階段的行為,這種對全局犯罪情況的刻意分離,會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消極后果,影響司法者對行為人所觸犯罪名的準確認定。
(一)被告人的行為不屬于“隨意毆打他人”
基于本案生效判決中的文字表述,法院認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用尋釁滋事罪加以規制更加合理。本文對此種觀點持否定態度,就尋釁滋事罪而言,我國《刑法》第293條規定了尋釁滋事罪的四種罪狀,其一便是“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從本案判決書中人民法院適用尋釁滋事罪規制被告人的解釋理由來看,“其主觀故意是無事生非毆打他人,不是成幫結伙互相毆斗……”,顯然法官認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屬于隨意毆打他人這一罪狀,這種觀點有待商榷。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隨意毆打他人中的“隨意”不能給予無限制的擴大解釋。隨意,一般意味著毆打的理由、對象、方式等存在明顯異常。換言之,當社會一般人從犯罪人的角度思考,也不能接受犯罪人的毆打行為時,該毆打行為便可以理解成是隨意的;從行為人角度而言,隨意,意味著行為人毆打他人沒有任何自我控制。[2]具體到本案,被告人祁某、李某毆打被害人李某甲的行為是因為被告人祁某、李某與李某甲有矛盾在先,而不是平白無故的隨意毆打他人,更不屬于臨時起意,該行為系事出有因爾后毆打特定人員,故不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從社會一般人的角度來看,被告人祁某、李某的毆打行為并不屬于明顯異常;從行為人的角度來看,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是經過預謀的,也是可以自我控制的。因此,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并不屬于隨意毆打他人的情形。
其次,在司法實踐中針對“隨意”的判斷標準有幾個參考因素:其一,毆打行為發生的場合;其二,毆打的對象是否為特定人員;其三,毆打行為的實施是否是無事生非;[3]其四,實施毆打行為是否適用了特定的犯罪工具。[4]具體到本案,無論是從毆打行為發生的場合,還是毆打對象的特定性以及毆打行為的無事生非性均不滿足上述標準。故,從這個角度也不能認定被告人的行為屬于隨意毆打他人。
最后,尋釁滋事罪作為兜底條款的口袋罪,若依據案件客觀事實可以適用其他罪名的情況下,不宜適用尋釁滋事罪來規制相關行為人。詳言之,尋釁滋事罪被規定在我國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一節之中,因其保護的法益是公共秩序或社會秩序,這已使尋釁滋事罪披上了口袋的外衣。[5]設置妨害社會管理罪的初衷是為了防止刑事處罰的法網百密一疏而產生放縱犯罪的結果,尋釁滋事罪身在兜底性罪名群之中難逃口袋罪之嫌疑;同時,從尋釁滋事罪描述的具體罪狀看,條文原文的表述為“隨意”“任意”“情節惡劣”“嚴重混亂”等其本身也具有口袋罪的特征,也即條文表述的不確定性導致價值判斷的模糊性。依據判決原文的表述,“……其行為更符合尋釁滋事罪”,需要指出的是“更符合”的引申含義是法院在確定罪名之時明知或可能預料到被告人的行為滿足除尋釁滋事罪以外的其他罪名(暫不論滿足的具體罪名),卻仍然使用尋釁滋事罪定罪量刑。綜上所述,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尋釁滋事罪中“隨意毆打他人的情形”,不構成尋釁滋事罪。退一步講,即使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那么在被告人行為同時還觸犯其他罪名前提下,將祁某、李某的行為評價為尋釁滋事罪有失偏頗,不僅違背了司法者審慎適用法律的原則,還存在僭越罪刑法定原則之虞。
(二)從全局化的視角剖析整個案件經過
從全局化的角度來剖析本案中祁某、李某的行為,可分為以下步驟:為了斗毆,糾集眾人——糾集完畢,雙方對峙于十四中學門前——因警察巡邏,當時放棄繼續斗毆,雙方離開現場——祁某、李某等人追趕李某甲——趁可乘之機,實施毆打行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等人與李某甲等人雙方人員在案發當天已經到達遼陽市第十六中學門前,也就是說雙方已經完成了糾集他人的“聚眾”行為且已然形成對峙局面,此時雙方的行為可以評價為已經實施了聚眾斗毆罪的著手行為(下文詳述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但由于警察在學校附近巡邏,雙方便決定改天再約,正是因為警察巡邏這意志以外的因素,切斷了聚眾斗毆罪中所包含的“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的緊密性,以至于從空間和時間這兩個維度上看先前的糾集眾人的行為和之后毆打他人的行為沒有直接聯系,正是因為這個理由本案的審理法官認為被告人祁某、李某的行為更符合尋釁滋事罪。這種觀點確實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無疑是片面的。
若以局部的視角單獨評價本案,大體上可分為兩個行為階段,對于行為人實施的糾集眾人且雙方對峙于遼陽市第十六中學門前的行為,雙方當事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被迫放棄繼續犯罪,那么應當認定行為人成立聚眾斗毆罪未遂或預備(就不同的著手標準而言);對于之后祁某、李某等人追趕李某甲并實施毆打的行為應給予另行評價,屬于臨時起意(引用判決原內容文)、另起犯意的實施犯罪行為,成立尋釁滋事罪或故意傷害罪,因此得出結論行為人所實施的上述兩個行為應該數罪并罰。從全局性的視角來評價本案,被告人祁某、李某等看見李某甲等人乘車離開,遂追趕李某甲等人至遼陽市白塔區政和旅店門前,見李某甲下車后,被告人祁某、李某對李某甲進行毆打的行為應屬于祁某、李某這方人實施聚眾斗毆行為的延續。警察在學校周邊巡邏這個因素并不異常,也因此不能中斷毆打行為與糾集眾人行為的因果關系,上述行為人每個具體犯罪步驟的實施以及每個犯罪步驟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從全局的視角考量,對于本案中發生的行為應當進行整體評價,在李某甲等人離開之前,可以認定祁某、李某對雙方可能即將發生的互毆行為已有心理預備,其主觀上具有聚眾斗毆的犯意。在客觀上祁某、李某也實施了毆打行為,雖然在時間節點上因警察巡邏這個因素導致毆打行為的實施在時間節點上稍有滯后,但僅憑這一點不足以阻卻聚眾斗毆罪的成立,應當認定被告祁某、李某成立聚眾斗毆罪。
三、聚眾斗毆罪的犯罪構成
(一)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
一種觀點認為聚眾斗毆罪是復行為犯:一是糾集眾人的行為,二是結伙斗毆的行為。[6]另一種觀點認為,聚眾斗毆罪不是復行為犯,而是單一行為犯,并從六個方面加以論述。[7]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多數觀點認為聚眾斗毆罪是復行為犯,也即此罪的行為模式包含“聚眾”和“斗毆”兩個行為,其中“聚眾”是指在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下,糾集特定或不特定的多人;“斗毆”則是指毆打對方或相互施加暴力攻擊人身的行為。在復行為犯的觀點下,判斷聚眾斗毆罪停止形態的前提基礎是確定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有觀點認為,從實質上看,在公開場合為斗毆而聚眾,本身就有擾亂社會秩序之嫌;從形式上看,就復行為犯而言,行為人只要實施客觀行為的一部分,即為“著手”,因此,聚眾斗毆罪的著手行為為“聚眾”;[8]還有觀點認為,如果雙方只完成了聚眾行為,而沒有斗毆,應認為仍處于聚眾斗毆罪的犯罪預備階段,沒有達到犯罪“著手”的程度。[9]概言之,第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聚眾”行為,即視為犯罪著手;第二種觀點的言外之意認為“斗毆”行為的開始可以視為聚眾斗毆罪的著手行為。
以上兩種觀點的不足在于,以“一刀切”式的方式看待“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忽略了“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的緊密相連性,忽略了“聚眾”行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不同階段的過程性行為,可以細分為“聚眾過程中”和“聚眾完成時”兩個階段的行為。不宜將 “聚眾”理解為本罪的實行行為,主要理由是就聚眾行為的功能而言,“聚眾”是為了實行行為的實施而進行的準備活動,這種糾集、召集眾人的活動尚不會對公共秩序造成現實的直接損害,因而屬于預備犯罪的性質。[10]對此,本文持肯定態度,對于聚眾斗毆罪“著手”標準的認定,應當以“聚眾完成時”為基本參考標準,并結合雙方互相對峙的客觀狀態,只有當行為人的“聚眾”行為基本完成且互相對峙形成準備斗毆態勢時才可以視為聚眾斗毆罪的著手,主要有如下理由:
其一,從社會危害性的角度看,實施“聚眾”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不大,沒有對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造成緊迫的危險。換言之,行為人糾集眾人的行為無論是對于公共秩序的安定和諧還是對于與社會秩序相關聯的個體的人身安全沒有造成實質上的影響。因此,單純“聚眾”行為沒有對刑法所要保護的社會關系產生緊迫、直接侵害的可能性,故不宜作為聚眾斗毆罪的著手起點。相比于單純的“聚眾”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和后果,行為人完成“聚眾”行為且形成對峙狀態所產生的影響和后果大為不同,以這種標準作為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無疑比較合理。
其二,就犯罪著手的界定看,我國刑法學界傳統觀點仍然是主客觀相統一說,這是未遂犯處罰根據上的主客觀統一說在實行著手問題上的引申。[11]隨著德日刑法學說傳入我國,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拋棄主客觀統一說,采用實質的客觀說,例如張明楷教授認為我國刑法理論應當以實質的觀點(實質的客觀說),根據法益侵害說認定犯罪著手。[12]對于此種觀點,陳興良教授也持有肯定態度。[13]本文也贊同以實質客觀說來界定聚眾斗毆罪著手標準,即只有在雙方聚眾完成后且互相對峙時才能認定為犯罪著手,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已經實施了與具體犯罪構成要件密切相接的行為,同時對聚眾斗毆罪所要保護的法益造成潛在的威脅和侵害;對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造成了現實的危險;也因此在實質上更符合對犯罪著手的界定。
其三,刑法目的不僅包括懲罰犯罪也包括保障人權。對于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而言,如果把行為人“聚眾”行為視為聚眾斗毆罪的著手行為,會導致刑法懲戒犯罪的法網無正當理由的擴大,從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角度來講,存在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風險。如此不當界定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顯露出國家權力蔓延的趨勢,蔓延的趨勢對法治國家的建設帶來的潛在威脅,我們應當警惕和關注。因此,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應是“聚眾”行為基本完成且雙發互相對峙時,這一方面體現刑法的謙抑性,適度克減不必要的犯罪認定,能夠節約司法資源;另一方面還有利于對聚眾斗毆罪的打擊范圍合理限制,契合不枉不縱的司法原則。
(二)以司法裁判結果為視角來看聚眾斗毆罪的犯罪構成
本文所探討的案例是實踐中經常發生的情形:行為人雙方因為矛盾糾紛,彼此約定在某處斗毆,一方已經聚集好了人員等候在約定地點,在另一方剛到達約定地點時,由于警察巡邏或者有人報案等理由,被公安機關及時制止或雙方約定改天再斗。對于此種情形,由于雙方已經完成糾集相關人員且形成了對峙局面,此時雙方的行為對于 “公共秩序”可能導致的潛在威脅和侵害不言而喻,因此屬于已著手實行犯罪,應定性為犯罪未遂,而不屬于“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犯罪預備。[14]
在“李天生等十一人聚眾斗毆、尋釁滋事”一案中[15],被告人范冰冰開車來到老制藥廠和被告人李天生等人坐三輛車共10余人攜帶砍刀趕至狀元橋,等候被告人趙偉一方前來械斗時,被公安民警巡邏發現,被告人李天生等參與斗毆人員逃離現場。安徽省無為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李天生、范冰冰等人的行為成立聚眾斗毆罪。在“楊建圍、趙鵬聚眾斗毆”一案中[16],被告人楊建圍、趙鵬等人因賭局放貸與“同行”發生沖突,遂產生聯系人員與對方“碰碰”的想法。在糾集同伙的過程中,被公安機關抓獲。棗強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的行為系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符合聚眾斗毆罪犯罪預備的條件,依法可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在“梁某某、鄧某聚眾斗毆”一案中[17],被告人梁某某與莫某等人發生糾紛,遂電話邀約被告人鄧某,被告人鄧某遂電話聯系岳某并通過岳某等人組織了20余人,分別乘坐幾輛小車由南充市順慶區出發前往武勝縣烈面鎮,在途中,因被公安民警發現,被告人梁某某、鄧某與岳某等人駕車逃離。武勝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梁某某、鄧某等人雖然邀約了20余人,但因在途中被公安民警發現,被告人梁某某、鄧某與岳某等人駕車逃離,未到達現場斗毆,成立犯聚眾斗毆罪(未遂)。
從以上三個案件的裁判結果可以看出,雙方因瑣事、矛盾或者糾紛約定在某一地點進行互相斗毆行為,無論在糾集同伙的過程中,還是在人員糾集完畢去往約定地點的過程中,亦或是其中一方到達約定地點等候對方前來的情況下,盡管法院針對聚眾斗毆罪停止形態上的觀點有些許差異,有犯罪預備的觀點,也有犯罪未遂的觀點(本文認為第三個判例中一審法院認定被告成立聚眾斗毆罪未遂有待商榷),這種差異的產生可能是由于對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標準持有不同的觀點。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犯罪構成和罪名的把握認定上,上述三個案例的被告人都被人民法院認定成立聚眾斗毆罪,而沒有認定為尋釁滋事罪或者其他罪名。因此,在祁某、李某一案中被告方祁某、李某等人已經糾集眾人完畢,而且雙方已經到達在十六中學門前,因警察在附近巡邏,雙方決定改天再約便離開。無論是依據該案件的客觀情況,還是綜合先前法院判例的結果,祁某、李某行為都成立聚眾斗毆罪。
四、結語
從司法實踐中具體案件的處理結果看,聚眾斗毆罪既不能依據一方行為人開始實施聚眾行為時為著手,也不能依據雙方開始實施斗毆認定著手。這是因為,如果雙方互相斗毆行為已經發生,行為人的斗毆行為處于既遂的犯罪形態是毋庸置疑的;在行為雙方沒有完成“聚眾”行為的條件下,對于聚眾斗毆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即社會公共秩序而言,在客觀上還沒有造成現實的危險,沒有侵害到具體的法益,故不應該以此為標準來認定已經著手實施犯罪,不然,認定犯罪著手的時間節點則會被不當提前。一言以蔽之,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應以聚眾基本完成且雙方形成對峙局面準備斗毆為標準。
對于聚眾斗毆罪的入罪標準,要以聚眾斗毆罪的著手為切入點,以全局性的視角加以考量,這樣不僅有利于防止司法擅斷,而且有利于不偏不倚定罪量刑。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化的司法需求是司法機關追求的崇高目標,真正做到不枉不縱,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法治國家之路,漫漫其修遠兮;司法為民之者,將上下而求索。
注釋:
[1]參見遼寧省遼陽市白塔區人民法院(2018)遼1002刑初56號刑事判決書。
[2]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 1063-1064 頁。
[3]參見徐劍鋒:《毆打型尋釁滋事罪與故意傷害罪的邊界甄別》,《中國檢察官》2015年第8期。
[4]參見何慶仁:《尋釁滋事罪研究》,《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4期。
[5]參見張訓:《口袋罪視域下的尋釁滋事罪研究》,《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3期。
[6]參見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中國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5頁。
[7]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 933-934 頁。
[8]參見黎宏:《刑法學各論》,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頁。
[9]參見馬克昌主編:《百罪通論》(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39頁。
[10]參見張啟環:《聚眾斗毆罪的實務問題研究》,《公安研究》2013年第2期。
[11]參見趙秉志:《犯罪未遂形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頁。
[12]參見張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場》,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頁。
[13]參見陳興良:《教義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32頁。
[14]同前注[10]。
[15]參見安徽省無為縣人民法院(2018)皖0225刑初16號刑事判決書。
[16]參見河北省棗強縣人民法院(2017)冀1121刑初77號刑事判決書。
[17]參見四川省武勝縣人民法院(2016)川1622刑初50號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