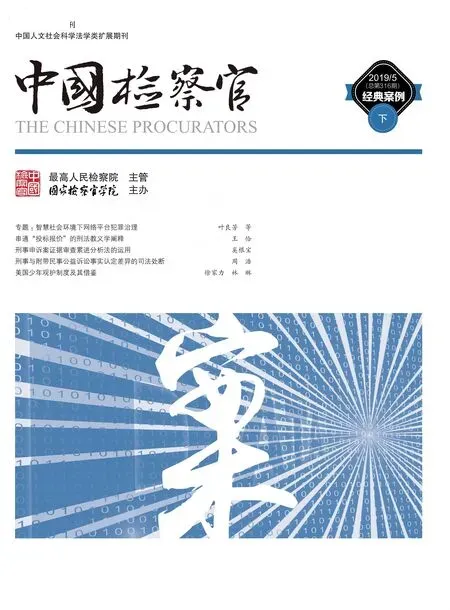民事虛假訴訟檢察監督困境破解
● /文
一、案例及問題的提出
(一)典型案例
劉某某與蕭縣梅村帆布廠借款合同糾紛案,一審法院認定:梅村帆布廠欠劉某某150萬元,事實清楚,有梅村帆布廠給劉某某出具的欠條在卷佐證,且梅村帆布廠對借款及約定利息的事實亦予以認可,借款的事實足以認定,應由梅村帆布廠償還借款150萬元及約定利息。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檢察院再審檢察建議提出:劉某某與梅村帆布廠借款糾紛一案,系王某、孫某、劉某某惡意串通,偽造證據,通過訴訟的方式,致蕭縣信用社的債權沒有得到及時清償,是一起虛假訴訟案件。安徽省宿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蕭縣梅村帆布廠法定代表人王某為轉移該廠的財產,逃避執行,在與劉某某不存在借款關系的情況下,惡意串通,虛構借款事實,進行虛假訴訟。再審法院認定的主要證據包括安徽省靈璧縣人民法院(2015)靈刑初字第00489號刑事判決書等書證,刑事案件突破后所取得的證人證言和當事人陳述等言詞證據。這些證據基本上實現了當事人雙方自認,虛假訴訟的事實足以認定。再審判決撤銷原生效判決,駁回原審原告的訴訟請求。[1]
(一)本案引發的問題
該案的突破依賴于當事人對虛假訴訟的承認,特別是在刑事案件的偵查中所取得的供述和證人證言。目前,這種查辦方式成為檢察機關監督虛假訴訟案件的主要路徑,民事虛假訴訟檢察監督呈現出案件線索發現難、查證難、監督難三大難題。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首批20例民事虛假訴訟監督典型案件中,通過民事案件辦理移送刑事犯罪線索或通過刑事案件移送線索辦理的民事監督案件就有13件,僅有6件案件是運用證據規則,再結合民行檢察部門自己調查核實的言詞證據提起的監督。就在5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剛剛發布的第十四批指導性案例虛假訴訟監督專題中,民事虛假訴訟在案件線索來源上,還是以當事人申請檢察監督為主。
二、民事虛假訴訟檢察監督困境分析
(一)案件線索發現難困境分析
1.虛假訴訟的表象具有合法性,與正常的訴訟在訴訟過程和裁判結果上很難區分。從虛假訴訟的案卷來看,虛假訴訟具備正常訴訟的所有形式要件,既貼近真實,又符合法律規定,隱蔽性很強。虛假訴訟的當事人之間多數具有特殊關系,或者尋找熟人冒充對方當事人,配合默契,雙方對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無實質性爭議,甚至為了使案件看起來更真實,愿意在訴訟過程中做出讓步,迅速達成合意,以獲取法院的調解協議;或者故意隱瞞對方當事人聯系方式等,通過缺席判決,規避法院的實質性審查。本文案例中,也正是王某、孫某與劉某某的惡意串通,且通過偽造證據進行訴訟的方式,侵犯了蕭縣信用社的權益。
2.當事人、案外人向法院申請救濟渠道不暢。如果虛假訴訟單純損害的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無實際受損失的案外人,實踐中由于責任主體的缺乏,很難發現此類虛假訴訟案件,只有在查辦相關職務犯罪活動中才有可能發現虛假訴訟案件線索,這就導致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遭受損害并處于持續狀態,而檢察機關則由于檢法信息不聯通而缺乏及時發現案件線索的渠道和手段。如果虛假訴訟損害的是一方當事人、案外人的利益,由于當事人、案外人未參加訴訟,通常在執行階段才能發現虛假訴訟的線索,當事人錯過了上訴的救濟途徑,申請再審也往往由于舉證能力弱,很難推翻生效的虛假訴訟裁判;案外人因不是案件當事人,無法向法院申請救濟,案外人撤銷之訴因權利主體范圍窄、舉證困難等原因,實踐中并未能充分發揮保護案外人利益的目的。
3.檢察機關受理當事人、案外人申請監督案件的途徑不暢通。當事人、案外人無法向法院申請救濟糾正錯誤虛假訴訟裁判時,往往直接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但是,根據《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的相關規定,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未上訴以及未經過再審程序、案外人控告、舉報的生效裁判監督案件,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對虛假調解案件是否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是否屬于檢察機關依職權監督的案件范圍也無明確的法律依據。
4.尚未完全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審判機關的審判、執行數據,檢察機關的監督數據,偵查機關的偵查數據未實現信息共享,大量能夠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發現的案件線索無法被及時有效發現,影響和制約了懲治虛假訴訟的智能化。虛假訴訟案件具有一些共性特點,如立案快、結案快、執行快,很多案件當日起訴、當日結案,結案后很快申請執行;有的案件一方當事人相同,案件事實基本相同,起訴時間、開庭時間、判決時間相同,僅是另一方當事人有差異。有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進行虛假訴訟的犯罪事實已經認定,但該訴訟并未得到及時糾正。
(二)查證難困境分析
1.被害方提供證據難。虛假訴訟是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精心制作的虛假案件,往往具有預謀性、證據完備性、證據證明力高等特點,而被害方往往遭遇突然襲擊,在證據的取得、保存等方面毫無準備,造成在訴訟中無證據可以對抗,或者證據不完整、證據的證明力弱,而且不排除個別情況下法院工作人員與虛假訴訟受益方相互勾結,在證據采信上傾向于虛假訴訟受益方。如Y市辦理的一起虛假訴訟案件,受益方以威脅方法取得被害方的空白授權委托書,指使受益方的人員冒充被害方參加訴訟,因授權委托書上的公章是真實的,被害方無法證明其未參加訴訟,這種情況下被害方舉證難,造成形式上是雙方當事人而實際上訴訟的對抗性受到破壞,訴訟完全由一方導演。
2.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權缺乏剛性。雖然《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但其規定過于原則,對調查取證的范圍以及程序缺乏細化規范,檢察機關缺乏有效的調查手段,影響和制約了調查核實的剛性。實踐中,檢察機關向有關人員調查核實,被調查對象通常尋找各種理由拒絕配合、不予理睬、躲避調查,或是委托代理人“合理”應付,有的承辦法官不配合調查,辯解時間太久、以案卷記載內容為準等,造成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因沒有剛性保障措施而對被調查對象無計可施。實踐中,檢察機關認定虛假訴訟依賴的往往是偵查機關運用偵查手段,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后獲取的證據以及認定的犯罪事實。
3.基層民行檢察辦案力量不能滿足查處虛假訴訟的要求。從Y市辦理的案件來看,虛假訴訟案件多以一審生效或調解結案,基層院是虛假訴訟監督的主力。但從目前的人員結構來看,基層民行檢察部門工作任務重,人員配備不足,而虛假訴訟案件隱蔽性強,涉及人員多(包括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案外人、承辦法官、證人等),作案方式不斷翻新,從案件受理到案件辦結辦案周期長、任務重,基層民行辦案力量不能滿足查處虛假訴訟的辦案要求。
(三)監督難困境分析
1.法檢兩院對虛假調解案件是否“損害兩益”認定標準存在分歧。法檢兩院對“損害兩益”的判斷標準存在分歧,部分法院認為僅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的虛假調解案件不屬于損害兩益,對檢察機關提出的監督意見不予采納。
2.法檢兩院對虛假訴訟的構成要素意見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防范和制裁虛假訴訟的指導意見》中主張虛假訴訟一般應包括“雙方當事人存在惡意串通”的要素。但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虛假訴訟典型案例看,檢察機關對虛假訴訟的界定則是基本上從廣義上去把握,包含了一方當事人偽造證據、捏造事實的情形。
三、困境破解之策
(一)統一法檢認識,明確監督范圍
對虛假訴訟的含義,學界眾說紛紜,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于是否必須雙方當事人有串通行為,一方當事人捏造事實、偽造證據提起的訴訟是否是虛假訴訟。認為當事人之間必須有串通行為的依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防范和制裁虛假訴訟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將“雙方當事人存在惡意串通”列為虛假訴訟應包含的五個要素之一;認為不需要當事人之間有串通行為的依據是《刑法修正案(九)》對虛假訴訟罪的表述: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2]筆者認為,無論是當事人惡意串通,還是一方當事人捏造事實、偽造證據提起的民事訴訟,都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違背訴訟誠信原則,造成訴訟權利的濫用和司法權威的損害,應對其予以嚴厲打擊,將其都納入虛假訴訟的范疇。實踐中,檢察機關辦理的虛假訴訟案件,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虛假訴訟指導性案件,既包括當事人惡意串通的,也包括一方當事人捏造事實提起訴訟的。
明確屬于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虛假訴訟監督案件范圍。虛假訴訟必然妨害司法秩序,損害司法形象,浪費司法資源,損害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而法律秩序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虛假訴訟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必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特別是虛假調解案件,是虛假訴訟的重災區,Y市2017年以來辦理的虛假訴訟案件中虛假調解占比高達94.85%,而其中直接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幾乎沒有,都是損害個體利益的。此類案件雖然披著“調解”的合法外衣,但這里的調解不是所謂的合法、自愿,而是當事人密謀自導自演的,直接侵犯了其他個體的利益,嚴重擾亂了司法秩序,損害了司法權威,浪費了司法資源,理應受到檢察監督的規制。
上述兩方面,在沒有統一的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可通過公檢法司等部門聯合會簽文件,達成共識,推動對虛假訴訟案件的查處力度。如江蘇省公檢法司聯合出臺《關于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的規定》就上述問題達成一致,該省在防范和打擊虛假訴訟方面成果豐碩。
(二)暢通申訴救濟渠道,主動挖掘線索
在明確虛假訴訟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當事人、案外人有證據證明可能存在虛假訴訟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可直接依職權啟動檢察監督程序。對于當事人、案外人僅能提供虛假訴訟線索的,檢察機關一方面要嚴格按照《民事訴訟法》第209條的規定把握受理條件,引導當事人正確行使申訴權利,另一方面可將當事人、案外人申訴做為案件線索來源,依職權進行調查核實,在條件成熟時再啟動檢察監督程序,維護司法權威。
對涉嫌虛假訴訟的案件,應不受向法院申請再審的限制。同時在申請監督主體方面,可予以適當拓寬,利害關系人在有初步證據證明案件當事人進行虛假訴訟侵害其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也可申請監督,為利害關系人的權利救濟提供合法途徑。另外,檢察機關還可積極主動挖掘案件線索。例如,江蘇省邳州市人民檢察院探索對民事虛假訴訟行為的監督,為拓寬線索來源,該院在轄區內各鄉鎮聘任“民事申訴案件聯絡員”,并聘任各律師事務所、基層調解機構、信訪部門等行業的法律工作者作為聯絡員,構建民行檢察市區、鎮、村三級全覆蓋網絡體系。針對虛假訴訟隱蔽性較強的特點,該院民行部門通過進社區、進企業、進鄉鎮,采用圖片宣傳、法律咨詢等形式,提高公眾對虛假訴訟的鑒別能力和防范意識;并通過走訪律師事務所及法律服務所、回訪當事人等多種方式,及時獲取虛假訴訟案件線索。[3]
(三)充分利用調查核實權,引導當事人救濟
鑒于虛假訴訟隱蔽性強、串通作證的特點,檢察機關調查核實,破解“假象”就至關重要。在監督方式上,檢察機關應充分利用再審檢察建議、提請抗訴、案件線索移送、檢察建議等不同的方式予以監督。另外根據案件所處的階段,采取不同的監督方法,引導案件當事人、利害關系人等采取合適的救濟方式。比如,在案件審理階段,可監督法院是否依法通知相關訴訟當事人參加訴訟,同時可以引導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另行起訴救濟;在判決、裁定等生效后,可對審判程序、裁判結果進行監督,以檢察監督的方式促使法院再審,也可以引導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在執行階段,可通過執行活動監督,對法院執行活動進行全方位的審查,同時為能及時止損,也可引導案外人提出執行異議之訴或者利害關系人提出執行異議,以達到阻止或暫緩執行的目的。
(四)建立虛假訴訟案件識別機制,加大依職權調查取證的力度
從已辦虛假訴訟檢察監督案件來看,虛假訴訟案件發生的領域集中,訴訟過程呈現“三快”特點,案件當事人關系特殊,案件多以調解結案等。總結上述特點,檢察機關應建立虛假訴訟案件識別機制,限定識別要素,對具備幾項識別要素的案件要時刻保持警覺,加大依職權調查取證的力度,進行重點審查,提高識別虛假訴訟的意識和能力,拓寬虛假訴訟案件線索來源。識別要素的設置可以考慮案由、當事人身份、訴訟周期、結案方式、關聯訴訟等。
(五)構建一體化辦案機制,形成打擊和防范虛假訴訟的合力
檢察機關要總結推廣一體化辦案的經驗和做法,充分發揮市級院的龍頭作用和基層院的主力作用,加強對內配合,對外協作。對內一方面要加強上下聯動,發揮市級院的指導作用,對于重大復雜虛假訴訟窩案串案整合全市民行力度集中突破,統一調配辦案力度,解決基層院辦案力量薄弱、人員不足等問題。另一方面加強與控申、刑檢、技術等部門的協調配合。對外要加強與偵查機關、法院、司法行政機關的協調配合,達成共識,形成打擊虛假訴訟的合力。特別是主動爭取偵查機關的支持配合,充分借助偵查機關在偵查取證方面的優勢,在固定刑事證據的同時強化民事案件證據的收集。加強與法院的聯系,就虛假訴訟的認定標準、“兩益”范圍等產生分歧時主動溝通、達成共識,跟進監督,確保檢察監督取得實效。
注釋:
[1]參見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b20b5d73-ccf5-47da-9a19-47825c172ec7,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4月6日。
[2]參見陸小濤:《論檢察監督視角下的虛假訴訟監督》,《黑龍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3]參見夏勝炎:《拓寬虛假訴訟案件線索來源渠道》,《檢察日報》201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