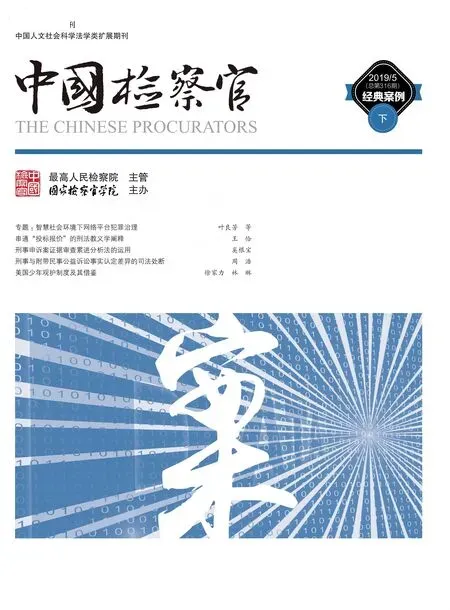非法采伐綠化委掛牌古樹的行為定性
——兼論《刑法》第344條和第345條的適用
● 鐘會兵/文
一、基本案情
2018年9月14日凌晨,施某某組織張某某、楊某某等人非法砍伐四川省C市W鎮某社區一棵綠化委掛牌楠木樹,連夜由唐某某開大貨車將被伐楠木運離案發現場。2018年9月16日,施某某等人偽造《木材運輸證》和《植物檢疫證》等手續,作價13萬元將涉案楠木賣給木材收購商劉某某。經查,該楠木樹由C市綠化委掛牌保護,案發后該市綠化委證明被砍伐的樹木系楠木,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保護級別為II級。2018年9月26日,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森公司鑒(植物)字【2018】469號鑒定意見書,鑒定上述楠木樹屬樟科(Lauraceae)楠屬(Phoebe)細葉楠(Phoebe hui),樹齡160年,不屬于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的國家重點保護植物。2018年10月23日四川楠山林業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1份,證實涉案被伐樹木立木蓄積為5.239m3。同日,四川省綠化委員會辦公室出具《關于明確C市樹齡160年的樹木為古樹的復函》,載明涉案樹木的樹齡達到160年,屬于樹齡100年以上的古樹。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施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私自砍伐政府登記在冊的古樹名木,謀取數額巨大的非法利益,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施某某等人的行為同時觸犯盜竊罪和盜伐林木類犯罪(包括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因兩者屬于普通法條與特殊法條的關系,按照特殊法優先于一般法的原則,應當以盜伐林木類犯罪定罪處罰。因涉案林木不屬于《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中的國家重點保護植物,應當以盜伐林木罪和非法收購、運輸盜伐的林木罪,追究施某某等人的刑事責任。
第三種觀點認為,涉案林木為國家登記保護的植物,屬于不能任意處分的自然資源,不具有一般財產屬性,不能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經四川省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確定被伐林木為“古樹”,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古樹”屬于《刑法》第344條規定的“珍貴樹木”,因此應當以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和非法收購、運輸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追究施某某等人的刑事責任。
三、評析意見
(一)涉案樹木并非不受限的私人財產,而是不得任意砍伐買賣的自然資源,不能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通說認為,盜伐林木類犯罪既破壞了森林資源,又損害了財產權,侵犯的是雙重法益,盜伐林木類犯罪與盜竊罪是法條競合關系。基于此,有的學者認為根據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的原則,盜伐林木的行為當然適用盜伐林木類犯罪;有的學者認為法條競合時能適用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可以以盜竊罪對盜伐林木的行為定罪量刑[1]。無論是特殊法優于普通法還是重法優于輕法,支撐盜伐林木類犯罪與盜竊罪構成法條競合的前提條件是,林木屬于盜竊罪公私財物的范疇。僅就財產屬性來看,林木可以買賣且具有價值,但是盜竊罪中的公私財物要求被盜對象應當對于被害人而言是具有財產屬性的,并且可以在市場自由以貨幣流通的方式處分之物, 而非僅以犯罪人是否獲取利益或者是否可以買賣為標準[2]。我國《森林法》第32條規定,采伐林木必須申請采伐許可證,按許可證的規定進行采伐。意味著,林木雖然可以由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但是該所有權是受限的,林木的所有權人在無采伐許可證的情況下亦不能以市場價值肆意處分林木獲得錢財。可見作為自然資源的林木并不等同于盜竊罪中的公私財物。
刑法將盜伐林木類犯罪放置于第六章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歸屬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類犯罪,且以林木株數和方量而非獲利數額作為定罪處罰標準,可見盜伐林木類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對林木作為自然資源的管理制度,而非其財產價值。因此,盜伐林木類犯罪與盜竊罪之間不是法條競的關系。但是并非所有的盜伐林木行為均不構成盜竊罪,當涉案林木是所有權人的財產而非所有權人不得任意處分的自然資源時,犯罪嫌疑人將其據為己有構成盜竊罪而非盜伐林木類犯罪。《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9條規定,“將國家、集體、他人所有并已經伐倒的樹木竊為己有,以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種植的零星樹木,數額較大的”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已伐倒的樹木與活著的樹木有著本質的不同,樹木被伐倒之后已經失去了環境資源屬性自動轉化為所有權人的財物,能夠被直接處分,故而竊走已經伐倒的林木構成盜竊罪是合理的。對于農村居民房前屋后、自留地種植的零星樹木,根據《森林法》的規定并不需要申請采伐許可證可以徑行采伐。
在本案中,施某某等人盜伐的政府部門掛牌保護的古樹屬于自然資源而非經營者、管理者可以自由處分的財物,因此不能以盜竊罪對施某某等人定罪量刑。
(二)年代久遠古樹屬于珍貴樹木,經省級以上有關部門確定,可以成為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犯罪對象
根據《刑法》第344條規定,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犯罪對象為: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的植物或珍貴樹木。《解釋》第1條規定,《刑法》第344條規定的“珍貴樹木”,包括由省級以上林業主管部門或者其他部門確定的具有重大歷史紀念意義、科學研究價值或者年代久遠的古樹名木,國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貴樹木以及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的樹木。本案中,根據司法鑒定意見書,涉案樹木為細葉楠(Phoebe hui),而非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下稱《名錄》)的楠木(Phoebe zhennan),因此不能直接援引《名錄》認定施某某等人的行為構成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只能從涉案林木否屬于“珍貴樹木”進行分析。
根據四川省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的復函,確定涉案樹木樹齡為160年,屬于年代久遠的古樹,但未直接明確其為珍貴樹木。司法解釋將“古樹名木”作為“珍貴樹木”的一種,在理解與適用上可能存在分歧:珍貴樹木既要求是古樹又要求是名木,抑或是古樹、名木任何一類。國家林業局2016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林業行業標準—古樹名木普查技術規范》明確把古樹與名木分開,其中章節3.1規定:古樹,指樹齡在100年以上的樹木;章節3.2規定:名木,指具有重要歷史、文化、觀賞與科學價值或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樹木。因此,四川省綠化委員會辦公室出具《關于明確C市樹齡160年的樹木為古樹的復函》,載明涉案樹木的樹齡達到160年,符合樹齡在100年以上的古樹認定標準,應當被認定為珍貴樹木。此外,認定珍貴樹木的行政主體是省級以上林業主管部門或者其他部門,四川省綠化委員會是省級機構,綠委辦公室代表綠委,有權作出認定,符合司法解釋規定。
(三)《刑法》第344條與345條屬于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在“特別法條畸輕”的場合,可適用第345條對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林木的行為定罪量刑
刑法將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與盜伐林木罪并列而行,連續表述。從犯罪客體來看,兩個罪名均屬破壞環境資源類犯罪,侵害的是國家對林木資源的管理制度;從行為方式上來看,均是在未取得相關許可、違反國家法律規定的情況,擅自采伐國家重點保護的植物或林木。無論是從犯罪客體還是行為方式,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和盜伐林木具有高度一致性。唯一不同的是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的犯罪對象限定為“珍貴樹木或者國家重點保護植物”,既包括珍貴木本植物又包括其他重點保護植物;而盜伐林木罪的犯罪對象則是受《森林法》所保護的木本植物。眾所周知,因為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具有普通林木所不具備的重大歷史紀念意義、科學研究價值或生態價值,所以刑法在盜伐林木罪之外單設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對其予以特殊保護。因此,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與盜伐林木罪之間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也即,當行為人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林木(不包含草本、蕨類、菌類等植物)時,既觸犯《刑法》第344條又觸犯了第345條。
當法條發生競合時,特殊法優先于普通法是一般處斷原則,但是,在特別關系的場合,還可能適用重法條優于輕法條的原則[3]。就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和盜伐林木罪而言,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屬于特別法條,盜伐林木罪屬于普通法條,在一般情況下,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林木的行為應當適用特別法條。但是,當適用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刑罰明顯低于盜伐林木罪時,為避免“重罪畸輕”現象的出現,可以適用法定刑更重的盜伐林木罪。《解釋》第8條規定,盜伐、濫伐珍貴樹木,同時觸犯《刑法》第344條、第345條規定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從刑法條文設置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來看,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屬于重罪,盜伐林木罪屬于輕罪。根據刑法及《解釋》規定,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無入罪數額標準,而盜伐林木入罪標準為2-5m3或幼苗100-200株,量刑幅度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達到情節嚴重數量標準只需要2m3或2株以上,盜伐林木達到“數量巨大”標準為20-50m3或幼苗1000-2000株,量刑幅度均為3-7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相同的量刑幅度內,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的入刑標準明顯低于盜伐林木罪。但是第344條僅規定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3-7年有期徒刑兩檔刑期,而盜伐林木罪除此之外對盜伐林木“數量特別巨大”的行為還規定了7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即,當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達到100-200m3或幼苗5000-10000株以上時,依照《刑法》第344條規定僅能在3-7年有期徒刑內量刑;而盜伐同等數量的普通林木,依照《刑法》第345條規定則能判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時若嚴格按照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的原則,則會出現“重罪輕罰、輕罪重罰”的現象。為保持罪責刑相適應,對于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達到100-200m3或幼苗5000-10000株以上的行為可以適用盜伐林木罪定罪量刑。
本案中,施某某等人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樹木,立木蓄積為5.239m3,未達到100-200m3或幼苗5000-10000株以上的標準,按照第344條規定,量刑幅度為3-7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而按照第345條規定,量刑幅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前罪量刑明顯重于后者,因此應按照第344條對本案定罪量刑。
(四)《解釋》部分條款與刑法規定存在沖突,為保持司法解釋與法律規定的一致性,建議對《解釋》部分內容予以修訂
1.關于非法采伐、毀壞非林木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犯罪量刑問題。《刑法修正案(四)》將“非法采伐、毀壞珍貴樹木罪”修改為“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使該罪的保護對象從“珍貴樹木”擴大到“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及其制品”。根據《中國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名錄(第一批)》規定,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包括蕨類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藍藻和真菌五大類,作為木本植物的“珍貴樹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縱觀《解釋》的第1條和第2條只對非法采伐、破壞“珍貴樹木”的行為進行內規定,而未對非法采伐、破壞草本植物、真菌、藍藻等其他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及其制品的行為進行規制,導致司法解釋未能全面涵蓋法律規定。在實踐中,即使是比照“珍貴樹木”的標準對非法采伐、破壞其他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的行為進行處罰也會帶來適用上的困擾。如藍藻類、真菌類植物體型小、無固定根系難以從“株”上予以界定,更不能以方量作為刑罰翻格標準。又如作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植物的野大豆(草本植物)遍布除新疆、青海以外的各省市,而作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植物的百山祖冷杉(木本植物)在我國自然分布區僅存林木五株,兩者無論在瀕危程度、科學研究價值還是在生態環境價值上均有天壤之別。但是比照現行司法解釋,采伐兩株常見野大豆與砍伐兩棵極瀕危百山祖冷杉在刑罰上并無二致。因此,應當根據植物的形態、瀕危狀態,分類別確定木本、草本、蕨類、真菌等不同形態的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的刑罰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指引。
2.關于非法收購、運輸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制品行為定性問題。筆者認為,既然《刑法修正案(四)》已經對第344條和第345條第3款作出修改,司法實踐應當適用新的刑法規定而非《解釋》第11條之規定。不管是否在林區,只要明知系盜伐、濫伐的林木或國家重點保護的植物,仍然非法收購、運輸且達到司法追訴標準的,就應當以非法收購、運輸盜伐的林木罪或非法收購、運輸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認定。
需注意的是,《解釋》第11條規定,“非法收購盜伐、濫伐的珍貴樹木2m3以上或者5株以上”“非法收購盜伐、濫伐的珍貴樹木5m3以上或者10株以上”才能分別構成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林木罪的“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而《刑法修正案(四)》把非法收購、運輸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與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放在同一條目下連續表述,從條文的一致性出發,非法收購、運輸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的入罪及量刑標準應當與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一樣,即無論數量多少,只要實施了非法收購、運輸行為即構成該罪,而非《解釋》第11條中2m3以上或者5株以上。同理,非法采伐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情節嚴重”的標準也應當適用于非法收購、運輸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即2m3或2株以上而非5m3或10株以上。
就本案而言,對于施某某、張某某、楊某某等人的行為,應當整體適用《刑法》第344條予以評價,而非按《解釋》的相關規定對采伐行為適用第344條,而對運輸、收購等行為適用第345條評價。
注釋:
[1]參見張明楷:《盜伐林木罪與盜竊罪的關系》,《人民檢察》2009年第3期。
[2]黃河:《盜伐林木罪與盜竊罪關系新論》,《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3]同前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