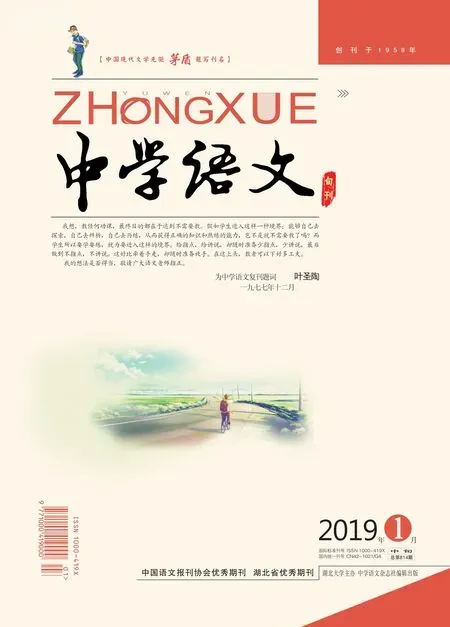時代驕子傳奇人生
鐘 江
回望錢學森
錢學森地位高,家里用著炊事員。一天,炊事員對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講,你爸爸是個有學問有文化的人。他兒子聽了,覺得好笑,心想,這事還用你說?炊事員不慌不忙,接著講,你爸爸每次下樓吃飯,都穿得整整齊齊,像出席正式場合,從來不穿拖鞋、背心。明白不,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錢學森的兒子聽罷一愣,懂得炊事員是在敲打自己。錢永剛聽了炊事員的話,從此就向父親學習,每逢去餐廳吃飯,必穿戴得整整齊齊。
1935年到1955年,錢學森在美國呆了20年,留下大量的科研手稿。錢學森有個美國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就把那些手稿收集起來,到了上世紀90年代又把它完璧歸趙,送還給錢學森。這些手稿,與其說是手稿,莫如說是藝術品。無論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計算、圖表,都工工整整,一絲不茍,連一個小小的等號,也長短有度,中規中矩。錢學森的手稿令人想到王羲之的《蘭亭序》,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進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還有一件事在美國期間,錢學森僅僅為了解決一道薄殼變形的難題,研究的手稿就累積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進展到五百多頁部分,他的自我感覺是:“不滿意!!!”直到八百多頁時,才長舒一口氣。他把手稿裝進牛皮紙信封,在外面標明“最后定稿”,繼而覺得不妥,又在旁邊添上一句:“在科學上沒有最后!”
天才絕對來于勤奮。錢學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猶太籍的校友回憶:“有天一大早——是個假日,感恩節或圣誕節——我在學校趕功課,以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個人,所以把留聲機開得特別響,還記得我聽的是有個特別響亮的高潮的《時辰之舞》。樂曲高潮到一半時,有人猛力敲我的墻壁。原來我打擾到錢學森了。我這才知道中國學生比猶太學生更用功。后來他送我幾份他寫的關于近音速可壓縮流體壓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論文,算是對于曾經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錢學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學生麥克則回憶:錢學森教學很認真,全心全意放在課程上。他希望學生也付出相同的熱忱學習,如果他們表現不如預期,他就會大發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麥克做一些有關扇葉渦輪引擎的計算,麥克說:“我算了好一陣子,但到了午餐時間,我就吃飯去了。回來的時候,他就在發脾氣。他說:‘你這是什么樣的科學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飯!’”
關于歸國后的錢學森,你注意過他的履歷表嗎?他是先擔任國防部五院院長,然后改任副院長。這事不合常規,怎么官越做越小,難道犯了什么錯誤?不是的。原來,錢學森出任院長時,只有四十五歲,年富力強,正是干事業的好時光。但是院長這職務,按照現行體制,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鹽。舉例說,底下要辦一個幼兒園,也得讓他撥冗批復。錢學森不想把精力耗費在這些瑣事上,他主動打報告,辭去院長職務,降為副院長。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集中精力,專門抓業務了。
(選自《讀者》)
錢偉長:科學巨子 傳奇人生
錢偉長,為中國人熟知的科學家,“三錢”中的最后一位,7月30日在上海走完了98歲的一生。錢偉長的傳奇人生,是一代中國學人希冀和奮斗的縮影。
1931年9月,清華大學招入了一批新學生。錢偉長的作文和歷史拿了滿分,理科卻幾乎是零分。所幸靠著文科成績,通過了考試,就讀清華中文系。誰能料到,第二天錢偉長就改變了自己的選擇,也改變了一生的走向。這一天,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九一八”事變。侵略,以中國軍隊的退讓告終。“我聽了以后就火了,”錢偉長回憶說:“沒飛機大炮,我們自己造嘛。所以我下決心,要學飛機大炮。”他想轉到物理系,于是幾次跑去找系主任吳有訓。吳有訓提出先讓錢偉長試讀一年,如果化學、物理和高數都考過70分,就允許他轉系。那一年,錢偉長除了吃飯睡覺,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撲在物理和數學上。功夫不負有心人,第一學期結束,錢偉長的物理及格了。到學年結束時,他的數學、物理、化學、外語等科目的考試成績都拿到八十多分,得到了以嚴格著稱的吳有訓的認可。
1943年6月錢偉長在獲得多倫多大學博士學位后,正式參加加州理工大學哥根海姆實驗室噴射推進研究所工作。錢偉長主要從事彈道計算和各種不同類型飛彈的空氣動力學設計,在初期的人造衛星軌道計算上做出了貢獻,他還完成了有關于火箭的空氣動力學設計、彈型設計、高空氣象火箭研究。1944年夏,由于錢偉長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為美國航空科學學會正式會員,并在得克薩斯州白沙試驗場進行下土式火箭發射實驗和液體火箭發射實驗。同年秋,他在美國航空工程學會上宣讀了 《超音速對稱錐流的攝動理論》,這是國際上第一篇這方面的論文。這幾年,是錢偉長的科研多產期,他成了馮·卡門的得力助手,一顆科學新星。
正當錢偉長在美國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選擇了回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讓他渴望回國效力。他如是描述當時心里的矛盾:“我愛國嗎?干嗎有本事為外國人服務呢?”錢偉長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見過面的六歲孩子為由,要求回國探親。1946年5月6日,錢偉長只帶了簡單的行李和幾本必要的書籍,從洛杉磯乘船回國。當時他34歲。
為了實現“科學救國”的抱負,錢偉長幾乎承包了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工學院的基礎課應用力學和材料力學,物理系的理論力學、彈性力學等課程,還擔任《清華工程學報》主編等審稿工作。
1952年院系調整后,錢偉長被任命為純工科的清華大學教務長。1956年錢偉長又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副校長,仍兼教務長和力學教授。錢學森回國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學研究所,錢偉長又兼任了副所長。1955年中科院學部成立,錢偉長成了第一批被選聘的學部委員。盡管兼職讓錢偉長忙得不亦樂乎,他并沒有打亂自己的科研節奏。這幾年他發表了20多篇科研論文,出版了《彈性柱體的扭轉理論》《圓薄板大撓度問題》等專著。1954年,錢偉長和他的學生合著的科學專著《彈性圓薄板大撓度問題》出版,在國際上第一次成功運用系統攝動法處理了非線性方程。1960—1966年間,錢偉長共講授了12門教學計劃外的新課,編寫了600萬字的教材。
70多年來,無論是從事科研或教育,錢偉長的原則只有一個。“我希望國家強大起來,”他說,“強大要力量,這力量就是知識。”
(選自《科技日報》)
季羨林留給我們什么?
“智者樂,仁者壽。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學問鑄成大地的風景,他把心匯入傳統,把心留在東方。”
2009年7月11日,國學大師季羨林走了。他帶走了自己對他人、對社會滿懷的愛與責任,帶走了自己的樸素、真誠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對文化傳承的反思。
“季羨林先生在東方學、古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主要社會學科都有極高的造詣,他留給我們的人文學術遺產豐厚翔實、珍貴無比。”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程玉綴說,“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能真正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他的吐火羅語研究打破了 ‘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他研究翻譯的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名著,已匯編成24卷的《季羨林文集》……”
季羨林曾說,所謂“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舉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學問納入到他研究的范疇:從佛典語言到佛教史、印度史,從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到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從唐史、梵文的翻譯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學作品的創作,他無一不精深涉獵。”季羨林的學生、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王邦維對記者說。
“季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上強調最多的是中國古代的智慧結晶—‘天人合一’觀點,即要先與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為貴’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種族所面臨的諸如全球氣候變暖、資源愈加枯竭、戰亂不斷等許多問題的解決之道。”程玉綴說。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標志著一個國學研究時代的結束,是中國文化界的巨大損失。”季羨林的老友、著名哲學家湯一介這樣評論道。
季羨林為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
程玉綴回憶起北大廣為傳誦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著樸素。在擔任北大副校長時,一個來報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對他說,‘我要去報到,行李太重,你幫我看一會兒。’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報到回來。第二天開學典禮時,這位新生發現主席臺就座的副校長正是昨天給他看包的老人。”
對外界為自己加冕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這三項桂冠,季羨林在《病榻雜記》的書中評論說,這令他誠惶誠恐,“請從我頭頂上把三項桂冠摘下來,還我一個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