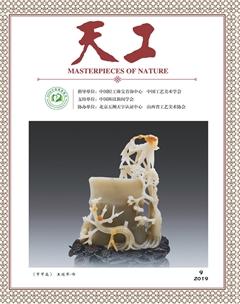民國“黃金十年”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述要
陳晨

[摘要]從1927-1937年期間南京民族形式建筑高潮的時代背景、城建政策入手,分析中國第一代建筑師在受學院派建筑教育中的“西方古典美學原則同東方審美,西方現代建筑材料與中國樣式,西方建筑結構標準同中國傳統木構架”的影響下,因為調和中西古今的手法不同,而形成的三種最常見細分風格類型。
[關鍵詞]民國;黃金十年;南京;民族形式建筑
一、時代背景與城建政策
1927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的十年,國民政府以南京為首都,以上海為經濟中心,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這是近代中國唯一一段相對穩定統一的時期,各項現代化制度初具雛形,被稱為南京十年或“黃金十年”。
“黃金十年”,城建是要沖。北伐結束后的南京“古老而殘破,還不是一個堪稱中國首都的城市,冬天寒冷,夏天濕熱,甚至沒有現代化的衛生設施”,因此,為了打造新都形象,南京國民政府在《規劃首都市區圖案大綱草案》《首都大計劃》等先聲陛規劃法規與草案的基礎上,以科學化的城市設計先行,而城市美化取量力而行的規劃主旨,于1929年制定了《首都計劃》。傳達政治正統性的民族形式建筑,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期間得到了官方支持。基于此,“要以中國固有之形式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當盡量采用”成為定位首都建筑形象的基本原則。這種形式建筑,遂成當時的建筑風尚。置身這一時代背景中的新興社會精英——中國建筑師。立足南京,并在國民政府制定的民族形式城建政策保障下,尋得可以與外籍建筑師、洋行競爭建筑市場的空間,由此催生了中國建筑師群體持續十年的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熱潮。
二、建筑的細分風格類型
復興中國固有形式是民族形式建筑的設計主旨之一。對于國民政府來說,這一文化復興政策落實在建筑上,更多地成為一種基于文化象征主義的形式創造;對于民國“黃金十年”執掌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建筑師來說,由于存在“學院派教育背景下以西方古典美學原則調控建筑比例”“調整西方建筑結構標準以適應東方審美原則”以及“混合西方材料于中國式樣”等多條探索路徑,因此,民族形式的具體風格特征,就不能以“中西合璧”籠而統之,而需從建筑各部位造型、裝飾與結構等方面加以細分,并歸納形成民族形式建筑的風格類型。對此,筆者經過實地調研與比較分析后發現,民國“黃金十年”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可以分為以下三個細分類型:
(一)大屋頂式中華古典復興式
這一建筑風格來源于官式建筑大屋頂,是國民政府借由傳統建筑與現代建筑的結合,宣揚國民黨正統形象的政治意圖使然。而對于國民政府來說,傳達精英文化價值取向的宮殿、寺廟建筑,其上顯赫的大屋頂最能代表“中國固有之形式”。加上國民政府嘉賞的外籍建筑師如亨利·墨菲等,極力推崇屋頂造型與建筑裝飾中的民族文化特色,進而掀起一陣宮殿式民族形式建筑熱潮,使得“黃金十年”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中這類民族形式建筑成為主流。
這類民族形式建筑的特征主要體現在檐部。具體而言:1.檐部材料趨于多元化,除煙灰色簡瓦、板瓦以外,出現棕黃色、土紅色、藍色、綠色琉璃筒瓦材質,如美齡宮、中山陵建筑群、勵志社、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舊址、中英庚款董事會等。2.部分建筑的檐下出現斗拱,多采用尺度較小、排布較密的清式裝飾性的斗拱,如中山陵祭堂檐下的坐斗和拱的組合構件。3.檐下額枋多施彩繪,大多采用旋子彩畫的圖形結構,或以青綠黃色為主,或以淺浮雕素色成型。前者如勵志社、華僑招待所、美齡宮,后者如中山陵祭堂、享殿等。4.重檐屋頂之間間距較大,多設置采光窗口。這是從使用功能入手,對中國傳統重檐屋頂的改良設計,如國民政府鐵道部、美齡宮、勵志社等。5.吞脊獸與檐部色彩統一。檐部材質、色彩多元化,鴟尾(吞脊獸)的色彩也趨于多樣化,但是整體造型簡潔,有向幾何化演變的趨勢,同時較少出現垂脊走獸。
這類民族形式建筑的墻身與南京傳統建筑墻身相比存在較大區別,這與鋼混結構取代磚木結構,現代功能主義建筑對采光、通風的需求以及學院派古典建筑的構圖比例有著密切關系。因此,墻身可以大面積開窗,或采用等距排列長條窗的文藝復興式府邸的立面形制,有些甚至突破了山墻上不開大窗的傳統建筑風水禁忌,而開設了面積較大的長條窗,旨在改變中國傳統建筑檐部深遠、影響采光的弊端。這既是大屋頂式中華古典復興式建筑墻身的特點,也是幾乎所有民族形式建筑的共性特征。
(二)簡約仿古式
簡約仿古式一般沒有顯赫的大屋頂,它是在現代板式混凝土建筑基礎上,于檐下、門楣、窗楣、腰線等處添加簡化后的傳統裝飾或瓦解了結構意義的建筑構件而成。這是一批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建筑思潮影響的留學歸國建筑師,在國民政府復興“中國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上與現代建筑形態、結構、空間之間尋求調適與折中的結果。代表作有:楊廷寶設計的中央醫院舊址建筑群,奚福泉設計的國民大會堂與國立美術陳列館等。這類民族形式建筑的檐部特征為:1.坐斗與拱的結合,如國民政府外交部檐部;2.夸大補間鋪座相接處的拱眼,并處理成鏤空幾何形態,如中央醫院舊址建筑的檐部;3.在檐部架設廊架,并于廊架梁柱之間增加幾何形插角,其上浮雕拐子紋,如中央醫院舊址主大樓的檐部,國立美術陳列館側立面的檐部;4.檐下增設螞蚱頭,多為淺浮雕祥云樣式,如中央醫院舊址主大樓門廊的檐部;5.檐下仿照彩畫的圖形結構,浮塑拐子紋,并在浮塑的彩畫裝飾之下增設螞蚱頭,如國立美術陳列館、國民大會堂的檐部。基于建筑結構轉型與現代建筑的功能訴求,這類民族形式建筑的墻身與大屋頂式中華古典復興式并無根本差異。
(三)傳承結構意義與邊疆民族建筑特點的現代式
這類民族形式建筑在黃金十年的南京比較特殊。一方面,雖然19世紀以來西方建筑評論中的結構理性主義標準流傳國內,但是用它來分析中國傳統木構架建筑,還存在觀念的隔閡和解讀的偏差。由于當時考古學實地考察和測繪剛剛起步,將結構演變視為中國傳統木構架建筑造型、美學品評的依據,還要等到營造學社考察、測繪了大量古建筑以后,才逐漸明晰,因此,基于結構理性主義與實證分析的研究法,同中國傳統的美術史學形式分析法相結合,并應用于建筑實踐的條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隨著國民政府的民族文化復興政策在南京強勢推進,美化國民黨政治形象的重要載體一民族形式建筑的文化象征內涵被有意地凸顯出來。
在傳承結構意義與邊疆民族建筑特點的現代式探索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童寯先生。由他主持立面設計的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與官舍工程,以及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古物保存庫,皆汲取藏族平頂建筑風格,模仿承德外八廟中須彌福壽之廟的大紅臺。但是,與色彩明烈的藏族建筑相比,這兩例建筑墻身或采用泰山面磚或采用青磚局部水泥砂漿抹面,色調素雅,戶牖簡潔,方整無飾,經濟實用。立面上也沒有那種遠離材料表現與結構理性的圖像化拼貼,只是在平整的墻面上開挖簡單窗牖,添加了樸素的壓頂線,檐下也沒有喪失結構意義的斗拱和贅飾。這是童寯否定大屋頂的“辮子藝術”,將契合于新技術、新材料的平屋頂與中國形式建筑相結合。他的學說觸及了建筑學科的核心——建構,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前具有相當的先鋒性,引領了當今趙辰、王駿陽、朱濤、陳薇以及王澍等一批建筑學者、建筑師的建構學研究與實踐。
民族形式建筑體現了近代南京的主要地方特色,即傳統文化根基深厚,西化、現代化進程不及上海、廣州、天津等租界城市、通商口岸,頻頻出現在建筑上的中國北方官式建筑大屋頂,明麗的旋子彩畫、簡潔古雅的裝飾以及馬歇爾公館上水戧發戧的江南特色的屋架,折射出六朝古都的城市意象。因而,民族形式可被視為南京近代城建史上最能展現歷史、地域文脈與時代精神的經典形式。
除了助推民族形式建筑普及南京的國民政府的民族文化復興政策,附帶政治規訓的目的以外,社會精英的家國意識與民族主義情結,以及第一代中國建筑師在“學院派建筑教育的受教育背景,同中國傳統建筑木構架體系、平頂式邊疆民族建筑特點與近代中國城建的實際需求之間”,探索形成的多元化民族形式設計手法、實踐成就,以及關于中國本土現代式建筑的學術觀點,對于倡導民族性、時代性的當今設計界來說,仍有啟發與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
陳晨,女,1982年出生,研究生學歷,金陵科技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建筑學/設計藝術學。
[作者單位]
金陵科技學院藝術學院
(編輯:劉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