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法系的特點及價值
許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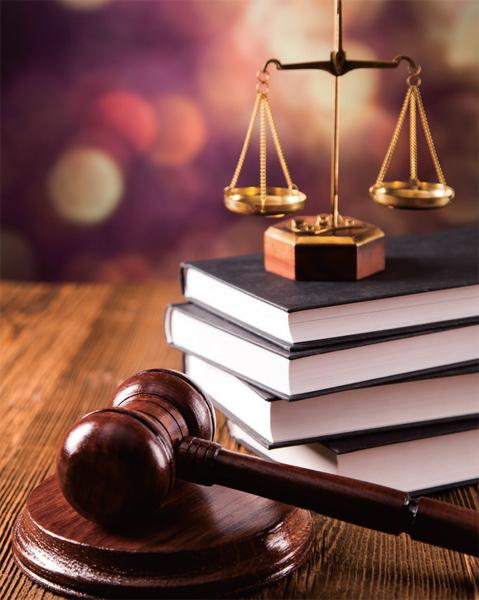
數千年陳陳相因、延續至今的制度建設和司法實踐,使中國形成了卓爾不群、自成一格的法制文明。承載著古代法制建設輝煌成就的中華法系,是傳統中國法制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中不斷演化而一脈相承的。中華法系雖然已經解體,但就其蘊含的法律文化因素而言,仍與今天中國的法制建設具有著密切的聯系。重新審視中華法系的制度內涵和文化意蘊,分析并總結其特征與價值,不僅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宏偉藍圖的實現將提供有力參考,而且對當前法治中國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也將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并產生積極深刻的推動作用。
一、中華法系的特點
(一)禮法結合,重禮輕法
中華法系中所稱之“禮”,是一種強調三綱五常、自成體系、全面規定國家基本制度與社會等級秩序的倫理規范。禮源于氏族社會時期人們所約定俗成的規矩、準則,最初作為一種儀式被用于原始社會的祭祀祈福活動,后來逐步演變成調整人們日常生活的風俗習慣,得以系統化、規范化。誠如一些學者所言:“禮”乃家庭生活之準繩,為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務與外事之規矩。同樣,“禮”亦統轄一國的內務外交,成為規范統治階級的行為準則。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禮所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與法的相互結合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禮與法的相互滲透與結合,構成了中華法系最本質的特征和特有的中華法文化。”[1]西漢以后法典的制定與編纂幾乎都是以儒家學說作為基本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在法典中貫徹“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儒法合流,使儒家經典法律化。但禮法結合并不意味著兩者并重,而是以禮為基礎,“重禮輕法”。該種價值取向寓意倫理與道德的原則優于普遍的法律規則。司法實踐中,可以直接運用倫理來判決案件而不受成文法的嚴格約束。《唐律疏議·明例篇》就提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一準乎禮”。具體到司法中也常常出現以禮折獄、棄律從禮的現象。
(二)法律體系上側重于刑事立法,民事立法較為分散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古代的法律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以刑代民”。這種看法不盡妥當。筆者認為,諸法合體著重是從法典編纂的意義上來看的,而民刑之間的關系則主要應從法律體系的實際內容入手來加以考察。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法典主要指刑法典,但法典中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早已超出了民法、經濟法所調整的范疇。古代存世法典內容豐富,經常可見民事、經濟等方面的規定,這樣的法典編纂情況往往帶給學者“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錯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從整個法律體系入手考察,民刑實際上是有區分的,中國古代除律之外,還存在著相當數量的民事、行政、經濟等方面的法律,其一般表以令、格、式等形式表現出來。它們或包含在律典里,或以單行法的形式發揮著其在民事方面的作用,所以對中華法系在法典編纂上的特征應是“諸法合體、民刑有分”。
(三)受封建傳統家庭本位觀念的影響,重農抑商,厭訴、息訴觀念影響深遠
“任何社會的法律,都是為了維護鞏固其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而制定的”。[2]中國在封建時期,一直以農業為重,小農自然經濟始終處于統治地位。商人比起被永久束縛于土地的農民來說,被認為更難管理和控制。將農業作為立國之本的傾向,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整個法律體系。體現在立法中,保護農業生產一直是歷朝歷代統治者關注的重中之重;具體到司法上,司法機關不受理春夏之季的非刑事案件就是為了避免妨害農事。
這種小農經濟給百姓的觀念中打下了安土重遷的烙印,在這樣一個熟人社會里,商品經濟尚不發達,人們相互間的經濟交往也較為有限,產生的糾紛自然也就不多。
穩定的地緣與血緣相互作用,使調處息訟在我國古代司法裁判制度中得以盛行。所以大部分糾紛是通過法律以外的調解來解決的,調解的依據主要有風俗習慣和禮法規范。由于這種解決糾紛的方式有其良好的社會效果,歷來被最高統治者高度提倡。但以“根絕訴訟、息事寧人”為目的的調處息訴的流行,使得原本就很不成熟的法學始終伴隨著民間普遍的“畏訴、厭訴”心理,其得到發展的機會和空間也都非常小,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中華法系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中國始終未能形成自己專門的法學職業家。
在鄉土社會的大背景下,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較為強調親緣血緣關系,倫理法因其調整的是以父權為核心的家族之間相互關系而一直占據重要地位。正因為家族內部的矛盾和沖突主要依靠德高望重者的調解,而非訴諸法律,這樣一來,真正告到官府去解決的案件數量就十分有限了。
(四)皇權至上,行政干預司法,行政機關兼理司法
中國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實行君主專制制度,君權的強大使得皇權法律化甚至凌駕于法律之上。對于侵犯皇權統治、威脅皇帝安全的犯罪,一向都被視為十惡不赦的大罪加以嚴厲制裁。皇帝不但是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的掌握者,而且還是最高司法權的擁有者,有時還親自參與法律的制定和頒行工作。例如,將死刑的最后裁判權通過“復奏”等方式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這是行政權至上、司法權附庸于行政權最集中的體現。除皇帝外,司法權同時也被朝廷中的官員所享有,比如,明清時期出現三法司長官會同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五部尚書等行政官員參與“九卿會審”的情況。具體到地方州縣,則更是行政長官、司法長官兩者合二為一。可見正由于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中國古代司法與行政不分的法制特點。司法權依附于行政權使得專業職業司法官缺乏,并且使司法權喪失了其本身具有的獨立性。同時,君權也因為缺乏必要的限制和權威的約束而極易膨脹。尤其是通過儒家“天人感應學說”的論證,君權又得到了上天的支持,為君權辯護的綱常禮教成了天理。相反,個人的權利則經常受到漠視和踐踏。
中華法系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和民族精神的體現。其特點中的禮法結合是中華法系最主要的傳統和特征,始終貫穿于中華法系的各個發展階段,成為古代中國的治國方略。儒法思想在漢代以后為統治者并重,甚至最終趨于合流,二者將刑罰與教化相結合,寬猛相濟,為立法與司法提供了指導并且成為中華法系的主導精神。
二、中華法系的價值——對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的啟示
(一)中華法系中的儒家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領會和諧的本質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法治中國的構建是建立在和諧社會的基礎之上,傳統儒家思想的許多內容就閃爍著有關和諧的理性之光,既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又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且和諧的程度根本上關乎社稷穩定與人民幸福。這一進程中形成了“息訴”、“無訴”的觀念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家族本位”,“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一系列特色鮮明的法治傳統。在今天,社會和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成為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保障。“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既是和諧社會的的總要求,也是社會和諧的主要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無疑是對中華法系“民本思想”、“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人和諧相處”等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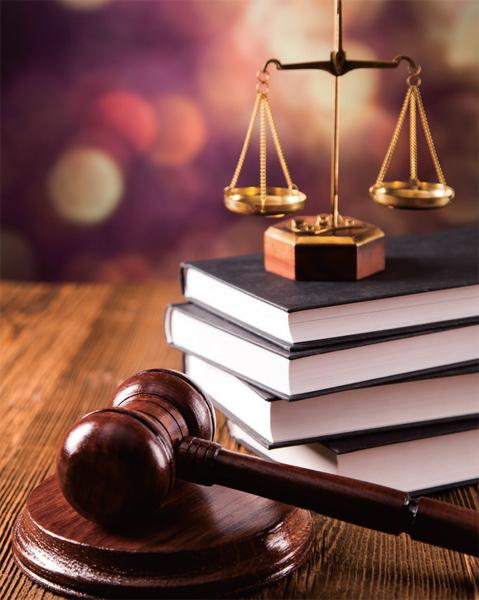
(二)中華法系中的倫理道德元素,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西方價值觀念不斷滲透,追求西方個人權利至上、輕視集體和國家權力的思潮風起云涌,加之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缺位,使該思潮大量充斥并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隨著法律在社會生活運用中矛盾頻出,外來法律與本國生活實際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適應性,所以我們在借鑒吸收域外法律文化時,也需要以正確的態度去認識和發揚中華法系寶庫中那些超越時空并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律文明要素,不斷發掘整理其中的優秀資源與有益成果,用以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法律困境問題。中國傳統法律秩序的固有基礎是“親親尊尊”、尊卑倫常,這根植于別具風格的中國特色的社會、歷史、文化土壤,是無法從西方直接移植的。因此,完全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是難以在中國存活下去的,我們應該承認并重視家族的地位和力量,讓傳統法律文化中倫理道德的有益元素繼續發揮作用,使家庭與家族成為社會力量的一種有力支撐。
當然,重塑不是盲目的復古,而是在借鑒之上的創新。傳統家族倫理中對人性的禁錮與自由的限制應堅決摒棄,而其中重孝道、講禮儀的倫常觀念以及調處息訴等理念對于調整當下的現實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諧仍具有進步意義,依然可以為今天立法所借鑒。
(三)中華法系“禮法合治”的特色內涵,有益于法治中國建設
目前,在建設法治中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進程中,思想道德體系建設嚴重滯后,法律規范的約束性很難較大程度地觸及道德倫理,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亦層出不窮,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法治進步與社會和諧。禮法結合是促進社會文化協調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倫理的法制化。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與每個公民休戚相關。公民作為權利義務主體和構成社會生活的基礎,不僅是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的受益者,更應該成為積極的參與者與有力的推動者。在新形勢下,公民一方面要有效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另一方面,還需要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從一點一滴做起改善道德滑坡和公德缺乏的現狀,讓諸多觸碰道德底線、突破法律底線的奇談怪相無處生根。今天提倡的 “禮法合治”,正是基于法治社會的構建、法治信仰的樹立與法治理念的落實,不在于簡單地用新的立法取代固有的法律體系,而是要引導公民形成以維護合法權利與公平正義、維護法律至上與法治至上的倫理道德,讓每個公民都能享有充分的權利與自由,把對法治的信念融入到自身血液中去、融入到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
因此,結合我國歷史文化傳統、道德倫理及環境因素等國情,借鑒西方法律模式,建立現代的法律體系,將重要的思想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并輔以相應的規章制度、獎懲機制,使之更具有權威性和約束性,成為法治中國建設的當務之急。惟有如此,才能逐步建立起一個精神文明發達的和諧社會與法治中國。
參考文獻
[1]張晉藩著.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2]瞿同祖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2頁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公安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