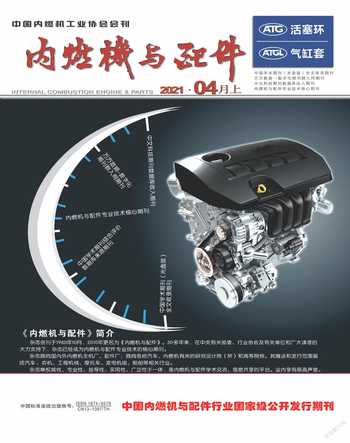數(shù)控機(jī)床十字滑臺(tái)實(shí)訓(xùn)設(shè)備的研究與改進(jìn)
汪相衡 楊亞琴




摘要:數(shù)控機(jī)床機(jī)械部件裝調(diào)課是數(shù)控設(shè)備應(yīng)用與維護(hù)專業(yè)的一門重要的專業(yè)核心課程。本文依據(jù)高技能人才培養(yǎng)目標(biāo),為解決實(shí)訓(xùn)設(shè)備不足的問題,滿足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結(jié)合企業(yè)實(shí)際需求,開發(fā)出一套實(shí)訓(xùn)用數(shù)控機(jī)床十字滑臺(tái)模擬設(shè)備,解決了教學(xué)和實(shí)踐過程中的裝配難題。
關(guān)鍵詞:機(jī)床裝調(diào);培養(yǎng)目標(biāo);整機(jī)裝配;裝配精度
中圖分類號(hào):TP273.2 ? ? ? ? ? ? ? ? ? ? ? ?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 ? ? ? ? ? ? ? ? ? ? ? ?文章編號(hào):1674-957X(2021)07-0090-02
0 ?引言
機(jī)械制造業(yè)是一個(gè)國(guó)家的基礎(chǔ)行業(yè),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支柱產(chǎn)業(yè)。目前我國(guó)機(jī)械制造業(yè)正處于發(fā)展關(guān)鍵期。當(dāng)前的機(jī)械制造雖然規(guī)模龐大,但是自主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少,制造產(chǎn)品多為仿制,高精尖裝備制造能力差。高端產(chǎn)品制造需要高精度的機(jī)床加工設(shè)備,而高精度機(jī)床設(shè)備需要制造者擁有較高的技術(shù)水平。滑臺(tái)在機(jī)床加工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依靠直線導(dǎo)軌實(shí)現(xiàn)水平方向的移動(dòng)。導(dǎo)軌的裝配精度直接影響到滑臺(tái)的運(yùn)動(dòng)精度,也影響了工件的加工精度,因此在機(jī)床裝調(diào)過程中,導(dǎo)軌與滑臺(tái)的各項(xiàng)精度調(diào)節(jié)需要操作人員擁有較高的技術(shù)水平。作為數(shù)維專業(yè)的學(xué)生,需要熟練掌握各項(xiàng)機(jī)床裝調(diào)技能,因此需要大量實(shí)踐練習(xí)來提升技術(shù)水平,但由于真實(shí)機(jī)床導(dǎo)軌與滑臺(tái)組合體型較大,且價(jià)格昂貴,如果在訓(xùn)練中操作不當(dāng)導(dǎo)致設(shè)備損壞,造成的損失較過大,不適合直接當(dāng)做實(shí)訓(xùn)設(shè)備。為解決實(shí)訓(xùn)設(shè)備不足的問題,滿足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結(jié)合企業(yè)實(shí)際需求,現(xiàn)需要開發(fā)出一套實(shí)訓(xùn)用數(shù)控機(jī)床十字滑臺(tái)模擬設(shè)備。
1 ?實(shí)訓(xùn)目的
《數(shù)控機(jī)床機(jī)械部件的裝調(diào)》是數(shù)控設(shè)備應(yīng)用與維護(hù)專業(yè)一門專業(yè)核心課程。這門課將為畢業(yè)生從事機(jī)床機(jī)械裝調(diào)工作打下一個(gè)堅(jiān)實(shí)的實(shí)踐和理論基礎(chǔ),也是后續(xù)從事數(shù)控機(jī)床維修和調(diào)試等技術(shù)工作所須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要學(xué)習(xí)環(huán)節(jié)。課程的主要功能是在了解數(shù)控機(jī)床結(jié)構(gòu)和工作原理的基礎(chǔ)上,以實(shí)際數(shù)控機(jī)床機(jī)械部件裝配為目標(biāo),掌握數(shù)控車床、加工中心的機(jī)械部件的裝配技術(shù)技術(shù),同時(shí)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質(zhì)量意識(shí)、團(tuán)隊(duì)合作意識(shí)和工作敬業(yè)精神。
我國(guó)正在進(jìn)行從制造大國(guó)變制造強(qiáng)國(guó)的轉(zhuǎn)變,想要實(shí)現(xiàn)這一轉(zhuǎn)變,需要大量擁有掌握高端制造技術(shù)的技能人才。大量高端機(jī)床被投入到了生產(chǎn)加工中。這些設(shè)備在日常需要進(jìn)行維護(hù)升級(jí)和維修,這就需要我們數(shù)維專業(yè)依據(jù)企業(yè)的實(shí)際用人需要,培養(yǎng)出合格的數(shù)維技能人才。
2 ?現(xiàn)有設(shè)備情況
近年來隨著數(shù)控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學(xué)校越來越注重培養(yǎng)生產(chǎn)、技術(shù)服務(wù)等崗位需求的實(shí)用型、技能型專門人才,進(jìn)一步提高學(xué)生的動(dòng)手能力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全面學(xué)習(xí)掌握數(shù)控系統(tǒng)的控制原理、數(shù)控編程、電氣設(shè)計(jì)方法及安裝調(diào)試與維修。但是,大多數(shù)高校面臨缺乏此類的數(shù)控培訓(xùn)設(shè)備。
在機(jī)床滑臺(tái)裝調(diào)環(huán)節(jié),通過使用實(shí)訓(xùn)用十字滑臺(tái)實(shí)驗(yàn)設(shè)備,結(jié)合真實(shí)機(jī)床結(jié)構(gòu)圖,使學(xué)生了解機(jī)床滑臺(tái)工作原理及裝調(diào)過程,并進(jìn)行動(dòng)手實(shí)踐。通過拆裝和精度調(diào)節(jié)加深學(xué)習(xí)印象,同時(shí)提升學(xué)生動(dòng)手能力。
目前的十字滑臺(tái)實(shí)訓(xùn)設(shè)備主要是讓學(xué)生了解了安裝過程,對(duì)于一些精度調(diào)節(jié)過程沒有設(shè)計(jì)實(shí)訓(xùn)環(huán)節(jié),因此學(xué)生對(duì)于裝調(diào)學(xué)習(xí)只有“裝”而沒有“調(diào)”。例如有些設(shè)備直接設(shè)計(jì)好了導(dǎo)軌槽,只需將導(dǎo)軌放入,再將螺栓擰緊就算完成了,對(duì)導(dǎo)軌直線度、水平度等精度完全沒有涉及,對(duì)學(xué)生起不到一點(diǎn)實(shí)訓(xùn)效果。
有些實(shí)訓(xùn)設(shè)備雖設(shè)計(jì)了精度調(diào)節(jié)環(huán)節(jié),但是在設(shè)計(jì)方面仍有欠缺,例如部分設(shè)備在直線導(dǎo)軌裝調(diào)環(huán)節(jié),導(dǎo)軌直接放在底板上,沒有任何定位裝置,完全依靠固定導(dǎo)軌的螺栓調(diào)節(jié),如圖1所示。這樣設(shè)計(jì)造成導(dǎo)軌左右直線度與上下直線度不能同時(shí)兼顧調(diào)節(jié),調(diào)節(jié)一項(xiàng)精度時(shí)必定對(duì)另一項(xiàng)精度造成破壞。這樣的設(shè)備不能達(dá)到訓(xùn)練的目的,反而浪費(fèi)學(xué)生大量時(shí)間。
目前存在的實(shí)訓(xùn)設(shè)備細(xì)節(jié)處與真實(shí)機(jī)床仍存在差別。例如在直線導(dǎo)軌兩頭未設(shè)置限位裝置如圖2所示,學(xué)生在調(diào)節(jié)導(dǎo)軌精度時(shí),容易將滑塊移出軌道,滑塊內(nèi)部的滾珠需要特殊機(jī)器安裝,如發(fā)生滾珠掉落會(huì)導(dǎo)致滑塊直接報(bào)廢,影響下次使用。
在滾珠絲桿直線度調(diào)節(jié)測(cè)試時(shí),沒有合適的輔助工具,無法在不改變百分表與絲桿螺紋相對(duì)位置的情況下,測(cè)得滾珠絲桿與直線導(dǎo)軌的平行度;需將百分表表頭與絲桿螺紋接觸后直接來回拖動(dòng)百分表,造成百分表側(cè)頭脫落,影響后續(xù)百分表的正常使用。市面上的實(shí)訓(xùn)設(shè)備有些設(shè)計(jì)與真實(shí)機(jī)床不符,反而會(huì)誤導(dǎo)學(xué)生。例如在地腳調(diào)平環(huán)節(jié)上,未仿照真實(shí)機(jī)床的情況進(jìn)行設(shè)計(jì),僅僅用螺栓代替地腳,并且螺栓直接與平臺(tái)接觸,在水平調(diào)節(jié)時(shí)工具不易使用,給操作者帶來不便。
目前這些現(xiàn)有數(shù)控設(shè)備裝調(diào)實(shí)驗(yàn)臺(tái)配備的十字工作臺(tái)存在設(shè)計(jì)不當(dāng)或設(shè)計(jì)錯(cuò)誤,不僅不能對(duì)提高學(xué)生技能水平,而且會(huì)對(duì)學(xué)生留下錯(cuò)誤印象,為日后工作生活留下隱患。
3 ?新型實(shí)訓(xùn)設(shè)備的開發(fā)與設(shè)計(jì)
為了適應(yīng)市場(chǎng)需求,提升國(guó)家數(shù)控設(shè)備維護(hù)專業(yè)整體技術(shù)水平,需要對(duì)數(shù)維專業(yè)學(xué)生進(jìn)行精確培養(yǎng),通過數(shù)控機(jī)床裝調(diào)實(shí)訓(xùn),使學(xué)生對(duì)機(jī)床有所了解認(rèn)識(shí),并通過實(shí)踐加強(qiáng)記憶。這將為學(xué)生畢業(yè)后從事機(jī)床機(jī)械裝調(diào)工作打下一個(gè)堅(jiān)實(shí)的實(shí)踐和理論基礎(chǔ),也是后續(xù)從事數(shù)控機(jī)床維修和調(diào)試等技術(shù)工作所須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要學(xué)習(xí)環(huán)節(jié)。
機(jī)床在加工中,主要依靠工件與刀具的相對(duì)移動(dòng),通過切削去除毛坯上多余的材料,從而獲得符合需要的零件。刀具或工件的運(yùn)動(dòng)由滑臺(tái)帶動(dòng)實(shí)現(xiàn),因此滑臺(tái)的運(yùn)動(dòng)精度直接影響到機(jī)床加工進(jìn)度,是機(jī)床性能的重要指標(biāo)之一。因此在裝調(diào)時(shí)需要安裝人員有較高的技術(shù)水平和豐富的經(jīng)驗(yàn),才能制造出符合設(shè)計(jì)的機(jī)床產(chǎn)品。
目前市面上現(xiàn)有實(shí)訓(xùn)設(shè)備大多存在一些設(shè)計(jì)缺陷,無法培養(yǎng)學(xué)生正確的裝配意識(shí),養(yǎng)成嚴(yán)謹(jǐn)認(rèn)真的工作態(tài)度。甚至有些會(huì)誤導(dǎo)學(xué)生。在此結(jié)合TRIZ理論基礎(chǔ),通過參考40種發(fā)明原理,開發(fā)一臺(tái)符合實(shí)訓(xùn)需求的十字滑臺(tái)實(shí)訓(xùn)設(shè)備。
3.1 直線導(dǎo)軌輔助定位
在現(xiàn)有設(shè)備中,直線導(dǎo)軌的定位精度普遍較差,甚至有些不存在定位,無法使學(xué)生在裝調(diào)過程中準(zhǔn)確掌握各項(xiàng)精度調(diào)節(jié)技能了解相關(guān)知識(shí)。在十字滑臺(tái)裝配過程中,導(dǎo)軌直線度與平行度尤為重要,但有的設(shè)備上無法調(diào)節(jié),有的無法做到各項(xiàng)精度兼顧調(diào)整直線度(上下)時(shí)會(huì)破壞直線度(左右)。在本設(shè)計(jì)中,通過底板臺(tái)階與側(cè)面定位螺栓的配合,為導(dǎo)軌直線度(左右)提供輔助定位,在直線度(左右)確定后,對(duì)直線導(dǎo)軌側(cè)的定位螺栓進(jìn)行預(yù)緊,再調(diào)節(jié)直線度(上下),避免在調(diào)整直線度(上下)時(shí)破壞先前調(diào)好的精度。如圖3為定位螺栓二維圖。
3.2 導(dǎo)軌末端限位裝置
現(xiàn)有設(shè)備中導(dǎo)軌末端缺少限位裝置,滑塊容易超出軌道造成滾珠掉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損失。在本設(shè)計(jì)中,通過在直線導(dǎo)軌兩端加裝限位裝置,防止滑塊超程,脫離軌道。為此設(shè)計(jì)了限位擋塊,緊貼直線導(dǎo)軌安裝在導(dǎo)軌兩頭,使用螺栓固定在底板臺(tái)階面,通過前方的擋片對(duì)直線導(dǎo)軌上的滑塊進(jìn)行阻攔。并通過有限元分析驗(yàn)證,將材料由鋁_6061更改為工程塑料,不僅降低了重量,同時(shí)還減小了受到撞擊時(shí)的形變量和最大應(yīng)力。
3.3 地腳水平調(diào)節(jié)裝置
現(xiàn)有設(shè)備中,底板采用螺栓直接支撐,通過旋轉(zhuǎn)螺栓控制底板上下調(diào)節(jié)水平。在調(diào)節(jié)過程中,由于螺栓頭部與工作臺(tái)直接接觸,使用工具調(diào)節(jié)時(shí)操作困難。在本設(shè)計(jì)中,在拖板下底面添加添加螺紋通孔,并設(shè)計(jì)了一款小型地腳底座,在底座上有螺紋孔。通過雙頭螺桿連接底板與底座,螺桿上端高出底板上頂面,并用螺母固定,螺桿下端與底座通過螺母將螺桿鎖緊,防止松動(dòng)。在雙頭螺桿中部銑出一段外六角,方便與扳手配合,便于精度調(diào)節(jié),圖4為雙頭螺桿二維圖。
4 ?結(jié)論
本文觀察了現(xiàn)有十字滑臺(tái)實(shí)訓(xùn)設(shè)備的設(shè)計(jì)結(jié)構(gòu)和使用方法,通過與真實(shí)機(jī)床的比較并結(jié)合學(xué)生實(shí)操時(shí)出現(xiàn)的情況,總結(jié)出了當(dāng)前實(shí)訓(xùn)設(shè)備存在的問題與不當(dāng)之處。結(jié)合超級(jí)發(fā)明術(shù)設(shè)計(jì)出多種實(shí)訓(xùn)用十字滑臺(tái)組合,并根據(jù)試錯(cuò)法挑選出最合適的設(shè)計(jì)進(jìn)行加工。最終設(shè)計(jì)的特色在于:①提升直線導(dǎo)軌安裝精度;②限制滑塊移動(dòng)防止超程;③地腳調(diào)平裝置符合實(shí)際。通過這些對(duì)原有設(shè)備問題的改進(jìn)創(chuàng)新,使數(shù)控設(shè)備機(jī)械部件裝調(diào)實(shí)訓(xùn)更加貼合實(shí)際,為學(xué)生培養(yǎng)扎實(shí)專業(yè)技能,養(yǎng)成良好工作習(xí)慣做好堅(jiān)實(shí)鋪墊。
參考文獻(xiàn):
[1]劉文濤.機(jī)床滾動(dòng)直線導(dǎo)軌副裝配方法和裝配誤差評(píng)定[J].機(jī)械工程師,2018,8:74-76.
[2]宋文學(xué).構(gòu)建高職數(shù)控技術(shù)應(yīng)用專業(yè)課程體系的改革與實(shí)踐[J].西安航空技術(shù)高等專科學(xué)校學(xué)報(bào),2005(5):l8-20.
[3]楊峻峰.深化課程教學(xué)改革,強(qiáng)化應(yīng)用能力培養(yǎng)[J].濟(jì)南職業(y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2):46-48.
[4]熊志卿.機(jī)械制造專業(yè)應(yīng)用型人才培養(yǎng)方案的改革與實(shí)踐[J].南京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9):49-53.
[5]張輝,于長(zhǎng)亮,王仁徹.機(jī)床支撐地腳結(jié)合部參數(shù)辨識(shí)方法[J].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14,54(6):815-821.
[6]田紅亮,余媛,張屹.機(jī)床支撐地腳結(jié)合部法向粗糙接觸建模[J].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工學(xué)版,2015,49(11):2111-2118.
- 內(nèi)燃機(jī)與配件的其它文章
- “互聯(lián)網(wǎng)+”在《發(fā)動(dòng)機(jī)構(gòu)造》課程中的應(yīng)用
- 新工科背景下《機(jī)械制造裝備設(shè)計(jì)》課程教學(xué)改革策略
- 汽車構(gòu)造課程在線教學(xué)培養(yǎng)模式的研究與實(shí)踐
- 探究賽教圓柱齒輪嚙合質(zhì)量的檢驗(yàn)與調(diào)整教學(xué)設(shè)計(jì)
- 關(guān)于提高技師院校汽車維修專業(yè)教學(xué)質(zhì)量的研究
- 基于一流特色專業(yè)群的《機(jī)械零部件測(cè)繪》課程實(shí)訓(xùn)零件設(shè)計(jì)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