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反思性研究的力作
張永清 李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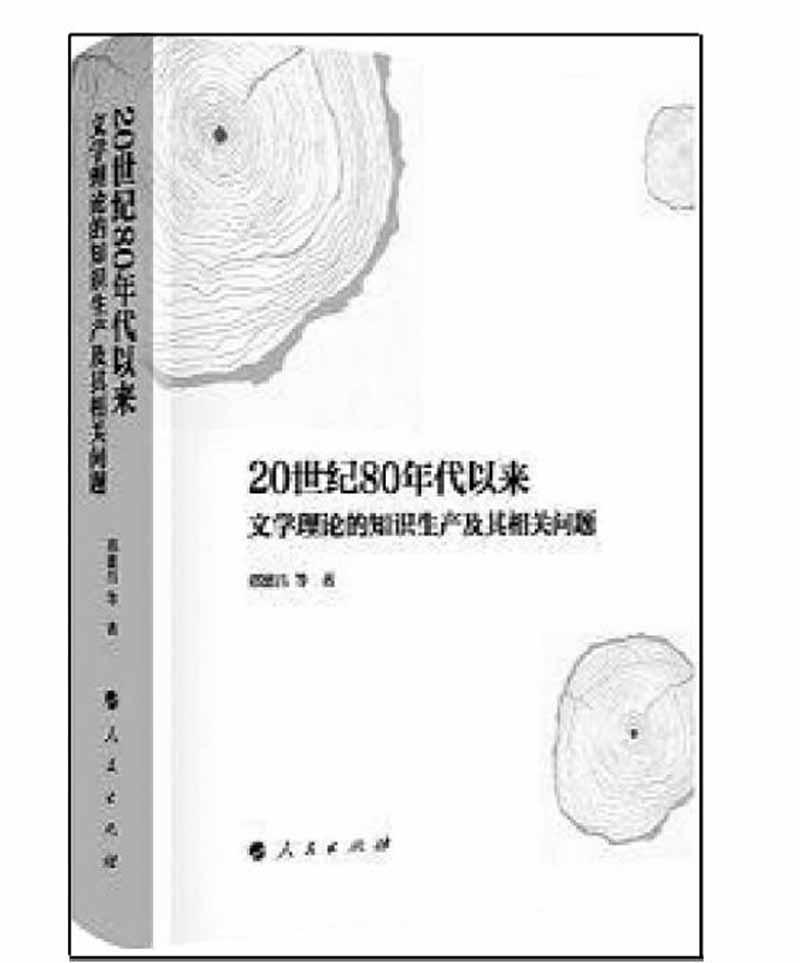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邢建昌等著,人民出版社,2019
從“知識”“知識生產”的視角反思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狀況,無疑是邢建昌等所著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更為接近文學理論本質的獨特的研究方法或理論視域。文學理論是一門知識嗎?是一門什么樣的知識?當今時代應該用怎樣的方法去介入文學理論知識狀況的思考?這不僅是普通學習者追問的問題,更是作為文學理論的書寫者與傳播者要不斷思索解決的問題。全書不僅圍繞文學理論和文學之間關系展開論述,更是在知識學層面探討文學理論的知識演進及內在規律,是將文學理論提升到學科化和專業化的高度而展開的富于學理和創新的理論建構。
在傳統知識學理論看來,知識的發現與接受過程主要依賴創造性和想象力,這些能力的自由發揮才是掌握知識的幸運之神。然而,僅有情感、想象、理解這些心理活動的參與,未經反思和抽象,獲得的只能是最淺表的人類經驗,還不能上升至知識的高度。知識社會學認為,知識并不能僅僅理解為對現實的摹寫,不是通過建立與對象的認知關系就可以完成的生產。它應是一個系統的體系,并且還受置身其中的人的社會位置的影響。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強調文化科學存在著對于經驗實在的思考整理,而這種思考整理本身是客觀的、科學的,是有效的“知識”生產方式。韋伯強調緊扣社會學對象的獨特性來“科學”而“客觀地”闡釋其中的規律。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正是從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福柯的人文知識考古學,以及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等來審視文學理論知識問題的。人文學科的“知識”,不同于自然科學知識,不是對感性材料被動的反映加工,有別于一般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一種“特殊的知識”。全書從“知識生產”這一視角考察文學理論知識狀況,使論域從一般認識論轉向價值論和生成論,從形而上學轉向知識社會學。只有在掌握文學基本理論問題基礎上,緊密結合社會、歷史、文化的語境,進行事實與價值、價值中立與價值判斷、知識與意識形態等問題的科學認知,才能深刻地揭示文學理論的存在機制和表達機制的復雜性和多維性。這樣的知識構架既有相對穩定的學理基礎,不斷滋養著審美與文學批評的實踐活動,又充盈著豐富的人文取向,引領人進入深邃廣袤的思想境地,去揭示可能性生活的意趣。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經歷了從“形象思維”的討論到審美反映文論的建立,從“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提出到文化研究的倡導,從“本質主義”到“反本質主義”的論爭,乃至于關于形式、語言、敘述、結構等的探討。文學理論40年的歷程,每一次論爭都帶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從審美現代性對啟蒙現代性的反思,到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整體反思,文學理論已經無可阻擋地進入一個多樣、混雜的狀態,文學理論領域的知識變革迫在眉睫。面對后理論時代的知識生產的多重性危機和焦慮,只有科學地思考和探索知識生產的合理路徑及其選擇,才能找到文學理論發展的基本方向。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不應只是一個學科自足性的概念,它應當面向社會文化公共領域,在知識范式上與跨界性和跨學科性相適應,突出反思性與思想生產的深度綜合,從而提供一種理論闡釋的綜合性框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高度評價《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的積極探索,從中我們欣喜地看到這種從整體上推動文學理論學科建設的努力。從知識學層面探討文學理論的知識演進及其內在規律,它所彰顯的價值就在于跨學科的知識建構力量。這是一種既與學科的知識譜系密切相關,又包含和融匯著其他學科的思想觀念、理論與方法的多元知識系統,從局部的知識生產走向跨學科的乃至跨國際的知識生產路徑。全書對“知識”“知識生產”進行概念內涵厘定,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發展的每一階段重要命題形成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語境進行揭示,不僅有對傳統命題的再認識,更有對知識化社會中最活躍的構成——媒介系統與媒介化活動的嶄新的思考,體現了在“知識共同體”平臺上確立自身言說優勢的胸懷、眼光和執著。其中的觀念預設和價值判定,既是對20世紀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的反思,也是對當下人文學科領域內觀念的“多元轉向”和“價值轉向”的自覺呼應。
真理、權力與知識生產三者之間的關系是當代法國哲學大師福柯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福柯特別強調知識生產的局部性,提醒書寫“被壓抑的知識”。這一思想體現在本書的研究中,就是呼喚敞開文學以及理論的本來面目,拓展文學理論的邊界,使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朝著更加差異化和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從這部著作中,我們深深感受到了作者在敞開文學理論知識過程中的思索與擔當。當我們再度進入文學理論反思研究之時,首先應該尊重的是文學理論的知識特殊性,重新激發審視文學理論的知識論域的信心與信念。如此,方能在主觀上不斷突破思維的固化,實現理論研究的創新,從而開拓出文學理論知識狀況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