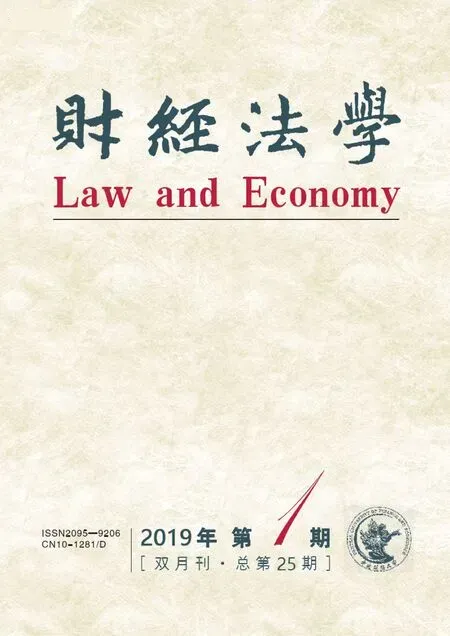定義論及其在法典編纂中的應用
雷 磊
內容提要:定義論是(語言)符號論的一部分,是確定某個語言符號之意義或者其句法結構的理論。它與概念論在諸多方面皆不相同。古典定義論提出了屬加種差的“標準公式”,現代定義論則在改進其缺陷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更精致和具有區分度的定義理論。定義論包括定義類型理論與定義規則理論兩部分。定義類型理論的基礎在于區分名義定義與實際定義,立法活動涉及的主要是名義定義,它可以分為兩大類五小類。定義規則理論包括基本原則與基本規則,立法定義至少要遵守兩大基本原則、八項形式規則和三項實質規則。不同類型的定義和規則都可以在法典編纂活動中得到檢驗。
定義無疑在法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法律推理中,只有對前提中出現的表述進行精確定義才能推導出可驗證的結論。對于某些重要的基礎性概念,立法者甚至會在法律條款中直接陳述其意義。因此,無論是對于研究法學基本概念、基本結構及其一般基礎的一般法學說(Allgemeine Rechtslehre)而言,[注]〔1〕參見雷磊:《法理論及其對于部門法學的意義》,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3期。還是對于以闡明法律規范及其所包含之表述的含義為主要任務的法律解釋理論來說,一種恰當的定義論(Definitionslehre)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旨在闡明定義論的基本內涵、規則及其在法律領域的運用。但這里首先要做一點限定:從主體的角度而言,法律中的定義可以由立法者給出,也可以由法官或法學家給出,由此形成立法定義、司法定義與法學定義(教義學定義)。本文僅關注定義論在立法領域,尤其是在法典編纂中的應用,而不涉及司法裁判與教義學說,盡管立法定義與后兩種定義之間無疑也存在聯系。本文將首先闡明什么是定義論(第一部分),接著分述定義類型理論、定義規則理論及其在法典編纂中的應用(第二、三部分),最后予以小結(第四部分)。
一、什么是定義論?
要弄清楚定義論的確切所指,就必須厘清三個問題:其一,定義無疑屬于語言的層面,而語言是符號的一種,所以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定義論與符號論的關系。其二,在法學研究領域中,我們經常使用法律“概念”而非這里所講的法律“定義”這一表述,那么定義論與概念論的關系為何?其三,定義論的范式在學說史上經歷過變遷,可以區分出古典的定義論與現代的定義論,兩者各自的內容和區別何在?這三個問題分別涉及定義論的學科定位、定義論與相鄰學科的關系以及定義論的內部構造。
(一)定義論與符號論
符號論(Semiotik)是一般性的符號理論。一方面,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各式各樣的符號,為的是用它們來指涉符號之外的事物。這些符號包括文字、圖像、聲音,也包括語言。因此,符號具有對象關聯性,即符號與現實中被符號所指的對象之間存在著關聯性。在符號學的術語中,這種關聯性被稱作“指稱”(reference),被指稱之對象被稱作“所指稱者”(referent)。正如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言,當我們去研究某個符號的對象關聯性時,我們就是從這一角度去觀察符號,即它代表著某個對象。[注]Vgl.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4, S.211.另一方面,借助于符號來理解世界時,符號又不能以任意或偶然的方式,而要依據特定的規則來使用。這種規則就是符號的使用規則。所謂使用規則,指的是某個對象必然具有的屬性,借此與使用規則相關的符號被正確運用于這一對象。[注]Vgl.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Wissenschaftstheorie für Juristen, Frankfurt a.M.: Alfred Metzner Verlag, 1980, S.209.因此,符號也具有使用規則相關性。也可以說,符號具有意義(meaning),這種意義就是由使用規則來確定的(符號所指稱之對象具有符合意義要素的屬性)。在這一意義上,索緒爾(Saussure)分別稱符號和其意義所指稱的對象為“能指”(signifiant)與“所指”(signifié)。由此,符號一方面與現實中的對象,另一方面又與意義(使用規則)產生了關聯。我們可以三角圖示的形式來展現出三者的關系,是為“符號學三角”(semiotische Dreieck),參見圖1:

圖1 符號學三角
在這個三角圖中:從符號到對象的箭頭是單向的,它代表符號指向或代表著對象,而不是相反。符號與意義之間的箭頭是雙向的,這代表著兩者有等值關系,箭頭兩邊是可以交換的。當符號的使用不成問題時,意義不需要被言明,這種可交換性也不起作用。但當有人質疑符號的使用方式且人們指明其意義時,就同樣可以用意義來指稱對象。在這一情形中就形成了意義對于對象的指稱關系(所以用虛線箭頭來表示)。
由于語言符號是符號的一種,所以這一三角也適用于語言符號理論,只是要把這里的“符號”替換為“語言符號”或者說“表述”(Ausdruck)而已[由此稱為“語義三角”(semantische Dreieck)[注]Vgl.Rolf Wank, Die juristische Begriffsbildung, München: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85, S.10.]。當然,對(語言)符號之雙重關聯性的這種展示需要一系列的認識論前提。[注]對此參見Jürgen Trabant, Elemente der Semiotik, München: Beck, 1976, S.15-47.但囿于篇幅,這里不再展開,而是直接采納了通說。只是要說明的是,顧名思義,“語義三角”只涉及了語義學(Semantik),而沒有涉及語言符號理論的全部,因為后者還包括句法學(Syntatik)與語用學(Pragmatik)。句法學涉及語言符號系統中各符號間關系的構造規則,語用學涉及符號的使用及其與使用目標之間的關系,兩者分別涉及“符號—符號”和“符號—使用者”之間的關系。關于語義學的研究對象則存在指涉理論(theory of reference,符號—對象)和意義理論(theory of meaning,符號—意義)之間的爭議。[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222-223頁。本文支持的是同時包含這兩者的、可用上述語義三角來呈現的語義學理論。在此基礎上,如果我們將這里的語言符號理解為一般表述而非專名(只指稱一個特定對象,如太陽),那么就可以區分出這種表述的外延(Extension)與內涵(Intension)。外延是特定表述適用情形的集合,它由相關謂述所涉及的那些個體的集合組成,或者說由具有被這一謂述所指稱之屬性的個體組成。[注]Rudolf Carnap, Einführung in die symbolische Logik, 3.Aufl., Wien (u.a.): Springer, 1968, S.40f.人們可以將一般表述適用于大量的對象,由此就會在每個具體的適用情形中出現例如這種形式的陳述:公司A是一個法人(在《民法總則》第57條的意義上)。這里的“是一個法人”就是謂述(Pr?dikat),“是一個”表明了被指稱之個體(公司A)是一般表述(法人)的一種情形。理解某個對象所具有的現實品質(即“屬性”)并在語言構造的層面上指涉這些屬性,就形成了“特征”。[注]關于屬性與特征的不同及其關系,參見Günther Patzig, Sprache und Logik, 2.Aufl,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1, S.86f.對必然適用于某個對象的特征(從而將特定一般表述正確適用于對象)的列舉就是內涵。可見,一般表述的內涵與外延其實指的就是符號的意義與對象(的集合)。這對于法律表述而言有重要意義。只是要指明的是,正如后文所顯示的,定義論不僅涉及包含界定內涵和外延的語義學,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句法學。所以,定義論是(語言)符號論的一部分,是確定某個語言符號之意義或者其句法結構的理論。
另外要說明的是,以上所處理的符號只具有描述的性質。因為這些符號代表或指稱著現實中的對象或事實,它以獨立于語言符號之對象或事實的存在為前提。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法律領域),我們還會使用另一類符號,即規定性的符號。規定性符號的作用在于作出某種規定或指示,它并不涉及和指涉任何既存的對象或事實。不如說它們規定了,要去建立某種(尚未)存在的狀態。這種狀態是根據符號的使用規則來建立的,因而不同于描述性符號的使用規則,規定性符號的使用規則指定的是有待實施之行為應當具有的屬性,而非對既有對象或事實之事實屬性的描摹。[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222-223頁。當然,如果作進一步考察,規定性符號之意義可以區分出兩種要素,一種是描述性的,一種是指令性的。例如,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6條規定,紅燈表示禁止通行。在此,“(亮)紅燈”這一規定性符號所包含的兩個要素就可以被解析為:(1)x是一項行為,它可以被描述為在停止線前停住(不通行);(2)去做x。當然這是一種為更清晰地呈現規定性符號被使用的不同方面而作的人為劃分。規定性符號的特點在于它將這兩種要素聯結在了一起。所以,如果綜合考慮到語言符號包括描述性與規定性符號這兩類的話,那么可以說定義論無疑更偏重于符號的意義或使用規則的確定。
(二)定義論與概念論
定義(Definition)有時與概念(Begriff)被混同使用,因而定義論常常被混同于概念論。但兩者是不同的,主要的區別在于:其一,定義屬于語言的層面,而概念屬于觀念的層面。定義用來闡明某個語言符號的內涵、外延或句法結構,屬于語言層面的活動;而概念是對象的內在或外在屬性在個人的精神中的呈現,屬于思維層面的活動。語言的主要功能在于交流,而思維的主要功能在于理解世界,構造精神呈現之復雜秩序。[注]關于兩個層面的區分可參見雷磊:《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嗎》,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思維是可以獨立于語言而存在的,所以概念作為一種觀念可以在不借助于語言表達的前提下存在。
其二,定義的范圍要超出確定概念的內容之外。雖然觀念可以脫離語言存在,但為了與他人交流觀念,概念很多時候需要用語言表達。此時就涉及了對概念內容的確定,即定義。[注]Vgl.Egon Schneider, Logik für Juristen, München: Verlag Franz Vahlen, 2006, S.45.然而,雖然對概念內容的確定屬于定義,但定義不限于確定概念的內容。前已敘及,定義論既包括確定語言符號的內涵和外延(語義學定義),還可能包括確證它的句法構造(句法學定義)。所以,(1)語義學定義不限于確定概念的內容,也包括確定概念的對象。概念是一種觀念或意義,而語言符號是對概念(內容)的表達形式。如果我們以“意義”(概念)為中心來看待語義三角的話,那么就可以獲得新的認識:語言符號的內涵(意義)其實就是概念,語言符號其實就是概念的表達形式,而語言符號的外延其實就是概念的對象范圍。這樣一來就可以看到,概念論關注的只是語言符號的意義本身,而定義論不僅要將語言符號與其意義(概念內容)聯系起來,也要將語言符號與其對象(概念對象)聯系起來。(2)句法學定義與概念無關,卻是定義論的一部分,也可能在法律領域有應用的余地。
其三,定義論屬于語言符號理論,而概念論位于邏輯學與語言哲學之間。定義論屬于符號論和語言符號論的一個分支,而概念論的定位則更為復雜。一方面,它是思維論(Denklehre)的組成部分,因此要服從于邏輯規則。另一方面,它又有屬于語言理論的部分,由于今日之語言理論的擴張,無法為邏輯學所完全容納。所以,概念論由于其同時與邏輯學和語言哲學存在緊密關聯而在這兩門學科之間持中間性立場。[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244頁。
最后,定義論與概念論研究的重點并不一致。概念論主要研究概念的性質、概念間的關系以及概念的類型。[注]a.a.O., S.277ff.在法學領域,尤其關注不同類型之法律概念的研究,如描述性概念、評價性概念與論斷性概念,描述性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與規范性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分類概念與類型概念等等。[注]參見舒國瀅、王夏昊、雷磊:《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2-99頁。與此不同,定義論關注的是確定語言符號之意義、對象或句法構造的方式有哪些,以及下定義時要遵守哪些科學的要求。前者屬于定義類型理論,后者屬于定義規則理論。并且,有的法律概念,如類型概念,是無法被下定義的。
當然,也不能否認概念論與定義論之間的關聯。僅就語義學定義而言,它與概念論之間就存在緊密的聯系。一方面,語義學定義指的就是針對某個給定之表達和某個給定之對象,從多種可能之意義中選出一個,即確定某個表達的內涵(概念內容)。[注]參見前引〔4〕,Rolf Wank書,第51頁。另一方面,只有當人們精確地理解和認識到了某對象時,才能下(語義學)定義。[注]參見前引〔11〕Egon Schneider書,第46頁。所以,在此意義上概念論又構成了定義論的前提。[注]但這只適用于實際定義,不適用于名義定義,對此請參見下文。盡管如此,下文只關注定義論,而不關注概念論。
(三)古典與現代的定義論
定義論從古希臘誕生起到現代同樣經歷了變遷。我們大體可以區分出古典定義論與現代定義論:前者以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為高峰,后者以帕斯卡(Pascal)為開端。現代定義論與古典定義論相比具有兩個特征:一是將定義視為規則;二是將定義作為命題來對待。[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03頁。另外,前者并不區分本體論與認識論,而后者將定義作為認識論層面的活動。
古典定義論認為定義由被定義項(Definiendum)與定義項(Definiens)組成,兩者可以用等值符號“=df”連接起來,等式的兩邊必須是可交換的。比如,“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公司”、“作者是作品的創造者”。古典定義論最著名的構造方式被表達為:定義就是最接近的屬加上種差(Definitio fiat per genus proximum et differentias specificas),簡述為:定義=屬+種差(以下簡稱“標準公式”)。這一公式有形式—技術的和內容的兩個面向。就形式—技術面向而言,它給出了下定義的方法,即上一級更高的屬概念加上特殊的種特征。例如,人被定義為“有理性的生物”,在這里,“生物”就是屬,而“有理性的”就是種差。再如,根據《民法總則》第57條,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這里,“組織”就是屬,而“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就是種差。就內容面向而言,在古代學者(如亞里士多德)看來,真正的定義必須是本質定義。也就是說,定義不僅說出了關于被定義項的某些東西,它還必須是本質性的東西,定義項所包含的種特征必須涉及對象的本質,且必須將對于確定此一本質而言所有必要的種特征都以正確的順序列舉出來。所以,按照“標準公式”構造出的是真正的定義。[注]參見前引〔4〕,Rolf Wank書,第51-52頁。事實上,這里已經涉及后文將提到的“名義定義”和“實際定義”的區分,只不過亞里士多德認為“真正的”定義就是實際定義,而不包括名義定義罷了。可見,對于古代思想家而言,認識論與本體論是一體的,思維的結構與存在者的結構沒有被區分開來。
現代定義論與古典定義論的上述兩個方面都進行了商榷。就形式面向而言,“標準公式”至少不足以應對這樣幾類定義/概念:(1)關系式或比較式定義。某些定義沒有列舉特征,而是與其他對象進行了比較。如“鋼比鐵硬”(“鋼是一種比鐵硬的金屬”)。嚴格地說,“比鐵硬”并非鋼的準確特征(種差),因為它并沒有提出區別于其他種(鐵)的客觀標準(根據這一定義,離開了鐵,我們就無法知曉鋼)。(2)功能概念。如物理學中,物質x的平均濃度被定義為:x的質量(克)除以x的體積(立方厘米)。這就沒法用“標準公式”來把握。(3)列舉式的定義。例如,我們可以將“東亞人”定義為“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或韓國人”。這其實是列舉出了語言符號之外延所包括的所有對象,所以也可被稱為“外延式的定義”或“目錄式的定義”。它在法典中被頻繁地使用。例如根據我國《刑法》第91條,刑法中的“公共財產”是指“國有財產、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和用于扶貧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產”。“標準公式”沒有考慮到這種定義。(4)部分定義。“標準公式”以等式的形式存在,即從兩個方向去讀都可以。但對于人文社會科學而言,通常不那么嚴格的定義,即部分定義就足夠使用了。[注]Vgl.Tadeusz Pawlowski, Begriffsbildung und Definition, Berlin (u.a.): de Gruyter, 1980, S.125ff.尤其是當立法者尚未透徹地明了哪些特征具有決定性時,陳述出哪些特征可以作為必要特征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就內容面向而言,“標準公式”本身必須與本體論假定割裂開來。在現代哲學的視野中,假定存在既有之“本質”和同樣既有之概念本身就是高度可疑的。當然,將定義與事物的本質切割開來并不意味著就一定要將定義與意義(及其根本特征)切割開來。定義時選擇任意的指稱顯然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定義項應使得有可能作出關于被定義項的盡可能多和盡可能重要的陳述。[注]Vgl.Franz v.Kutschera, Elementare Logik, Wien (u.a.): Springer, 1967, S.354ff.而哪些特征是重要的則取居于下定義的目的,在不同類型的定義那里有所不同。
在建立起演算化的邏輯系統后,現代定義論發展出了一套更精致和具有區分度的定義理論。簡言之,現代定義論將定義分為兩大組。第一組是原本的定義(或真正的定義),它包括:[注]參見〔德〕烏爾里希·克盧格:《法律邏輯》,雷磊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27頁。(1)廣義上的明確定義。這是對有待使用之符號的約定,采取的就是前述等式的形式“X=DfY”。它又可以被進一步區分為狹義上的明確定義和操作性定義。前者是指被定義項僅由新符號或新符號組合組成的定義,后者則指被定義項除了新符號或新符號組合外還包括其他要素。換言之,操作性定義是關于一個新符號的約定,這個新符號本身并沒有意義。(2)隱含定義。這種定義并未明確界定符號的意義或對象,但可以從它所處的體系、根據它與其他符號的邏輯關系來得出。(3)通過抽象化的定義,指的是可以通過不同對象之相等性關系抽象出抽象化之類后產生的定義。(4)歸類定義,它將對象歸于特定的符號或符號組合。第二組是非原本的定義(偽定義),它包括兩類:(1)實質說明,也就是對某個事物或對象的科學陳述。(2)符號說明,也即是對既有符號之使用規則的正確查明。當然,并非所有這些類型的定義都適用于法律和法典編纂的領域,對此下文將會闡明。
可見,現代定義論要比古典定義論更加豐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必須完全否定古典定義論。拋開其內容面向的混淆不提,“標準公式”迄今仍在法典中被使用,尤其被用于構造概念體系(明確上下位概念的關系、進行概念分類等)。所以,采用何種定義理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立法的合目的性考量和立法的技術。下文在闡述定義類型理論,尤其是定義規則理論時,將主要、但不限于借助于現代定義論的成果。
二、定義類型理論及其應用
(一)名義定義與實際定義
對于定義類型理論而言具有基礎性的分類是名義定義(Nominaldefinitionen)與實際定義(Realdefinitionen)。[注]名義定義/實際定義與原本的定義/非原本的定義之間并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系,至少符號說明(分析性定義)就屬于名義定義。名義定義涉及對某個符號的討論,而實際定義涉及對某個對象的陳述。為了便于說明兩者的區分,我們先來舉兩個例子:
例1 “漁業水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水域中魚、蝦、蟹、貝類的產卵場、索餌場、越冬場、洄游通道和魚、蝦、蟹、貝、藻類及其他水行動植物的養殖場所。[注]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實施細則》第2條第3款。(名義定義)
例2 魚是一種永久在水中生活的動物。(實際定義)
可以發現,名義定義與實際定義可以從三個角度進行區分:其一,通常情況下,名義定義屬于元語言層面的表達,而實際定義屬于對象語言層面。[注]關于法學中對象語言與元語言的一般區分參見Rolf Wank, Objektsprache und Metasprache, Geltungsprobleme bei Verfassungen und Rechtsgesch?ften, Rechtstheorie 13 (1982), S.465, 471ff.后者是在特定語言中所做的關于某個對象的陳述,而前者則是關于語言本身的陳述。[注]Vgl.Eike v.Savigny, Grundkurs im wissenschaftlichen Definieren, 5.Aufl.,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S.12ff.在上例中,例2是在中文中所做的關于魚這種對象的陳述,而例1則是關于“漁業水域”這一語言符號在特定語境(《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的陳述(這里所用的引號本身就表明了其語言符號的性質)。當然,從語言層面角度的區分有時是困難的,因為很多時候名義定義并沒有明確表明自身是在元語言的層面上表述。[注]Vgl.Paul Weingartner, Wissenschaftstheorie (2.1): Grundlagenprobleme der Logik und Mathematik,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76, S.238-240.當都屬于元語言層面時,也無法區分這兩種定義。因此還需要別的區分標準。
其二,名義定義的目的在于確證(Festsetzung),而實際定義的目的僅在于確認(Feststellung)。[注]關于確證與確認的區分,參見Hans-Joachim Koch und Helmut Rü?mann, Juristische Begründungslehre, S.15, 24.實際定義取向于對實際存在事物的確認,名義定義取向于對事物應當為何的確證。可以確認的是自然發生之事,即客觀事實。可以確證的是有待建立的某種語言用法(A在未來被命名為B)或其他行動(X是要去做的),它的目的在于對語言表述的簡化和標記。所以,實際定義的興趣在于認知(X是什么),而名義定義的興趣在于行動(X應當是什么?)。[注]參見前引〔4〕,Rolf Wank書,第60頁。實際定義的目的僅在于認識和描述實際存在的事物,所以例2的目的在于認識現實世界中的對象(魚)究竟是什么。相反,名義定義的目的在于做出規定,如例1的目的就在于建立某種語言用法,即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所使用的“漁業領域”一詞所稱呼或指代的內容。借用哲學家安斯康姆 (Anscombe) 的話來說,實際定義具有“語言對于世界的適應指向” ,而名義定義具有 “世界對于語言的適應指向” 。[注]這一區分參見G.E.M.Anscombe, Inten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56.
其三,名義定義只有合乎目的和不合乎目的之分,而實際定義有真假之別。人們可以依據實際定義是否與現實(的觀念)相符來檢驗它的真假。[注]這里可能會引起誤解,認為實際定義一定與某種特定的概念觀,即唯實論相聯系。但實際并非如此,定義屬于語言的層面,語言與現實對象之間的聯系是人自己建立起來的。因而在這兩者之間,以人的觀念為中介。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實際定義是對涉及現實對象之觀念的語言表達。如果實際定義能準確表達出這種觀念,它就是真的;如果不能,就是假的。前面說實際定義取向于對實際存在事物的確認,同樣以觀念為中介,只是無論如何,它都是為了去認識現實對象。例如,對例2中的定義表示懷疑的人可以通過指出龍蝦也是永久生活在水中的,來反駁將魚定義為“一種永久在水中生活的動物”的做法。由此,下定義者可能會因為這一“錯誤”而修正其定義(如“魚是一種永久在水中生活的、能游泳的動物”),這恰恰表明他的定義是有真值能力且能被反駁的。[注]這也表明,必須可以提供某種關于特定對象之適用方式的信息來檢驗實際定義。舉出龍蝦的例子之所以能反駁對魚的實際定義,是因為人們很確定龍蝦不是魚。這意味著,人們必須提供其他的方法來識別魚,否則可能就無法確信龍蝦究竟是否可算作是魚了。對于不熟悉“魚”這個詞的人,必須向其提供關于其適用方式的信息。判斷某個實際定義的真假以這種信息為前提。而對于名義定義而言,則不存在這種獨立于定義的信息。當然,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相反,名義定義只有是否與其目的相符的問題(合乎目的或不合乎目的),而沒有真假的問題。所以,它無法在事實領域被證偽,只可能是不合目的的。[注]Vgl.Urs Konrad Kinderh?user, Zur Definition qualitativer und komparativer Begriffe, Rechtstheorie 12 (1981), S.226.例如對于例1,我們就不能用“公海上的相關場所難道不屬于漁業場所”或漁民群體中既有的不同語言用法來反駁《漁業法實施細則》的這個規定,并由此證明《漁業法實施細則》中的定義是假的。再如,假設例2是個名義定義,也就是對相關語言用法的建議(例如在制定相關漁業法規時)。此時,反對者依然可以舉龍蝦的例子提出要對這一建議進行修正,但理由并不在于它是假的(與現實不符),而在于它是不合目的甚或違背立法意圖的,因為它會帶來不可接受的后果(例如將龍蝦也歸入“魚”的范疇從而過度損害了漁民的利益)。
對于法學討論而言,名義定義與實際定義的區分具有重要意義。在涉及對定義的判斷時,法律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辨別它究竟屬于何種定義。如果涉及的只是名義定義,那么去探討其真假就沒有意義,反對者只能主張它在文體上是不完善或不合目的的。相反,如果涉及的是實際定義,那么實質的爭論就是有意義的,人們可以去檢驗它的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由此,可以避免將名義定義當作具有真值能力的實際定義的風險,并引導討論的方向。[注]Vgl.Maximilian Herberger, Normstruktur und Normklarkeit, Frankfurt a.M.: Metzner, 1983, S.24f.回到本文的語境:在法典編纂的過程中,立法者給出的定義只可能是名義定義。[注]Vgl.Viktor Knapp, Einige Fragen der Legaldefinitionen, ARSP 66 (1980), S.511.因為立法是一種意志行為,旨在規范而非描述特定的對象或行為,所以立法者在下定義時或多或少是自由的。
(二)名義定義及其應用
名義定義可以被進一步區分為其他子類型。為了獲得直觀的印象,我們可以用圖2來表示:[注]在此參照了Joseph M.Bocheński, Die zeitgen?ssischen Denkmethoden, 10.Aufl., Tübingen (u.a.): Francke, 1993, S:91; 前引〔4〕,Rolf Wank書,第56頁。這里要說明三點:其一,通過抽象化的定義對于立法而言意義不大,因為它只適用法學研究,所以在這里不列;其二,語義定義包括了前述真正的定義中的歸類定義與非真正的定義中的符號說明,但它采用了分析性定義和綜合性定義的新分法,因為后者更能體現語義的不同形成方式;其三,涉及法律領域的定義論通常會包括狹義上的明確定義,或者說立法定義(Legaldefinitionen),它其實包括了本文所說的約定式定義與綜合性定義。

圖2 名義定義的子類型
句法定義指涉純粹的規則,它允許用某個(通常更簡短的)符號來取代另一個符號。[注]參見前引〔36〕,Joseph M.Bocheński書,第90頁。語義定義則是將某種意義歸于某個符號。換言之,句法定義并不意在確證某個表述或語言符號的內涵,而只是在特定體系中用它來替代其他一些更為冗長的表述;而語義定義則要去確證這種表述或語言符號的內涵,它之所以同樣屬于名義定義,是因為它不涉及事實本身,而只涉及語言用法。以下分述之。
1.約定式定義
這類定義具有明確的被定義項和定義項。如我國《民法總則》第96條的規定:“本節規定的機關法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合作經濟組織法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為特別法人。”再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六)項規定:“‘近親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從語義三角的圖示看,它們基本屬于外延式的定義。從功能上講,它們都涉及立法者的確證,也即是說位于被定義項一側的只是“特別法人”“近親屬”這樣的語詞,它們所作的只是關于如何使用這些相關語詞的約定。這種約定原則上可以任意地來做出,只是要受到合目的性視角的約束,比如考慮到相關教義學的發展史,它們的可理解性、通俗性,與實踐需求的相關性等。但這些都不是邏輯上的要求。[注]當然,從邏輯的角度看也存在某些條件,如下文要講到的定義論的規則有部分(只是部分)就涉及邏輯的要求。使用它們只是為了簡化文本,在各該法典中出現它們之處都可以用相關定義項來“消除”。同時,這也說明了為什么將這類定義歸為句法定義,而非語義定義。因為立法者只是要在特定體系或語境(《民法總則》第3章第4節或刑事訴訟活動中)約定某種表達的用法而已,而非去探求相關表達之固有的意義。
2.操作性定義
對于法典中的大多數表述而言,缺乏立法者對其用法的明確確證,但這些表述依然具有一種或多或少可以被確定的意義(至少對于法律人而言是如此)。在操作性定義中,相關表述不是通過單獨的定義項來定義,而需要通過一組條文來界定。例如,刑罰這個基本概念在我國刑法中從未得到過明確的定義,但立法者依然不斷地使用它。刑罰這一表述的意義需要通過它所出現于其中的語詞組合和條文集合(如我國《刑法》第13條,以及第32—89條)的意義來闡明。當然,操作性定義相對來說是不那么精確和精致的,也并非毫無疑問地被給予定義等式的形式。當立法者傾向于采取操作性定義時,實際上要么是默示地以某個不證自明和眾所周知的被預設的、狹義上的明確定義作為前提(如《民法總則》中的“自然人”),要么是因為立法者沒有把握給出一個合理的定義。在后一種情形中,操作性定義相當于在很大程度上留待學說和實踐去發展其內涵。盡管如此,在法典中使用這類表述不可能是任意的,既不能單純訴諸日常語言,也不能完全放任解釋者自身的理解,而是只能根據(表述被使用之)相關法條的語句或整體來做理解。當然,立法者在塑造操作性定義時,也應當顧及法律語言的特性和迄今為止的教義發展。[注]Vgl.Peter Noll, Gesetzgebungslehr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3, S.98ff.之所以仍將操作性定義歸為句法定義,是因為立法者仍是將它作為一種規定性符號,作為其調整世界之計劃的一部分來對待的。
3.隱含定義
嚴格說來,隱含定義與通過抽象化的定義一樣只有在公理化體系之中才有意義。因此,擁有相關學科或子學科的公理體系是使用這類定義的前提。由于迄今為止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實現公理化,所以這類定義尚未被法學充分研究。但是,今日之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已使得法律體系日益趨向于可精確操作和演算的公理體系,所以未來在法典編纂中使用隱含定義的可能性值得期待。事實上,早在90年前,卡爾納普(Carnap)就已借助關于人類親屬關系的公理化系統(也包括提出了一些法律概念)對隱含定義進行了說明。[注]Vgl.Rudolf Carnap, Abriss der Logistik, Wien: Springer, 1929, S.87-88.
4.分析性定義
分析性定義的目的在于陳述出某個表達對于特定受眾而言可從經驗上加以確認的內涵。故而,在構造這樣一類定義時,必須通過分析來查明“在一組人群中既有之符號的含義”。[注]前引〔36〕,Joseph M.Bocheński書,第90頁。分析性定義本身并無真假,只有與此相關的主張——分析性定義正確反映了既有的語言用法——有真假。例如,假設上述例2并非實際定義,而是一個反映既有語言用法的名義定義(“根據特定語言體系,魚是一種永久在水中生活的動物”),那么它的目的就在于反映這個語言體系或生活在這個語言體系中的人對于“魚”這個符號的理解,而不指涉魚這種客觀對象。以此為標準,一個普通人的相關主張有真假之分,端視它是否符合既有的語言用法。但是,由于立法是一種意志行為,盡管可能法典中所采納的分析性定義在內容上來自于所在語言體系的習慣性用法,但在性質上依然是一種確證。所以,假如在一部漁業法中立法者采納了這個關于“魚”的既有語言用法(而不是像立法定義那般指明“魚”在“本法中”所指代的內容),那它就是分析性定義。[注]立法者當然也可以不理會既有的語言用法而采用綜合性定義或者立法定義,但那是另一回事。
5.綜合性定義
綜合性定義是在不與既有語言用法相聯系的前提下賦予某個表達以意義,被用于立法者創造概念的場合。[注]斯塔姆勒稱規定立法定義的法條為“提出概念的法條”[Rudolf Stammler, Lehrbuch der Rechtsphilosophie, Berlin (u.a.): De Gruyter, 1928, S.362.]。也就是說,人們在進行這類定義時使用的是一種人為的、以綜合的方式產生的結論。它包括這樣幾種情形:其一,立法者直接規定專業術語的定義或對日常用語中固有的表述作了不同于日常語言用法的定義。前者如,《刑法》第21條將“緊急避險”定義為“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行為)”。這一術語只出現于法律領域,只能采取綜合性定義。后者如民事代理法律體系中的“本人”就被定義為“被代理人”,而與日常語言用法中的“我自己”有別。再如《刑法》中的“告訴”(如第98、257條第3款)指的是向法院控告起訴,也不同于日常語言用法。其二,法典編纂中更常見的綜合性定義是擬制定義。所謂擬制,指的是以反事實的方式將某個對象視為屬于某表述之外延,從而將這一表述的法律后果賦予該對象。例如那個關于女浴室規章的著名的例子,這個規章在“只許女士進入”這個條文之后規定:“浴室的男管理員也是本浴室規章意義上的女士。”[注]此例參見前引〔22〕,烏爾里希·克盧格書,第141頁。再如我國《民法總則》第18條第2款規定,十六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就是將“十六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擬制為“成年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賦予了“成年人”不同于一般理解的新意義。其三,立法者在對特定表述給出了明確定義之外,又將不屬于相關外延之對象以該表述論。如我國《刑法》第93條第1款本已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但接著又在第2款規定,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這是為了維系第1款中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定義本身之準確性的同時,賦予兩者同樣的法律后果。
當然,對名義定義的以上劃分只是理想類型的劃分。在具體的法典編纂過程中,立法者究竟使用了哪種定義,抑或是哪幾種定義類型的混合,可能會存在爭議。但無論如何,理論上的清晰劃分有助于認清立法者所使用之定義的性質,有助于改善立法質量。另外仍要強調的是,無論屬于何種類型,立法者的定義都是名義定義,因而只有合理與否的問題,而沒有真假的問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法典編纂中下定義的活動不受任何規則的制約。
三、定義規則理論及其應用
定義規則理論包括定義論的基本原則與一般規則。前者包括可消除性(Elimierbarkeit)和非創造性(Nicht-Kreativit?t),后者至少包括八項形式規則和三項實質規則。[注]這里要說明兩點:其一,說“至少”包括,是因為作者無法擔保下文的列舉是完整的或窮盡性的,有可能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會發展出更多的定義規則。其二,定義規則理論不應被理解為以這樣的價值立場為前提,即立法者應盡可能多地去下定義。相反,作者認為,法律中的許多表述或許留待司法實踐或法學去定義(司法定義或教義學定義)更為合適。這里的主張只是:如果立法者要下定義,那么就應當遵守這些定義規則,否則就是不理性的。其中,形式規則是對基本原則的具體展開。
(一)定義論的基本原則
1.可消除性
也被稱為“可替代性”(Ersetzbarkeit),它說的是,被定義項必須在每一情形中都可以被定義項所替代(從而被消除)。這是因為,定義項是被用來討論需要討論之被定義項的。而只有在定義項在每一個被定義項的位置上都能出現時,這種討論的目的才能達成。對此的例證是法律人在編纂法典時采用的“總則”技術,如果在法典的這一部分包含著定義的話,按照立法者的目的,在這部分得到定義的被定義項在隨后的部分(分則)中出現之初,應當都可以被所屬的定義項所取代。例如,我國《刑法》第97條將“首要分子”定義為“在犯罪集團或者聚眾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所以,當第103條第2款規定“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時,對于第97條被定義項指明的犯罪分子,就要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2.非創造性
如果人們給一組特定的命題附加上某個定義(它在其定義項中包含著這些命題中出現的概念),那么就可以推導出新的命題,也即是在引入定義前無法推導出的命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德國民法典》第182條第2款規定,對于法律行為的同意不需要特定的形式(命題1)。而我們知道,同意包括事前的同意與事后的同意。所以,事前的同意是一種同意(命題2)。而從該法第183條可以提煉出這樣一個定義:批準(Einwilligung)=df事前的同意(定義E)。所以,可以推導出,對法律行為的批準不需要特定的形式(命題4)。命題4是新的,因為它在離開定義E的情況下無法從命題1和命題2中推導出來。因為離開定義E在到那時為止的詞匯中還沒有“批準”這個詞。但是,命題4沒有揭示出任何關于現實的新信息。很清楚的是,如果我們用“事前的同意”去替代“批準”,那么就會獲得這個命題:對法律行為的事前同意不需要特定的形式(命題3)。而命題3是可以在不借助定義E的情況下從命題1和命題2中推導出來的。所以,將定義加入命題系統之中,盡管改變了既有詞匯的用法,但卻沒有改變在引入定義前命題所包含的關于現實的信息。因為立法者的定義是關于語言用法的建議,對此只能提出合目的性的考量(如簡化術語)來進行支持或反對。它不能被法典的適用者用來省卻或逃避個案中的論證負擔。[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21-327頁。
(二)定義論的一般規則及其應用
定義論的一般規則既包括形式規則,也包括實質規則。形式規則是下一切定義時都要遵循的普遍規則,而實質規則則與定義的領域密切相關。[注]之所以稱它們為一般規則,主要是因為:就形式規則而言,它們的適用不限于立法(法律)領域,其實是一般意義上的定義規則在立法領域的應用;就實質規則而言,它們也是針對一切立法定義的,而沒有區分不同的立法領域來做更細致的把握。根據相關著述,我們將定義論的形式規則概括為如下八項:
1.定義的清晰性
這又包括兩項規則:其一,定義本身要盡可能地清晰。這似乎是當然之理,因為在法律推理過程中,只有大前提所包含之概念被定義清晰才能得到準確的適用。但有疑問的乃是清晰性的標準是什么。強版本的標準認為,如果借助某個內涵可以確鑿無疑地將出現之對象歸屬于某個概念,那么它就是清晰的。提出這一標準的是現代邏輯創始人弗雷格(Frege)。在他看來:“對概念的定義必須是充分的,也即是說它必須能清楚地確定每一個對象,看它是否落入概念之下。不能有任何這樣的對象,依據定義它是否落入概念之下是有疑義的。”[注]Gottlob Frege, 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Paderborn: mentis, 2009, S.69.也就是說,定義必須這樣來下,當運用它時不會出現任何“中立候選項”。[注]關于中立候選項及其與肯定候選項、否定候選項的區分,參見前引〔28〕,Hans-Joachim Koch und Helmut Rü?mann書,第195頁。定義項必須精確,它不能是模糊的。但這種高要求很難完全達成,尤其是在法律領域,總是會出現未被預料到的新情形,通過下定義的方法永遠無法窮盡這類情形。尤其是當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時就更是如此了。例如,什么是“重大過錯”?什么是“誠實信用”?很多時候只有當出現了新的案件時才能結合個案來確定。立法者即便事前能給出一些標準,也必然是(過于)一般性的,而達不到上述清晰性標準。甚至可以說,之所以運用不確定概念就是為了保持一定的開放性以應對未來的情形。所以對于立法中的定義,我們似乎只能要求一種弱版本的清晰性標準,即定義應當在盡可能少的情形中被證明是模糊的。[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16-317頁。其二,定義必須要比有待確定之概念更清晰。或者說,定義項必須要比被定義項更清晰。立法中使用語言符號只是為了簡化表述,所以它們一般都是高度濃縮的,定義就是為了使得這種高度濃縮的表述具體化和清晰化。如果定義項與被定義項一樣、甚至更加模糊,就實現不了定義的功能。例如一本行政法教科書將“故事片”定義為“包含連續故事情節的影片(它就是為此被構造出來的)”。再如一位德國法學家將德國刑法上的“自主犯罪”定義為“具有非獨立之構成要件的獨立犯罪”。[注]參見前引〔11〕,Egon Schneider書,51-52頁。這些定義都只會使人更加困惑,或至少無助于概念的澄清。
2.定義的必要性
它要求:定義不得包含任何多余的特征且不能遺漏任何根本性的特征。例如,“陳述是陳述者之特定內心想法的表達”這個定義就違背了這一規則。如果當被告人出席后,一位女證人在法庭上泣不成聲或尖叫著暈厥過去,這應當算作“陳述”么?這個定義顯然太寬了,因為它遺漏了根本性特征。有太多的情形(如上述這個女證人的例子)與之相匹配,因而它是無用的。有時它甚至是危險的,如果適用者咬文嚼字地、摳字眼式地去運用它的話。而這種情形在法律的場合并不罕見,甚至有相應的價值考量在內。[注]法律本身就具有形式性,它說出來的東西本身就很重要,對此參見Frederick Schauer, Thinking like a Lawy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7-18.斯卡利亞甚至認為正是形式主義“使得政府成為一個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一個人治的政府”(參見〔美〕安東寧·斯卡利亞:《聯邦法院如何解釋法律》,蔣惠嶺、黃斌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頁)。由此會造成個別情形中不公正的結果。同樣,“行政是國家為滿足其目的的活動”這個廣為流行的定義也過寬了。因為它將立法也囊括進了行政之中,而這么做對于現代法治國家而言是不合目的的。[注]參見前引〔11〕,Egon Schneider書,第52頁。
3.定義要素的無混淆性
被定義項不得包含任何命題聯結詞。包含命題聯結詞的被定義項被稱為“分子式被定義項”(molekulares Definiendum),它的定義式例如為:AxBx=dfCx。在定義式中,被定義項是需要討論的表述,而定義項是服務于討論的表述。如果需要討論的表述是一種分子式被定義項AxBx,那么Ax和Bx各自都是需要被討論的。但如果定義被表達為AxBx=dfCx時,人們只知道服務于討論的Cx是用來討論AxBx整體的。被定義項中需要各自被討論的組成部分Ax和Bx并不能分別直接從Cx中獲得信息。因為我們不知道Cx中哪部分是適用于Ax,哪部分是適用于Bx的,甚或是否需要額外的內容。這無疑是不經濟的。另外,也會有混淆的風險,因為有人可能會將定義項Cx視為給出了單獨關于Ax的信息,但實際上并非如此。例如,《德國基本法》第18、21條使用了“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的表述。聯邦憲法法院曾對此進行定義(BVerGE 2, S.12f.)。但是,這個被定義項其實包含著“自由之基本秩序”(Ax)和“民主之基本秩序”(Bx)兩部分。如果對這一分子式表述下定義,我們并不知道定義項中哪些部分涉及基本秩序的自由要素,哪些又涉及它的民主要素,它們是否有混淆的風險,又是否需要為這兩個要素各自引入新的定義項。[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28-329頁。又比如德國憲法學中常用的“社會法治國”的表述也面臨相似,甚至更嚴重的問題,因為“社會國”和“法治國”這兩部分要素之間可能存在高度緊張。[注]參見劉剛:《德國“法治國”的歷史由來》,載《交大法學》2014年第4期。
4.定義變量的相異性
某些定義涉及二階關系,此時被定義項中只能出現彼此不同的變量。如果某個二階的語言符號Fxy用表述A來定義,那么定義項A除了可以來替代Fab,Fcd外,也可以被用來替代Faa,Fbb,Fcc,Fdd等情形(此處的a,b,c,d指個體常量)。因為不同的變量可以用相同的常量來填入。相反,如果用相同的變量來標示語言符號,即Fxx,那么就不用替之以不同的常量。所以,Fxx=dfA這一定義只能處理Faa,但不能處理Fab的情形。一旦采取這種定義,如果出現Fab的情形,就必須引入一個別的定義項。假如這個定義項仍是A,即Fxy=dfA,那么Fxx=dfA就是多余的,因為前者已經包含了后者(剛說過不同的變量可用不同常量來代入)。假如新的定義項是B (B不等同于A),即Fxy=dfB,那么對于Faa這樣的情形就有雙重定義的風險(見下文)。例如,在刑法學中有“包庇”的概念(涉及包庇者和被包庇者的二階關系)。如果用Bxx來定義,那么就只能來指代自我包庇的情形。由此還要引入Bxy的定義來指代包庇他人的情形。這是不經濟的,甚至如果定義不同時是有危險的。在一本德國刑法典評注書中,撰寫者就分別給出了“包庇”和“自我包庇”的定義:“包庇是犯罪之后對犯罪者的支持”,“自我包庇不受刑罰,它指的是先前的犯罪者確保或嘗試確保已獲得之利益不被奪走的行為”。[注]Vgl.Adolf Sch?nke (Begr.), Horst Schr?der(Forts),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9.Aufl., München: Beck, 2014, § 257, Rn.3, Rn.29.從邏輯上講,包庇包括了自我包庇。所以根據前一個定義(對犯罪者的支持)的結果,自我包庇者就是可罰的,這就與后一個定義的結果發生了沖突。[注]之所以在實踐中還沒有產生嚴重問題,是因為根據《德國刑法典》第257條第1款,包庇被限定為非反身關系,也即是包庇他人,從而避免了與自我包庇的矛盾。 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30-331頁。
5.禁止循環定義
它說的是,被定義項不得出現在它自己以及先前的某個定義項之中。也即是說,不僅不得出現在它本身的定義項之中,也不得出現在同一法律體系的定義鏈條中在前的定義之中。只有這樣才能防止一個語詞直接或間接地自己給自己下定義。[注]參見前引〔22〕,烏爾里希·克盧格書,第144頁。循環定義具有Ax=dfAxBx的形式。禁止循環定義的規則既是為了保障定義的可消除性,也是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矛盾。如果被定義項出現在定義項中,人們就無法通過過渡到定義項來消除被定義項。如果被定義項出現在定義項中,定義項中除被定義項外的其他要素(Bx)與被定義項(Ax)合在一起相當于限縮了被定義項(Ax)自身的內涵,從而產生矛盾。如,“鐵路是致力于在其上運輸對象的鐵路”,相當于一方面認為鐵路(在邏輯上)包括了“致力于在其上運輸對象的”和“不致力于在其上運輸對象的”的兩種情形,另一方面又將鐵路限定在“致力于在其上運輸對象的”這一情形。就像“人是男人”一樣。此外,循環定義也無法實現定義的功能。大多數時候定義是為了澄清被定義項,也就是消除被定義項適用方式的不清晰性。但如果在定義項中再次出現了需要被澄清的被定義項,就無法實現這一功能。法律領域的循環定義可能是明確的,也可能是隱蔽的。[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13、 332-333頁。前者的例子如:“某塊地產的利用方式是‘當地通行的’,指的是它據其使用方式是‘當地通行的’……”[注]Wagner, NJW 1971, S.596.轉引自a.a.O., S.313.后者更為常見,它的一個例子是《德國聯邦傳染病防治法》第1條:“本法所說的傳染病指的是由病原體引發的疾病,它們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傳染給人。”這里的被定義項“傳染病”中的“傳染(可傳染的)”的含義與定義項中“可以……傳染”的意思是一樣的,盡管進行了一定改述。[注]之所以這個定義看上去似乎不成問題,是因為“傳染(可傳染的)”在醫學中得到了相對精確的定義,而一般語言用法與此接近。但這不能改變這一定義屬于循環定義,因而比較糟糕的事實。
6.盡量不下否定式定義
與其他定義規則不同,這一要求是相對的。它說的是:一般而言,定義不得在其定義項中僅以否定的方式來把握。換言之,定義當以肯定的方式來作出。[注]參見前引〔11〕,Egon Schneider書,第53頁。理由在于,定義應當說出某個對象是什么或在使用某個語詞時哪些特征是關鍵的,而對象的屬性或語詞的特征無法完全通過它缺乏什么來澄清。完全以否定的方式來下定義無法實現定義的功能。例如,“盜竊不是窩贓”就不能被作為盜竊的充分定義。因為還有大量的其他行為“不是窩贓”,但同時也不是盜竊,例如搶劫、強奸、貪污等等。所以,這種類型的消極定義無法滿足被定義項與定義項可相互交換的要求。當然,前面說過,這一規則在邏輯上不是絕對的,它以一個條件為前提,那就是,被定義項與定義項中被否定的選項合起來未窮盡上位概念之全集。對于比較簡單的二分法而言,這就不是問題。比如,“人”可以分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所以“成年人”就是“不是未成年人的人”,而“未成年人”就是“不是成年人的人”。同理,之所以上述關于盜竊的說法不是充分的定義,是因為盜竊和窩贓合起來沒法窮盡所有的犯罪行為。如果將除這兩者之外的其他犯罪行為類型(搶劫、強奸、貪污等等)都作為定義項中被否定的選項,那么還是可以通過否定的方式告訴我們關于盜竊的信息的。但在上位概念被區分為數個下位概念的情況下,很多時候我們無法一目了然地判斷,這些下位概念合起來是否已窮盡上位概念之全集。它對于與被定義項相關的體系性認識有很高的要求,也無法防止上位概念下會產生新的子類型。例如,《德國民法典》第1939條規定,立遺囑人可以通過遺囑將其財產利益贈予他人但不指定其為繼承人(遺贈)。這一條款相當于在“通過遺囑贈予財產利益”這一上位概念之下,通過否定的方式(“不指定其為繼承人”)來界定“遺贈”。它的前提在于,“通過遺囑贈予財產利益”僅由“指定繼承人”和“遺贈”這兩類情形構成。但事實上,第1940條還規定了“遺囑負擔”這第三種類型,所以第1939條就不能視為對“遺贈”的充分定義。[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14-315頁。當然,我們并不一概排斥立法者采取否定列舉法明確將某些對象排除于一個表述的適用范圍之外。這在法律適用上是有實益的,但很難說這種做法是對這一表述的定義(甚至連部分定義似乎都談不上)。
7.禁止重復定義
它說的是,在同一個法律體系中,被定義項不得被多次定義,即一會這樣、一會兒又那樣來定義。違背這一規則的情形有時是這樣的:立法者一開始不加定義地使用了某個表述X,但其實預設了X的某種默示地被接受的意義,隨后又明確地給X下了一個不同的定義。也有可能是這樣的:立法者在相關法律體系中沒有給X下一個一般性定義,而在運用X的各個場合卻分別架設了不同的默認定義。所以,盡管使用了同一個表述,事實上卻在指涉不同的對象或意義。這會給法律適用和法律推理帶來困惑。[注]推理領域所謂的“四詞謬誤”就涉及這種情形(關于這一謬誤,參見〔德〕阿圖爾·考夫曼:《法律獲取的程序》,雷磊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2-93頁)。除非可由此推導出的命題即便離開這個重復定義也可以被推導出來,[注]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34頁。但這樣一來定義本身就是多余的。將一個被定義項用不同的定義項去定義可能會導致不同后果。如果定義項是內涵,那么不同的內涵有可能對應相同的外延,也有可能對應不同的外延。如果是前一種情形,盡管不會產生大問題,卻是適用者必須去證明的,這無疑加重了他的負擔;如果是后一種情形就會產生矛盾。如果定義項是外延,那么不同的外延只可能對應于不同的內涵,這同樣會產生矛盾。另外要指出的是,禁止重復定義僅限于“同一法律體系”。如果對同一個被定義項的不同定義出現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法律體系之中,或者不同部門法體系之中則不在禁止之列。后者的一個例子是前面提到過的“近親屬”。刑訴法中的近親屬指的是“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根據相關司法解釋,民訴法中的近親屬指的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行政訴訟法中的近親屬指的則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三者雖然不同,但在各自的體系中都只出現了一次,也沒有默示地預設其他不同的定義,所以并不違反本規則。
8.禁止嗣后解釋
嗣后解釋的情形與重復定義類似,區別只在于,在這里被定義項X出現在法律體系在前的位置上,但既沒有明示也沒有默示地作出界定。所以,禁止嗣后解釋說的是,在同一個法律體系中,不得對某個被定義項嗣后作出不同于先前出現時的定義。換言之,關于X的定義必須要能從這個體系中推導出來,同時在前的主張嗣后不得作不同于先前的解釋。[注]參見前引〔22〕,烏爾里希·克盧格書,第145頁。這種情形多發生在司法解釋的場合,即嗣后的司法曲解。[注]相關解說及其例證參見前引〔3〕,Maximilian Herberger und Dieter Simon書,第336、 375-376頁。在我國語境中理論上也可能發生在嗣后進行立法解釋的場合,但對于法典編纂而言基本不會出現。
定義論的實質規則依賴于相關學科領域的科學標準。在法律領域(包括法典編纂領域),立法者雖然有權任意下定義,但從合目的性的角度而言他卻不能隨意為之。他在下定義時至少要考慮這樣三個規則:
1.下定義時要顧及事實及其后果
法律旨在調整現實世界中的行為或事實,所以立法者必須要顧及客觀事實及其在事實世界中的后果。[注]Vgl.Rolf Wank, Grenzen richterlicher Rechtsfortbildu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8, S.154ff.例如,我國《繼承法》第31條規定了“遺贈撫養協議”,假如立法者在給它下定義時僅將協議的主體限于個人,就違反了既有的事實,也會帶來不利的后果。因為遺贈撫養協議就是在農村“五保戶”和供給制度長期實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實踐中,對于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鰥寡孤獨的老人,一種有效的贍養方法就是由集體組織“五保”(吃、穿、住、醫療、喪葬),老人死后的遺產歸集體組織所有。[注]參見王作堂:《試論遺贈撫養協議》,載《政治與法律》1985年第6期。
2.下定義時要顧及相關條款的體系性關聯
任何立法條款,包括定義性條款都必須被加入其余法律體系之中,所以立法者同樣要受到體系性關聯的拘束。[注]參見前引〔68〕,Rolf Wank書,第187ff頁。這種體系性關聯,最典型的體現在一國憲法的要求上。憲法構成了一個國家法秩序中的最高層級,也構成了法律體系的其余部分都不能違背的“客觀價值秩序”。例如,我國《刑法修正案(九)》規定的“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如果被立法者定義為包括批評、控告和檢舉特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內,那就違背了《憲法》第41條及其體現的人民主權原則和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精神。
3.下定義時要顧及既有的教義學發展
立法要受到教義學的拘束,并不意味著要取消立法的形成空間,而只是意味著要對立法者的權力進行理性限制。因為缺乏法教義學上的預備工作和體系化,立法在法律文化上就會處于較低的層次,也不合乎清晰易懂性和可靠性這些法治的要求。[注]參見雷磊:《法教義學能為立法貢獻什么?》,載《現代法學》2018年第2期。立法者在下定義時,同樣要考慮到長久以來發展起來的教義學說,尤其是“通說”(herrschende Meinung)的主張。這既是為了滿足已經形成的交往預期,也是為了獲得法律人共同體的支持。
四、結 語
本文并不意在運用定義論對現有的立法進行批判,亦不意在建構一套定義論的理性法則。它的目標毋寧是較為有限的,那就是:結合法典編纂(立法)的語境,較為體系化地梳理定義論既有的研究成果并予以印證。據此,定義論是(語言)符號論的一部分,是確定某個語言符號之意義或者其句法結構的理論。它與概念論在諸多方面皆不相同。古典定義論提出了屬加種差的“標準公式”,但在形式—技術方面和內容面向方面都存在缺陷。在改進這些缺陷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現代定義論,即以演算化邏輯系統為基礎的更精致和具有區分度的定義理論。但兩者對于法典編纂活動均具有其意義。定義論包括定義類型理論與定義規則理論兩部分。定義類型理論的基礎在于區分名義定義與實際定義,立法活動涉及的主要是名義定義。它可以分為句法定義與語義定義兩大類,包括約定式定義、操作性定義、隱含定義、分析性定義、綜合性定義五小類。定義規則理論包括定義論的基本原則與基本規則。前者包括可消除性和非創造性,后者至少包括八項形式規則和三項實質規則。不同類型的定義和規則都可以在法典編纂活動中得到檢驗。
最后要指明的是,本文只是將符號論和法律邏輯理論應用于法律領域的一個初步嘗試。與其說它解決了什么難題,不如說它只是開放出了問題域并提供了思考的線索。它也留下了許多尚待去深究的問題。比如,能不能在適用于所有領域的一般定義規則之外,歸納出只適用于立法領域的特殊規則。再如,定義謬誤的表現及其對于立法的影響。[注]對此可參見前引〔22〕,烏爾里希·克盧格書,第228-230頁。所以,本文最多只能算作拋磚之作,它所期待的,是未來能出現更多對于定義論及其在法律領域之應用的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