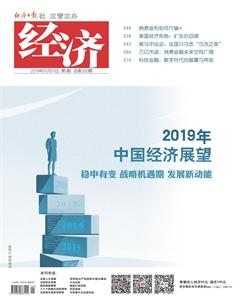黃馬甲運動:法國只可改可改之革
趙永升
“黃馬甲運動”幾乎點燃了整個法國,已經持續四周有余。縱使馬克龍總統12月11日在電視講話中,宣布不但暫停上調燃油稅、從2019年起將最低工資每月增加100歐元、不會恢復財富稅,而且將取消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退休人口的征稅,法國人依舊不依不饒。盡管受歲末節日來臨的影響,參加運動的人數有所減少,但“黃馬甲運動”并沒有偃旗息鼓的勢頭。
面對突如其來的這場運動,馬克龍及其智囊團顯得有些束手無策,無奈之下只得近乎全面“妥協”。其實,這也算不得什么丟人之事,此一時彼一時么。不過,馬克龍的11日電視講話,只是應對突轉形勢的治“標”之策;真要治“本”,尚需從“黃馬甲運動”中汲取教訓,即法國不可改“當下不可改之革”、只可改“可改之革”。
那么,何為“當下不可改之革”?筆者認為在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在法國這樣典型的“歐洲大陸文化”國家,有些領域其實早已進入近乎“不可改革”之列,例如增加稅收和減少福利。此處的“不可改革”并非指客觀上的完全不可能改革,而是指基于法國的現有政體,執政者已在主觀上不愿再觸及此類改革。“誰改革,誰下臺”,已有太多的教訓擺在那里。
這場被不少媒體稱為“十年一遇”甚至“五十年不遇”的“黃馬甲運動”,正是由馬克龍總統上調燃油稅的提議所引發。倘若在經濟上行的年份,對燃油加稅尚屬對社會中上層乃至上層的“薅羊毛”之舉,那么在多年危機過后、經濟形勢有待明朗之際,對燃油加稅就容易引起例如使用燃油較多的農業種植戶們的不滿,進而引發整個社會低收入階層的呼應。其實,基于“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早已造就了切莫妄動的“增加稅收”這塊奶酪,尤其是將波及社會中下層的加稅政策。
而比增加稅收更為敏感的是減少福利。在歐美社會,福利最高的是北歐國家,其次就是西歐國家。目前法國實行的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加起來多達400余種,涉及家庭、養老、失業、醫療、教育等各個方面。例如在法國有孩子的失業者,其可領到的失業金是失業前稅后工資的70%,比德國的67%還要高出3個百分點。換言之,在法國一個失業之前的稅后工資是3000歐元雇員,可以領到2100歐元的失業金;一個失業前稅后工資2000歐元的雇員,可以領到1400歐元的失業金。
憑借筆者在法國十余年的生活、工作感受,“社會福利”著實是一樣“只可給出、不可收回”之物。到了馬克龍總統,僅將每月個人住房補貼減少了5歐元,就已經引起了法國社會不小的抗議。
那么接著,何為“可改之革”呢?上文所述,增加稅收和減少福利已入“當下不可改革”之列,但這并非就意味著如今的法國就已“不可改革”。筆者對法國的改革依舊抱著謹慎的樂觀態度:有些領域尚屬“可改之革”的領域,例如提升法國工業的核心競爭力和提高法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度。
實際上,不少人對法國的工業核心競爭力是低估的。總體而言,法國的工業結構不但全面而且合理。無論在核能、航天、航空領域,還是在造船業、汽車制造業,抑或在高鐵業、制藥業,作為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法國依舊占據著不可小噓的地位。
若仔細排查法國的各個工業部門,不難發現其間尚存有不小的提升空間。這種提升,需要改革來實現;而此類改革在法國國內固然重要,但由于受限于法國的市場規模大小與資源配置能力,與例如中國這樣大型新興經濟體在第三方國家的合作,將會給法國的工業帶來一種新的思維和機遇。僅以核能為例。法國在核能領域的技術,尤其在核能的民用領域,毋庸置疑世界領先。但就現有可考數據,筆者僅能查到法國和中國在英國進行核能合作。實際上,完全可以探索中法兩國在其他更多的第三方國家或地區進行核能合作。
至于在進入后工業時代的現代社會中,法國在第三產業的不少領域也領先世界。根據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收集的數據,法國是世界旅游排名第一的國家。這個不到6700萬人口的國家,僅在2017年全年就共接待了外國游客近8900萬人次,即是一個明證。顯然,法國旅游發展署提出“在2020年接待國際游客一億人”的目標,并非空中樓閣。
在加稅和福利受限的條件下,除了競爭力還有一個可以作為之處是勞動力市場。根據不久前公布的數據,2018年第三季度法國的失業率(本土與海外領地),季調為9.1%,而前數值為9.1%。同時,根據法國央行的預測,法國2019年失業率也將從2017年的9.4%和2018年的9.1%,進一步降至8.8%。
由于在失業率的統計方法上,法國與英美文化國家的差異是不小的。筆者經過計算認為,法國9%的失業率(基于“折合全日工”法)約等同于英國6%的失業率。這般,到了2019年法國的就業業績顯然令人鼓舞,尤其法國政府還可以在勞動力市場僵化現象的“軟化”上下些功夫。
勞動力市場僵化現象的“軟化”,筆者指的是與英美文化國家相比,法國的勞工市場監管有余、調節不足;在傳統上過細的工種劃分,固然有其在當時歷史時代下專業化程度高的優勢,但隨著環境的快速演變也應隨之而更新才是。例如筆者的一個友人是一名法學博士,新近通過了“律考”,接著拿到了律師資質。只是后來在選取具體從事何種業務之時,發現法國在具體某一種法里往下細分到如此多層。一旦選取了一個細小分支終端的業務,以后若再要變更,還得重新再考一遍。
當然,此類工種劃分的僵化,也要追根溯源到高校的教育機制。例如一個在中國已經拿到管理學專業碩士的中國學生,若要繼續在法國深造經濟學專業,理論上講是需要從經濟學的大一開始讀的。因而,筆者認為勞動力市場僵化現象的“軟化”,不但要對現有的法國工種劃分法進行改革,也要對現有的法國大學專業設置法加以革新。若能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度到顯著程度,失業率就能得到相應降低;甚至在未來的兩年內,法國失業率降到7.2%(約等同于英國的4.8%),又未嘗不可呢?
總之,“黃馬甲運動”在表象上確實夸大了法國社會存有問題的嚴重性。這個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亟需改革,但筆者認為法國不可改“當下不可改之革”(例如增加稅收和減少福利)、只可改“可改之革”(例如提升工業核心競爭力和提高法國勞動力市場靈活度)。只要別出大的亂子,法國的經濟形勢將總體向好無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