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才是科幻片最大的硬核
闕政
2500年,這是劉慈欣小說《流浪地球》里,地球逃離太陽系、泊入比鄰星軌道、開始“新太陽時代”需要的時間。
30億,這是電影《流浪地球》在2019年賀歲檔公映10天后,取得的票房。
100多場路演,這是導演郭帆伴隨著《流浪地球》開始的同步“流浪”——從大年初二開始,他每天都會在不同的城市醒來,以至于當記者詢問他身在何處時,郭帆思考了好幾秒鐘才想起來,自己正在武漢。
這一場流浪,還要從20年前開始說起。
被譽為“以一己之力將中國科幻小說提升到世界頂級水平”的“大劉”劉慈欣,2000年時發表了他的短篇科幻小說《流浪地球》。80后的郭帆看到這部小說,還要再等幾年,等到他上了大二。
從小就愛看《科幻世界》《奧秘》等科學雜志的郭帆,在大二那年與大劉精神相遇了,《流浪地球》里“全人類帶著地球一起跑路”的奇思妙想讓他覺得很酷。同樣酷的,還有遲至1993年才引進中國的好萊塢大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只能靠盜版碟一睹真容:1991年的《終結者2:審判日》,讓郭帆第一次被導演詹姆斯·卡梅隆深深震撼,立志將來要拍科幻片。“卡神”早在20多年前已經成了他的神。
20多年后的一天,中影集團拿出私藏多年的大劉三個IP《超新星紀元》《流浪地球》《微紀元》,四處尋覓合適的導演。那時的郭帆,剛和高曉松合作了青春電影《同桌的你》,2000萬成本4億多票房的成績,讓無數青春愛情片前來找他,卻都被他一一拒絕。他想拍的,是大劉和卡神的結合體——科幻大片。
大劉曾說,中國人拍科幻片,缺技術、資金、經驗,但最缺的是科幻的情懷,而郭帆的優勢就在于他有情懷。
一拍,即合。

4年后,《流浪地球》公映,郭帆在微博上寫了“給《流浪地球》的一封信”,將這個電影項目昵稱為“小破球”:“小破球,你已經四歲半了,今天,你會正式離開家,來到外面的世界,無論風雨荊棘,之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
一把火點燃木星
有人說,“小破球”只拍了原著中“地球經過木星”的幾百字,其實不然。
大劉的原著講了這么一個科幻故事:太陽即將發生“氦閃”劇烈爆炸,爆炸之后的太陽將變成巨大的紅巨星,膨脹到足夠把地球吞沒——人類無法在太陽系中繼續生存,就只有向外太空的恒星際移民。距離最近的半人馬座比鄰星,有4.3光年路程。整個移民計劃被稱為“流浪地球”,需要經過2500年,歷經100代人來完成。按照計劃,人類的這次集體“帶球逃亡”被劃分為五個時代:剎車時代,用發動機使地球停止自轉,隨之而來的海嘯、極寒和高溫迫使人類不得不遷入地下城生活;逃逸時代,全功率開動發動機,使地球飛出太陽系,途中還要借助木星的引力,讓地球進一步加速;加速時代,發動機繼續工作,使地球加速到光速的千分之五,再以這個速度繼續航行;減速時代,地球重新開始自轉,調轉發動機方向進行減速;新太陽時代,地球泊入比鄰星軌道,獲得重生。

如果完全按照小說的宏大宇宙來拍,電影可能會變成一部壯麗的科教片,這顯然不是郭帆的初衷。在他看來,電影最善于表達的,還是人和情感,“小說的長度不受限制,大劉原著講的是一個人的一生,而地球要流浪足足2500年——我們在2500年里實際上是選取了36個小時來強化沖突。”
他口中的36個小時,指的應當是“逃逸時代”的一個瞬間:地球經過木星,獲得加速度。但正如小說善于鋪陳前因后果,草蛇灰線也是電影的拿手好戲。在影片《流浪地球》里,木星與地球PK的主情節自然牽動人心,而觀眾也可以從中一窺“剎車時代”留下的痕跡——極寒、地下城,以及已經工作了幾百年的上萬臺發動機。
大劉一支筆營造的科幻世界,眼下正被郭帆貼上皮膚,逐格臻顯——在電影里,我們見到了“上帝的噴燈”,比珠峰還要高2000多米的發動機;見到了無數隧洞組成,深達5000米的地下城和它的居民;也見到了凍成冰棍的上海“三大神器”,一派末世荒涼。說它“草蛇灰線”,還因為不僅有這些明顯的原著科幻景觀呈現,就連你以為被電影忽略的文字,比如“飛船派”與“地球派”的叛亂、中斷2個世紀以后又恢復舉辦的奧運會,都會隱藏在一個小小的布景或者道具里,讓眼尖的原著粉會心一笑。
不過,讓原著粉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把火點燃木星”。
地球在逃亡過程中遇到木星,并不是一次意外,反而是要借助木星的引力被甩向太空,獲得更大的逃逸速度。但在電影里,這次“相遇”出了問題——他們挨得太近,即將突破“洛希極限”。所謂的“洛希極限”(Roche limit),指的是當兩個天體的距離小于這個極限時,就會被“潮汐力”撕碎——按照木星的體積,碎掉的只能是地球。怎么辦呢?只有放火燒木星了!點燃由木星的氫氣和地球被木星吸引過去的氧氣組成的混合氣體,借助爆炸的推力,將地球推開木星!
這個點子,大劉沒有貢獻一個標點符號,在電影中卻成為整出戲的重大爆點,不得不說,非常大膽。
有意思的是,當其中一位編劇最早提出“點燃木星”這個想法時,還被郭帆罵了一通,怎么能點燃木星呢?!結果劇本改來改去,情節推導到必須有一個更大事件出現作為刺激點,郭帆自己也想放把火燒木星了,“還以為是我第一個提,完全忘了有編劇提過”。總之,“燒木星”這個戲眼背后,有個“真香”的故事。

不被證偽即可想象
直到電影首映,大劉才看到這個新加的“硬核”操作。在整個劇本創作和影片拍攝中,大劉都給予了劇組絕對的自由。
影片公映之后,毫無意外也引起了眾多科學愛好者對于劇情合理性的爭論,常見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這么幾點:第一,發動機推力那么大,地球怎么會不散架?第二,點燃木星產生的化學燃燒不足以對地球產生足夠推力,即便推力足夠,地球怕不是還得散架?第三,太空艙里的人工智能Moss居然一把火就被干掉了?
有多少人在為影片中的科幻尋找科學依據,就有多少人在挑科學bug。
這樣的事情,郭帆在拍片之前就已經開始做了:找到中科院的科學家,咨詢片中涉及的天體物理方面的科幻“硬核”。“我們對天體的認識其實大部分都基于數學,是計算出來的,所以許多問題只能假定,包括黑洞、暗物質、暗能量……這也是為什么引力波被探測到的時候我們那么興奮,因為它曾是100多年前就被科學家假設存在的。”
科幻需要科學,更需要想象力。郭帆最終給《流浪地球》定下了“中等偏寫實”的科幻基調,“像《星球大戰》那樣——星戰里的激光劍就有點像中國的武俠,不要求非常高的寫實度。”
郭帆面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像另一位大神諾蘭拍《星際穿越》那樣,所有劇情都按照真實的科學狀態去編寫,找來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索恩(Kip Stephen Thorne)當科學顧問,在電影里呈現最接近真實的黑洞形態,所有的場景道具都極其逼真,連特效都做到根本看不出來是特效的程度,電影拍完,還出了幾篇學術論文——但郭帆心知肚明,這么“高科學”的標準,帶來的拍攝難度是巨大的,別說中國電影工業的水平達不到,投資額也遠遠不夠。就拿木星和地球的“洛希極限”來說,要得到比電影中的“7.44萬公里”更精確的數字并非不行,但是僅僅計算這一個數字就需要中科院專家帶領一個團隊忙活一個半月。
郭帆放棄了。他最終選擇了另一種標準:不被證偽即可放膽想象。“就像當年《西游記》里寫千里眼和順風耳,在那個時代看起來也像是瞎扯,放到今天就可以實現了。那我們現在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不能被證偽,就不能說將來沒有實現的可能。”
科幻需要科學,更需要想象力。郭帆最終給《流浪地球》定下了“中等偏寫實”的科幻基調,“像《星球大戰》那樣——星戰里的激光劍就有點像中國的武俠,不要求非常高的寫實度。”地球有沒有可能不散架?當科學家沒法斬釘截鐵回答一定會散架的時候,電影就可以肆意去放飛想象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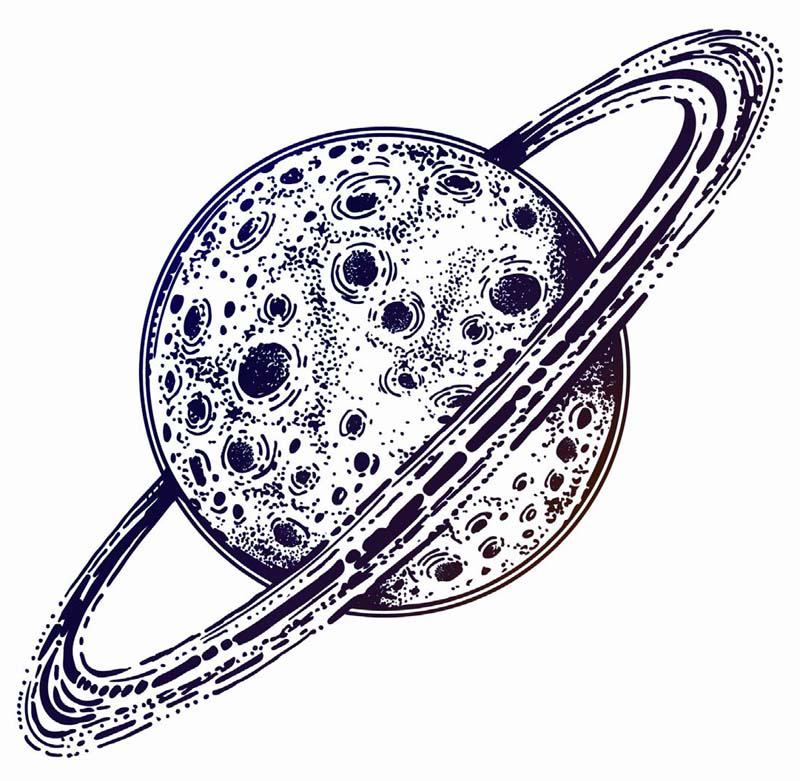
跑路也要帶球跑
有趣的是,大劉曾說自己是個明確的“飛船派”。所謂“飛船派”,就是選擇在地球末日棄球跑路,一小群人帶著人類和動植物的DNA飛向外太空去尋找出路;而郭帆說自己本來也是個“飛船派”,但當了父親之后就變成了“地球派”,就算跑路,也要帶上家庭、昂貴的房子,還有土地。
大二那年被“流浪地球”奇思妙想震撼的郭帆,當時并沒有想到,整個“流浪地球”計劃里最打動他的,其實是一種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內核:“一開始我只是覺得把地球推離太陽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不知道酷什么。直到我去了美國,發現美國人不會有這樣的思維方式,他們會覺得這種做法不夠高效也不夠經濟——但中國人不會,我們對土地的熱愛讓我們連跑路也要帶著球跑,這是中國人才有的精神內核。”
科幻不僅追求“大片感”,還要先落實文化內核和情感支點,這是郭帆從一開始就堅定的想法。“不然我們就只是在模仿別人的科幻故事。”
除了對土地的熱愛,集體主義精神也是《流浪地球》尋找到的另一個支點——片中出問題的不是一個發動機,而是5000座發動機,李光潔帶領的救援小隊只是5000個救援隊伍中的一支。郭帆不想像美式超英大片那樣,安排一個救世主一般的超級英雄,拯救地球的,應該是無數個平凡的地球居民。
影片末尾,吳京飾演的宇航員劉培強舍生取義,犧牲自己去換取地球的安全。看起來有點像是好萊塢模式下的超級英雄,但郭帆并不這么認為。“最后劉培強并不是變成了唯一的超級英雄,而是在那個環境下就只剩下他一個人在太空艙,那一刻,我想給他和兒子劉啟都安排一個獨立的空間,讓父與子之間實現一次單獨的對話。在那一刻,他們沒有任何職務身份,只是簡單的父與子。這也是我對自己父親的一種紀念。”
有趣的是,大劉曾說自己是個明確的“飛船派”。所謂“飛船派”,就是選擇在地球末日棄球跑路,一小群人帶著人類和動植物的DNA飛向外太空去尋找出路。
父子情在郭帆這里仍然延續著中式傳統:不善于表達的父親,卻愿意為孩子付出一切。大劉在小說里提出過一個倫理問題:“當洪水到來時,一個只能救走一個人的男人,是去救他的父親呢,還是去救他的兒子?”這個問題對中國男人來說,等于無解。
大劉雖然已被“封神”,也并不是沒有遭到過質疑——地球還沒開始流浪,已經因為停轉引起的地震海嘯犧牲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茍且生存的地下城,“藝術和哲學之類的教育已壓縮到最少,人類沒有這份閑心了”——這真的不是反人文唯科技論嗎?唯科技論會不會帶來新的宇宙獨裁?這樣的疑問,也許非一時一地一位作者可以解答,但它恰恰證明:價值觀對于一部科幻作品的重要性。
《流浪地球》開拍前最早的一份準備工作,就是編寫世界觀,總共花了八個月。劇組撰寫了從1977到2078年間100年的編年史,還撰寫了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社會文化、科技發展在內的整個故事背景。
《星球大戰》導演喬治·盧卡斯曾說:“科幻片的難度,就在于你必須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世界,還得讓人相信它真的存在。”

創造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世界很難,讓人相信它真的存在,更需要一些拉近彼此距離的小技巧——《流浪地球》里鬼畜了N遍的那段“北京第三區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萬條,安全第一條。行車不規范,親人兩行淚。”便是其一。其實片中類似的標語還有很多,比如“天災無情人有情,孤兒領養暖人心”。這些標語和被觀眾吐槽“都多少年過去了怎么還那么丑”的校服、地下城充滿煙火氣的酒吧麻將館烤串店、慶賀春節的張燈結彩一起,勾連出了我們對于這個陌生新世界的熟悉感。“那地方有我們熟悉的生活,熟悉的東西,如果沒有這些,最后它被毀掉的時候,觀眾就不會覺得心疼。”

在第三交通委的安全標語被大家搶著蹭熱度的同時,也有觀眾對《流浪地球》的價值取向提出疑問——這是不是一部太空版《戰狼》?《流浪地球》被賦予一定的政治意味進行解讀,這并不是郭帆的初衷。“作為創作者,我描繪了我心目中理想的世界——一群人互相信任團結完成一件事,這很像我們劇組的狀態,拋開爾虞我詐,一心為了電影。正因為知道現實中沒有那么美好,才希望文藝作品可以給大家正向的激勵。不是簡單的集體主義或者愛國主義。當然每個人可以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解讀,但延伸到電影之外的解讀,并不是創作者自己想要的。”
75%的特效國內制造
喬治·盧卡斯曾說,“科幻片的難度,就在于你必須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世界,還得讓人相信它真的存在。”這句話還有后半段:“還好現在有CG技術,讓一切不可能都能成為現實。”
這句話放在拍了50多年科幻片的好萊塢也許是對的,然而放在中國電影產業,就還要打一個問號。
2014年,郭帆和幾位年輕導演一起去美國派拉蒙電影公司參觀學習。這次經歷給了他很大的震撼:“別人開上了小汽車,我們還在騎自行車。即使別人告訴你怎么才能造出小汽車,也不是馬上可以投入生產的。”這些年,中國電影的工業化發展一直在被提及,而在郭帆看來,工業化的底層邏輯就是標準化,“可以拆分,可以分工,才能提高效率。文藝創作上的拆分怎么去量化?正常來講順序應該是先建立格式,字號、間距,先讓編劇把場景和對白落實到格式里,變成數據庫,可以隨時調用細節,看清楚哪個演員說了多少話、占據多少百分比,一切都可以量化統計,才好對接后續的軟件工具,比如導演類的、制片類的、場記類的……但是國內連標準的劇本格式都尚且沒有。”
這也是為什么好萊塢的成功經驗無從借鑒:“搭建團隊要分部門和工種,而我們別說是部門,連人都沒有——舉個例子,有些道具需要機械工程師去設計,我們的生產能力非常強,什么樣的工業產品都能制造,但這些人才都不在電影工業的產業鏈上,而假如做電影的人要去聘請專業的機械工程師,那就昂貴太多了。”
郭帆希望將來中國的電影工業可以在標準化上做到三七開,30%講規則,70%人性化,相比好萊塢,這個標準中的人性化比例已經很高——而現實卻是,10%的標準化都做不到。
但《流浪地球》沒有退路,視覺效果決定了它一大半的成敗。2016年3月,劇組啟動了概念設計,總共完成3000張設計圖;開拍前,一共繪制了8000張分鏡圖;拍攝的4000多個特效鏡頭,最終保留下來2000個——其中上海高樓坍塌的鏡頭,反復修改了251次。
在影片片尾,我們可以看到字幕中有“維塔工作室”,而《流浪地球》出色的視覺效果也一度讓人以為,特效大都出自曾經制作過《指環王》的這家新西蘭公司手筆。不過郭帆告訴《新民周刊》,《流浪地球》只有物理特效部分,比如李光潔穿的骨骼盔甲、吳京的太空休眠艙、發動機的火石等機械裝備,是維塔工作室制作的,“這方面國內還很薄弱”,而其余多達75%的CG特效,則都是本土公司完成的——原因很簡單,沒錢。
因為沒錢,很多地方只能用自行車零件裝出小汽車的感覺,比如吳京呆的休眠艙,“應該是可以平滑開啟,但我們是隨機的,每次拍出來都不一樣,有時候還打不開,最后只能用威亞吊著蓋子,人工去拉,后期再把威亞痕跡擦除。”
不過沒錢并不代表時刻都以省錢為目的,該花的錢還得花——《流浪地球》中有大量的實拍鏡頭,置景面積達10萬平方米,許多場景都是實景搭建,還有超過1萬件實景道具。
CG貴還是實景貴?答案是實景更貴。“實景越多,特效就越真實。”郭帆說,“你看《變形金剛》就有大量實景,除了機器人和變形過程是假的,其他基本都是真的。再說《瘋狂外星人》,里面不只外星人是CG做的,猴子也是CG做的,但是你看片的時候幾乎看不出來是假猴子,正是因為影片有很多實拍的場景,真假混在一起,假的才更逼真。如果沒有實拍,哪怕是最頂級的CG,也不會帶給你真實感。”
為了追求真實感,《流浪地球》選擇了前蘇聯重工業美學風格,這是郭帆唯一能找到的、和中國人有情感連接的工業設計。大到發動機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小到一把加特林槍,就連道具槍上鐫刻的“QBZ47 5.8”都要符合解放軍兵器的命名規范,口徑還要符合國情。一切都是為了讓你相信,讓你投入。
電影公映后,不少觀眾前去二刷三刷——電影用心拍,觀眾是能看到的——刷出的細節越多,越看出劇組的誠意。郭帆也在微博上給網友發現的“彩蛋合集”點了贊,“等有空了,我要自己寫一篇彩蛋合集。”
一個點,撬動科幻元年
《流浪地球》不僅留下了一地彩蛋,還流傳出一個“空手套戰狼”的故事:郭帆請吳京幫忙客串,沒想到串著串著,預算嚴重超支,吳京不但不拿片酬、戲份越演越多,還拿出6000萬追加投資,解了燃眉之急。

悲壯的末世氦閃,會成為《流浪地球2》所要主打的視覺奇觀嗎?郭帆卻說,對于續集,他最先要考慮的不是宇宙奇觀,也不是科幻硬核,而是影片的文化和情感內核。
后來吳京說,郭帆跟他介紹的那些故事、那些天體物理,他其實一點都沒聽進去。但是在郭帆的執著面前,他仿佛看到正在籌拍《戰狼1》的自己:到處跟人介紹直升機、坦克、飛機……“我們都如同打了雞血卻又瀕臨崩潰,因為很多人都不看好。”最后他跟郭帆說:“我可以幫你,但我就一個條件——當你成功之后,要記得去幫助另一個‘吳京、‘郭帆,去幫助新類型影片的那群年輕人就行。”
幫忙的不只是吳京,還有借出拍攝場景的寧浩、賣車挺電影的制片人龔格爾,還有七千多名臺前幕后的工作人員。從這一點來說,《流浪地球》的成功,和影片主題一樣,確實是集體團結的力量。細心的觀眾將影片中多位導演的友情客串都找了出來——寧浩飾演了地下城烤串店的老板,路陽飾演了地下城入口掃碼放人的安檢員,張小北飾演了酒店廚師……令人感佩的是,這些導演中有不少是在2014年和郭帆一起赴美學習的同伴,那次自行車碰撞小汽車的旅程,不僅讓中國電影人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讓他們團結一致,把拍出好電影當成了共同的使命。
眼下,《流浪地球》不僅在國內票房口碑雙豐收,在國外也有60多家影院公映,更在北美刷新了華語電影票房紀錄,開創了國產科幻大片的新局面,也被無數媒體譽為“啟動了中國科幻元年”。
一部影片的成功,有沒有可能迅速推動同類型影片?從資金流動上來看一定是有的:投資獲得回報,就會有更多投資涌入。但更重要的是,這部影片能夠留下什么可供同行借鑒的東西。

郭帆說,等路演結束,他將開始《流浪地球》項目的復盤和整理,“準備把各個部門的人都召集回來,記錄經驗和教訓,把這些都整理成文字,公開分享到業內,讓大家盡量規避我們曾經犯過的錯誤。”這份文字材料,預計將有幾十萬字。“經過《流浪地球》一役,最起碼,有意拍攝科幻片的導演,知道可以從哪里找到人員和團隊了。我知道可能有些工作人員又回到了原單位,干回之前的活。所以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還是要從產業入手,比如說我們聘請一個電影車輛設計師,那么薪資起碼不能比他在汽車廠做設計時低,留不留得住人才,還要看政策上有沒有優惠。再往根上說,電影院校有沒有針對電影層面的設計專業?同樣是汽車,電影工業的汽車設計實用性不用很強,形式感則要加強,這是和其他工業設計不同的。《流浪地球》找到了一個點,但中國電影工業不是單點式的,它應該是一個網狀的結構。”
一個點,就是一個開始。正如郭帆在給“小破球”的信中所寫:“今天,你將離家而去,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未來的路上,你要繼續吃苦,繼續堅持,繼續學習,不斷地強大自己;未來的路上,你會碰到越來越多的‘小破球,你們會結伴而行,慢慢地,你們會越來越壯大,越來越團結,你們會有同一個名字,叫‘中國科幻,對此,我堅信不移!”
因為《流浪地球》的成功,《流浪地球2》也被提上了議程。在原著中,還有一個驚心動魄的情節未曾被影像表現——當“飛船派”認定太陽氦閃是“地球派”捏造的騙局后,他們將5000名“地球派”統領集體處死,正在此時,太陽氦閃爆發了——“在太陽的位置上出現了一個暗紅色球體,它的體積慢慢膨脹……而水星、火星和金星這三顆地球的伙伴行星這時已在上億度的輻射中化為一縷輕煙。”
悲壯的末世氦閃,會成為《流浪地球2》所要主打的視覺奇觀嗎?郭帆卻說,對于續集,他最先要考慮的不是宇宙奇觀,也不是科幻硬核,而是影片的文化和情感內核:“父子情講過之后,下一部講什么樣的感情,這是我最先要確立的——新手編劇往往會在一開始做劇本就著急編故事,這是不對的,你需要先明確自己想要表達的感情是什么,再去增加奇觀,增加跌宕起伏的情節——情感才是科幻片乃至所有電影最大的‘硬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