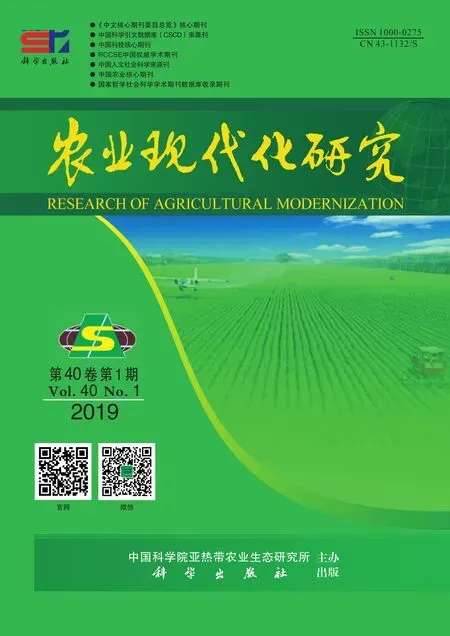我國糧食生產重心變遷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楊宗輝,李金鍇,韓晨雪,劉合光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糧食生產問題具有地域性和時序性,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我國糧食的主產區、主銷區以及各省市之間的區域變化明顯。總體而言,傳統的糧食主產區的省區糧食生產格局變動更為顯著,而其他非糧食主產區的省區則能保持相對較為平穩的狀態。從區域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東部部分省區糧食生產地位在逐步下降,而東北和西部的部分省區糧食生產地位在不斷增強并逐步成為新的糧食生產主要省區[1],全國糧食總產量總體呈波動增長趨勢,北方糧食產量增幅大于南方[2]。從糧食生產重心的變化看,我國傳統的“南糧北調”格局正逐漸被“北糧南運”格局所取代,糧食生產重心不斷由南方向北方和由東部向中部推移。糧食生產重心的北移,意味著北方地區要承受更大的糧食生產壓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會打破原有的生態平衡,產生嚴重的環境問題,包括耕地質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環境污染等嚴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會制約我國糧食增產的可持續性[3]。
糧食生產格局變遷的驅動因素可從自然稟賦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兩方面考慮。其中,從自然資源稟賦方面看,地區間不同的人均耕地面積、灌溉面積、農作物受災情況等資源稟賦條件是影響糧食生產格局的重要因素[4],播種面積差異及上一年度的糧食產量是糧食生產省際差異的主因[5],經過科技進步,科技投入增加而獲得改變的糧食單產與基期糧食生產同樣會對糧食生產格局的形成有影響[6]。從社會經濟條件看,生產技術包括農業機械化水平、非農就業機會、地區城鎮化發展水平、地區人均GDP、農業投入、農業政策、農業基礎設施等都是諸多學者所關注的因素[7-8]。其中,多數學者通過選取某一時段某地區糧食產量及相關影響因素的數據建立回歸來實證分析影響糧食生產的因素,一般認為糧食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農業機械總動力以及農業科技水平等對糧食生產有正面的影響,而成災面積對糧食生產有著明顯的負向影響[9-11]。
糧食生產重心是糧食生產格局的一種重要體現,當前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呈現出一定的北移趨勢,這種趨勢如何衡量和刻畫,影響因素和機制是什么,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基于1997—2016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不包括港澳臺)的面板數據,本文以糧食產量作為衡量糧食生產的指標,運用重心模型分析我國糧食生產重心的具體演變軌跡,并且著重通過固定效應模型來探究影響我國糧食生產重心變遷的主要因素以及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北移的驅動機制,該研究對把握我國糧食生產格局、優化糧食生產戰略布局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方法和研究數據
1.1 研究方法
1.1.1 重心模型 在研究某一經濟現象的空間特征及空間變化時,通常會用“重心”來衡量其空間特征及變化。重心,在物理學中是指可以使物體在受到一定力的作用下能夠保持平衡的點。在經濟研究領域,重心通常是指在某一經濟區域空間中,使得各方的經濟力量趨向平衡的一點。重心模型能夠很好的反映某一區域經濟重心的軌跡變化情況與走勢,探究經濟重心軌跡的移動,能更全面、更直觀的知悉某一經濟變量在某一經濟區域或國家中的走向和未來發展趨勢。本研究以1997—2016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為研究對象,通過引用地理重心模型來更加精準、直觀形象的描繪我國糧食生產空間重心的軌跡變化情況。

重心分析模型為[12]:式中:n為研究的31個省級行政區,第i個單元的地理中心坐標為(Xi,Yi),Mi為該地區的糧食產量,重心坐標即為(,)。其中X、Y分別表示某一區域某種屬性的“重心”所在地理位置的經度值和緯度值;Xi、Yi分別表示第i個次一級區域重心的經度值和緯度值;Mi表示第i個次一級區域的某種屬性的量值。實際問題分析中,Xi、Yi一般選用次一級行政首府或中心城鎮的地理坐標[13]。由于本文探討的是糧食生產的重心問題,故文中的Xi、Yi選取的是各省級行政區其糧食產量最大地區(地級市)的地理坐標。在度量“糧食生產重心”時,采用糧食產量作為某一區域的糧食生產量值。
重心轉移距離[14]:

式中:d表示相隔的年份間某種經濟屬性重心移動的距離,α,β分別表示不同的年份,(Xα,Yα)與(Xβ,Yβ)分別表示第α年,第β年某一經濟屬性重心所在的空間位置的經緯度,k為常數,一般取111.111。1.1.2 面板固定效應模型 本文構建面板數據模型來實證分析影響我國糧食生產重心變化的因素,為消除共線性與減少異方差,除比例變量外,其他自變量均進行理論對數化處理[15]。具體模型如下:

式中:GYLDit為被解釋變量,i,t分別代表31個省份和年份(1997—2016),β1,β2,…,β10為待估參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面板數據模型主要包含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及混合估計效應模型三種形式,Hausman檢驗的結果為85.48,P值為0.000,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拒絕了隨機效應的原假設,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同時,F檢驗結果為74.75,P值為0.000,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拒絕了混合估計效應的原假設,進一步論證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糧食生產重心的轉移源于不同區域糧食產量的變化,而糧食產量變化主要受自然稟賦、社會經濟水平、農業技術進步、市場化程度以及政策等因素的影響。
自然條件:耕地面積的影響。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及南方地區城鎮化進程較快,農用地的數量在逐漸減少,而北方地區相對而言城鎮化速度并不及南方地區,因此耕地的減少也相對較緩慢,這是驅使糧食生產重心轉變的重要因素。其次,相關研究指出,在氣候變化作用下,我國糧食生產的結構和地區布局將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導致我國糧食產量波動變化,甚至影響到國家糧食安全[16]。最后,在全球變暖的大趨勢下,氣溫的升高會使得糧食作物的熟制發生一定的變化,可能會使得全國的種植制度界限有一定程度的向北偏移[17]。
社會經濟條件:農業生產投入包括灌溉面積、化肥施用量、機械化水平及農業勞動力數量等因素。研究發現,北方地區灌溉條件的改善是驅使糧食生產重心轉變的重要因素[18]。北方地區近幾年的有效灌溉面積呈增長趨勢,灌溉的發展提高了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同時為良種、施肥、改進耕作栽培及機械化等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創造了條件,這些因素都驅動著糧食生產重心的變化。農業勞動力數量對于糧食主產區、糧食主銷區和糧食產銷平衡區糧食產量的影響不同[19],在本研究中其影響方向待定。
政策條件:國家關于糧食生產出臺了有關糧食直補、農機購置補貼、生產者補貼等一系列針對糧食主產區的補貼形式,用以支持糧食生產,這些補貼政策對于具有豐富耕地資源的北方地區尤其是東北地區而言,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可通過糧食作物播種比例以及復種指數來呈現。
根據上文分析,將自然稟賦因素、農業生產投入(包括技術進步)因素、經濟因素三個層面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的具體說明及預期影響見表1。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估計模型所采用的數據為1997—2016年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除港澳臺)的面板數據。其中,糧食產量、有效灌溉面積、農業機械總動力、化肥施用量、成災比例等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8—2017年),城鎮化率、農業勞動力數量數據根據各省(市)統計年鑒(1998—2017年)計算得出,其中農業勞動力選取的是第一產業從業人數,城鎮化率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人均耕地面積根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的耕地面積數據與各省(市)統計年鑒中的農業人口數相除得出。復種指數為糧食播種面積與地區耕地面積的比重,其中糧食播種面積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8—2017年),地區耕地面積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8—2017年),氣溫變量以每個省級行政區劃的省會城市的年平均氣溫來衡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8—2017年)。

表1 模型變量說明及其預期影響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s and their expected effects
2 結果與分析
2.1 糧食重心演變過程
根據上文糧食生產重心模型及重心轉移距離模型,運用ARCGIS10.2軟件分別求得1997—2016年我國糧食生產重心的坐標、重心轉移軌跡及各年份之間糧食生產重心的轉移距離。
從糧食生產重心的坐標上可以看到(表2),1997—2016年20年間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地理坐標介于114°0'38.8368"E~115°2'3.2172"E,33°34'24.5022"N~35°15'56.7282"N之間。整體上糧食生產重心位置變化不強烈,大部分年份的糧食生產重心在河南省境內,2011—2015年糧食生產重心位于山東省境內,20年間糧食生產重心由河南省的中東部地區轉移至河南省的東北部地區及山東省的西南部地區。
從糧食生產重心的移動距離看(表3),1997—2016年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向東北方向移動,整體向東北移動了172.56 km,年均轉移速度為8.63 km/a;各年份間糧食生產重心轉移的最大距離出現在1999—2000年,轉移距離為65.75 km。糧食生產重心最小的年際移動距離出現在2011—2012年,轉移距離為2.56 km。從糧食生產重心的轉移距離看,20年間我國糧食生產的重心有向北移動,但移動距離并不強烈。

表2 1997—2016年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坐標及其所在地Table 2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base coordinates and location from 1997 to 2016

表3 1997—2016年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年際轉移距離與轉移方向Table 3 Annual shifting distance and direc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16
根據上文所得我國糧食生產的重心坐標,各年份的重心轉移距離以及我國糧食生產重心軌跡的變化圖,可大致將近20年我國糧食生產重心的轉移分為4個階段(圖1)。
第一階段:1997—2000年。這一時期糧食生產重心由河南省的周口市西華縣向其西南方向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轉移,在此期間糧食生產重心的轉移方向有所波動,1998年糧食生產重心較1997年向東北方向轉移,自1999年之后開始向西南方向轉移;這一時期糧食生產重心整體的轉移距離為47.02 km,年均轉移速度為15.67 km/a。
第二階段:2000—2006年。這一時期的糧食生產重心總體上是向東北方向轉移,糧食生產重心由河南省的漯河市郾城區轉移至河南省開封市杞縣。僅有2003年與2005年糧食生產重心呈現出微弱的向西南、西北方向轉移的趨勢。這一時期糧食生產重心整體的轉移距離在各階段中最大,為152.24 km,年均轉移速度最快,為25.37 km/a。
第三階段:2006—2009年。這一時期,糧食生產重心由2006年的河南省開封市杞縣轉移至河南省開封市祥符區,其總的轉移趨勢是向西轉移。這一時期糧食生產重心整體的轉移距離在各階段中最小,為32.67 km,年均轉移速度最慢,為10.89 km/a。
第四階段:2009—2016年。這一時期,糧食生產重心的整體轉移方向依然是向東北方向轉移,由河南省的祥符區轉移至河南省新鄉市長垣縣,其中2011—2015年糧食重心位于山東省菏澤市東明縣地區。從2013年之后糧食生產重心轉移程度較之前各階段變小,且趨于穩定,糧食生產重心有微弱的向西轉移的趨勢。這一時期糧食生產重心整體的轉移距離為83.57 km,年均轉移速度為11.94 km/a。

圖1 1997—2016年我國糧食生產重心軌跡變化情況Fig. 1 Shifting path of grain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from 1997 to 2016
2.2 糧食重心變遷影響因素分析
考慮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時間效應,本研究首先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來進行估計。運用stata15.0對加入時間變量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中顯示,時間效應即年份變量并不顯著(表4),因此可直接采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

表4 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個體固定效應回歸結果顯示(表5),模型的F值、R2均十分顯著,說明模型的解釋能力比較好。估計結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積、有效灌溉面積、化肥施用量、機械化、糧食作物播種比例、復種指數均對糧食產量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積及糧食作物播種比例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良好的農業生產投入條件,包括由灌溉水利設施改進帶來的有效灌溉面積的增加以及糧食生產投入中化肥施用量的增加會促使糧食產量得到提升,使得糧食生產重心發生變化。除此之外,糧食作物播種比例對糧食生產來說影響巨大,糧食作物播種比例上升1,會帶來糧食產量185.7%的上升。近20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與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使得南方地區的糧食播種比例較之前有很大程度的下降,而北方地區尤其以東北地區為例,其糧食作物播種比例較之前是上升的,這一因素使得南北方之間糧食產量有了較大差距,糧食生產重心不斷向北轉移。

表5 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one-way fixed effect model
其他因素中,人均耕地面積、復種指數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耕地是從事糧食生產的基礎,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使得東南沿海地區耕地面積減少,而北方地區相對而言城鎮化速度并不及南方地區,因此耕地的減少也相對較緩慢,進而使得糧食生產重心向北方轉移。復種指數指的是某一地區的糧食播種面積與地區總耕地面積的比值,糧食作物播種比例及人均耕地面積的影響會使得復種指數同樣呈現出相似的影響。機械化變量對于糧食生產的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意味著機械化水平對糧食產量有一定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大,即機械化水平對于糧食生產的影響潛力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成災比例變量對糧食產量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成災比例每增加1,會使得糧食產量下降6.8%。各地區受災害程度的不同也會導致糧食生產重心發生一定的波動。而農業勞動力、城鎮化發展水平以及氣溫變量對于糧食生產重心的變化并沒有顯著的影響。
2個一級指標“資源保護”與“活化利用”的比重是四六開,說明專家們認為保護與利用并重,且利用村鎮歷史文化資源,注入新的活力比單純的保護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歷史文化資源與具體生活場景的融合,才能使場所煥發新生。保護是為了利用,利用是為了發展。筆者在村鎮調研走訪過程中,也曾見到修繕一新的傳統建筑大量空置的現象,村民不愿意搬入其中居住生活,這種現象是保護做得很好,而缺乏活化利用,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保護與利用相得益彰的案例也有許多,有的村鎮將老祠堂修繕后,用作村民平時各種公共活動的場所,傳統建筑和現代生活渾然一體。
3 結論
本研究基于1997—2016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運用重心模型分析了我國糧食生產重心的演變過程,進一步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我國糧食生產重心變遷的影響因素,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1997—2016年間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地理坐標介于 114°0'38.8368"E~115°2'3.2172"E,33°34'24.5022"N~35°15'56.7282"N之間。整體上糧食生產重心位置變化不強烈,大部分年份的糧食生產重心在河南省境內,少數年份糧食生產重心位于山東省境內。
2)1997—2016年我國糧食生產重心主要向東北方向轉移,重心總的轉移距離為172.56 km,年均轉移速度為8.63 km/a。
3)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積、有效灌溉面積、化肥施用量、機械化、糧食作物播種比例、復種指數均對糧食產量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是驅使糧食生產重心北移的因素。
4 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為進一步優化我國糧食區域生產能力,保證各區域糧食自給能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4.1 保護耕地數量與質量,加強對耕地的管理以及監測
耕地是進行糧食生產的基本依托與根本保證。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耕地面積通常會因為城市的快速擴張而不斷減少,過少的耕地面積對糧食生產來說必然會產生不利的影響。此外,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帶來的潛在環境污染問題也會對耕地質量造成一定的威脅。因此,要嚴格保證耕地的數量與質量,做好對耕地的維護與監測。對于現有的耕地資源來說,首先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不動搖。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各地區要做好相關的土地利用規劃,嚴格規定城鎮用地與農業用地的區別與界限。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優先考慮占用荒地,要最大程度的減少對耕地資源的占用。對個人或單位等非法占用耕地改造耕地的行為要嚴加懲罰。此外,要加強對拋荒土地的整治和充分利用,最后,適當的開發能夠利用的潛在耕地,將部分可利用的荒地通過改造變成可以進行農業生產的耕地,多措并舉。當耕地數量與質量得到一定的保證時,相應地,復種指數也會隨之提高。同樣地,對農民來說,也能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這對于保障糧食生產具有積極的作用。
4.2 加大農業生產投入與科技投入
成災比例對糧食生產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因此,應通過先進的農業科技手段,結合氣象監測與預報等技術,建立糧食生產防災預警機制與治災機制,對可能出現的災害,比如旱災、洪災等加以防范。探索新型農業保險手段,通過農業保險來保護農民的權益不受損害。通過防災與治災手段,促進糧食生產可持續發展,從而保障糧食安全。
4.3 探索多樣化農業補貼形式,保障糧農利益
2003年之前,我國糧食產量并不高,自2004年實施了一系列的糧食補貼政策,包括糧食直補、良種補貼以及2006年取消農業稅等,對糧食生產具有重要意義,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但隨著我國糧食產量的不斷增長,糧價開始逐漸走低,出現了谷賤傷農的現象,農民種糧面臨著成本高、收益低的問題,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出臺有效的緩解了這一問題,也提升了農民的積極性。近些年國家一直在調高糧食最低收購價,但有可能造成糧食供過于求的現象。因此,應探索合理的糧食收購價保護制度,適當調整糧食最低收購價,使糧食生產向著更合理的結構方向發展,對相關的糧食補貼政策,要加大財政投入,適當的提高糧食補貼的水平,探索一些新型的補貼機制,以此來穩定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保障農民的利益。
4.4 構建區域糧食供需協調機制
從我國糧食生產的重心看,當前我國糧食生產重心集中于北方地區,南方地區的糧食生產地位在逐漸下降,各省份糧食生產與糧食需求并不均衡,因此,應加強各省份之間糧食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我國的糧食配給由過去的南糧北運轉變為現在的北糧南運的流通格局。北糧南運,對于產區而言,增加了種糧農民收入,助力產區糧食產業發展;對于銷區而言,提供了優質糧源,有效推動糧食區域供求平衡[20]。對這種產區與銷區之間的糧食流通,國家應加大對其支持,鼓勵銷區企業實現產銷合作。此外,對各省份自身的糧食生產而言,由于糧食生產具有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各省份之間應加強彼此的溝通與交流,通過農業科技及灌溉技術等的空間溢出效應,來實現本地區此類糧食生產條件及農業技術等的進步,穩定糧食生產與糧食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