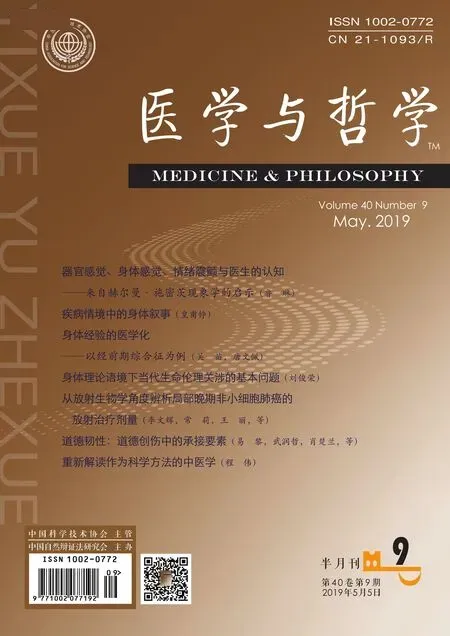身體理論語境下當代生命倫理關涉的基本問題*
劉俊榮
人作為生命倫理的關懷主體,既不是純粹思想的“心靈實體”,也不是純粹廣延的“機械身體”,而是具身的(embodied)存在。國內也有學者將“embodied”譯為“涉身的”、“緣身的”等。筆者認為用“具身的”更能反映其本意,一方面“具身”強調人是具有身體的主體和存在,這與笛卡爾的心靈主體相區別;另一方面,強調身體是不同于肉體的主體,它具有與外部環境、物理客體等進行互動感知的能力,從而與拉美特里的機械身體相區別。只有認同人是“具身”的存在以及身體的屬“我”性,才可能進一步探討身體在認知中的意義等“涉身”問題,因此,與“涉身”相比,“具身”有著更基礎、更廣泛的適用性。人首先是肉體的、軀體的、生物性的存在,其次才是理性的、文化的、社會的存在。身體理論的興起和哲學主體間性的建構,消解了近代西方哲學中祛身的自我,使自我返回到了世界和塵世,對我們反思當前生命倫理的基本問題,提供了別樣的視角。身體作為自我構建的始基,既不是純粹的肉體,也不是心靈的容器,它是人與人進行交往、對話的場所,是自在與自為的統一。生命不能脫離時空而存在,人的生命的界定既需要考慮時間因素,也需要考慮空間因素,人的生命與身體在時空上具有統一性。
1 人的生命與身體的共時性與歷時性
“人的生命”與“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人的生命只是人的一種屬性,作為個體存在的人除此之外,還具有其他多方面的規定性,如充當特定的社會角色、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和義務、遵循社會道德和法律法規等。但是,二者又相互聯系,人的生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失去了生命,人就不能稱之為人。
在生命倫理學領域,關于人的生命之起始有著不同的界說。其一,生物學標準從人的種生命出發,把受精卵作為人的生命的開始,如《阿根廷民法典》則規定“人的生存自孕育于母腹之時開始”[1]。1962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聲明中指出:“無論何時精神性的靈魂被創造以構成一個人(位格),生命從一開始就必須被小心地保護。”因為人為的干預要么阻礙了受精卵發育成為正常人的可能性,要么影響了胚胎作為一種“人”的正常發育,這種思想似乎能夠從柏格森的時間觀得到說明。按照柏格森的真正時間觀,生命是無間斷的、不可分隔的、非空間化的綿延,人的生命從精卵結合之時已經確定,此后的空間性變化如細胞的分裂、組織的分化、器官的形成等,只能就其空間時間而言,只是真正時間的空間化過程。這種觀點,僅僅把人看作了純粹的生物存在,看到了人的種生命,而忽視了人的類生命。顯然,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它與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所認可的人工流產、人工生殖及利用受精卵或胚胎進行合法研究的科學活動相背離;其二,授權標準從人的類生命出發,認為胎兒只有得到父母或社會的接受才算生命的開始。法國天主教道德神學家波希爾等認為,完人的生命或人化的生命必須在親屬這個名義之內才能算數[2]。這種標準固然考慮到了生命的社會性,但卻否認了生命標準的客觀性,把父母或社會的“接受”看作生命的標準,必然走向相對主義,最終導致標準的混亂,并可能成為某些棄嬰行為的辯護借口。
筆者認為,人的生命的界定既不能僅從種生命出發,但也離不開種生命,種生命是類生命的物質載體,只有依賴于種生命才能進一步說明人的類生命。所謂“種生命”就是“被給予的自然生命”,而“類生命”則是“自我創生的自為生命”[3]。種生命具有自在的性質,受自然法則所支配,而類生命是由人所創生的,為人所特有,受后天條件所影響,因個體創造能力的不同而表現出異質性。對于人的種生命,不能僅從動物的種生命的意義上去理解,更不應視作構成生命基本單元的細胞層次(包括受精卵)上的生命,不能以“遺傳學上的連續性”為由,強調受精卵已具有人類的種生命,人的種生命是社會化了的種生命,它不同于動物純粹的種生命,受精卵只有一般生物的自然生命,人類的種生命并不是簡單的基因序列,它的存在是以人的實體存在為基礎的。就人的生物發育過程而言,人的身體雛形只是到胎兒階段才得以形成,但是這一時期所謂的身體也只不過是肉體,只具有純粹的生物學特征,而缺乏基本的文化體驗和認知功能。直到分娩前,由于胎兒與其孕母仍然是一元的存在,尚隱藏于母體之中,完全依靠母體,不能扮演任何社會角色,還沒有進入社會化程序,也稱不上是人的種生命。只有分娩成功,新生兒誕生之后,新生命與孕母的關系才由一元存在變為二元存在。這時,雖然他仍然依賴母體的營養和照料,但新生兒與胎兒不同,它已成為家庭和社會的一員,可以扮演子女、病人等角色,其身體可以感觸父母的撫摸與呵護,可以進行包裝和修飾,并已開始與他人發生心身的交互,具備了基本的認知圖式(這已被心理學家皮亞杰的認知理論所揭示)。只有從此開始,它才實現了與外界的直接聯系,才真正成為人類中的獨立個體和道德意義上的具身主體。
當然,剛剛出生的嬰兒并沒有自我意識,但這并不影響它作為個體的人而存在,因為它已完全具備了人的直觀表象,并已成為文化、制度、技術等規訓的對象,已開始進入“自我意識”和“社會關系”的社會程序之中。盡管“自我意識”并非為人類的每一個體所具有,但就類的屬性而言,它是人的生命與其他靈長類、受精卵、胚胎、胎兒的生命區分開來的本質性特征。正是由于自我意識,促成了個體發展的整個生命過程中的質變:即當個體發展到產生自我意識時,人的種生命開始發展出人的類生命,但種生命并未因此而消失,而是進入了社會化程序,成為社會化的種生命。而當人的自我意識不可逆轉的喪失時,又復歸為人的種生命或二者同時消失。但自我意識的喪失并不必然意味著類生命的完全喪失如植物人狀態,就植物人來說,盡管其類生命的自我創生能力已不復存在,而其所承載的父親、母親、兒子等社會角色依然存在,只不過其類生命已處于次要的方面,屈從于種生命,成為種生命化的類生命。由于自我意識的產生離不開社會實踐,大腦僅僅是思維的外殼,只有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實踐過程中,意識才能得到產生和發展。立足于社會關系,不但可以進一步區分人與胚胎、胎兒的生命,而且還有助于比較深入地認識人與其他靈長類生命的異同,如:在鏡子中能辨認自己的黑猩猩,似乎也有自我意識,但不符合社會關系的標準。因此,我國學者邱仁宗[4]認為:人是在社會關系中扮演一定角色的有自我意識的物質實體。這不僅說明了人的種生命,同時也強調了人的類生命,人的生命應該是種生命和類生命的有機統一,單純的種生命或類生命都不能稱其為人的生命,缺少或失去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的人都不應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或正常的人。
因此,從發生學上說,人的種生命與類生命、人的身體與生命具有共時性和歷時性。也就是說,在時間坐標中無論從縱向上還是橫向上看,人的生命的孕育過程與人的身體的形成過程都遵循著完全一致的時間生成軌跡,分娩前的生命至多是人的種生命,此時的身體也僅僅是肉體。只有胎兒娩出這一刻之后,人的類生命才得以形成,肉體也才轉化為身體,胎兒才成為具身之人并進入社會化進程。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法律和我國《憲法》《國籍法》《刑法》《民法通則》《母嬰保健法》等法律中,均將個人基本權利的時限界定為出生之后,尚未出生的胚胎兒不能成為法律關系中的法律主體,這就從法律上確認了人的生命之起始。
但是,人的生命與人畢竟不是一回事,人是有生命的存在,是生命的物質表象或載體,生命是一種流變、沖動、過程和存在方式,生命有生命質量與生命價值之分、有種生命與類生命之別。種生命與類生命的統一性關系是就人類的生命而言的,就某些生命個體來說,種生命和類生命并非總是統一的。也就是說,擁有高質量的種生命并不一定就擁有高質量的類生命,擁有高質量的類生命也未必就擁有高質量的種生命。例如,某些身強力壯、十惡不赦的罪犯,其類生命質量可能為零甚至負值;某些殘疾人或病患雖然其種生命質量較低,但其類生命質量即生命價值并不小于某些正常人,霍金就是例證。因此,種生命與類生命、生命質量與生命價值并非總是正相關的。我們不能因為類生命質量的降低或消失而完全否定其種生命的存在和意義,也不能因為種生命質量的受損或降低而否定其類生命的質量和價值。更不能因為某些病患如植物人、無腦兒等沒有自我意識,類生命質量低劣,而否定其種生命的尊嚴和神圣。
2 人的生命與人的空間性:關于胎兒生命的再定位
人的生命作為種生命與類生命的統一既然始于出生,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胎兒的生命?它是不是人的生命?是否具有生命的權利和尊嚴?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闡明胎兒是不是人?由此,又勢必需要界定什么是人?
關于人是什么?“我是誰?”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無論古希臘的人學理論,還是基督教、文化人類學者等學派的人學理論,都沒有能夠擺脫原有觀念中關于人的靈魂、理性、情感、心智等認識的困擾,將思維者、行動者的特性類推到一切人類個體,并試圖從思維抽象中揭示人的本質,忽視或漠視了感覺直觀中的人,其結果事與愿違,抽象的本質并不能適用于無限多樣的個體。對人的界定應當從最簡約的、最具普遍性的特征入手,考慮到人類的每一個特殊個體,包括正常的和異常的不同情形,尊重每一個個體的人,避免踐踏個體及生命尊嚴的現象。現象學方法為我們達成這種目的提供了可能,現象學強調研究者從傳統的觀念、理論、思維、偏見中解脫出來,擺脫一切理論性的先入之見,從原初看到的“純粹”現象中認識事物,從事物本身洞察事物,主張“只有回到直接的直觀這個最初的來源,回到由最初的來源引出的對本質結構的洞察”[5]27。這種方法通過“相似性統覺”揭示不同個體間的共性,發現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本質,把所研究體驗的描述還原到它的基本要素或本質。就此而言,人首先是我們能夠體驗到的像你、我、他有著一般人所具有的頭顱、軀干、四肢的動物。這是我們對人的類生命特征的直觀體驗,這種直觀體驗是我們進一步判斷某物是否是人的基礎。從外部直觀來說,也許某一個體缺失了常人所具有的手、腳甚至四肢,但只要他具有人的頭顱和軀干,有著人的基本生命體征如脈搏、呼吸、體溫、進食、排泄等,他所呈現給我們的仍然是人的直觀,我們決不會因為他缺少了手、腳或四肢而否定其作為人的存在,頭顱和軀干的共在是人之生命活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解剖學要素。至少就目前的生命科技水平而言,沒有頭顱或軀干的人是無法存活的。脫離了軀干的頭顱或與頭顱分離了的軀干,都不能稱其為人。因此,頭顱和軀干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形態,這是我們基于對人類不同個體的“自然相似性”獲得的最簡約的直觀體驗和認識。盡管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個體在膚色、頭發、眼睛顏色等方面存在的差別,但我們總能看到不同個體在頭顱和軀干上的結構相似。基于這些自然相似性,我們便獲得了他人存在的前提條件之一:一種通過感知類比而獲得的相似性。“只有在我的原初領域內,對作為另一個人的身體的軀體進行類比,才能從根本上說明如何得以把握那里的那個與我的軀體相似的軀體。”[6]而靈魂、理性、情感、心智等作為意義建構和意識抽象的結果,只是特定階段的正常人才具有的特征,如果將其強加于人類的一切個體,必然會將該階段之外的或非正常的個體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如嬰兒、無腦兒、植物人等可能均被排除在人類之外,這顯然是難以令人接受的。事實上,嬰兒、無腦兒、植物人等,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特殊個體的人。之所以是人,并不是因為他們擁有人的理性、情感與心智,也不是出于對這些特殊個體的憐憫、同情與責任,而僅僅是因為他們能給予人以人的感覺直觀且擁有人的基本生命體征。不可否認,當言說他們能給予人以人的感覺直觀時,我們并沒有完全脫離意識中原有的關于人的整體表象,但我們并沒有被原有的表現所桎梏,而是將一般常人的整體表象予以懸置,保留其最基本的要素。事實上,徹底的還原是不可能的,現象學“還原法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完全還原的不可能性”[5]31。如果完全懸置了對人的一切認識、理念和習慣,人的概念就無從談起,它至多是一個無以言表的客觀存在。
事實上,將人作為如其所是的直觀體驗,并沒有也不意味著漠視人的精神、意識與情感,相反,關注人的精神和意識正是現象學與實證主義方法的根本區別。從最基本、最簡約的直觀體驗還原到一般的人,所需要給予的正是精神和意識,使其在被懸置之后得以再現。我們只有根據直觀體驗將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個體加以考察和審視,回歸真實的生活世界,才能得到原初的生活體驗,并對其加以無偏見的描述,達到生命的直觀,看到形態異彩的世界,實現最基本、最簡約的本質還原。也只有在最基本、最簡約形態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揭示復雜的群體形態,歸納出類的不同層面的共性和特征。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從最簡約的、直觀的人的概念出發,再賦予其不同層次、不同屬性的類的特征,就可以還原到現實中不同狀態的人類群體,如包括正常人、殘疾人、病患者、嬰兒、兒童、青年人、成年人、老年人等。也可以再進一步將道德、法律、文化等屬性賦予不同的群體,并進行更深一層次的分類。相反,如果對人的界定的起點太高,反而不具有廣泛的適用性,而且會造成對人類個體生命的踐踏。在部分學者如辛格等關于人的分析中,之所以出現否定無腦兒、植物人等作為人類之個體的歸屬,其根源就在于沒有從最簡約的直觀體驗觀察和描述對象,用一般常人的標準去衡量非正常的人,違背了科學哲學中的經濟思維原則。
綜上所述,人的界定需要以身體為準繩,人就是如人所有的頭顱、軀干及基本生命體征而獨立存在的具身個體。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揭示復雜的群體形態,歸納出類的不同層面的共性和特征。
胎兒尤其是28周以后的胎兒已具備人的頭顱和軀體,已符合人的最基本條件。但是,如果以自我意識、靈魂、理性為標準,無疑胎兒不是人。我們對此結論持肯定的態度,但并不贊同其否定的理由。因為自我意識作為人的正常狀況下類的屬性并非適于一切人類個體,并非所有的人類個體都有自我意識,沒有自我意識的個體未必就不是人。因此,我們不應以自我意識的缺失而將胎兒排除在人類個體之外。事實上,胎兒雖沒有自我意識,但有發生自我意識的潛能,只不過胎兒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僅具有人的基本雛形,與社會還未發生任何現實的聯系,其生命是純粹的種生命,其身體也還是純粹的肉體,沒有任何文化、技術、社會的印跡,尚沒有進入社會化程序,也沒有具身認知的能力。無論古希臘的人學思想、現象學的人學視點,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人首先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是具有自主認知能力的主體,要么是一種理性的實體、先驗性存在,要么是一種經驗性存在或對象性存在。作為主體與其周圍世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聯系,或者將世界視為自身的對象或者視為自身的有機整體。即使宗教神學,也只是要求尊重胚胎、胎兒的生命并沒有明示胎兒是人。如在《生命福音》通諭的聲明中雖強調“墮胎是故意殺害一個無辜的‘人’”,但其中的“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而不是“person”,即指人類存有或生物的人而不是位格或社會的人。
筆者認為,關于胎兒的道德屬性的界定,不能僅僅以時間來衡量,還必須考慮到空間上的差異。例如,一個孕35周的胎兒,如果存在于母體的子宮之中,就只能稱之為胎兒,不是現實意義上的人。但是,如果早產或人為地將其從母體中取出并放在保溫箱中,它就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因為它已經進入了經驗的世界和社會化程序,能夠扮演特定的社會角色,形成了現實的對象性關系,實現了種生命的類化,具有了類生命的特征。事實上,僅就其剛剛從母體娩出的瞬間而言,它在生物學組成、生理機能、意識狀態等方面與娩出前并無顯著的差異,只是存在空間和存在方式的不同。這表明,人的生命不僅具有時間性,也具有空間性,生命通過存在于時間、空間之中的身體等現象表現出來。正如蘭賽(Paul Ramsay)所說:“作為一個有靈魂的身體,我們的生命具有身體的外形和軌跡。”[7]
因此,對胎兒的道德地位、胎兒是不是人的判斷不能僅僅從時間上來考慮,空間判斷有著特定的意義和價值。可以說,正是空間的變換,種生命才開啟了類生命的社會化進程,肉體才獲得了身體的意義,胎兒才成為嬰兒并標志著新生命的誕生。
3 無心之身的生命:以植物人為例
種生命是類生命的實體依托,心靈、意識是類生命的策動之源。就類的屬性而言,心靈、意識是類生命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之一。但面對多樣化的、不同生命質量的個體,如何評判其地位和意義?僅有種生命而沒有自我意識的個體是否為人?例如,植物人的大腦皮層功能嚴重受損,認知能力完全喪失,除具有一些本能性的神經反射和物質能量代謝外,無任何自主活動,處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狀態。這樣的人是否還具有人的生命?如何判斷其作為人的道德地位?
按照笛卡爾的二元論,植物人是一個沒有理性、心靈和理智的不能思維的身體,更不用說擁有尼采所強調的權力意志。它僅僅是一個具有廣延性的“機械結構”,是沒有生命的“尸體”,稱不上能夠“我思”的、具有生存意志或權力意志的人。辛格與此持一致的態度,并否定了植物人生命的內在價值,他在《實踐倫理學》中指出:植物人“沒有自我意識、理性和自主,因此,對生命權和尊重自主的考慮就不適用于他們。如果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經驗,那他們的生命也就沒有內在價值。他們生命的航程已經終結。他們在生物學的意義上還活著,但在傳記意義上已經死去”[8]。而邱仁宗先生則從意識能力的角度否定了植物人作為人的生命的存在,他認為:“一個已經不可逆昏迷的人,或者腦死亡,或者處于永久性植物狀態的人,他們也具有所有的人類基因組,并且有一個人體,但也不是‘人’。”[9]顯然,以上觀點均將理性、意識、自主當作了評判人的必要條件或生命內在價值的依歸,而否定或淡化了軀體中本能性的神經反射如咳嗽、噴嚏、打哈欠以及呼吸、心跳、物質能量代謝等在對人進行道德判斷中的價值,更沒有兼顧到伊德、梅洛·龐蒂所強調的涉身主體的意義。在梅洛·龐蒂看來,笛卡爾二元論背景下的“身體”及其各組成部分與其對象之間只具有外在的機械因果關系,其實質是處在機械自然觀的客觀世界中的一種廣延實體,它是建立在機械因果模型下的傳統生理學基礎之上的,在傳統的生理學理論中,身體的“刺激-反應”行為只能用刺激、接受器和感覺之間的機械因果關系來描述,身體被構想為客觀世界中的一個自在對象,并可以從第三人稱視角對身體行為進行外在觀察,此即“對象身體”。梅洛·龐蒂試圖通過“幻肢現象”表明身體并不是純粹客觀意義上的認識對象,他提出了“現象身體”的概念。所謂“現象身體”就是自在存在與自為存在的綜合,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是“在世存在的載體”。現代生理學研究表明,身體并非單純被動地接受外部刺激,也能排斥特定刺激。身體行為并非是單純的機械因果關系,還包含著某種主動性或目的性的成分,身體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主動地加工和選擇刺激,表現出自組織的功能。作為“現象身體”的身體主體與意識主體的根本區別在于其自身不是純粹和透明的,而是曖昧的、含混的。身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二者來自于同一個“形體領域”即活的肉體,它們不是彼此并列且外在聯系起來的實存,相反,它們是彼此交疊和共存,相互糾纏并不可分割地互相連接。事實上,身體本身就是意義表達的能指,身體動作、身體姿勢承載著一種比理性意識更本源的運動意識或知覺意識,這種知覺意識“是通過身體以物體方式的存在”,它不同于作為對象性、反思性意識的“我思”。正是身體提供了人類基本感知的條件,將人置身于世界,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并使之成為世界的中心。
植物人雖然已不具有人的意識和認知能力,但他仍具有人的直觀表象,并且保有著人的基本生命體征如脈搏、呼吸、血壓、體溫等,并且具有人之為人的身體。我們可以否定它作為意識主體的存在,但卻沒有足夠的理由否定它不再是一個身體主體。當一個陪伴植物人的人熟睡在植物人旁邊,難道一個陌生人能區分出二者誰死誰活,或者能說出哪一個是沉睡的人,哪一個是植物人嗎?然而,一個具有認知和分析能力的熟睡的機器人,無論他睡得再深,也無論機器人偽裝得再像,你也不會說機器人是人,也能夠區分出哪一個是人。而做出以上判斷的依據絕不是認知能力和思維,而是其具有直觀表象的身體和基本的生命體征。故而,在判斷生與死的問題上,身體死亡與意識喪失同等重要,傳統死亡標準之所以至今仍被不少人所固守,正是因為它能給人們更直觀體驗的東西。
因此,筆者認為,對人及其生命的理解,不能拘泥于二元論立場,僅僅將其看作活力、機能、功能、精神、思想等,而應從身體理論的視域,將身體作為生命的應有內容。人的生命是人的身體與意識、意志、沖動等精神形態的統一即人本身,生命的結束也就意味著身體的死亡,身體變為尸體。梅洛·龐蒂認為:“身體自身的運動包含著自身進入所詢問的那個世界……每一個世界都對另外一個世界保持開放。”[10]植物人雖因失去意識和認知能力而區別于常人,但也不同于沒有思維、沒有意識、沒有認知能力的動物,更不同于具有思維和認知能力的機器,其身體是文化、權利、尊嚴等社會屬性的載體,具有人的社會關系屬性,是其與他人進行交流、對話的場所。植物人仍然具有人的種生命并扮演著病患、父子等現實的角色關系,不能因為其意識的消失而完全否定其作為人的存在。
意識與意識能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無意識不能作為評判人的標準,否則剛出生的嬰兒、處于全身麻醉狀態的人等都將被列入非人的范疇。筆者認為,“自我意識能力”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概念。新生嬰兒、處于全身麻醉狀態的人等雖然此種狀態下不具有自我意識,但他們有發生或恢復自我意識的能力。自我意識能力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范疇,一個人的能力包括自我意識能力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而且它與科技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無腦兒、植物人等就當下的科技水平而言,已不可能再發生或恢復意識,不具有自我意識能力,但若有朝一日通過大腦移植或修復等技術,植物人能夠恢復意識、無腦兒可以治愈,他們就有可能成為“正常”的人。就自我意識能力而言,胎兒具有發生自我意識的潛能與植物人具有恢復自我意識的潛能是不同的,前者要變成現實需要生殖科學的支撐,后者要變成現實需要臨床醫學的支撐。由于前者還不是獨立的個體,在情感、價值等方面與后者曾經為人且已與社會發生過現實聯系的事實是不同的。前者所具有的種生命與后者所具有的種生命是不等價的,后者是一種類化了的、社會化了的種生命。因此,人工流產與放棄對植物人、深度昏迷者的治療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是不同。但無論如何,不應當否認人類種生命的神圣性,只不過不同狀態的個體的種生命的價值不同罷了。對不同狀態的種生命的價值評估應當從內在與外在兩個方面分析,植物人的種生命的價值并不因其已被社會化而必然大于胚胎的種生命的價值,但也未必小于胚胎的種生命的價值。一個胚胎既可能發育發展成一個健康的有用的人,也可能發育成一個如無腦兒的無用之人。
如果說植物人仍屬人類個體意義上的人,其尊嚴、權利和價值等社會屬性與常人何異?這些問題直接關涉著對植物人的臨床治療態度和治療行為,關涉著植物人的治療意義和治療價值等問題。
按照“理性-尊嚴說”,人的尊嚴源自于人的自主意志和選擇能力。無論“自主-尊嚴說”、“道德自主-尊嚴說”,還是“自我目的-尊嚴說”,盡管其主張的內容不完全相同,但都認為尊嚴是以自由意志、理性能力為前提的,奧古斯丁、斯多葛學派、康德等都持有此類觀點。依此,無腦兒、植物人因沒有或失去自由意志及選擇能力,就無人的尊嚴。顯然,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判斷。自主意志、選擇能力雖然影響尊嚴,但并不是人的尊嚴存在的必要條件。人的尊嚴可分為生命尊嚴、社會尊嚴和心理尊嚴,自主意志、選擇能力所體現的僅僅是人的社會尊嚴或心理尊嚴,而生命尊嚴是人所固有的,是人的自然屬性,只要是人類成員,就擁有超越于其他物種的生命尊嚴。德國憲法法院在一項判決中寫到:“有人的生命的地方,就有人的尊嚴;起決定作用的并不在于尊嚴的載體是否意識到這種尊嚴或者知道保護這種尊嚴。從開始便建構在人的存在中潛在的能力就足以對這種尊嚴做出論證。”[11]142依此,只要是人的生命都享有生命的尊嚴,其生命都同樣神圣不可侵犯,植物人作為人的生命的存在,與常人一樣擁有生命的尊嚴。尊嚴與生命并不是直接同一的,生命尊嚴僅僅是人的尊嚴的最基本的方面。已逝者雖不再擁有生命和生命的尊嚴,但不等于無尊嚴,其榮譽、名譽等社會尊嚴依然存在。人的社會尊嚴、心理尊嚴會因人的社會地位、角色權利、心理感受而不同。同樣,生命尊嚴也有大小、高低之別,受生命狀態、生命質量、生命價值的因素的影響。“早期胚胎與胎兒、潛在的人與現實的人、健康的人與生命末期的人等,由于其扮演的角色及承載的義務不同,其生命權大小也不同。”[11]142早期胚胎與胎兒,雖然具有人的基因組甚至人的種生命,但還不是一個獨立狀態的人,尚不具有人的生命尊嚴。尊嚴作為一項權利,“這項權利的載體卻又不像生命權利的載體那樣廣泛。如胚胎或胎兒,雖然享有生命權,但因感受不到侮辱,故無法享有尊嚴權……尊嚴這項權利并非為所有人類生命形式所享有,就像選舉權的擁有必須是以一定的認知能力為前提條件那樣”[11]160。尊嚴是人維護自我的獨特性、相互關懷、避免侮辱的權利,它源自人作為人所內存的規定性及其基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一個罹患絕癥生命垂危而又痛苦不堪的人,雖然其生命的尊嚴依然存在,但因痛苦的感受和對醫療器械的依賴,其心理尊嚴無疑會受到損害,植物人盡管感受不到自己尊嚴的損害,但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即社會尊嚴可能會有所改變。我們雖然不能將人的生命價值與生命尊嚴劃上等號,但人的生命價值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他人對其生命尊嚴的道德判斷。由于植物人已失去自我意志和意識,失去了對尊嚴的內心感受,已無其內在的目的和價值,更不可能再為家庭、他人或社會創造外在的價值,如果此時仍繼續對其進行無意義的救治,在身體上插滿胃管、尿管、氧氣管等異物,不僅是對其身體主體的粗暴干預,也是對其社會尊嚴、形象的損害。因此,在現有的醫學技術條件下,筆者贊同放棄對植物人的救治,但這并不意味著植物人不再是人或已經死亡,而是因為繼續救治已不可能提升其生命尊嚴和心理尊嚴,放棄治療更有助于留下其曾有的健康形象、聲譽和價值,維護其社會尊嚴。同樣,對于腦死亡患者,盡管其心跳、呼吸等生命體征可能會短暫地持續,但已經臨床判定、神經腦電確認試驗、自主呼吸激發試驗等加以判定,其種生命就不可逆轉,其類生命也將隨著種生命的終止而消失。即使心跳、呼吸尚在進行的那一刻,其身體反射包括植物人所具有的膝跳反射等功能亦不復存在,作為身體主體業已死亡,身體已成為尸體,繼續救治更無益于其生命尊嚴和社會尊嚴的捍衛。當然,作為人的社會尊嚴并不因種生命和類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其曾經的名譽、聲望、貢獻等仍應得到與生前一樣的保護和尊重。
總之,人的生命是種生命與類生命的統一,需要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來界定,應當有身體的在場。意識與人并非是直接統一的存在,對人及其生命的詮釋關涉著生命倫理的本原性問題,影響著胚胎、無腦兒、植物人等生命個體道德地位的厘定及其處置方式,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