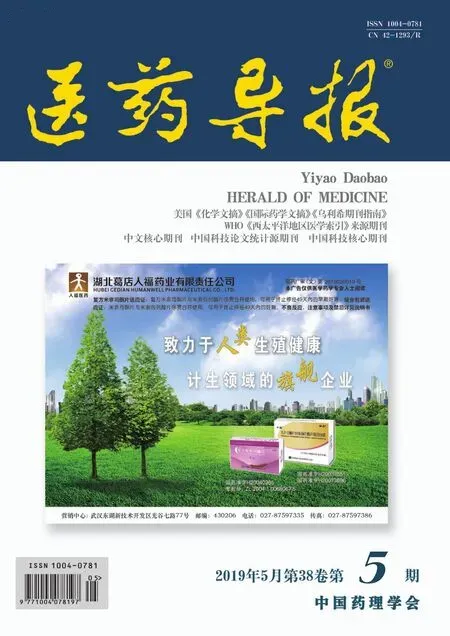替加環素臨床應用剖析*
肖婷婷,肖永紅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感染性疾病診治協同創新中心,杭州 310003)
細菌耐藥已經成為全球嚴峻的公共衛生挑戰,尤其是泛耐藥的肺炎克雷伯菌、鮑曼不動桿菌等,臨床對這類細菌感染缺乏有效的抗菌藥物[1-2]。2017年2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了目前急需新藥研發的20種耐藥細菌清單,如碳青霉烯類耐藥腸桿菌科(Carbapenem-resistantEnterobacteriaceae,CRE)。
替加環素(tigecycline)作為一種新型甘氨酰環素類抗菌藥物于2005年6月被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批準上市,用于治療成人復雜性腹腔感染和復雜性皮膚及皮膚軟組織感染,2008年批準用于治療社區獲得性肺炎[3]。目前全球共有50多個國家批準和上市了替加環素。替加環素于2011年末在中國批準上市,用于3個適應證[4]。但是基于體外抗菌活性結果,替加環素也被廣泛用于治療多重耐藥菌(MDR)引起的醫院內獲得性肺炎(hospital acquired pneumonia,HAP)、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VAP)和血流感染(bloodstream infection,BSI)等[5-6]。這些臨床應用大多屬于超適應證使用,缺乏嚴格的臨床研究結果支持,無法證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相反,近年來部分文獻報道,替加環素的應用會增加這些感染患者的病死率[7-8]。替加環素作為新一代抗菌藥物給患者帶來希望的同時又有些困惑,筆者將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歸納整理,關注替加環素的相關作用機制、藥動學/藥效學(PK/PD),客觀分析其臨床療效及安全性,為臨床合理應用替加環素提供參考依據。
1 抗菌作用與耐藥現狀
作為一種廣譜抗菌藥物,替加環素對革蘭陰性需氧菌如腸桿菌科細菌、大多數革蘭陽性需氧菌包括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厭氧菌和非典型病原體均具有較好的體外抗菌活性[9]。替加環素主要作用機制類似于其他四環素類藥物:通過與核糖體30S亞基結合并阻止氨酰化tRNA分子進入核糖體A位,抑制細菌蛋白質翻譯(肽鏈延長)。初期的研究提示替加環素作為在米諾環素9位分子上添加叔丁基甘氨酞胺基團而衍生的一種新型四環素類抗菌藥物,與其他四環素或抗菌藥物不易產生交叉耐藥,能夠克服或限制核糖體保護和外排泵這兩種四環素耐藥機制[10]。
隨著替加環素的臨床利用逐年增加,世界范圍內革蘭陰性菌中替加環素耐藥逐漸發生并呈增加趨勢,常見于鮑曼不動桿菌、腸桿菌科細菌[11]。PFALLER等[12]收集了2016年來自亞太地區(3443株分離株)、歐洲(13 530株分離株)、拉丁美洲(3327株)的33 348份非重復菌株,進行替加環素耐藥監測,結果顯示CRE對替加環素的耐藥率為2%,碳青霉烯類藥物不敏感鮑曼不動桿菌對替加環素的耐藥率高達25.6%。
細菌對替加環素耐藥主要有以下4種機制[13]:①RND型外排系統過表達,腸桿菌科主要是ramR失活和ramA上調的突變引起AcrAB外排泵活性增加,導致替加環素抗性;鮑曼不動桿菌adeS和adeR基因的點突變或者在adeS 基因前插入序列ISAba1,引起AdeABC外排泵過度表達,導致鮑曼不動桿菌對替加環素敏感性下降。②核糖體蛋白結構變化,如核糖體蛋白S10結構的變化可引起鮑曼不動桿菌、糞腸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對替加環素敏感性下降。③細菌細胞膜的改變,如替加環素耐藥的大腸埃希菌中發現了脂多糖中核心多糖生物合成途徑的相關基因(lpcA、rfaE、rfaD、rfaC和 rfaF)的突變。④各種酶類,如RecA蛋白酶、甲基轉移酶等;在替加環素不敏感鮑曼不動桿菌中亦檢出tetX1基因編碼的依賴黃素的單加氧酶TetX,后者可羥化替加環素,從而產生耐藥。
2PK/PD
替加環素靜脈注射后呈線性PK特點[14]。在健康受試者的I期臨床試驗中,推薦劑量為首劑靜脈注射給予100 mg,后每12 h(q12h)50 mg續注。替加環素峰值血清穩態濃度(Cmax)可達(866± 233)μg·L-1,半衰期為37~67 h,血藥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AUC) 為300~580 μg·h·L-1。替加環素具有良好的組織穿透力,能廣泛分布于身體各組織器官,其穩態分布容積約為7.2~8.6 L·kg-1。研究表明,替加環素在肺、骨骼、肝、脾、腎和皮膚等部位有較好的分布[15]。藥物主要通過膽汁/糞便排泄消除[16]。其總劑量的22%以原型經尿液排泄代謝產物,腎功能不全(包括血液透析)患者無需調整劑量;但建議在嚴重肝功能障礙(Child Pugh C)患者中需要調整劑量(首劑100 mg后維持劑量為25 mg,q12h),并密切關注后續情況。
替加環素與華法林合用時會降低后者的清除率,故需監測凝血酶原時間,并進行抗凝檢測。與地高辛聯用時兩者劑量均不需調整。替加環素不抑制以下6種細胞色素P450(CYP)的亞型:1A2、2C8、2C9、2C19、2D6和3A4,與此相關藥物不會影響替加環素的清除。目前未報道替加環素具有明顯的藥物相互作用,體外研究顯示替加環素與其他常用抗菌藥物之間沒有拮抗作用,并顯示出與某些抗生素可能具有協同作用,如替加環素聯合阿米卡星對40%~100%腸桿菌屬、肺炎克雷伯菌、變形桿菌屬具有的協同作用[17]。
替加環素屬于時間依賴性抗菌藥并且有較長的抗菌藥物后效應,因此AUC/MIC常作為替加環素療效評價的PK/PD指標。BHAVNANI等[18]研究結果顯示,替加環素fAUC0-24 h/MIC與臨床療效和微生物根除率有關。當fAUC0-24 h/MIC>0.9時,78%的HAP能取得滿意的臨床療效;當fAUC0-24 h/MIC>0.35 時,77.8%的患者感染部位的微生物根除率高。但其常規劑量所能達到的最大穩態血藥濃度遠低于常用的試驗藥敏折點標準(≤2 mg·L-1),且其為抑菌劑,可導致細菌的不完全清除,從而造成臨床療效不理想。
有關兒童的PK/PD研究較少,一項納入58例年齡為8~11歲的嚴重感染患兒接受替加環素多劑量梯度(0.75,1.00,1.25 mg·kg-1,q12h,最大劑量不超過50 mg)的II期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提示替加環素劑量為1.2 mg·kg-1,q12h可至適當的AUC/MIC水平,從而達到理想的治愈率[19]。
3 臨床研究現狀與挑戰
3.1替加環素抗耐藥菌作用 目前,替加環素主要被用于多重/泛耐藥(MDR/XDR)菌株感染的患者群體中,如產碳青霉烯酶的肺炎克雷伯菌、產I型新德里金屬β-內酰胺酶菌、碳青霉烯類耐藥鮑曼不動桿菌感染等,屬于超適應證使用,大多缺乏嚴格臨床研究依據。
3.1.1CRE感染 CRE存在多種耐藥機制,對臨床常用抗菌藥物廣泛耐藥,常常僅對多粘菌素和替加環素呈現較高體外敏感性[20]。有多篇臨床研究表明替加環素與其他抗菌藥物聯合治療產碳青霉烯酶細菌感染有一定療效,NI等[21]系統性評價了26項臨床研究,發現替加環素組在總死亡率方面與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3),亞組分析顯示接受替加環素聯合治療的患者30 d死亡率明顯低于接受單藥治療(P=0.03)和其他抗生素治療方案的患者(P=0.01);此外,對重癥監護室(ICU)患者病死率而言,大劑量替加環素方案與標準劑量方案顯著不同(P=0.006);研究結果表明,替加環素治療CRE感染的療效與其他抗生素相似,替加環素聯合治療和高劑量方案可能分別比單一療法和標準劑量方案更有效。同時也有報道稱替加環素單藥治療CRE所致嚴重感染的療效差,患者具有較高的死亡風險,可能與其不理想的藥動學特征有關[22]。因此,FDA不推薦常規使用該類藥物,只有當細菌幾乎全耐藥時,可基于其體外敏感性,推薦與多黏菌素類、碳青霉烯類或氨基苷類等聯合應用[3]。
3.1.2多重/泛耐藥鮑曼不動桿菌(MDR/XDRAB)感染 2016中國CHINET監測提示鮑曼不動桿菌碳青霉烯耐藥率接近70%,泛耐藥鮑曼不動桿菌達到18.7%,后者僅對替加環素或者多粘菌素敏感率較高[20]。王佳等[23]納入10篇關于替加環素聯合頭孢哌酮/舒巴坦鈉治療MDR/XDRAB所致的肺炎療效的隨機、對照試驗(RCTs),結果顯示替加環素聯合頭孢哌酮/舒巴坦鈉組明顯高于單用頭孢哌酮/舒巴坦鈉組;聯合用藥組細菌清除率也顯著高于單用頭孢哌酮/舒巴坦鈉組。同時需注意替加環素耐藥鮑曼不動桿菌也日益增多,其耐藥機制主要是AdeABC外排泵系統的過度表達。目前認為替加環素聯合治療方案是治療替加環素耐藥鮑曼不動桿菌的主要選擇,LI等[24]進行了1159株菌株的Meta分析得出,替加環素與多粘菌素、阿米卡星等體外聯合藥敏及時間殺菌曲線提示聯合用藥對于耐藥菌株具有一定的殺菌作用。國內對于多重耐藥革蘭陰性菌感染治療的專家共識中認為對于MDR/XDRAB感染可選用替加環素,但建議聯合用藥[25]。
3.2替加環素已經獲批的適應證臨床研究現狀 替加環素國內已獲批準的適應證包括:18歲(含)以上由敏感菌株引起的成人復雜性腹腔內感染(complicated intraperitoneal infection,cIAI)、18歲(含)以上由敏感菌株引起的成人復雜性皮膚和皮膚軟組織感染(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oft tissue infections,cSSSI),社區獲得性細菌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bacterial pneumonia,CAP)。治療cIAI及cSSSI推薦療程5~14 d,治療CAP推薦7~14 d;實際療程應根據患者的臨床感染的嚴重程度及部位和細菌學進展情況而定。
3.2.1cIAI cIAI常由多種細菌尤其是耐藥菌引起,臨床常給予患者廣譜抗生素治療。國內外已在替加環素治療成人cIAI進行了數個多中心的隨機雙盲的臨床研究,提示替加環素與亞胺培南/西司他丁治療效果相似,并且在單病原體和多病原體感染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6-27]。陳昭燕等[28]對5項共計4185例患者的關于替加環素對比IMI/CIS治療復雜腹腔感染的隨機對照試驗分析,發現TG并不比IMI/CIS顯著提高cIAI臨床療效,但增加了胃腸道不良反應與二次感染的發生率。2017年美國外科感染協會修訂了腹腔感染治療指南指出[29]: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建議使用替加環素進行經驗性治療(1-B級);如果是耐藥菌感染的成年患者,無敏感藥物的情況下可考慮使用含替加環素的聯合治療方案(2-B級)。綜合國內外研究成果發現,發生cIAI時,應優先選用敏感藥物,如碳青霉烯類等廣譜抗生素,若無敏感藥物可選時可選擇替加環素治療。
3.2.2cSSSI cSSSI常需外科手術治療,目前常規抗生素治療方案為萬古霉素和氨曲南聯用。ELLIS-GROSSE 等[30]對cSSSI住院成人患者進行的兩項III期雙盲研究,結果顯示不良事件相似,替加環素組惡心和嘔吐反應發生率增加,萬古霉素-氨曲南組皮疹出現率高和肝轉氨酶水平升高;替加環素單藥治療與萬古霉素-氨曲南組合治療cSSSI患者一樣安全有效。但LAUF 等[31]的III期隨機雙盲試驗納入了糖尿病足患者944例,分為TG組(每日大劑量靜脈注射替加環素150 mg)與厄他培南組(每日靜脈注射1 g或聯合萬古霉素),兩組治愈率分別為77.5%和82.5% ;合并骨髓炎的糖尿病組患者中,TG組治愈率低于36%,且胃腸道不良反應發生率高,其可能與療程不足有關。
3.2.3CAP DARTOIS等[32]對574例成人CAP隨機雙盲對照的III期臨床研究結果顯示,替加環素組與左氧氟沙星組的療效接近。對兩個CAP感染臨床試驗組的患者進行分析發現,替加環素fAUC0-24 h/MIC≥12.8組的HAP患者臨床療效好(退熱更快)(P=0.05);同時多變量邏輯回歸模型證明替加環素AUC高于閾值6.87 mg·h·L-1和女性是惡心或嘔吐等不良反應的危險因素(P=0.004)[33]。2016年中國CAP指南中指出應根據患者年齡、疾病嚴重程度及藥物敏感性等綜合評估,選擇恰當的抗感染藥物;替加環素可作為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腸桿菌科、高產AmpC酶腸桿菌科、產碳青霉烯酶腸桿菌科以及不動桿菌屬的次選抗感染藥物[34]。
3.3替加環素超適應證應用研究 由于替加環素具有廣譜的微生物覆蓋性,體外藥敏試驗常呈敏感,故臨床仍用其來治療泛耐藥菌引起的各種感染,如HAP、VAP和嚴重復雜性難治性艱難梭菌性腸炎(severe complex and refractory clostridium difficile enteritis,sscCDI)。但有關臨床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國內外指南的推薦也存在差異。
3.3.1HAP/VAP HAP患者中最常見的病原體是鮑曼不動桿菌、大腸埃希菌、銅綠假單胞菌和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了提高臨床治愈率并降低病死率,在HAP管理指南中強調了恰當的廣譜抗生素治療的重要性。目前關于替加環素治療HAP的療效仍具爭議。 2010年9月FDA發布了安全公告,指出HAP患者替加環素治療組病死率上升。PRASAD等[35]對13篇臨床研究分析發現,替加環素會增加患者病死率[風險差異(RD)0.7%;95%CI(0.1%,1.2%);P=0.01]和非治愈率[RD2.9%;95%CI(0.6%,5.2%);P=0.01]。隨之2013年9月,FDA要求替加環素說明書添加黑框警告,不推薦常規使用該類藥物治療HAP,只有當細菌幾乎全耐藥時,可基于替加環素具有較高的體外敏感率,推薦與多黏菌素類、碳青霉烯類或氨基苷類等聯合應用[3]。2018年AMBARAS等[36]綜述了IDSA/ATS 和JAID/JSC等相關指南,表明對于早發性HAP / VAP,經驗性治療應從窄譜抗生素如青霉素類或頭孢菌素類開始,而對于遲發性HAP/VAP,指南建議使用更廣譜的經驗性抗生素,如碳青霉烯類和氨基苷類。2018年中國成人HAP/VAP指南中將替加環素推薦作為HAP中MDRAB和CRE感染的主要藥物之一[37]。
3.3.2sscCDI sscCDI的治療方案包括口服萬古霉素、非達霉素或者聯合萬古霉素口服與甲硝唑靜脈注射。替加環素對于艱難梭菌體外抑菌效果好,并通過糞便排泄,多篇案例文獻報道了替加環素單一或聯合可用于sscCDI,但效果仍未確定。2014年歐洲臨床微生物學和傳染病學會和2016年澳大利亞傳染病學會CDI指南將替加環素列為嚴重病例的三線治療藥物[38-39]。BISHOP等[40]對澳大利亞某一醫院2013—2016年13例患有sssCDI并接受了替加環素治療的患者(在兩個情況下使用替加環素聯合治療:①腹腔感染或者全身感染需要抗生素治療的嚴重CDI患者;②需入住ICU的嚴重復雜疾病患者)進行評價,30 d 總體的全因死亡率為8%(嚴重CDI者無病死,嚴重復雜性CDI患者病死率為25%),77%患者實現了臨床治愈;從而認為替加環素在嚴重CDI中作為聯合治療的是安全有效的,并且可早期給予。目前替加環素單一或者聯合用藥治療嚴重復雜性難治性艱難梭菌性腸炎的有效性以及用藥時機仍未確認,故需要大型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進行評估;另外,替加環素本身導致CDI發生的情況也需要加以考慮。
3.3.3血流感染 無論是動物實驗或是臨床個案報道,替加環素治療BSI的療效結果不一。 WANG 等[41]進行了替加環素治療血流感染療效的系統評價,發現替加環素的全因病死率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85,95%CI(0.31,2.33),P=0.745];替加環素單藥治療組的病死率與替加環素聯合治療組(6項研究,250例患者)相比,OR為2.73,95%CI(1.53,4.87),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中5項研究共報告了398例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患者,其替加環素治療組的病死率明顯低于對照組。QURESHI等[42]使用替加環素聯合其他抗菌藥物治療產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菌血癥,單用與聯合用藥組28 d病死率分別是57.8%和13.3%(P=0.02)。然而,多數臨床研究仍報道了替加環素會增加了感染患者的總體病死率,可能與藥物血藥濃度低、患者病情嚴重等因素有關。CHENG等[7]報道了在替加環素MIC>2 mg ·L-1的MDRAB血流感染亞組中粘菌素-替加環素組14 d病死率超過了粘菌素-碳青霉烯組[(OR=6.93,95%CI(1.61,29.78);P=0.009]。XIAO等[43]回顧分析了370例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發現替加環素組30 d病死率明顯高于非替加環素組(51.2%和12.2%;P<0.001),同時多因素分析顯示感染后替加環素的使用是患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且OR高達2.300。上述研究結果與2010年FDA就靜脈內注射替加環素的安全性發布說明相符,其指出當患者出現嚴重感染時應考慮選擇其他藥物來代替替加環素[3]。目前治療嚴重耐藥菌BSI缺乏有效抗菌藥物,本品與粘菌素聯合治療是否可能是治療BSI的選擇值得研究。
3.4替加環素臨床療效不滿意的可能原因
3.4.1替加環素治療劑量 隨著多重耐藥菌感染的出現,越來越多的臨床案例提示按照替加環素說明書推薦給藥方案無法達到預期的治療效果。替加環素在血漿濃度較低,常規用藥后其峰濃度(0.87 mg·L-1)甚至低于腸桿菌、不動桿菌或厭氧菌的MIC值(2~4 mg·L-1)。為此,大劑量方案可能比小劑量方案更有效。對于傳統劑量的替加環素未能治愈感染的患者,常常需增加劑量,這也是近期中國專家共識中推薦的方法[24]。然而,目前支持大劑量替加環素方案對治療有效的臨床證據仍有限。JEFFREY等[44]對34例患者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替加環素療效評估,發現每日一次大劑量替加環素治療MDR革蘭陽性/陰性病原體以及艱難梭菌引起的嚴重全身感染非常有效。同時,也有部分研究顯示大劑量方案也無法提高療效。DE PASCALE等[45]研究了大劑量(4例替加環素單藥和29例聯合)和標準劑量組(6例替加環素單藥和24例聯合)治療多重耐藥菌感染,兩組病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2.25;95%CI(0.52,9.63)]。
3.4.2單一用藥或聯合用藥 就替加環素療效是否與單一用藥有關方面也有爭議。GOMEZ-SIMMONDS等[46]回顧性地分析了2006—2013年美國紐約市兩家醫院141例碳青霉烯類耐藥肺炎克雷伯菌BSI,發現單一用藥與聯合用藥患者病死率無明顯差異(P=0.4)。KENGKLA等[47]對2529例MD/XDRAB感染患者的29項研究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雖然各治療方案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是使用粘菌素、舒巴坦和替加環素的三聯療法具有較高的臨床治愈率。對此,國內對于多重耐藥革蘭陰性菌感染治療的專家共識建議[24],不推薦替加環素單藥用于多重耐藥菌血流感染的治療,但可聯合用藥或提高劑量來治療嚴重感染,如成人cIAI、HAP和VAP等。
4 結束語
替加環素是一種廣譜抗生素,體外對大部分革蘭陽性需氧菌、革蘭陰性需氧菌、厭氧菌和不典型病原體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具有較長的半衰期和廣泛的組織分布。已經獲批的適應證包括:cIAI、cSSSI和CAP,但基于其本身藥學屬性和臨床研究,大多數國內外指南也不推薦其作為一線治療藥物。對于泛耐藥細菌所導致的HAP/VAP、BSI等,已經進行了大量的臨床觀察,但效果尚不確定,該藥物相關的總病死率增加的現象仍然是一個問題,故在重癥耐藥菌感染,不推薦作為一線治療藥物,只有在缺乏有效藥物情況下作為備選治療方案,且需要進一步研究用藥劑量、聯合用藥等有關問題,確保患者治療有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