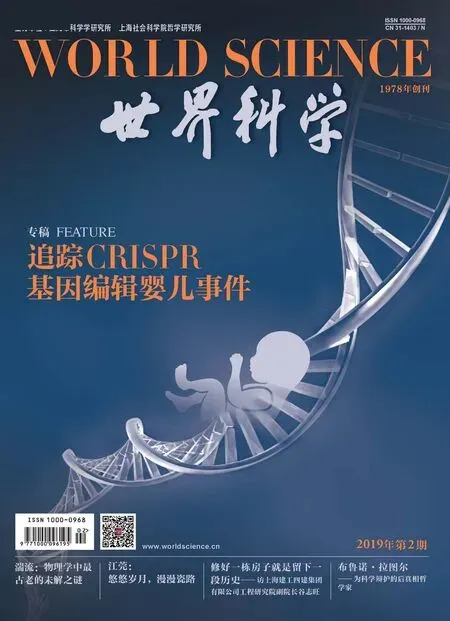“設計細菌”:下一個流行性傳染病或源自實驗室
編譯 費文緒

2 018年12月的第一周,世界各國外交官在瑞士日內瓦集會,這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WC)締約國年度會議的一部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有一條重要的訓令:禁止簽字認可該公約的182個締約國發展、生產和貯存生物武器。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以及廣大生物安全共同體,更關注有明確可能性被用作生物武器的現有病原體,比如炭疽桿菌、肉毒桿菌和Q熱(編者注:由伯納特立克次體引起的急性自然疫源性疾病)致病菌。此外,健康安全專家還擔心下一個全球流行性傳染病的暴發。
流行性傳染病通常是人畜共患的,例如,埃博拉(Ebola)、寨卡(Zika)、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全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癥,SARS)和艾滋病(HIV)等。
這樣的傳染病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發性基因突變和環境因素。所以,產生了這樣一個令人膽戰的想法:也許未來的流行性傳染病不取決于不同動物物種的偶遇和偶發的基因突變,而可能是人為設計出來的。合成生物學領域的新工具賦予了科學家超越自然選擇,徑直設計和制造出最危險病原體的可怕能力。
這一威脅一直縈繞于管理安全的官員的腦海。2018年5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CHS)組織美國前參議員和行政管理人員參與了一場演練,模擬國家應對生物工程病原體的國際性大暴發。在虛擬情境中,一個恐怖分子團伙創造了一種既致命又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這一人為制造的流行性傳染病暴發一年多后,全世界的死亡人數激增到1.5億人,道瓊斯指數下跌了90%,城市騷亂,大規模的難民處于饑荒中。
過去幾十年里,生物技術飛躍發展。僅僅在75年前,我們甚至還不確信DNA是決定基因遺傳的主要物質。時至今日,我們已能夠越來越容易地讀寫和編輯基因組。
但是,生物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為善,也能作惡。生物技術的進步使得越來越多翻天覆地的巨變成為可能,我們擔心只需現有的技術工具,就能人為制造出流行性傳染病,進而造成新的巨變。足夠有能力的肇事者可以復活過去最致命的病原體,比如天花病毒和西班牙流感病毒,或者修改禽流感病毒等現有的病原體,使其更具傳染性和致命性。隨著基因工程技術變得更強大,進行此類修改將變得更容易。
這樣的“恐怖幽靈”有意(或無意)地對病原體進行基因工程改造,就可能造就比歷史上最致命的流行性傳染病更惡劣的傷害。沒有明顯的物理或生物約束來預防這樣強危險性的生物武器。據生物安全專家皮爾斯·米利特(Piers Millett)稱:“如果你試圖創造致命的、容易傳播的病原體,而又沒有恰當的公共衛生措施來緩解疫情,那么,你所創造的是這個星球上最危險的東西之一。”
緩解這種生物安全風險,正成為21世紀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不僅因為風險很高,而是因為我們和解決方案之間存在無數障礙。
幫助我們的技術也可能傷害我們
曾經發生的流行性傳染病相當恐怖,讓我們猝不及防。比如,美國官方記錄的首例艾滋病于1981年出現3年后研究人員才確定病因是艾滋病病毒。又過了3年,首個治療艾滋病的藥物才被研制出來并獲準使用。現在,盡管抗逆轉錄病毒治療使得那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能夠有效應對這一疾病(前提是,如果他們能夠負擔得起昂貴的治療費),我們仍然缺乏一種艾滋病疫苗。
實際上,我們抗擊新出現的自然疫源性病原體的裝置很差,比這更糟糕的是,我們更沒有準備好應對生物工程病原體。未來幾十年,人類有可能創造出這樣的病原體,它們恰好在現代醫學能夠發現、治療和遏制的傳染病原體范圍之外。
更糟糕的是,圖謀不軌者可能會有計劃地打造能擊敗現有健康防御措施的致病菌。所以,當合成生物學領域的進步,使我們更容易發明抵御流行性傳染病的新療法和其他技術的同時,也可能使得國家和非國家的圖謀不軌者能夠設計危害性更大的病原體。
比如,新的基因合成技術赫然聳現,使得通過拼接并自動生成更長的DNA序列成為可能。這將給基礎和應用生物醫學研究帶來裨益——但是同時,它也將簡化病原體設計。

2017年8月15日,美國猶他州達格威,一名專家在美軍達格威試驗場的智能實驗室。工作人員在此地處理一些地球上最致命的病原體
與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相比,生物工程病原體的資源密集型程度更低。盡管圖謀不軌者目前可能需要大學才擁有的實驗室和資源,方能制造生物工程病原體,一個更大的障礙往往是信息的獲取。一些信息,像如何熟練地使用某個特定的儀器或是細胞類型,只能通過數月乃至數年在導師指導下的科研訓練才能獲得。但其他信息,像病原體基因組序列的注釋,可能通過公共數據庫就能輕易獲得,比如通過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運營的那些數據庫。
如果像病原體基因組序列或合成生物學協議類似的信息可以從網上獲取,那會使得圖謀不軌者輕易構造出病原體。但是,即使這些信息不上網,黑客照樣可以從生物技術公司、大學和政府實驗室的數據庫中竊取敏感信息。
稍有閃失,只需一個有足夠專業背景的恐怖分子團伙或是一個無賴的國家就能制造大規模的騷亂,這一事實使得預防生物工程病原體的破壞這件事變得更復雜。即使大多數的科學家和國家遵守協議,但只需出現一位圖謀不軌者,就可能危害人類文明。
而且,一些傷害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從2004—2010年,美國實驗室發生了700多起“選擇性病原體和毒素”遺失或泄露事故。在11起案例中,實驗室員工遭受了細菌或真菌感染。在一個案例中,一貨船的有害真菌遺失,而且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稱,在運輸過程中已被毀壞了。無意但有時粗心的生物學家正在實驗室創造危險的微生物,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這樣意外的泄露事故甚至可能造成駭人的后果。
一個全球性問題
像自然發生的流行性傳染病一樣,生物工程病原體無國界。在某個國家釋放的傳染性病原體將會傳播到其他國家。防御生物工程病原體的行動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一個例子——既然一種致命的生物工程病原體將會危及世界各國,那么,采取防范行動是一項造福全世界的事業。
全球公共產品面臨的一個基本挑戰是它們往往很有限。如果可以,各個國家更喜歡免費享用單邊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而不是自己開發。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各國不會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只是各國往往只做不得不做的事。比如,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只會考慮一種生物工程病原體可能對其3.25億國民造成的危害,從而采取相應行動防止危害發生,但是,如果美國考慮的是生物工程病原體可能對全世界76億人口造成的傷亡,那么它應該會采取更廣泛的行動。
為了解決這一困境,20世紀70年代,世界各國領導人締造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公約的重要目標是限制生物武器的發展,但是在實踐中,公約在核查和強制性服從方面是缺乏效力的。
不像《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主要的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條約具有廣泛而正式的核查機制。《核不擴散條約》(NPT)自1970年生效,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約有2 560名員工)核查締約國的履約情況。《禁止化學武器公約》(CWC)自1997年生效,通過禁止化學武器組織(以下簡稱“禁化武組織”)核查履約情況。禁化武組織榮獲了2013年諾貝爾和平獎,有500名員工。相比之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履約核查機構”是該公約的唯一辦事機構,目前只有4名雇員。而且生物武器具有特定特征,相比于化學武器和核武器更難進行核查和強制實施。
讓我們想想核技術,核電站只需低水平的鈾濃縮(一般是5%左右),而核武器要求高濃縮鈾(一般是90%以上)。提煉高濃縮鈾需要精密離心機這種大型工業設施。當獲準訪問時,視察員相對比較容易確定何時某個核設施用于生產高濃縮鈾。
一部分是由于上述這些原因,沒有一個國家在成為《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期間,敢明目張膽研制核武器。在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中,美國、蘇聯(其核武器現在為俄羅斯獨占)、英國、法國、中國,以及以色列(有可能),在條約實施前就擁有核武器。印度(于1974年進行首次核試驗)和巴基斯坦(于1998年進行首次核試驗)從未簽署《核不擴散條約》。朝鮮于2003年退出條約,在2006年,進行了首次核試驗。

2012年9月22日清晨,紐約市賓州車站,由美國生化事故反應部隊(CBIRF,隸屬于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成員領導的一次生物防備演習中,應急人員從一列美鐵列車的過道走下來
史蒂芬·平克認為:“恐怖分子不會把流行性傳染病病原體變成武器,因為恐怖分子一般不是造成損害而是追求戲劇效果。”
相比之下,生物工程微生物所需的資源更少,制備的設施更小,而且更難明確地分辨出正在研發的微生物究竟是用于科學研究,還是心存不良的企圖。
縱觀歷史,《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在防止擁有生物武器方面并沒有創下良好的記錄。蘇聯于1975年簽署公約后,依然堅持開展一個大型的生物武器項目。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在已經成為締約國期間,于20世紀80至90年代仍然持有生物武器。
美國害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侵入性核查會危及敏感的知識產權,進而削弱美國在尖端生物技術領域的競爭力,其在2001年公約第五次審議大會上選擇退出談判。美國后來又重新加入了這些談判,但是改進公約的核查和強制實施機制的嚴厲舉措并沒有得到執行,談判達成的協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
盡管存在對核查的侵入性的擔憂,越來越多的意見一致認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必須變得更有效。美國生物防御藍帶研究小組2015年兩黨報告呼吁副總統和國務卿主持召開一系列會議,邀請相關內閣成員和專家參加,就核查協議達成共識,使得核查協議既能滿足美國的利益,同時又能足以強制締約方遵守條約。美國生物防御藍帶研究小組的組長是2000年美國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和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時期首任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湯姆·里奇(Tom Ridge)。該研究促成了《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法案(2016)》(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Act of 2016)的引入,該法案至今仍在等待投票。
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發布了《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盡管這份文件很少提及美國將如何強化《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也沒有提及藍帶研究小組的提議——由副總統主持召開內閣級別的會議。
當然,也有人質疑生物武器會造成嚴重的威脅。比如,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認為:“生物恐怖主義可能只是臆想的威脅。恐怖分子不會把流行性傳染病病原體變成武器,因為恐怖分子一般不是造成損害而是追求戲劇效果。”也有其他人認為,即使恐怖分子想要制造一種病原體作為武器,他們也缺少必要的生物學知識和技術來完成這項任務。
雖然事實上(而且相當幸運地)這些因素至少降低了現在發生生物襲擊的風險,但這是于事無補的安慰。未來幾十年,非國家行為者只會變得越來越容易獲得和利用強大的生物技術為非作歹。而且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國家也有造成嚴重風險的可能。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發起了毀滅性的生物戰。日本731部隊在中國投下了裝滿大群感染瘟疫的跳蚤(生物炸彈),很可能殺害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平民。731部隊的指揮官石井四郎發現瘟疫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因為瘟疫本身可以作為一種天然的流行性傳染病,通過人際傳播,可以殺害大量的人。
除此之外,美國開展了一項從1943年持續到1969年的生物武器項目,尤其還制作了宣傳視頻,吹噓在人體上試驗的生物武器。蘇聯在簽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后,仍然繼續實施隱秘的生物武器項目,在20世紀80年代項目巔峰時期擁有的雇員比臉書(Facebook)公司目前的雇員還要多。
當我們談及生物工程病原體可能造成的災難性風險時,很多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回答。比如,導致人類疾病的微生物有哪些?哪種微生物最有可能被用作生物武器?諸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美國非政府組織“核威脅倡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等正在努力回答這些問題。
但是,并不代表我們不知道可能存在的問題,我們就沒有問題的答案,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在預防生物武器風險方面無能為力。
開展全球化思考和行動
首先,我們應該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框架下建立一種機制,來應對生物技術進步。目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缺少一個專門的平臺,供人們探討生物技術的新進展對公約的影響。此外,其他國際協議,比如《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有專門的科學顧問委員會,來跟蹤和應對新的科技變革。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沒有這樣的專門科學顧問委員會。
在這個議題上有一些新進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2018年12月初在瑞士日內瓦舉辦了一場活動,討論《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如何設置,以應對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至關重要的是要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內部建立一個永久的管理機構,來應對生物技術變革。
這全都涉及另一個優先事項:提供《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履約支持機構更多資源。履約支持機構所承擔的責任包括:支持和協助締約國履約,管理一個協助請求的數據庫,促進各方的溝通等。但該履約支持機構僅有4名員工,其所承擔的巨大責任遠遠超出了其現有的能力。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履約支持機構擁有的資源仍然很少,尤其是相比其他國際公約。分配給《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會議及履約支持機構的年度投入,還不到分配給《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年度投入的4.5%。預算不足釋放出一個警示信號:世界目前還沒有嚴肅對待不斷增長的生物武器風險。
另一個全球性的優先事項應該是找到管制善惡兩用的基因合成技術的途徑。生物學家為了方便開展研究,通常從專門從事相關生產的公司訂購定制DNA短片段。2009年,國際基因合成聯盟(IGSC)提出了基因合成公司甄別客戶購買潛在危險DNA片段訂單的準則,比如那些在有害病毒或毒素基因中發現的DNA片段。大多數公司自覺遵守這些準則,這些公司代表了80%的全球市場份額。
然而,即使現在遵守IGSC推薦的甄別程序的基因合成公司,也只能檢測客戶訂購的DNA序列是否與那些已知的病原體匹配。一種攜帶新的基因組的基因工程病原體可能會逃脫這種篩查。
現在,基因合成市場正在國際化地擴張,基因合成成本不斷下降。迫在眉睫的是各國政府既要采取獨立的行動,也要采取多邊的行動,要求基因合成公司對DNA序列和客戶進行適當的篩選。正如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凱文·埃斯韋爾特(Kevin Esvelt)寫道:“對所有合成DNA進行充分的篩查,能夠杜絕生物技術被非國家行為者濫用,進而避免造成嚴重危害。”
應對實地和實驗室的生物風險
除了發展新的全球標準并付諸行動,我們還需要采取更靈活的應對措施,來面對生物工程病原體的威脅。正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最近的一份報告所指出:“應對流行性傳染病(尤其是對于新出現的傳染病)暴發的最大挑戰之一,是通過可靠的診斷分析手段,快速準確地確定感染狀況。”
基于尖端基因組測序方法,能夠診斷出血樣中存在的所有病毒和細菌甚至包括全新的病原體的詳細信息。與此同時,基因組測序技術變得更便宜了,能夠更廣泛地應用于臨床實時研究。
我們還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來研發更廣譜的抗病毒藥物。相比專門針對單個已知病原體的療法,也許這樣的廣譜抗病毒藥物更可能減緩工程菌的擴散。
而且,我們也應該開發能夠進行疫苗快速研發的“平臺”技術。目前,設計、試驗和生產一種預防新病原體傳播的疫苗,需要耗費數年時間。理想的情況是,我們在識別出病原體的幾個月內,就能夠讓所有存在感染風險的個體通過接種疫苗獲得免疫。加速疫苗研發進程,要求我們創造出區別于傳統的新技術,比如,載體免疫預防或核酸疫苗。
即使我們加速這樣的創新性研究,我們也應該謹慎對待自我傷害的可能性。為了防止可怕事故的發生,國際生物醫學界應該在病原體研究方面構建更牢固的防御意識。
現在,職業晉升、經濟回報和原始的好奇心驅使所有層面的生物學家挑戰極限,我們所有人都會從他們的努力中獲益。但是,同樣是這些動機,有時候也會導致研究人員冒很大的甚至可能是不正當的風險,比如發展出危險的更具傳染性的流感病毒株,或是公布培育天花病毒近親的方法。生物學家盡其所能推動一種謹慎、敬畏的文化非常重要,這種文化能夠緩和這種知識分子冒險精神。
鼓舞人心的是,合成生物學的杰出人物——埃斯韋爾特和哈佛大學的喬治·丘奇(George Church)正在倡導這樣一種文化,他們正在開創技術防御工作,以緩解生物工程病原體意外泄露風險,并倡導相關政策和規范,使21世紀的生物學成為危險性更低的科學追求。隨著合成生物學工具擴展到其他學科,其他學科也應該以生物學領域的做法為榜樣。
上文列出的應對方法的前提是,我們需要有一種緊迫感。隨著我們的生物技術能力的增長,生物工程病原體帶來的威脅也會增長。一種生物工程病原體不會以高聳的蘑菇云來宣告它的出現,但是受其感染的個體感受到的痛苦的真實性不會減少分毫。
資料來源 vo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