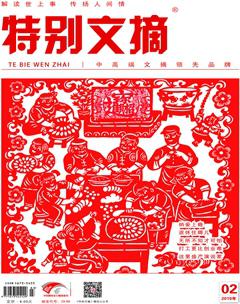“洗腦”廣告
李在磊
“廣告狂人”葉茂中第一次被“洗腦”是在候機大廳。
有一年,在等待航班的間歇,大廳喇叭不停播報找人:“張國榮先生,張國榮先生,張國榮先生,請馬上到登機口登機。”
葉茂中是張國榮粉絲,起身跑過去守株待兔,想一睹偶像風采。沒承想,只等到一個矮矮胖胖的中年男子,行色匆匆趕來。
葉茂中略感失落,怏怏地往回走,三個字徘徊往復,始終揮之不去。打那兒起,他有機會就拖延,等著乘務員吆喝“葉茂中請登機”,“不多喊幾遍不動身”。
此番,他把“機場喇叭”搬到了世界杯舞臺。2018年世界杯鏖戰正酣,葉茂中操刀的“你知道嗎”與“為什么要上馬蜂窩”兩部廣告片以及紅制作操刀的BOSS直聘廣告片,一舉成為熱議焦點,并列世界杯三大洗腦廣告。
綜觀洗腦廣告演化史,產業變遷與媒體迭代共同塑造了廣告業態,表現形式日新月異,但是它的內核始終如一。
招人煩是廣告的特性
“好的廣告從來都不讓別人喜歡,招人煩是廣告的特性。”葉茂中不認為自己的廣告僅僅是洗腦重復,而是高水平的創作,是情緒的遞進。
葉茂中拿過“中國廣告30年突出貢獻大獎”,是頗具傳奇色彩的“營銷大師”。對他來說,評價一個廣告的標準很簡單,就是銷量、點擊量。“我要做的是根據科學的分析,逼著觀眾記住廣告,消費產品”。
但外界對他制作的廣告評價卻更多是“洗腦”“惡俗”,還有網友用溫情脈脈的泰國廣告來與之對比。
葉茂中對此回應稱, “泰國的廣告能夠把亞洲廣告獎全拿了,但是一個能記住的品牌都沒有,那才叫爛廣告”。
一句話流行語
1989年,舞美出身的葉茂中,被分配到泰州電視臺。一家空調廠提著錢找上門,想讓他們幫忙拍攝一部影視廣告,偌大一個單位,沒人拍過這種片,沒人敢接。葉茂中初出茅廬,一口應承下來。不懂就學,當天跑到圖書館,把影視類書籍挨個找出來,一本一本翻,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四點。
這還遠遠不夠,他又跑到上海電影制片廠,跟著專業人士學技術,“臺長說,小葉你就待在那,把片子弄完了再回來。”葉茂中說,最后片子交上去,效果很不錯,廠家支付的那筆經費,剔除各項開支,自己落下1300元,而他當時一個月工資只有100多元,“我就決定,不在電視臺干了,出去賺錢去”。
這個時候,有實力的企業想做廣告宣傳,首先想到的渠道就是電視臺,電視行業的霸主便是CCTV。
1993年,譚希松調任央視廣告部主任,剛剛上班沒幾天,山東一家名叫孔府宴酒的企業,想在《新聞聯播》前頭做廣告,但擔心會有風險,就給企業做工作,把廣告時段挪到了《天氣預報》,“播出之后效果非常好”。
另外一家名叫孔府家的酒廠,很快找上門,也想在同樣的位置打廣告。為了照顧兩家企業的強烈需求,就在天氣預報,劃出同樣大小的畫面,賣給了兩家企業。
“生意好得不得了,年底一算賬,翻倍增長。”譚希松說,兩款酒不是一個工廠兩個牌子,而是分屬兩家企業,都來自山東相鄰的兩個縣,還為爭奪商標權打過官司,可是消費者沒耐心做過多區分,兩家生意都很好,“買孔府家的跑到孔府宴去了,買孔府宴的跑到孔府家去了”。
1994年,越來越多的企業找上門,想在天氣預報上做廣告。廣告部想出投標的方式,解決企業旺盛需求。
《新聞聯播》與《天氣預告》之前沒有廣告時段,譚希松向臺里申請,劃出30秒的時段,后來又增加到1分鐘,公開招標。他們把企業大致劃分為12個大類,制作了12板塊,每個類別的企業進行競爭,價高者得。最高的酒類廣告,一年拍到4000萬元。
一分鐘的時段,被劃分成12個小板塊,這意味著,每一則廣告只有短短的5秒。5秒鐘能講啥,就是企業名字,加上一句話。類似于“維維豆奶,歡樂開懷”“大寶明天見,大寶天天見”這樣的一句話廣告語,開始流行起來。
一句話流行語,成為當時廣告流行模式。在電視臺摸爬滾打過的葉茂中,走過很多彎路才慢慢摸索出一整套話術體系。機緣巧合下,他接拍一單保健品廣告,洗腦才能開始迸發。“怕冷就穿北極絨,地球人都知道”“一年去兩次海瀾之家”“關鍵時刻,怎能感冒”等等耳熟能詳的廣告語創造出來。
(摘自《南方周末》 圖/子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