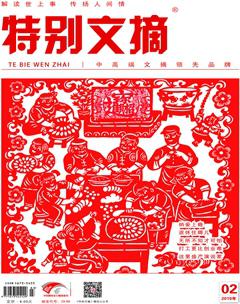心想喜鵲
宋曉亮
兒時,媽讓我猜的頭一個謎語是:“打南邊過來個點頭點,白嗉兒、黑豆眼。”我想都沒想,張口就說:“是喜鵲。”老家那方天地間,可謂盛產喜鵲呀!
愛喜鵲不摻假。“喜鵲叫,好運到。”在我童年的心田里像是刻下了深深的印記。而老家的院墻外,那棵粗壯茂盛的紅杏樹,更為喜鵲們提供了隨時歌唱的“大舞臺”。至今不忘,我5歲那年一個秋高氣爽的清晨,從杏樹上飛下幾只大喜鵲,圍著我家院落一唱再唱。我手舞足蹈地問媽媽,它們在唱什么呀?媽說,來報喜。
我佩服媽媽,她怎么一說一個準兒!到了中午,爹就拿回一封信,拆開一看,我大姐要從大連回來了。獲此喜訊,把我高興得逮誰跟誰說:“我大姐要回來啦!”
自此,喜鵲是喜慶、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也漸漸地變成了我的“心靈圖騰”。
時光荏苒,我長大了,從山東嫁到北京了。感覺中,北京的喜鵲比老家的還要多。日常所見,有灰喜鵲,其顏色藍綠發灰;山喜鵲只是黑白兩色。不管是哪一種,我均視為“山東老鄉”。一聽到它們的叫聲,那份親切、那種興奮,會讓人精神振奮、心情舒暢。
20世紀的80年代初期,在丈夫只身赴美奮斗的日子里,留守北京的我,領著一個小禿小子,若少了喜鵲的叫聲,挨過那孤苦而又漫長的1360多個夜與晝,該有多難!
中國人愿把喜鵲視為吉祥鳥。喜鵲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標志之一。傳說喜鵲文化起源于春秋時代。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美麗的傳說:“牛郎織女七夕天河鵲橋相會”的神話故事,實為婦孺皆知。而那一幅又一幅的“喜鵲登梅”圖,更是“畫遍”了黃河兩岸、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不僅如此,看民間的繪畫、對聯、剪紙、小說、散文、詩詞及歌曲、影視、戲曲等方面,哪個能少了喜鵲的參與?
我定居美國近30年了。在這超出1/4個世紀里,等候喜鵲唱枝頭的記錄至今還在這兒空白著。見不到喜鵲并不影響我想念喜鵲。哪怕是空想,也會讓人懷有美好的期盼與向往。
(摘自《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