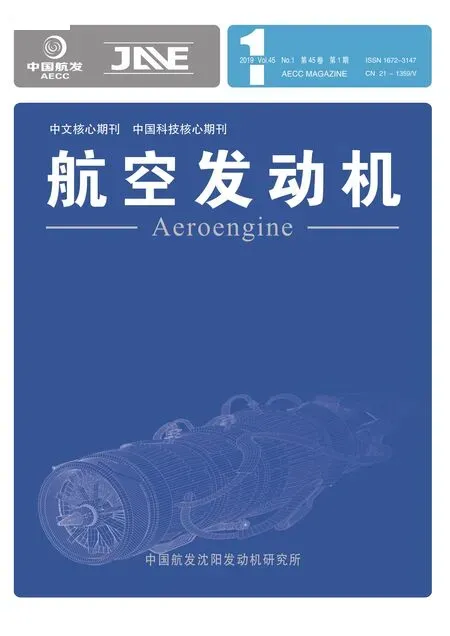考慮徑向摻混的軸流壓氣機通流徹體力模型計算及驗證
蔡北京,胡 駿,郭 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南京210016)
0 引言
20世紀70年代,Smith等[1]在GE公司12級軸流壓氣機試驗研究中發現,在某些級之后出現了重復級流動現象,具體表現為上級靜子葉排出口的氣流角和軸向速度等流動參數經過重復級之后沿徑向的分布趨勢基本保持一致;McKenzie、Cumpsty及Howard等[2-6]先后在其他型號壓氣機中也觀察到這種重復級流動現象;目前,學者們普遍認為重復級流動現象是由壓氣機徑向摻混引起的[7-10]。但對徑向摻混機理的認識存在不同觀點,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不同的徑向摻混模型,如Adkins-Smith[7]和Gallimore-Cumpsty[8-9]模型。Adkins和Smith提出徑向二次流帶來的對流影響是引起軸流壓氣機中徑向摻混的主要原因;Gallimore和Cumpsty則在2臺4級壓氣機上進行試驗,利用示蹤氣體技術驗證了在多級壓氣機后面幾級出現徑向摻混過程的主要機理是隨機湍流擴散過程。這2類模型關于徑向摻混機理的認識不同,但都成功預測了徑向摻混帶來的影響。相比Gallimore-Cumpsty模型,Adkins-Smith模型包含更多的經驗參數,在實際工程應用中受限更大。
本文基于Gallimore-Cumpsty模型的指導思想,利用通流徹體力模型[11],在守恒形式的Euler方程組中添加黏性應力項及熱傳導項,以某4級低速壓氣機為研究對象,分析徑向摻混模型對通流徹體力模型計算結果的影響,并基于試驗測量結果,對模型展開了驗證。
1 計算方法
1.1 控制方程
采用柱坐標系下穩態、軸對稱、帶源項的準3維歐拉方程求解子午面流場。考慮通道主流區氣體沿展向的摻混,根據Gallimore等[9]提出的摻混模型的基本思想,在方程中加入湍流黏性應力及湍流熱傳導項。將葉片力模化為控制方程中的源項,葉型厚度對葉片區域內部流動的影響通過葉型堵塞系數b描述。控制方程最終形式為

其中


本文關于徹體力的計算是基于Marble[12]的思想,將徹體力分解為垂直于相對速度W的非耗散力φ以及平行于相對速度W的耗散力f。耗散力的大小通過熱力學定律由葉片區域當地熵增沿子午面流線梯度確定,非耗散力的周向分量則由軸對稱、穩態周向動量方程確定,隨后依據力與速度的相關關系,確定3個方向的力。由于源項的引入,導致式(1)不封閉,需輸入葉排損失系數ωˉ及落后角δ,并結合當地瞬時流動參數進行求解。通流設計中主要通過進口馬赫數和攻角來關聯ωˉ和δ,具體關聯方法見文獻[8]。
1.2 徑向摻混模型
本文基于Gallimore-Cumpsty模型的指導思想,在守恒形式的Euler方程的基礎上添加黏性應力項及熱傳導項。在該模型中,在計算黏性應力及熱傳導項時保留了分子黏性應力及分子熱運動引起的熱傳導,同時保留了徑向速度梯度值,使其適用于更一般的情況。類比分子黏性系數μl引入湍流黏性系數μt,其確定方法沿用Gallimore-Cumpsty模型中的計算方法,近似認為摻混系數處處相等,即指定μt/ρvzL為常數,L為壓氣機的特征長度,該準則的量級一般在0.005以內。熱傳導系數kl及kt分別通過指定層流普朗特數Prl和湍流普朗特數求得一般取值為Prl=0.72,Prt=0.9。
文獻[13]中關于黏性流體能量方程的描述,式(2)為葉型堵塞系數為1時考慮徑向摻混之后黏性流體的總能量方程。右邊分別為徹體力作功、熱傳導和黏性輸運項。黏性輸運項的存在表明即使沒有徹體力做功項和熱傳導項,黏性流體微團的總焓沿跡線也是變化的,黏性應力能夠在相鄰跡線間輸運能量,但不改變能量的總和,只改變能量在空間中的分布。

2 計算結果及分析
為考核有無徑向摻混對通流計算結果的影響及徑向摻混模型的準確性。本文通過以下2個算例來展開研究:
(1)以無葉長直管道為算例,在徹體力源項為0的情況下,單獨考核湍流黏性擴散對無葉區內流動參數沿展向分布的具體影響;
(2)以某4級低速軸流壓氣機為算例,分析有無徑向摻混項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利用4級壓氣機試驗測量結果,開展本模型的驗證工作,考核本模型的可靠度和精確性。
2.1 無葉直管道算例
為更直觀展示出湍流黏性擴散對流動參數沿展向分布變化的影響,本模型以長直管道為計算對象(如圖1所示,L=12d),有葉區的葉型堵塞系數b=1,葉片徹體力源項F=0。進口給定沿管道高度呈拋物線形式變化的總溫和總壓沿徑向均勻分布,軸向進氣,出口背壓給定80 kPa。進口總溫沿管道高度的變化如圖2所示。通過調節不同的湍流黏性系數μt,考察氣流參數在管道中沿展向分布的變化。分別考核了有摻混和無摻混的區別,即 μt/ρvzL=0,2×10-3的2種情況。
在不同摻混系數下,長直管道進出口截面上總溫、總壓、子午速度等氣流參數沿展向分布的變化對比如圖3所示。當摻混系數值為0時,即不考慮徑向摻混,管道出口氣流參數的分布與進口氣流參數的分布保持一致。當摻混系數值給定為2×10-3時,即考慮徑向摻混的影響,管道出口氣流參數的徑向分布與不考慮徑向摻混相比,沿葉高的分布更加均勻。此外,在有摻混的作用下,管道進出口總溫均值保持一致,只是沿葉高分布發生了變化,表明在湍流黏性應力作用下,沿葉高不同跡線間發生了能量的輸運,但總能量不變。在摻混系數 μt/ρvzL=2×10-3時,管道內氣流參數的徑向分布在不同軸向位置上的變化如圖4所示。0.4L和0.7L分別表示該軸向截面到管道進口距離為0.4倍和0.7倍管道長度,即圖1中的section1和 section2截面。在管道不同位置處,徑向摻混的效果不同,越靠近管道下游,氣流參數沿展向的分布越均勻,徑向摻混的作用越明顯。

圖1 無葉長直管道

圖2 進口溫度沿管道高度的分布


圖3 不同摻混系數下,長直管道進出口氣流參數變化對比


圖4 μt/ρv z L=2×10-3時管道內不同軸向位置處氣流參數的徑向分布
2.2 4級低速壓氣機算例
以某4級低速軸流壓氣機為算例,考核徑向摻混模型對通流徹體力模型計算結果的影響。該4級壓氣機是為了模擬某高壓壓氣機而設計的4級重復級低速壓氣機,該4級壓氣機的試驗臺如圖5所示。采用等內外徑設計,設計轉速為900 r/min,導向器葉片數為60,轉子葉片數為64,靜子葉片數為84,設計流量系數為0.47,設計總壓比為1.065,對該壓氣機進行了詳細的級間流場測量以及設計轉速下總體特性測量,試驗測量的簡要介紹方法參見文獻[14]。
針對該壓氣機建立的計算模型的子午流面網格如圖6所示。為單獨考核徑向摻混模型對計算結果的影響,控制各葉排的落后角及損失系數保持不變,即各葉排落后角參考試驗測量值,損失系數參考文獻[9]的方法,沿徑向分布上采用簡單的拋物線形式分布給定,如圖7所示。

圖5 4級壓氣機試驗臺

圖6 4級壓氣機子午流面計算網格

圖7 4級壓氣機落后角及損失系數給定值
通過給定不同湍流黏性系數μt,研究分析氣流參數在葉片通道中的變化。在 μt/ρvzL=0,2×10-3及 5×10-3,進口總壓為 1.0267×105Pa,總溫為 287.65 K,出口輪轂處背壓為1.072×105Pa工況下,對4級壓機總體特性影響的計算結果見表1。
從表中可見,不同摻混系數對壓氣機總壓比影響較小,等熵效率隨著摻混系數的增大略微降低,主要是因為在無黏歐拉方程中引入摻混項,考慮了黏性力所做的變形功,把流體運動的機械能不可逆地轉換為熱能而消耗,體現了黏性力將機械能耗散為熱能這一不可逆的作用。

表1 不同摻混系數下4級壓氣機總體特性計算結果
有無徑向摻混以及徑向摻混系數對葉排出口流動參數沿葉高的分布有顯著影響。在不同摻混系數下,第1、3級壓氣機出口以及壓氣機管道出口靜溫、總壓以及周向速度等氣流參數沿葉高分布規律的差異如圖8~10所示。從圖中可見,總體趨勢上與不考慮徑向摻混相比,湍流摻混項的加入使氣流參數沿葉高的分布更加趨于平坦,且這種趨勢隨著摻混系數的增大更加明顯。此外,后面級出口的氣流參數在不同的摻混系數下沿葉高的分布差異明顯高于前面級出口的氣流參數分布。壁面處速度梯度較大,黏性力的輸運效果更加明顯,所以與主流區相比,有無摻混計算對端壁區氣流參數的徑向分布影響更為顯著。同時,與其他流動參數比較,徑向摻混對靜溫及總溫沿葉高分布的影響程度要高一些,主要是由于總溫表征氣流的總能量,考慮徑向摻混引入黏性項,黏性應力能夠在相鄰跡線間輸運能量,改變能量的空間分布,使不同葉高的氣流沿徑向發生能量遷移,即如果不考慮徑向摻混的影響,無法預估出能量沿徑向的遷移。所得結論與文獻[9]中的結果一致,說明給定相同的落后角以及損失系數,采用不考慮黏性影響的通流徹體力模型計算的氣流參數沿徑向分布結果與實際氣流參數的徑向分布存在差異,在通流計算中需要考慮徑向摻混的作用。

圖8 第1級壓氣機出口靜溫差、總壓比以及絕對周向速度分布

圖9 第3級壓氣機出口靜溫差、總壓比以及絕對周向速度分布

圖10 壓氣機管道出口靜溫差、總壓比及總溫差分布
2.3 模型驗證
湍流摻混系數 μt/ρvzL=2×10-3,進口給定總壓1.0267×105Pa,總溫 283.65 K,軸向進氣,通過給定出口輪轂處背壓調節流量。穩定邊界的判定方法采用Koch最大靜壓升系數法進行壓氣機穩定邊界的判定[15],根據壓氣機失穩有效靜壓升系數(Ch)stall和有效靜壓升系數 (Ch)ef確定壓氣機的穩定邊界,在不同轉速下,模型中有無徑向摻混計算的對應小流量工況下壓氣機各級相對有效靜壓升系數的分布如圖11所示。第4級壓氣機的相對有效靜壓升系數接近于1,判定此工況為壓氣機穩定邊界點。

圖11 近失速點壓氣機各級相對靜壓升系數分布
在不同轉速下,模型中考慮徑向摻混效應和不考慮徑向摻混效應所計算獲得的壓氣機總體特性以及試驗結果的對比如圖12所示。從圖中可見,模型計算出的總體特性與試驗結果吻合較好,設計點總壓比誤差為0.1%,效率誤差為2.25%,均在工程誤差允許范圍之內。由于湍流黏性應力只改變能量在空間中的分布,不改變能量的總和,所以在圖12中是否考慮摻混效應計算出的特性線差別很小,有無徑向摻混對壓氣機總體特性的計算結果影響很小。此外本文還對比了模型中是否考慮徑向摻混所計算出的壓氣機設計點第3級靜子葉排出口氣流參數沿展向的分布與試驗測量結果的差異,如圖13所示。模型中有無徑向摻混計算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端壁區流場參數的展向分布上,端壁區流動梯度大,黏性輸運效果明顯。與不考慮徑向摻混相比,模型中考慮徑向摻混所計算出的流場參數更接近試驗結果,說明通流徹體力模型引入徑向摻混之后可以更準確地預估出流動參數的徑向分布。通過與試驗數據的對比,驗證了引入徑向摻混的通流徹體力模型具有較高的可靠性與適用性。

圖12 4級壓氣機總體特性對比

圖13 有無徑向摻混計算出的設計點氣流參數沿葉高的分布與試驗結果的對比
3 結論
(1)有無徑向摻混對壓氣機總體特性的計算結果影響不大,徑向摻混模型考慮了湍流黏性造成的損失,計算出的效率比不考慮摻混的略低。考慮徑向摻混計算出的葉排出口氣流參數分布比不考慮摻混的更加趨于平坦,且隨著摻混系數的增大趨勢愈加明顯。
(2)黏性力的輸運作用使得相鄰流體間發生能量和動量的交換,端壁區流動梯度大,摻混效果明顯,在通流計算中考慮徑向摻混的影響,可較好預估出壓氣機后面級端壁區流場。
(3)通過對某4級低速壓氣機不同轉速下總體特性以及設計點葉排出口流動參數徑向分布的計算結果與試驗數據的對比,驗證了本模型在低速壓氣機上具有較好的適用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