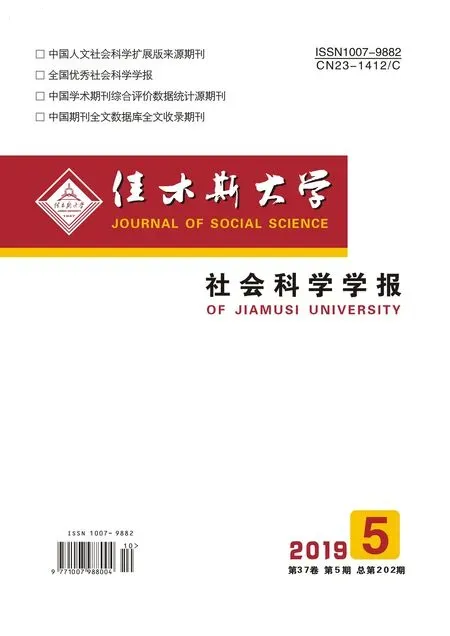新時期以來鄉土小說中農民代際更替與鄉土意識的嬗變
廖 斌
(武夷學院 人文學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鄉土意識是“指農民對于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土地和鄉村生活環境所表現出來的強烈依戀心理。”[1]世代耕作、居鄉繁衍的農民, 對如母親般養育他的鄉土充滿愛戀依賴, 終其一生在土地上開荒、墾殖、收獲,恰如臧克家的詩作《三代》: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爺爺/在土里埋葬。這首詩道盡了農民之于土地難分難舍、愛恨交加的情感。在舊社會,即使因戰爭災荒等天災人禍迫使農民逃離家園, 一旦風平浪靜, 他們又重返家園整飭旗鼓, 除極少手工業者、走卒販夫,很少有農民挈婦將雛外出謀生。鄉土意識是傳統農耕文明的產物, 執守鄉土一方面是由于戶籍制度將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另一方面是“農本商末”思想的阻礙,再加上城市就業崗位少,農民缺乏必要謀生技能。趙園認為,“土地之于農民,更是物質性的,其間關系也更具功利性;他們因而或許并不像知識者想象的那樣不能離土;他們的不能離土、不可移栽,也絕非那么詩意,其中或更有人的宿命的不自由,生存條件之于人的桎梏。”[2]總之, 故土難離、葉落歸根等鄉村倫理與農民相互纏繞, 代代相傳,農民的鄉土意識越發根深蒂固而對鄉土“愛得深沉”。1980年代以后,國家逐漸放松了嚴苛的城鄉戶籍制度,農民得以沖破土地束縛,浩浩蕩蕩地進城務工,開始了與城市文明、工業文明的親密接觸,在遭遇到現代性啟蒙后,農民的鄉土意識日益發生嬗變與分裂,呈現出代際差異和從外到里與鄉土割裂的姿態。陳仲庚指出了如下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陸鄉村大量青壯年外出打工,農村人口從‘不離土不離鄉’到‘離土不離鄉’再到‘離土又離鄉’,以致形成了一個個龐大的‘空心村’……這種荒涼正是當下中國農村現狀的一個縮影。”[3]
本文通過文本細讀,從“代際”等角度探討新時期以來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幾代農民各自的“現代體驗”以及對“鄉土”的不同態度,并以此反觀鄉村現代性轉型下的興衰榮辱與振興。
一、老農民的熱戀:不離土不離鄉與抵抗遺忘
代際理論是描述和研究不同代的人之間思想和行為方式上的差異和沖突的理論。代溝和代際沖突一般出現在社會整體轉型的大背景下。當代中國處于一個巨變的新時代,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眾多的思想代溝和代際矛盾。周曉虹教授曾經列舉“文化反哺”(類似西方社會學中的“后喻文化”)的例子,就足以表征當代中國在“西風東漸”和現代化進程中,親代和子代“文化傳承”的反向逆動是一個獨特的社會景觀。對中國當代社會發生的“匪夷所思”的許多現象,用代際理論則可能得到某種合理的闡釋。新時期作家王潤滋的小說《魯班的子孫》呈現的“父子沖突”、柏原《伙電視》描繪的小山村三代農民對現代傳媒“利器”——電視“入侵”的不同態度等等,無不展現了農民代際之間的思想差異和觀念沖突,可以看作是文學對當代鄉村轉型的忠實記錄。
韓長賦將農民工分為三代:第一代農民工是1980年代農村政策放活以后出來打工的農民,他們絕大部分在鄉鎮企業打工,亦工亦農,離土不離鄉;第二代農民工大多是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農民,他們中有的人留在城市,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隨著年齡增長選擇了回鄉;第三代農民工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他們從來沒有種過地,對土地沒有父輩那樣的感情,對農村沒有父輩那樣的依戀,他們進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為改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打工不過是進城的途徑,簡言之,他們出來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農村。[4]鑒于農民工屬于農民階層的一部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與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有很強的同構關系,本文依上述劃分,將改革開放后的農民大致分為三代。農一代大約出生在1950年代、60年代初,農二代誕生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農三代降生于1980、90年代。當然,他們之間存在交叉和邊界模糊。
對于身處1980年代的農一代而言,鄉土是他們全部生命的意義所在,他們的生老病死、祖先崇拜、精神寄寓、血脈傳承、文化記憶完全附著在鄉土之上,就像福斯特創作的黑人風格歌曲《故鄉的親人》所傳唱“我生死都要回到故鄉,回到母親身旁”。確然,在這一代農民魂靈里,鄉土與“母親”“親人”融為一體,說不上鄉土和母親,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幻。“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5]他們的鄉土熱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近打工,不離土不離鄉,身份比較模糊,亦農亦工,但是以農民為體,打工為用;農民是職業,打工是手段。打工實際上是他們農業耕作之外的兼職和副業。比如梁鴻《中國在梁莊》中眾多鄉親就近在村里的磚廠務工,“80年代初期,村里有許多人都在這個磚廠干活,從早晨一直干到晚上八九點鐘,掙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學費。”二是與舊有的生產生活方式,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感。李杭育《最后一個魚佬兒》中,有一個愚頑不化的漁民很能說明問題。主人公福奎終其一生都在葛川江上打魚,隨著工業化侵入鄉村,岸上修路建廠,江里竭澤而漁,漁民們生活難以為繼,紛紛選擇洗腳上岸,改行當“莊稼佬”或到村里的工廠打工。福奎的相好阿七為他在味精廠謀了一個當工人的職位,可是福奎窮得連褲衩都要向阿七討要,也寧愿堅守這片鄉土和古老寧靜的生活生產方式,決不肯到工廠去當有固定收入、工作規律的工人。有學者指出,“在城市的沖擊中 , 與農戶陳奐生相比 , 漁佬兒福奎更明確地表現出了不離鄉土的意愿。”[6]結尾處,福奎把小船劃到葛川江心,施施然躺在船板上,“他想,他情愿死在船上,死在這個像嬌媚的小蕩婦似的迷住了他的大江里。死在岸上,他會很丟臉的。”福奎之所以貶抑“岸上”而崇尚“江里”,并希冀死在船上、魂歸江里,不僅是因為福奎打小就在葛川江里討生活,在江上風吹浪打慣看春月秋風,更因為,他“仿佛天生就是個漁佬兒”,江里圍繞著他的小船的小雞毛魚,讓他覺得“仿佛蝦兵蟹將簇擁著龍王”——江就是生養他的水上“疆土”、攝取他心魄的“小蕩婦”(可視為母親、親人形象的變體),是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存空間、靈魂棲息之地。只有在船上、江里,他才有歸屬感和認同感,才可安頓身心擁夢入懷。
隨著現代化的狂飆突進和國家多項“三”農政策的實施,福奎式的固守已經過時了。最直接的就是近年大力推進的農村“城鎮化”和土地征遷,使得大量失地農民被遷徙出家園,他們的土地有的用于建設工業園區,有的被征用蓋商品房,農民被安置在城鄉結合部或者整體搬遷到更加適宜人居的地方。離開家園的農民割斷了與鄉土血脈聯系之臍帶,失去了與土地接壤的“地氣”,連同他們的祖墳、房子、田地、小船、籬笆女人狗和所有的記憶。福奎們就像滄桑的一塊懷表,停擺在1980年代日落的霞光中,他面對現代性在葛川江橫行霸道時的迷茫心態、挫敗性的體驗,用雅斯貝斯的話來說,即“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這一無力感使“人傾向于認為自己是被種種事件拖著前行的。這些事件,在他比較樂觀時,曾是他希望加以引導的。……然而,今天,那種想要認識一切的驕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從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響了所有的大門。但與此同時,這類驕傲與自高自大所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種可怕的虛弱感。人該怎樣適應這種情況而不受其影響?這是當代狀況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7]。于是,對鄉土的執念,成為他們抵抗遺忘,為故鄉“招魂”的一種方式。
《在天上種玉米》中三橋村的村長王紅旗就是另一個倔強的鄉土熱戀者。其兒子王飄飄循循善誘開導父親,希望父親能夠解開心結:“這些年,山里的往鎮里挪,鎮里的往縣上挪,你看到哪一個把地名也帶著走的?”在親人身上找不到寬慰和溫暖,苦惱煩躁的王紅旗只好拉住自己的老鄉黨張沖鋒,嘮叨內心的失望與懊喪:我現在特想回家,回我們的三橋去。這話里透著孩子氣,但張沖鋒知道他這時候比任何時候都要認真。……我原來想這里雖然是北京,但住的都是我們村的人,也就是一整家人挪了個窩罷。所以我想把這里還當是家,是我們的三橋村。可現在看來這些都是我們在妄想,再怎么妄想,它也是北京的善各莊,它不是三橋,不是我們的三橋。我真的,真的好想回去。王紅旗的涕淚交零的鼻音變成哭腔,最后干脆抽抽噎噎地哭上了。張沖鋒覺得,這時候坐面前的不是王紅旗,而是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告訴他,他想家,想家里的親爹親媽。
老邁的王紅旗雖然在城市安營扎寨, 但本質上, 他感覺自己是一個“過客”,鬧著要“回家”。城市對他而言, 仍是一個陌生、具有壓迫感的異域。在城市無法安身的境況下,失去往昔在鄉土如魚得水樂感的王紅旗們,只好在屋頂上面堆土種玉米,以此來緩解和熨帖他們身心無所依傍的苦痛與焦灼。恰似小說所指出,他“是個孩子”,正是這個從古典鄉村世界猛然“穿越”到現代城市的“孩子”、缺乏現代啟蒙難以進入城市生活的“低能兒”,在此表現得無所適從、茫然無助,他需要“種玉米”這樣“過家家”性質的“奶嘴”來撫慰。弗雷澤認為,古老的巫術使用相似律和觸染律這兩種原始交感思維方式來“溝通”世界。其中,相似律就是只要兩個東西相似,那么互相之間就會形成神秘的關聯,這樣巫師就可籍此施法。我們經常道聽途說的是扎小人,通過制作布娃娃來替代被詛咒的某人,然后在玩偶上施法就可以讓其遭災。觸染律就是兩樣東西通過物理接觸,就會發生災患傳遞。如果將某人頭發纏縛在布娃娃上,對頭發施法也會影響到他,這就疊加了觸染律。在筆者看來,讀者忽視了這個細節的文化人類學的深層意義:王紅旗在屋頂上種玉米,不僅是在建構一塊精神“飛地”來得到慰藉和滿足,更是相似律、觸染律的當代城市的推演。王紅旗們雖然不一定會有“原始巫術”的能力和自覺行動,但千百年來,沉潛在老農民文化心理結構中的“無意識”被喚醒和激活,借助對“種玉米”這種改頭換面的原型結構的模仿和接觸,以此來接續與鄉土的聯系,獲取土地和家園源源不斷的加持。這種深具儀式感的 “類巫術”,撫平了老農民的創痛,使得王紅旗們得到了鄉土的“地氣”并“復活”,重建了心中的鄉土,有了茍活下去的勇氣和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依然將王紅旗的行為有意無意地比喻為“是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告訴他,他想家,想家里的親爹親媽”——此間,“鄉土——家園——母親”這樣的譬喻結構仍舊頑強地重現出來,并不在于它的“落入窠臼”與“俗不可耐”,而確鑿地表明,無論是農民還是作家,都真心實意地把鄉土當作了親人。孟繁華認為,“鄉下人進城就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人,鄉村的經驗越多,在城里遭遇的問題就越多,城市在本質上是拒絕鄉村的。因此,從鄉下到城里不僅是身體的空間挪移,同時也是鄉村文化記憶不斷被城市文化吞噬的過程,這個過程對鄉村文化來說,應該是最為艱難和不適的。”[8]
二、中生代農民的別戀:向城求生與離土不離鄉
到了1990年代,第二代農民開始有意無意背棄父輩的鄉土觀念,諸如“窮家難舍, 故土難離”“金窩銀窩, 不如自己的狗窩”等“守舊”的鄉土意識。在現代化的征召下,前赴后繼地向城求生,自從一腳踏進城市,現代文明之風就吹皺了他們心中的漣漪,躁動著他們不安分的靈魂。高加林(路遙《人生》)、芝英(方方《火光中奔跑》)、疤子(《誰動了我的茅坑》)等眾多的文學人物形象,已然開始展現了對鄉土的分離傾向。但是,他們的重心仍然立足在鄉土,以資進退有據。其中,在家鄉“蓋房子”的敘事單元,不僅在《火光中奔跑》等眾多文本,也在日后梁鴻的“梁莊”系列“非虛構”小說“(或稱之為“農民口述實錄”)中被反反復復凸顯,他們是這一時期農民離土不離鄉的主流。
這一時期,農民“別戀”或者向城求生主要有兩種類型。1980年代,農村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熱情,解放了生產力,廣大農民逐漸溫飽有余。比如陳奐生摘掉“漏斗戶主”的帽子, 由一窮二白變得“圍里有米、櫥里有衣, 總算像家人家了” , 而且趁著 “稻子收好了,麥壟種完了, 公糧余糧賣掉了, 口糧柴草分到了”的空當還能“出門活動活動, 賺幾個活錢買零碎” 。但在1990年代之后,三農問題日漸凸顯,“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一語成讖,如賈平凹《土門》中仁厚村的土地被城市化蠶食,房屋被拆除,農民變成失地的“流浪兒”,盡管仁厚村的父老鄉親不懈反抗也徒勞無功,城市化以千軍萬馬之勢橫掃鄉村,曾經的仁厚村徹底消失。再看關仁山的《天壤》,“縣里鄉里村里轟轟烈烈搞開發,三級開發區都占用了韓家莊的耕地,……七百畝耕地,都被鐵絲網圈了起來。只蓋了一幢高樓,開發區就沒有資金了。“在農業稅費居高不下、生產生活資料漲價、賣糧難、生活拮據、資本入侵土地的背景下,農民離開家鄉進城務工成為最無奈的選擇——這是第一種類型。一時間,“百萬農民工下廣東”成了20世紀末最為壯觀的社會景觀。有學者在分析作家關仁山的《傷心糧食》時指出:“現實的特別是農業本身的種種,造成了王立勤們生產生活的苦難,他們無法在土地勞作和農業生產中獲得應有的物質報酬,更無法獲得最基本的人格尊嚴,他們所能選擇的,只能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像王立勤那樣毀掉家園永遠逃離土地,另一條是像王立勤的父親、大哥那樣無可奈何地走向死亡。土地簡直蛻變成農民厄運的魔咒。”[9]
在農業萎縮、鄉村凋敝的情況下,農民進城無論是主動尋夢還是被動逃離,都不可避免受到現代性全方位的革新,而不由自主被整飭進現代的行列。 “盡管大多數城市農民工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心理上處在城市的邊緣,但誰也無法否認城市對農民工產生的影響。這種在新的時空中的新體驗,在與農民的傳統意識發生碰撞、交融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形塑著他們的人格和行為,賦予他們以現代特質。”[10]
但是,農二代離開土地進城,身負傳統與現代交織的精神特質,鄉土仍然是他們的依傍,是他們在城市遭受創傷后可以以資退守的最后堡壘和依靠。在他們心里,鄉土充滿了脈脈溫情,是母親倚門倚閭的召喚,是受傷后可以療治的溫床。第二種類型是為了筑夢尋夢而執著進城,到鄉土之外的城市去體驗新生活,嘗試以非農業方式謀生,尋異路體驗別樣的人生。正如一位研究者斷言, 鄉下人進城大抵“只為服膺于一個城市先期現代化的神話, 他們幾乎一致地認定‘城里好活人’的信念”。[11]梁鴻《中國在梁莊》中的韓建升——從梁莊到北京打拼小有成就的保安公司小頭目,是這一人物譜系的代表。他于90年代初甫一進城即展示出與眾不同的“現代”氣質和崇高夢想,他的最高理想:“我要好好干活,做人就做邱娥國,干活要如趙春娥。” (注:此二人均為全國勞模,是當時官方大力宣傳的楷模)在筆者看來,韓的這一指向顯示了農民身上“罕見”的“現代性”新鮮質素,具有某種形而上的價值取向;終極目標是:“一心想著,干得好了,說不定到時候自己還有可能轉正啥的。”讀者可以從這些細節中辨識出,韓建升這個“胖頭大臉、庸俗”的鄉下人,以勞模為榜樣,渴望通過自身的貢獻而贏得社會肯定,獲得身份認同和人生價值實現。這個完全為“現代性”所改造的、徒有其表的農二代,是對鄉土移情別戀的劈腿者,是脫胎換骨的現代人。但是,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問及“將來想不想回梁莊”,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想梁莊,咋不想?我夢見過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到家里,家里那幾間爛房子也找不著了,最后哭醒了……。在北京,沒有歸屬感,就好像風箏斷了線。在家還是有種安全感”。由此可見,“鄉土”仍然是中生代農民精神世界中習焉不察的,也是他們缺乏安全感后魂牽夢縈歸來的最后依怙。丁帆認為,“20世紀90年代鄉土小說強調的不再是農民被趕出土地的被動性和非自主性,而是他們逃離鄉土的強烈愿望以及開拓土地以外新的生存空間的主動姿態;離土農民也不再是在城市尋找類似土地的穩定可靠的生產資料,以維持其鄉民式的生存原則和價值觀念的‘祥子’們,他們以嘗試與傳統農民人格抵觸的商業活動的,體驗與土地沒有直接依附關系的人生。”[12]
直到新世紀來臨,命運多舛如高加林者,他的子輩才實現了他離鄉進城的夢想,如果說高加林對鄉土的“別戀”是一個異數,或者“離不了鄉”具有某種宿命性質,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鄉土作為一種原鄉意識,仍然在這一代農民身上鐫刻下深深的屐痕印履。
趙本夫《木城的驢子》中木城出版社的總編石陀崛起于隴畝之間,進城后當上了木城的政協委員,他每年都在“兩會”呼吁:提議官方“拆除高樓,扒開水泥地,讓人腳踏實地,讓樹木花草自由地生長”,這樣的提案在別人看來簡直荒誕不經——石陀就是“迂腐”,他每晚孜孜不倦所做的是“從懷里掏出一把小錘子,幾下砸開一塊水泥磚,露出一小片黑土地。……他知道要不了幾天,這里肯定會長出一簇草,綠油油的一簇草。……他一直有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就是喚起木城人對土地的記憶”。小說還寫到鄉下人天柱用麥苗綠化城市,用蔬菜瓜果裝點城市。小說塑造了一個眷戀鄉土,近乎“病態”的、離土但又在夢想中偏執地“不離鄉”的“農民”形象,與其說他的不離鄉,是因為城市鋼筋水泥的叢林的逼仄,不如說是對原鄉的懷念,是文化鄉愁的銘心刻骨,讓他做了反向運動。小說“題記”:“花盆是城里人對祖先種植的殘存記憶” 極具哲理性,不僅喻示石陀這個“病人”癥候的精神向度,也宣示了作家本人的寫作倫理。小說寫到:“事實上 , 木城人已經失去對土地的記憶。”從這個角度出發,石陀們的努力,就是在回天無力地抵抗著對土地、鄉土的遺忘。福柯認為:“在那里有真正的斗爭在進行著,爭奪的是什么?爭奪的是我們可大略稱之為人民記憶。由于記憶是抗爭的重要因素,如果控制了人民的記憶,就控制了他們的動力。同時也控制了他們的經驗,它們對過去抗爭的理解。”[13]今天,人們反反復復強調“記得住鄉愁”,或許正是對鄉村現代性的某種矯枉反撥。
三、新生代農民的失戀:離土離鄉與“城市生活更美好”
有學者梳理總結了“廢人——廢鄉”的鄉土文學書寫線索。在本文看來,正是這一“廢鄉”以及農民接受的現代化思想觀念,終結了他們之于鄉土的眷戀,義無反顧地走向城市,開啟新的人生。
新世紀前后,新生代農民基本的活動場域在城市,除了身份的曖昧模糊,他們已經與城里人沒有本質的差別。恰如一份資料顯示,“第一,他們從來沒有種過地,對土地沒有父輩那樣的感情,對農村也沒有父輩那樣的依戀,這是其最鮮明最突出的特點;他們經常打工,不是為了生存,而是以打工作為進城的途徑和機遇;簡而言之,他們進城打工就不想再回農村了。第二,這批人都念過書,一般都有初中文化,不少人還有高中文化,因為有文化,再加上他們是伴隨著電視機、手機長大的一代人,比較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城市文明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農村好,這是他們比較堅定的信念。”[14]綜上所述,新生代在與現代性的遭遇中,孕育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離土離鄉”之“失戀”是他們最迫切的愿望和生活的主要動力。
作家張繼寫了一篇有意思的小說《去城里受苦吧》,不少評論將小說定位為“對鄉村權力異化“的批判。本文感興趣的是主人公貴祥狀告村長李木背后所呈現的反諷結構與黑色幽默。《受苦》是農民告狀的故事,但它與《我不是潘金蓮》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與農村婦女李雪蓮執拗地上訪不同,貴祥實在是個沒有血性、進退失據的“懦夫”。貴祥告狀,是因為生計問題,因為村長李木把他的好地——“聚寶盆”賣掉了,他的生活就有了問題,于是背井離鄉“去城里受苦”。貴祥因為城市女人李春的幫助經營了一個門市部,忙碌的生意和日漸寬裕起來的生活使貴祥“忘卻”了告狀一事。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他如果贏了的話怎么辦?貴祥發自內心地問自己說:李木如果把地補給了我,那么,我還要回家去種地嗎?這個事實上已經存在許久,感覺上卻突如其來的問題,剎那間就使貴祥汗流浹背起來。”——在“鄉村貧窮”和“城市富足” 間的轉型體驗使他“頓悟”。再后來,當民工老劉告訴他市長表叔的電話,讓他試圖找大官扳倒李木時,剎那間,前塵往事涌上心頭,貴祥突然覺得遙遠而虛幻,呆立半晌,自言自語地說:“現在看這件事,怎么這樣小呢”。比他還更老練適應城市的老婆徐欽娥搶白他:“生意都忙不過來了,還告什么狀?再說,那地就是給了咱,咱也沒法種了,也是個累贅,算了,不告了。”衣錦還鄉后,村長李木主動提出要補償貴祥3畝地,他老婆斷然拒絕: “他就是給我們補三十畝,我們也不想要了”,并感嘆“你沒看出來,咱在城里呆了這幾天,連村長都高看我們幾眼,別說其他人了。我給你說,在城里做一只老鼠都比在村里做人強”。
就此,貴祥完全醒悟,夫婦兩人如魚得水般迅速融入城市。這讓我們想到一句令人愛恨交加的廣告詞——“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對于貴祥來說,正是城市教會了他舍棄虛無縹緲的“面子”,安住于現世安穩、豐衣足食。鄉下的一畝三分地有什么好呢?他和城市是如此般配、天衣無縫——城市,的確讓他的生活更美好。鄉村,他是再也不想回了。
“沒有了地我心里怎么有點不踏實呢?”貴祥對這一絲猶豫還來不及琢磨,就馬上被城市的眼花繚亂拉回現實。于是,一切有關土地、有關家鄉,都變得異常模糊和不堪回首,被拋到九霄云外了。重要的是,要對付眼前的紅火生意。這讓我們想起了劉震云筆下的國家部委公務員小林,他的鄉下小學老師因患癌癥到北京治療,提著一桶香油去拜訪昔日的學生,卻被小林勢利的城里老婆小李的白眼“趕走”,送別佝僂著背頭發花白的恩師擠上公共汽車,小林心里一陣愧疚,但是小林來不及難過,就立馬被一地雞毛的現實瑣事淹沒。于是,對老婆的怨懟、內心的自責都化做自我解脫,一切又回復到原狀。在這里,貴祥對“田畝”的“看破”“放下”,與小林夫婦對老師的“驅趕”“送別”,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對象征鄉土的人與事的如釋重負的遺棄和毫不留情的背叛。孟德拉斯曾經如此斷言,“農民沒有把自己固定在干粗活的角色中,實際上,他們能夠接受現實擺在他們面前的新條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實現現代化、進行擴展和適應市場要求,變成有著進步意識的小企業家。”[15]97透過貴祥終日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們似乎隱約看到了一個“新農商”的崛起。
而在王十月的詩化小說《尋根團》中,主人公王六一再次逃離家鄉時自忖:“突然覺得,這么多年過去了,故鄉終究是落后而愚昧的,當年逃離故鄉,不正是向往著外面世界的文明與先進么,怎么在外面久了,又是那么的厭惡外面世界的復雜與浮躁,在回憶中把故鄉想象成了世外桃源。” 王六一以其清醒的認識終結了當代鄉土的“欺騙性”,揭穿了人們之于鄉土想象的“虛幻性”,離土又離鄉就此完成。
就在人們嘆惋“曾為之感嘆的神秘的鄉村、地氣氤氳的鄉村,被我們看作生命的家園、文化的命脈還存在嗎?鄉村的潰敗是歷史性的,城市化進程勢不可擋。……都要到城里受苦去了,我們已無鄉村可回”[16]的時候,貴祥等農民早已在城市樂不思蜀,甘之如飴——他們確然在城市苦樂參半,卻再也不想回鄉了。如果說從事買賣營生的貴祥以在城市“受苦”為樂事,那么,即使如尤鳳偉《泥鰍》中的農民工國瑞,在痛苦勞累的城市打工生涯中,盡管歷經艱辛,也堅決拒絕重返故鄉;而《出梁莊記》中農三代的丁建設說得更加直白:“那能咋樣?但凡有辦法,說啥也不要在工廠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悲想,沒意思。——但是,他表示他也不會回家,回家沒意思,他不想干農活,他承認他已經不習慣干農活了。”——與先輩猶疑彷徨于自己的“身份認同”相比,年輕的丁建設和他的“小伙伴”們早已決絕地卸下了這個可有可無的精神枷鎖,重要的是身心自在,樂享城市生活。
作為現代體驗的一環,鄉村教育也加入到了“遠走高飛”的組織動員機制中來,加速了新農民的逃離。有教育學者指出,鄉村父母、老師就常常以“好好念書,念好書就再也不用割小麥了……不好好讀書,一輩子就這樣跟農活打交道……”[17]的話語來規訓鄉村子弟。農民大學生涂自強(《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正在身體力行這個命運指南, “他目標很清晰,只是想在一個城市待下來。”出生80后的涂自強來自偏僻貧窮的鄉村,到武漢上一個二本大學,畢業后,他沒有響應號召“到農村去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是留在了武漢,因為他想“雖然這是我自小生長的地方,是我的家鄉,可它的貧窮落后它的骯臟呆滯,又怎能讓我對它喜愛?又怎能拴住我的身心?難怪出去的人都不想回來。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了。這個地方我是絕不會回來的。”涂自強像所有的“漂一族”那樣,離土又離鄉寧可“蝸居”城市,哪怕是從事外賣員、推銷員、企業文案等低微的工作,屢屢受騙碰壁屢撲屢起,也決不愿回農村。涂自強是當下千千萬萬個在城市上學的農三代的縮影。行文至此,也許李敬澤的點撥更能讓我們釋懷于城鄉的二元對立,“生命的意義與故鄉、與兒時的生活世界無關,那意義在遠離故鄉的地方,在山外山、天外天”。[18]如果超越了“城市”(市民) /“鄉村”(農民),未來的新時代農民就變成了國家“公民”。
新世紀之后,在城里出生長大的農四代(也有部分農三代),實質上是“城市化的孩子”(參見熊易寒相關論著),在他們的心目中,基本割斷了與鄉土的精神臍帶和血脈傳承,沒有“文化鄉愁”、“原鄉意識”。鄉土成為他們填寫各種表格時的“籍貫”,是失去血緣、文緣、業緣的形式和內容的空洞能指,一個外在于他們生命意識、生活經驗、情感體驗的抽象概念,是一個地緣意義上陌生的“他者”,是他們頭腦中的“闖入者”,而與鄉愁無關。《尋根團》有一處細節描寫彰顯了農民代際之間的沖突和巨大落差:外出打工發家致富的楚州籍張老板帶著年少的兒子利用清明節返鄉尋根掃墓,由于旅途勞累困頓,父子發生沖突。他兒子嘟囔著罵父親是“鄉巴佬”,“鬧著要下車,說是不去楚州了,說是鄉下有什么好看的。”——顯然,在農四代的心目中,早就忘卻了“農民”的身份,已經自然而然把自己劃歸到了“城里人”的陣營,并在對鄉下人的蔑稱中建構起了強大的“城市意識形態”。
在此,我們不無遺憾和傷感地看到,鄉土的背影已漸行漸遠漸,就像今天,當我們與農三代、農四代只能用普通話進行攀談時,他們對鄉土的一無所知和漫不經心一樣,連同古典時代無改的“鄉音”也隨風飄逝。湖南衛視主持人汪涵曾經說過:“普通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可以讓你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讓你不要忘記你從哪里出發,普通話讓你交流極其順暢,而方言讓你感受到無限的溫暖。”[19]的確,互為表里的鄉土和她的文化表征——方言,早已經被當做“土氣”“難聽”而被遺棄在現代化的垃圾堆,面臨消失的危險。有學者指出:“世代之間文化聯結承繼的最佳指標——至少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就是看家庭中父母能否把社會文化觀念清晰、準確、有效和令人信服地授受給自己的子女。倘若這個過程不能順利地進行,青年人不愿向成年人認同,那么,也就預示著社會文化發生了斷裂和錯位,也就醞釀著青年一代反叛舊文化、尋求新文化的心理動機。”[20]
四、余論:城鄉一體和鄉村振興
鄉村現代化的腳步無法停止,社會轉型所帶來的代際差異與沖突也難以調和,且讓他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實現各自的人生理想。然而,年輕一代農民已然無可挽回地離土離鄉去了。孟德拉斯在其《農民的終結》一書中,懷著斷零、懷慕的現代體驗宣告了“農民的終結”;同時他又清醒地意識到:“憑什么要迫使農業勞動者繼續生活在過時的生產結構中呢?這種結構使他們無法得到勞動分工的好處,注定要走向貧困。“[15]251在作者眼中,鄉村社會的坍塌、農民的離土離鄉是鄉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農民的終結”并非表征著鄉村社會的不可救藥,這僅僅是社會整體轉型和現代性的過程,經過了30多年城鄉均衡發展與城市對農村的反哺之后,法國的鄉村社會“起死回生”:“10年來,一切似乎都改變了:村莊現代化了,人又多起來。在某些季節,城市人大量涌到鄉下來,如果城市離得相當近的話,他們甚至會在鄉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來了,一個擁有20戶人家和若干處第二住宅的村莊可能只有二三戶是經營農業的。這樣,鄉村重新變成一個生活的場所,就像它同樣是一個農業生產的場所。”[15]279
1980年代的法國鄉土復歸田園牧歌和黃昏放牛的迷人風姿:產業興旺、生態優美、安全宜居、生活富庶的景象觸眼皆是。“鄉鎮在經過一個讓人以為死去的休克時期之后,重新獲得了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15]269我們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將來,隨著鄉村振興計劃在中國的深入實施,古老鄉村的新子民會一如他們前輩離土離鄉一樣,懷著喜大普奔的心情重返鄉土母親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