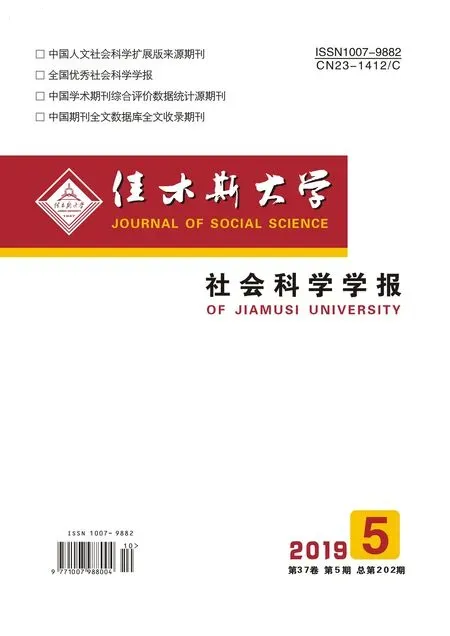神圣·實用·情感
——清代宦臺官員衙署之空間特性與文化內涵
鄭麗霞
(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臺灣衙署是清代宦臺官員在臺權力的象征,也是其在臺期間的生活場域,不僅連結其辦公、社交、休閑等所有日常空間,同時也是清政府跨海而治的政治延伸。諾伯舒茲指出:“當人們定居下來,一方面它置身于空間中,同時也暴露于某種環境特性中,這兩種相關的精神可稱之為‘方向感’(orientation)‘認同感(identification)’。要想獲得一個存在的立足點,人必須要有辨別方向的能力,他必須清楚身置何處,同時在環境中認同自己。”[1]18據此而言,場所的環境特性是由生活于其中之人所界定的,“是人們在某處空間實際生活的體驗、參與的凝聚。主體的意向性投射在其中的實質感受,賦予某空間意義,而生成地方感,再經由社群的往來聯系,形成某區域獨有的空間秩序。”[2]97-98空間內的事物,通過“占有地方(taking place)或是占有和轉換空間與自然,而共同建構、維系和塑造了地方。”[3]91是故,這個由集體共同營造的地方,承載了主體投注其中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而對空間中的一草一木產生熟悉的親切感,或對其中的人文歷史與文化情境生發出濃厚的情感牽系。對于這些空間內涵,段義孚認為:“附著于鄉土是通常的人類情緒。它的力量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時期皆有差異。附著愈多而情緒的結合愈強……因為可以有一個以上的感情結套。”[4]152他以南太平洋島民對島上某山峰的情感結加以說明:
南太平洋的小島Tikopia上的Reani峰,像島的皇冠,航海的島民對它至少有三個情感結,第一,它能使大海漂泊者作距離的地標,估計距離陸地還有多遠,這是實用性的原因。第二,它也是情感的對象,當一位流浪者離開的時刻,山峰的景點漸漸失落在海浪之下而感到悲傷,但在回程時,山峰突然浮現在海浪上的第一眼,則可帶來無限的喜悅。第三,它是神圣的地方,它是神降臨大地時最初站立的地方。[4]152
可見,一個景觀往往兼具實用性、情感性與神圣性等內涵,三者并存構成地方感的整體。本文將從這三個層面,分別探討臺灣衙署的空間特性與內涵,分析中原文化與儒家道統如何通過官署場域,得到傳承、發揚與深化。同時聚焦于臺灣衙署內的著名景觀——澄臺與斐亭,呈現官員在衙署內的生活實踐與文化展演,以及從中折射出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附著。
一
相較于源遠流長的中原文明,清初臺灣草昧初辟,荒蠻未化,無論是陰森詭譎的海上航程,亦或是迥異中原的海島風情,于宦臺文人而言均帶有“理亦難明”[5]6的困擾與憂慮。季麒光《寓望園記》指出,臺灣乃“東寧荒海之島,不入職方,有山則元翳于蔓草,有木則鹵浸于洪濤,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是蓋造物者之有所缺焉,以俟乎名賢之補救乎。”[6]109于是,整治并經營一套符合中原文化的地理景觀,成為清政府理臺的重要一環。楊廷耀為高拱乾《臺灣府志》作序曰:
我朝應運鼎興,圣明接武,指揮萬國;雖已建旐、設旄于禹貢、職方之外,然未有遐荒窮島如閩之臺灣者。……若臺者,素為積水島嶼,竊計流寓之外,其民若盲之初視、寐之初覺,雖更數載,猶是鴻蒙渾沌之區耳。[7]5
傳統士人眼中,臺灣是塊“鴻蒙渾沌、盲之初視、寐之初覺”之地,務以“德教”風化,積極導入中原文化與儒家道德倫理,使臺地“既富且教”[7]6,逐漸步入中原文明生態圈。為使宦臺官員身處蠻煙之地而不覺郁陶,且能凝聚認同感,明確身負“振綱飭紀,分揚清激濁之任焉;正己勵俗,有端本澄源之責焉”[7]270的教化重任,于是將官廳公門營造出莊嚴肅穆的秩序感與威儀感。
清初臺灣府署多沿用明鄭舊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載,“臺灣府署舊系偽宅,兩座毗連;后左畔一署傾圮,惟存右署,規制稍隘。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愷即左畔基址恢廓重建,大堂、川堂、二堂、東西齋閣、廂房以及大門、儀門悉具”[8]64,經過改造,府署顯示出比較正式的公門規模。此后,歷任官員陸續增設、擴建,“雍正九年,知府王士任建三堂一座,又置四層住屋一所,為東寧新署。署右側舊有榕梁、四合亭遺址,地甚寬敞。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改建官廳二間,曲檻回廊,重樓復閣,池臺亭沼,各色悉備”[8]64,舊日宅院,轉而成為具有權威象征的政府機構,尋常人難以隨意出入。衙署是地方行政制度的象征,首任知府蔣毓英曾親題匾額“開疆立本”[7]29,明確點明衙署所承載的責任,即治理臺灣,教化百姓。
即便是級別較低的縣署,也極力營造出公門應有之氣勢。諸羅縣令孫元衡有感于轄內缺少衙署之設,一則無所承宣圣諭以教民,二則不足以彰顯朝廷威嚴,遂動工興建縣署,其《新建諸羅縣署記》曰:“雖丹漆未施,而公堂內署已井然有序矣。從此蒞政之暇,或與邑紳士坐論桑麻,即不敢侈規模之大備,亦不至以百里官署等諸荒田野草,是則余之所差慰也。”[9]379衙署對于朝廷權威與官吏身份的重要性,可窺一斑。是故,歷任官員在原有設施的基礎上,或擴充,或新建,并借助公堂議政、升堂問案等形式,構建出神圣莊嚴、合乎中原文化的空間規范,借此宣揚清朝威嚴。臺灣道署,同樣如此,高拱乾《臺灣府志》曰:
臺廈道署,在府治西定坊,西向。由大門而儀門、而廳事,扁曰“敬事堂”。堂之右,為齋閣、為駐宅。其前,為校士文場。堂左,則椽史案牘處;其中慎出入,加扃鑰焉。堂下左右廨舍,輿隸居之。庭前植榕樹四株,皆移根會城;今扶可盈丈,郁可觀矣。大門之外,左為文職廳、右為武職廳;其為照墻、為鼓亭、為轅門,悉如制。照墻外,為巡捕廳。轅門之左有屋三楹,則為府、縣屬僚詣謁停驂之所。[7]28
道署內分三進,具有政務、議事、官邸等功能,從廳堂配置到功能設施,簡單有序,具有明顯的官廳秩序感。署內設有公文案牘存放處,專門加鎖,常人不能隨意進出,更顯道署之森嚴。此外,道署外的文職廳、武職廳、鼓亭、轅門,以及府、縣屬僚詣謁停驂之所,亦井然有序,彰顯出作為臺灣最高官方機構的莊嚴肅穆。
衙署不只是辦公之所,宦臺官員往往在衙署一隅另辟室或亭,營造具有自身風格的私人空間,使之成為在臺為官生活的場所。而他們在場所中的生活模式、行為模式又體現了空間的文化特征,“不只說明了你的住處或家鄉,更顯示了你的身份”[10]136。以道署為例,其內增設的斐亭、澄臺,雖是休閑好去處,卻非位高權重者難一窺其貌,即使朱仕玠、鄧傳安之流亦需受邀方可入內,可見衙署空間乃是權力的象征,宦臺官員對于衙署的修筑,是基于自我對陌生場所的認同感與支配權。道署內的澄臺、斐亭,此后更是超越了官員的生活場域,成為“文化的記憶庫”與“過去言行與知識的殘余”[10]28,成為清政府連結大陸與臺灣的文化憑借。道光十三年(1833),臺灣道劉鴻翱《綠野齋集》曰:
因考臺灣自前明紅毛與鄭氏相繼為患,潢池中雷擊電掣,波濤騰沸。我國家龍興遼海,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惟浙閩洋面祲氛未靖;施大將軍瑯掃除蛟鱷鯨鯢之怪,然后海若肅清,蓋二百年于茲。今余蒙圣恩觀察是邦,睹是臺之命名,思與僚佐戮力永澄海疆,不僅夸游覽之壯也已。[11]76
身為清朝官員,維護統治,力求邊疆安定,是其職責所在。受固有思想與文化背景影響,他們在考察臺地風物時,會在不自覺間以中原文化作為參照系,字里行間流露出自尊自貴的文化優越感與神圣感。于大陸文人而言,增辟景觀的背后,不僅夸游覽之壯,更在于彰顯清朝的顯赫皇威,是朝廷政治權力的延伸。而觀者的視線范圍,也會從該場所透顯出來,“透過地景(Vista,亦即物體在一段距離外呈現)這個觀念,視覺控制了地產”[10]28。劉鴻翱《臺灣道署澄臺記》云:“惟道署之澄臺,見西南海之一角。臺下屋三楹曰‘斐亭’,郡志所謂‘斐亭聽濤’也。登高遠矚,則安平晚渡、沙鯤魚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初日、西嶼落霞,近在珠簾畫棟間。蓋臺灣之八景,道署有其二,澄臺又兼擅八景之美。”[11]76對此,有學者指出:
從官署與安平地區的相對地位,可以視為從斐亭與澄臺觀看“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等三景,亦即“臺灣八景”中安平地區的景致入選,除了位居地域上的地緣關系外,更是由官署所望出去的景致,……觀看之人就是前面所言的官吏。居于澄臺的高處,官吏俯瞰安平一帶的景致,而眼界所見的人們,都為治理上的人們,……大有“眼見之人皆為我邦之民”之意。[12]23-24
上述所言有一定的合理性,登臨澄臺,既可欣賞道署內的二景,也可遍覽道署外的其余六景。這個視線展現的不只是觀者的角度,更顯示出清政府收服并治理臺灣的政治理念,代表政治權力的運作與延伸。此一趨向,可從數量龐大的臺灣八景詩中,窺知一二。試以《澄臺觀海》詩為例,如婁廣的“海國淼無窮,澄臺瞰四封。自從歸禹貢,何水不朝宗”[13]408;金文焯的“層臺軒爽俯神州,島嶼凝茫一望收”[8]987;以及王善宗的“巍峨臺榭筑邊城,碧海波流水有聲。濟濟登臨供嘯傲,滄浪喜見一澄清”[7]290等。上述詩歌多作于康乾年間,詩人均為奉旨入臺的官員,具有官方身份,他們的作品字里行間傳遞出莊嚴神圣的家國意識。以上詩作多被方志收錄并重復刊刻,一定程度上傳達出官方的審美形態與理臺意識。
作為地方行政制度的象征,臺灣衙署兼具文化傳播的功能。乾隆二十八年(1763),臺灣府知府蔣允焄于衙署后方增設“鴻指園”,既作游覽、休憩之所,也兼宴集飲聚會之地。乾隆四十年(1775),知府蔣元樞,基于“臺郡為海外重任,團齋為司土者所居;綱紀政地,自宜整飭,以壯觀瞻”[14]79的理念,重新經營官署空間,打造出“迎暉閣”“景賢舫”“夜告臺”“書齋”[14]79等傳統士人的文化空間。這些空間,可供游賞,可供宴集、吟詠、也可供朝拜神祇、夜觀星象。這些由官員發起的文化展演,展現了傳統士大夫式的生活模式,進一步傳遞出儒家秩序化的深刻內涵,借助這些士大夫所起的示范作用,希冀能夠潛移默化地教化百姓,從而塑造淳厚有序的社會風氣與文化氛圍,使臺灣成為日遷善而不自知的文教之地。
二
如前所述,清代臺灣官署多沿用舊有建筑,較為簡陋。是故,歷任官員往往加以修整,重新布局,改造成集政務、社交、休閑于一體,且適合自身品味的空間,同時努力營造新的文化傳統,通過“參與這些日常操演(performance),得以認識地方,覺得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15]59。改造的典型特征是在衙署后開辟一方具有江南風格的園林景觀,規模雖小,但亭臺樓閣,假山池沼,一應俱全,“茲則五六同心……相與乘舟弄月,蕩漿迎風……,使數萬年以來蠻煙瘴雨之鄉,有茲游為獨開生面,當亦嫦娥之所許也。”[6]112公務之余與同僚俯仰其中,宴飲吟詠,別有一番閑情雅趣。
晚明以降,美學風氣盛行,文人醉心經營水澤山林,將其打造成宜居之所,坐臥行住悠游其中。清代宦臺者致力于空間改造,進而熟悉空間,復置身于空間恣意游賞,不可謂不受此風氣濡染。首任臺廈道周昌“于署后筑小室,中置圖史尊彝,瑯軒滿壁,珍賞盈幾。庭前只植花竹,盆魚拳石依約。西園南墅傍構一亭,顏曰‘寓望’,……復結草作亭,顏曰‘環翠’,以蕉陰竹韻依繞左右。”[6]109-110頗為雅致。草亭右前設一方臺,“天空海闊,而安平勝狀如在幾席。若夫朝潮漲紫,晚照留紅,飛鳥翔煙,孤帆映浪;霧之晨,星之夕,波濤澎涌,爭奇逞媚于樓之前者,皆公麈尾之談資也”[6]110。庭園空間不大,論意境、論韻味,卻并不遜色廣袤的江南園林。繼之的高拱乾在“寓望園”的基礎上興筑“澄臺”與“斐亭”,此過程見諸《續修臺灣縣志》:“巡道署:在西定坊,西向。中曰敬事堂(‘舊志’),其后堂曰鶴馴堂,右有廳曰‘若濟’(俱乾隆五十三年,觀察楊廷理題,有跋)。署后有園,舊曰寓望園(康熙二十五年觀察周昌辟);有亭,曰斐亭(康熙二十二年,觀察高拱乾建。叢篁環植,翠色猗猗,故取衛詩有斐之義。每夏秋間,清風掠樹,竹韻璆然,與海濤聲相和答。亭雖屢圮,后亦屢修,且常易其故處焉。嘉慶四年,觀察遇昌修建)。亭之右,曰澄臺(亦觀察高公建。臺可觀海,升高曠覽,滄溟島嶼,悉入望中。故舊志所稱八景,有‘斐亭聽濤’‘澄臺觀海’之語。嘉慶四年,觀察遇昌題匾)。”[16]86乾隆時翟灝在衙署后興建的“聚芳園”,與澄臺斐亭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春日融和,黃蜂滿院,欹枕聽畫眉聲,雌雄相應。時而隔簾香透,花影參差,蓋酴醉將卸也……蘭蕙、素馨之類,隨地布置,欄檻芬芳,溢于亭榭。[17]9
畫眉、黃蜂、花影,尋常之物卻蘊含著不尋常的生命樂趣,“夫人惟不滯于境之內者,斯可超于象之外……視君之茅舍柴扉,紙窗竹屋,不啻霄壤也”[17]9。作者融情入景,拉近了對象物與自我的距離,使彼此的存在有‘互有主體性’的關系,從而感受‘生活經驗’與‘生存情境’,透過‘生命意識’的升揚,心靈自由的擴大,達到一種‘生命智慧’的體驗過程。[18]284-285這或許是園林給予宦游人最突出的實用性所在。道光十三年(1833),劉鴻翱《臺灣道署斐亭記》曰:
道署小平泉西兩檻外,叢竹千竿蔽日,濃陰交錯;院中有亭翼然,名曰“斐”,蓋取“淇澳”之“菉竹有斐”以名。由亭之東折而北,為“寄云曲舫”;早起,云常滿室中。澄臺在其東南,可望海。臺之外為圃,可習射。泉溢為池,池中堆石為島;雙鷗戲水面,時飛時止。芭蕉大如樹;畜麋鹿,每日午臥蕉陰下。海外奇木異卉,如佛桑,洋桃、文元、桂子、番石榴、黃梨之屬,經冬花蕊不斷。[1]74
斐亭的空間布局極為精巧,室內煙云迷漫,室外濃陰交錯,泉溢為池,堆石為島,各臻其妙。園圃中奇木異卉,經冬不謝。澄臺憑眺,大海咫尺,午臥樹下,或觀雙鷗戲水,或聞滿室花香,愜意之極。有學者指出,“經過修飾整理過的村莊園圃,提供文人閑游觀賞自然生態的場景,植梨花,以待香雪滿庭,植柏樹,除避暑取涼外,夕陽佳月的微光,由搖曳的樹葉間隙透漏投影到居室衣物,均為文人生活中極動人難得的審美景致”[19]326,頗有道理。
道光二十七年(1847),徐宗干在澄臺下方另辟一室,其《退思錄》云:“每日澄臺下小室午后焚香趺坐,閉目靜養片時,最為得力。有句云:綠紗窗裹香煙裊,仙鶴一聲午夢醒。生平嗜新茶,有句云:呼童掃葉烹秋露,對飲清茶是菊花;又,午夢初醒檐溜滴,知曾有雨潤花來;又,詠臺地氣候云:寒露重分身馬路,秋風清拂紙鳶天;又,日添一線紙鳶風,臘月榴花照眼紅。”[20]65斯室清幽,閑暇之余,悠游其中,或焚香打坐,或沉思吟詠,怡然自得。又在荷花池畔修筑“君子軒”,其《君子軒偶記》曰:“檐前結布幔承雨貯缶中,聞挈壺聲;呼童煎茶,聞瓶笙聲。此靜中籟,惟能靜而后其動也中。斐亭前植籬落、種瓜豆,蓄水蒔稻,并種地瓜(即番薯),可以驗晴雨之時。”[20]53聽雨、承雨、煎茶、品茗、筑籬、種植,安靜的時光,慵懶的幸福,儼然成為徐氏生活中的一部分,帶給他一份心靈上的寧靜與安穩。甚者,徐宗干竟在庭院中養起鵝來,其《壬癸后記》云:
斐亭有鹿無鶴,以鵝代之,戲題其欄曰“鶴鶴”。一日,大風雨,斃之,余一雌;友人饋一雄配之。時卵已累累,或云未配以前,卵而不能育也。既配,生二卵,尚未和合,而氣已相感矣。雌伏墻下四十余日,不思飲啄。而鷇出,淡黃可愛。其母已狼狽不堪,雄者同保護之,貍犬皆不敢近。彌月而一鷇死,仍以翼覆之,三月不去。攜而棄之,戛然長號,聞之惻然。此可以見為人子者當思父母恩勤之岡極矣。[20]75
上述描寫極富生活情趣,徐氏從養鵝中收獲諸多樂趣,更從母鵝的護仔行為,感受到人間至愛。這份安寧自適的“使署閑情”讓徐氏備感珍貴,遂延請畫家蒲玉田為其描繪在臺為官的生活圖景,“屬畫臺地花果六幅,又為乘風破浪圖一、登岸圖一、斐亭課子圖一。嘗擬畫冊十二幀,曰重譯宣綸(歸化生番)、靜參定讞(登臺打座)、斐亭草疏、榕壇選文(海東書院)、鶴堂校書(署有馴鶴堂)、鹿場習射、北郊試馬、西港造舟、禳風釃酒(祭海)、喜雨品茶、瓜圃學農(有句云:曰晴而晴、曰雨而雨,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竹軒聽讀(斐亭前荷池,其旁有廊,新題君子軒)。”[20]80以上場景,可以說囊括了徐宗干在斐亭、澄臺,以及澄臺下方“君子軒”的全部生活,公務與休閑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傳統士人的閑賞美學于此清晰可見。
三
現代人文地理學認為,“地方”的形成取決于人類對空間的意向,而空間要轉而為地方,必須經由人的居住、以及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性”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的建立。[3]86對宦臺者而言,離開故土,任職于臺灣這塊邊疆之地,羈旅之愁在所難免。何以解憂?顯然,在衙署內修建類似中原風格的園林亭臺,悠游其中,能使身心得到放松,從而消解羈旅之苦,逐步建立起“家園”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宦臺文人在陌生的場域中扎根,并建立屬于自己的領域,有學者指出,這是“為了一種歸屬(belonging)的感覺,全然是我們天性的一部分。在場所中,有根使我們在面對世界時有了一個起點,并讓個人在事物的秩序中掌握住自己的位置。”[21]7且看臺廈道高拱乾《澄臺記》一文,修筑動機與目的可窺一斑:
臺灣……厥土斥鹵,草昧初辟,監司廳事之堂,去山遠甚。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安息之所,耳目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郁陶,四顧隱然,無以宣泄其懷抱;并所謂四省藩屏、諸島往來之要會,海色峰光,亦無由見。于是捐俸鳩工,略庀小亭于署后,以為對客之地;環繞以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筑臺于亭之左隅,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7]270
高氏言臺灣地處偏遠,雜沓無章,在臺為官常有心志郁陶之感,筑臺乃為舒嘯消憂之故。于是,在官署一隅辟建室與亭,營造具有中原風格的亭臺樓閣,目視佳景,耳聽濤聲,既可消愁解憂,達到“浩渺心俱闊,澄清志若何”[7]286的超然物外;也可登臺觀海,回望故土,聊卻思鄉之情。同時,將渾沌漫亂的地理景觀重新修葺,營造成文人宴飲、交游、聚會之所,進而將其納入中原文化圈,借此建構起個體與地方間的歸屬感,“這樣的賞景位置不僅僅因‘美感距離’,形成了‘距離美感’,而且這個‘距離美感’還使得蠻荒的臺灣景色不再具有危險性。這種‘俯視’‘全覽’的觀景位置不僅消解了大陸文人對荒蠻臺灣所產生的恐懼感,也使得創作者觀賞臺灣山水時產生較為朗闊的心情”[22]133。
高拱乾編纂《臺灣府志》時將“澄臺觀海”“斐亭聽濤”列入“臺灣八景”,二者也因此成為宦臺文人鐘愛的吟詠題材。八景作為具有象征意義的景觀,實是一種建構出的文化認同,“認同(identification)意指去經驗一個有意義的完整環境,然而在這整體之中有些事物的特殊重要性必然會顯現出來”[23]202,自高拱乾修筑澄臺、斐亭,并劃定臺灣府八景來說,此后開啟縣級、廳級,乃至于園林的八景取景與命名風氣,相關八景詩作品紛然而至,達五百三十二首之多。[24]141可以說,清代臺灣八景的產生與鑒賞,來源于宦游文人集體認同感的凝聚,“他們擇定、興建景觀,并透過一連串的八景詩加以吟詠,且詩作又多收錄于方志之中,重復抄錄、吟詠,其傳達出的意識形態,讓八景成為一個既定的‘專門詞匯’,而這樣反復經由個體與社群之間互動經驗的累積,物質空間被編排成有意義的秩序,空間秩序的長時間聚合,于是成為了該地方的實質內涵”[25]29。在這樣的空間內涵中,宦游文人才得以充分感受到適得其所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乾隆初年,斐亭倒塌,臺廈道莊年于舊址上重修斐亭,修繕一事見其《重葺斐亭記》。乾隆三十一年(1765),臺灣知府蔣允焄“增飾澄臺舊跡,更移構斐亭于其東偏”[26]49,“亦于署后構褆室,又創延熏閣、挹爽廊、檥月樓、魚樂檻、接葉亭、花南小筑、花韻欄,復辟叢桂逕、得樹庭、小仇池、瑞芝巖、疊云峰、醉翁石”[26]49。新辟的十三處景觀,名稱多雅致有趣,彰顯文人的文學涵養與生活情趣,并與原有的二景,合為“褆園十五景”:“計新辟者凡十有三勝,各有記。澄臺、斐亭或新堊之,或移置之,名從其舊,不復記,然合之為勝十有五,凡此皆有室也”[16]87。這些景觀,從布局到命名,從內在的經營理念到外在的建筑格局,均與江南園林異曲同工。置身其中,仿佛回到故土中原,從而產生深厚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漂泊之苦得以暫時消除與忘卻。
此外,臺灣海峽以風濤噴薄、瞬息萬變著稱,外加科學知識的不足與航海技術的落后,橫渡重洋可謂是一場生死搏斗,葬身魚腹者十之八九。而當他們成功越洋,回望彼岸時,曾經波云詭譎的海洋卻又成為鄉愁的誘發因子,“海上棲遲及早秋,登臺騁望思悠悠”[8]975,登臺遠眺,觀景傷情,揮之不去的是對故土的眷戀與渴望。“澄清惟此景,聳立素懷開”[7]294,澄臺、斐亭的出現,同時又為這份無法言喻的離愁別緒提供了傾吐憑借。覺羅四明有詩曰:“駭浪吼聲度竹,高臺雨氣生寒。莫道天涯寂寞,憑欄是處奇觀。”[8]960登臨澄臺,目之所極盡是變幻萬千的“奇觀”,天涯寂寞得以盡情釋放。又如劉鴻翱的《臺灣道署澄臺記》:
余家東海之表,萊郡有勺蠡亭,緣事至郡,必登亭俯瞰滄溟……庚寅,余升守彭城,登云龍戲馬臺,顧視黃河洪流;而觀于海者難為水,未嘗不思勺蠡,冀得再覽其勝。癸巳,余由南韶連道調臺灣道,……惟道署之澄臺,見西南海之一角。臺下屋三楹曰“斐亭”,郡注所謂“斐亭聽濤”也……余鄉勺蠡之奇特,殆未能逾乎此也![11]75-76
不難發現,對宦游者而言,家鄉永遠是最美的守望,不管任職何地,游覽何處勝景,總在不自覺中以故鄉作為參照系,借由澄臺遠眺,抒發渡海的無奈與惆悵,以及濃濃的游子情。乾隆十年(1745)出任巡臺御史的范咸,其《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之二曰:“云日有情隨我往,鯤鮞未辨悔空游。劇憐春瘴迷人目,清夢何從覓九州。”[27]42處處透顯出羈旅異鄉的寥落與孤寂。又如張琮《澄臺觀海》:“微軀薄宦重洋隔,欲叩君恩仗呼吸。”[13]413鋪陳出任職他方的無奈和濃郁的愁緒。“借問中原路,奔騰落日邊”[9]30,他鄉“縱有閬苑蓬瀛,不若吾鄉瀲滟空蒙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系吾思也”[5]42,深沉的鄉愁,溢滿筆端。
言而總之,衙署是地方行政制度的象征,作為當時權力核心的一部分,衙署后方所開辟的園林景觀及其相關詩文書寫,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宦臺官員入臺后,面對陌生空間,選定、修筑、甚至改造景觀,不只是建構自身與場所之間的地方感,同時勾連出家園的認同意識,并以此重新詮釋臺灣的人文歷史與文化情境,從而構筑出中原文化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通過官署這一空間場域,將中原文化價值與儒家秩序化的深刻內涵予以發揚、深化。而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官署則融入了個體獨特的生活美學,經過重新置放、編排過的衙署空間,清幽雅致,置身其中,或煮茶,或品茗,或聽雨,舒嘯解憂,怡然自得,透過宦臺者在衙署中日常生活的文化操演,展現了傳統士人的閑賞美學。而情感性的地方內涵則反映出濃郁的鄉愁,憑欄遠眺,腦海中浮現的是魂牽夢縈的故土之景,筆端流注的則是深切的生命體驗。風行草偃,對于景觀的欣賞與經營也從衙署空間延伸出去,成為文化意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