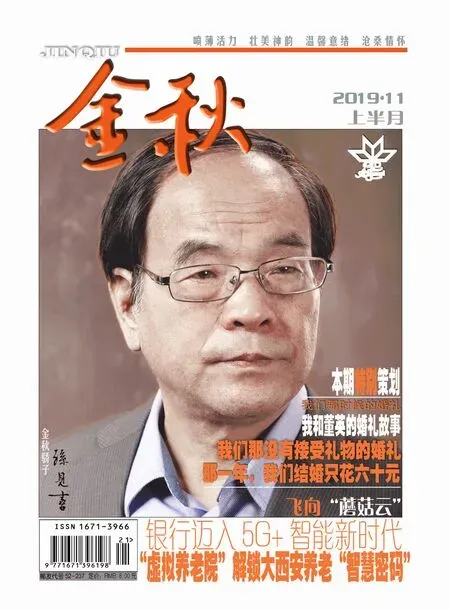飛向“蘑菇云”
文/李民倉
我國在進行核試驗時,能參觀核爆炸盛況的人,都要在遠離爆心的安全距離之外并戴上10萬倍的護目鏡。但有一群人,卻要在原子彈爆炸時,冒著核沾染的風險,駕駛飛機飛向原子彈爆炸時產生的“蘑菇云”進行“取樣”。取得樣品后,再經過有關科研機構的儀器分析,可以準確評價核爆炸當量和沖擊波大小、光輻射強度以及放射性沾染能量的釋放效果。
用飛機穿越“蘑菇云”取得的樣品,雜質最少,純度最高。但飛機取樣穿云進入過早,“蘑菇云”還未完全形成,沖擊波能量正在釋放中,擾動氣浪強、熱度高、渦流大,有可能造成機毀人亡;穿云進入過晚,蘑菇煙云逐漸散開,雖然安全系數增大,但取得的樣品能量不夠、質量差,難以達到核爆炸試驗劑量的收集標準。考慮到安全問題,國外取樣都用無人機。開始我國沒有無人機,只能由飛行員駕機取樣。執行取樣任務前,許多飛行員都像戰爭年代上戰場一樣,做了犧牲的準備,有的交了“最后一次黨費”,有的寫了遺書。

在飛機取樣的同時,還有其它手段取樣。比如地面盤取樣、火炮取樣、火箭取樣等。地面盤取樣是在原子彈試驗時,在試驗場區的地面上布設許多取樣盤接收從“蘑菇云”中沉降下來的放射性粒子。火炮取樣是用122加農炮向“蘑菇云”發射直徑為45厘米的白色降落傘,采集云中的放射性粒子。火炮取樣雖然簡單易行,但不能滿足防化分析的更高要求。1966年5月,在我國第三次核試驗即第二次空爆試驗后就不再使用。我國從第一次氫彈試驗開始,即使用“和平二號”固體火箭取樣。但之前主要依靠飛機穿過“蘑菇云”取樣。
馬蘭村場站是1960年專為核試驗而建立的一個場站,擁有馬蘭、開屏兩個機場。馬蘭村場站1963年前隸屬于國防科委21試驗基地,1963年轉隸空軍。我從1968年起在這個場站服役18年半,基本參與了這期間的所有核試驗,見證、參與保障了1968年后的各次核試驗的投彈和穿云取樣工作。1985年馬蘭村場站轉隸航空兵37師,我又先后任該師110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和不少參加過穿云取樣的同志有共事之誼。
伊爾12、伊爾14運輸機穿云取樣
1964年10月16日,我國首次核試驗(塔爆)成功。擔任穿越“蘑菇云”取樣任務的是一架伊爾-12運輸機(03號),機組有機長郭洪禮、副駕駛李傳森、領航長季獻康、領航員張連芳、通迅主任王景海、空中機械師耿君等。取樣飛機攜帶兩個蘇制138取樣器實施取樣。飛機由開屏機場起飛,上升到7000米平飛兩次穿過“蘑菇云”。16時26分完成任務,在開屏機場落地,投下取樣器。兩個多小時后,在場的另一架伊爾14運輸機起飛,將樣品送往北京進行分析化驗。分析結果表明,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1965年5月14日,空36師李源一、于福海機組駕蘇制杜16(4251號)轟炸機,成功完成我國第一次空爆原子彈試驗。取樣飛機是各攜帶兩個210型取樣器的兩架伊爾14(14512號、14501號)。飛機在8300米高度穿越蘑菇云,兩分鐘后再次穿越,圓滿完成任務。
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四次核試驗—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這是我國進行的唯一一次兩彈結合的核試驗。兩架伊爾14飛機進行取樣,這是我國最后一次用運輸機取樣,以后的核試驗取樣均由殲擊機承擔。
殲擊機穿云取樣
1966年5月9日,我國第三次核試驗。新聞公報特意指出這是一顆含有熱核材料的原子彈,說明中國已經向氫彈進軍了。這次試驗,空14師出動了9架殲6飛機,在爆后30分到70分鐘之內實施取樣。這是我國第一次用殲擊機和第一次用09—1型取樣器采集煙云樣品,標志著我國的飛機取樣取得了重大進步。
1967年6月17日,空36師108大隊政委徐克江機組駕轟六甲型轟炸機(代號726)第一次空投氫彈試驗成功。空6師16大隊三中隊6架殲六飛機分4批參加了空中取樣,同時首次使用固體火箭取樣。同年12月24日,空投核裂變試驗成功,空6師4架殲六飛機參加了空中取樣。
1968年12月27日,我國進行了第一顆使用钚的熱核試驗,空10師出動轟五4架(主1備3)實施空投,取樣由空24師出動10架殲六完成。1969年9月29日和1970年10月14日,還進行了空投氫彈試驗。
從1971年開始,穿云取樣的任務由空軍航空兵第37師的109團、111團分別擔任。109團駕殲六飛機參加穿云取樣的先后有4批10人,111團駕殲六參加穿云取樣的先后有4批15人。空軍烏魯木齊基地軍史館稱他們為穿越核蘑菇云的25勇士。
1971年11月18日,含钚原子彈以塔爆形式爆炸。1972年1月7日,空5師的楊國祥團長駕強五K(11246號)強擊機空投小型核武器試驗。這次任務由于氫彈推進裝置電路短路,投彈失敗,成為世界核試驗史上絕無僅有的帶氫彈著陸的一出傳奇故事。之后的5年中,還進行過4次核試驗。
1976年9月26日,局部溶解“特殊核彈”試驗,爆炸當量2萬噸。111團飛行二大隊副大隊長宋占富、中隊長張增榮、飛行員高國明參加穿云取樣。這次試驗中,還進行了我軍唯一一次原子條件下的陸空聯合演習——7601演習。總指揮是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空9軍副軍長郭子潭為空軍前指(設在開屏機場)指揮員。空降兵15軍、空36師、空37師、陸軍4師等部隊參演。109團的飛行副大隊長李國英、飛行員陳敬海在原子彈爆炸前擔任偵察藍軍陣地任務;爆炸后先起飛通過爆心航拍照相,再次起飛擔任空中掩護地面紅軍突擊藍軍陣地任務。任務在場期間,毛澤東主席逝世,故9月18日,空軍試驗指揮部組織在場的參試部隊在馬蘭村場站露天廣場舉行了追悼大會。
圖2為該器件的轉移特性曲線(反向柵壓掃描)和輸出特性曲線,器件的最小亞閾值斜率為0.95 V/dec,具有約6.5個開關比,器件的最大遷移率約為3 cm2/(V·s)。該器件的輸出特性曲線如圖2(b)所示。在坐標原點附近,其轉移特性曲線基本呈直線,表明該器件的源、漏金屬/半導體接觸質量較好;但仍有微小的整流特性,表明源、漏接觸區域存在一定的肖特基勢壘。通過適當的退火或其他優化處理,可以進一步減小肖特基勢壘[8]。
1976年11月17日,我國最大當量500萬噸氫彈空投試驗。由于生成煙云的底高要超過17000米,一直使用的殲六飛機因其升限不夠,改用殲七飛機取樣。
使用無人機取樣
實際上在1977年的那次空爆試驗時,就進場了5架無人機,但那時只是做滑行試驗,并未用于取樣。
1979年進行21-715空爆任務時,第一次用無人機空中取樣。9月13日空爆零時定為12點,由于核彈減速傘的引導傘技術上出了毛病,造成核彈“光彈”落地,未在空中爆炸(落地后化爆),試驗沒有取得預定效果。取樣原計劃由兩架無人機擔任,第一架無人機在飛機投彈后按預定計劃起飛了,但發生了失控,落在大漠深處。按試驗指揮部要求,在空軍開屏指揮所擔任指揮員的空9軍司令部楊振升副參謀長帶領我和空一基地王康副主任、南航一名領導、基地作試處一名副處長和基地一名志愿兵司機乘米八直升機升空尋找無人機。記得第一次沒有找到,第二次起飛在大漠深處找到了。經檢查,由于沙漠沙層很厚,無人機完好無損(當時的無人機無起落架,機腹著地)。但無人機根本無法運出去,所以當場決定:由南航拆取飛機上的自動駕駛儀和幾個重要部件后放棄回收。
1980年10月16日,進行了爆炸當量20萬噸的我國第23次核試驗,因是我國實際上的最后一次大氣層核試驗,故被稱為羅布泊上空升起的最后一朵“蘑菇云”。取樣用的是“長空1號”無人駕駛飛機,還最后一次使用了1979年備而未用的6枚“挺進-2號”火箭取樣,都取得了圓滿成功!
本來,我國還要在1985年進行一次空爆試驗,代號21-717。參試部隊從1984年10月初陸續進場,其中有轟六飛機兩架、無人機3架、殲六飛機兩架(模擬無人機飛行),要求11月中旬完成一切準備待命試驗。但到1985年1月3日情況起了變化,外交部給中央打了報告,講了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有8條不適宜搞空爆的理由。經總理、總書記、鄧小平主席批示,中共中央決定不執行本次任務,今后也不再搞大氣層核試驗,轉為只進行地下核試驗。1996年7月29日,我國在成功進行了一次地下核試驗之后宣布:“暫停核試驗”。1996年9月,我國政府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無私奉獻的參試人員
每次核試驗,都有無數參試人員的無私奉獻。
飛機取樣過程中,為了防止放射性煙云微粒進入座艙,要關閉供氣開關飛行,座艙容易產生負壓,機務人員要在本場或到馬蘭機場想方設法使座艙的密封性由原來不得低于90秒增加到3分鐘以上。有的還要對飛機重新噴漆,以減少飛機表面細小縫隙進入放射性微粒。取樣飛機到場后,要由馬蘭村場站定檢中隊和任務機組卸下原來的發動機,換上中隊保管的專門取樣用的發動機。再由中隊高空取樣組對飛機總掛部分進行簡單改裝,也就是在殲六飛機的火箭架位置加掛空中取樣器。1970年,空12師由師長帶領4架殲六飛機進入馬蘭機場擔負取樣任務時,場站高空取樣組萬云喜同志發現殲六飛機上沒有火箭架便立即向在場的蘭空工程部孟憲志助理報告,為此還驚動了空軍現場總指揮蘭空楊煥民司令員。楊司令當即決定,派專機讓12師軍械人員回去取火箭架來現裝。原來12師這次到馬蘭,由于保密等原因,上級沒有交代清楚,他們以為是出來打仗的(不需要帶火箭架)。

穿越“蘑菇云”取樣返回的飛機,機身沾滿了強放射性物質,成了一個大的污染體。馬蘭機場滑行道西側北邊400米停機坪,是歷次空爆試驗的洗消坪。取樣飛機落地后滑行轉向洗消坪5米左右,機務示意飛行員剎車停住,50米半徑內,輻射測量儀器“嘀嘀嘀”響個不停。機務人員卡著表,進行“標準化”操作:飛機滑入洗消坪3秒,搭好扶梯6秒,擰開密閉把手10秒,攙扶飛行員下飛機20秒;打開總電門,投下取樣器;檢查起飛時的1、4、7電門,恢復射擊按鈕,關閉座艙蓋,插銷子,堵進氣道,堵炮口,蓋蒙布。完成這些動作,大約需要七八分鐘。
定檢中隊的高空取樣器組,在飛機投下取樣器后,將兩臺取樣器分別裝入專用袋,由4名同志抬著快速走向取樣間,取出取樣的核心件樣品濾布,交研究單位密封,待后由專機送北京防化研究所進行分析。
防化連洗消組負責人員和裝具的洗消。取樣飛機飛行員的所有衣服,由防化人員放入專用爐焚毀。飛行員要到達洗消帳篷,一遍遍的涂抹香皂、一遍遍的沖洗,洗完要經過儀器檢測,超過0.3倫,儀器就“嘀嘀嘀”報警。洗消完換上新的服裝,然后由場站衛生隊救護車送去基地546醫院檢查觀察。處理完飛機的機務人員、高空取樣組人員、防化人員最后也必須洗消。1973年6月27日,當量300萬噸旳氫彈爆炸試驗成功,109團取樣機的01號機組代理機械師賈西軍回憶說:我在洗消室里,全身打上肥皂拿毛巾使勁搓,沖洗了3次都不合格,當時洗消室就剩我一個人了。洗到第6遍時,身上多處已擦破了皮,在我拿第7條新毛巾擦干身體出門,才終于達標過關。
防化連的劑量偵察組從飛機落地開始,就要分別對幾架取樣飛機進行定點測量,每架飛機有十幾個點,每隔半小時測一次。大約一周后,等沾染降到一定程度,再由洗消組配合定檢中隊、機組對飛機進行洗消。洗消一架飛機的時間,由開始的37天縮短到25天,最快的加班加點不休息也要干19天。到飛機沾染由開始的幾十萬,降到2200個蛻變數后,才算完成了洗消任務。然后由定檢中隊對飛機機身重新噴清漆、噴機徽、機號,使飛機煥然一新。國防科委曾對參加取樣已過3年的飛機沾染情況進行過跟蹤測量,測量人員說,還能測出核輻射,但對人員健康影響不大。
隨著我國大氣層核試驗的停止,1980年12月底,空軍馬蘭村場站定檢中隊(在試驗中榮立過一次集體二等功、一次集體三等功)被宣布撤編。那42臺多次穿越過核蘑菇云的渦噴六發動機經長效油封,移交給了場站航材庫保管。空軍馬蘭村場站防化連(先后參加了17次核試驗,1979年被空軍評為“硬骨頭六連”式連隊,榮立過集體三等功),在1981年8月編制撤銷,改編為烏指防化連。
穿云取樣是一種精神
原子彈爆炸后的情況轉瞬即逝,進行取樣的飛行員生怕穿云淺了取不到樣,許多同志冒著超劑量核幅射,甚至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完成任務。就拿空37師飛行員取樣來說,按規定飛機進入“蘑菇云”一次,取到1.6倫就可以了。為保險起見,37師讓飛行員掌握,可以不超過2倫。不少飛行員進入“蘑菇云”一次后,本來已達到劑量要求,但擔心取少了影響試驗評價,只要時間允許,就瞞報劑量不足,請示指揮員要求再進入一次,以便超額完成規定的取樣劑。
盡管科學家對穿云取樣的安全性經過多方論證,也采取了當時能夠采取的各種措施,但穿云取樣對飛行員及相關人員的身體傷害還是非常大的。據有關資料顯示:空軍飛行員駕機穿越“蘑菇云”,一次受照射10倫以上的飛行員共9名,他們是:孫榮華22.6倫;潘國興16.0倫;黃仁祥13.0倫;高國明13.0倫;高樹發12.7倫;陳富華11.4倫;翟守東11.0倫;汪亮10.5倫;胡光強10.3倫。一次照射5倫以上不足10倫的有張增榮(9.5倫)等共23名。
取樣飛行員在取樣后身體普遍反應強烈。1964年第一次核試驗駕機取樣的機長李傳森說,他取樣回來10天后,在馬蘭546醫院進行觀察治療時,機組6人頭發全部掉光,5名男性精液滅活75%。機組唯一一名女飛行員張連芳當時28歲,時隔50多年后接受采訪時說,她取樣后第二年結婚,一連兩年,她兩次懷孕都因胎兒發育不正常而流產。幾乎所有飛行員都出現了如白細胞下降、脫發、睡眠不好、無食欲、身體抵抗力下降等癥狀。空37師參加取樣的25名飛行員中,除王汝平同志因飛行事故犧牲外,已有劉懷德(50歲)、李芳春(47歲)、陳富華(75歲)、高樹發(67歲)等均患肝癌相繼過早病故。1976年參加穿云取樣的飛行員高國明取樣后不久頭發全部掉光,白血球大幅下降至危險指標,很多年后才恢復正常。現在他早早出現了雙眼底黃斑性病變,兩個孩子抵抗力弱,總是傷風感冒,連孫子身體抵抗力都比較差。但他毫不后悔地說:核試驗要成功,總得有人付出生命和健康的代價,我有幸能為國家做出這樣的貢獻是我一生的榮幸。從空37師副師長位置上轉業到云南省糧食廳的高樹發同志,患肝癌臨終前一再重復:“我們這代人,確實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國家,個人犧牲與國家利益、國防利益是無法相比的”。
由于保密及其他原因,我們現在還找不出一個完整的投彈、穿云取樣飛行員的名單。空37師飛行員馬既森的老伴和兒子是46年后才知道他當年參加過穿云取樣。2011年清明節前夕是空12師飛行員湯世才(患肝癌,享年54歲)病故近20年,他愛人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湯世才用鉛筆寫的幾頁發黃的信簽,才知道丈夫1970年曾駕機穿越“蘑菇云”取樣。
飛行員取樣帶有記載核輻射劑量的劑量筆,還有一個受到核輻射的劑量記錄,而更多的地面人員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多少核污染。代理機械師賈西軍同志在保障穿云取樣飛機時,剛過18歲生日。但到他近50歲時,剛上大二的兒子被確診為惡性腦瘤,醫生說,兒子的病和他先前所從事的工作有關。當年在馬蘭曾經流傳過幾句話:為了試驗獻青春,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兒孫。這些話正是對許多參試人員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