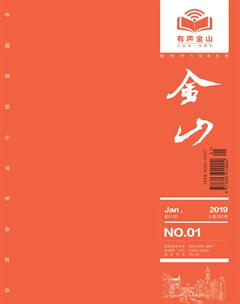1974年天空的魚
津子圍
這 個故事是朱余講給我的,那時我們住圖 書館旁的老宿舍,寢室在一樓潮濕的西北角,對門就是廁所。我記得那是一個雨夜,雨打窗戶的聲音遮蓋了廁所里的滴水聲。半明半暗中,我看不清朱余的表情,只聽到他干澀的聲音。朱余說故事是他父親講給他的——
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很淘氣,常常平白無故地搞點兒惡作劇,比如他用土黃色的包裝紙包一個包兒——那種一斤餅干或者槽子糕或者桃酥的包裝包兒——放在馬路邊兒。點心包放下沒一會兒,準有人撿起來,四下張望,或者尋找丟失者,或者察看目擊者,然后鬼鬼崇祟地放到自己的背包里或者撩開衣襟藏到里面,匆匆忙忙或者慌慌張張地離開。很顯然,那里面沒有點心,是父親放的泥皮兒,那些泥皮兒是泥塘干涸后干裂的一層,很像餅干。拾到點心包的人回家(有性急的也許半路)打開一看,自是空歡喜了一場。父親想象著那個場景就肚子一抖一抖地發笑,甚至笑得岔氣兒。父親的惡作劇之所以屢試不爽,主要是因為點心是那個年代的稀罕物,要錢要糧票,絕對的奢侈品。
我父親最高級的惡作劇是在1974年7月的第一個禮拜天搞的,那天陽光燦爛,父親去供銷社買了一瓶紅燒肉罐頭和兩棵大頭菜。那個時候我父母結婚不久,母親是護士,新婚第三天就隨醫療隊去支援牧區,一走就是三個月。父親接到母親的電報,知道她下午到家,準備晚上包餃子迎接母親。父親哼著小曲走出供銷社的大門,來到街邊,隨意地手搭涼棚,看了看熱辣辣的太陽,望的時間并不長,等他放下手時,發現身邊有兩個人也跟著望向天空。
一個齜著黃板牙的矮個子問父親:“你看見什么了?”父親狡黠地笑了,又開始鄭重其事地看著天空。“到底看到什么了?”另一個滿臉青春痘的瘦高個兒問。父親不說話,只管抬頭看天。
不一會兒,湊過來十多個人,人們都仰望天空,一邊望還一邊議論著。“看見了,看見了!”有人說。“在哪兒?”有人問。“在那兒,你沒看見嗎?你真笨!”“哎呀,可真是的,我看見了,看見了!”“哪兒呢,哪兒呢?”
越來越多的人圍攏過來,還有老人、小孩和婦女。一個人在父親身后拍了一下,說:“閃個空兒,你擋住我了。”我父親挪了兩步,又聽到一個老人喊:“別擠!擠什么呀!”一個女人喊:“你踩我腳后跟兒啦!”“我踩了嗎?別瞎賴呀!”男人的聲音。“缺德!”女人嘟噥。
“別碰我啊!”小伙子的聲音。“我碰你怎么啦?”另一個小伙子的聲音。“你再碰我一下試試!”“我就碰了怎么的!……”兩人吵了幾句,就找地方武力解決去了。
我父親已經悄悄擠出了人群。走出大約一百米后,他回頭望了望,發現人們還在仰望天空。
父親向家走去,笑了一路。
朱余說:“自那天算起,10個月后我來到這個世界,我父親給我起的名叫朱魚。我覺得這個名字太土,上大學之前給改成了朱余。”
畢業后我和朱余天南海北的,聯系也少了,可他講的故事我久久不忘。一個雨夜我給朱余掛了電話,問他:“你講的故事和你的名字‘朱魚有什么關系嗎?”他一時沒反應過來,我復述了他父親仰望天空的事兒,朱余笑了,他說那天傍晚,母親回家對父親講,供銷社門口一群人在看天空的魚。父親問母親:“你也看了?”母親說:“是啊,我不僅看了,而且我還隱隱約約看到了魚。”
朱余問我:“這么晚了給我打電話就這事?”
我說:“嗯!”
(獲第十六屆中國微型小說年度獎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