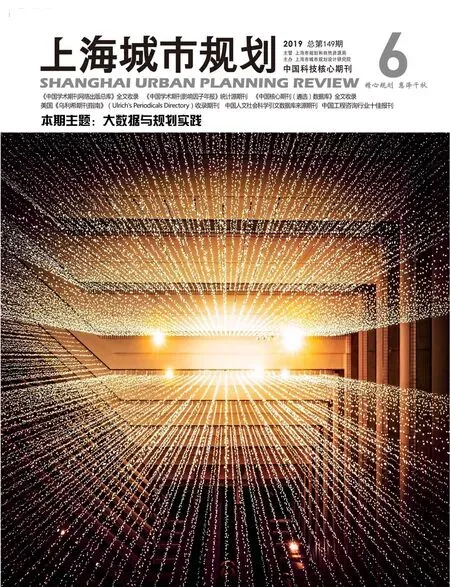基于多源大數據的軌道交通線網與上海城市中心體系匹配度測度研究*
謝昱梓 鈕心毅 XIE Yuzi, NIU Xinyi
0 引言
超大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城市中心體系。軌交線網與城市中心體系的耦合和互動是城市交通與用地一體化發展長期關注的議題。隨著上海多中心城市空間結構的不斷發展,發展大容量、高速度、低耗能的軌交成為必然選擇。上海軌交網絡在外環以內已經實現網絡化運營。軌交在承載上海城市功能流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上海軌交運營里程不斷增長、城市多中心格局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協調軌交線網規劃和城市中心體系規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軌交與城市中心體系互動、軌交支撐城市多中心空間結構等議題已有較多研究。比如,從軌交站點、線路出發,通過對站點數量、軌交線路附近服務人口數量等進行測算[1];或是從城市中心出發,計算中心附近某一范圍內的軌交站點數量等指標來衡量軌交與城市中心體系之間的匹配程度[2]等。
近年來,城市空間結構研究中出現了用功能聯系表征空間結構的新研究范式。很多學者從功能聯系視角研究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并取得了一定進展[3-4],他們使用交通調查數據來表征功能聯系,或是通過問卷調查獲得功能聯系數據[5-6]。隨著手機信令數據等大數據出現,從中提取的功能聯系特征也能用于城市空間結構研究。其中,根據手機信令數據的時空特征,從中分離出通勤等功能聯系,用于研究城市就業中心體系[7]487、公共活動中心體系[8]65,[9]。此外,隨著各個城市軌交系統普遍使用智能公交卡,軌交刷卡數據也能在城市空間結構研究中發揮作用。從軌交刷卡數據中提取出乘客使用軌交出行的流向、流量,也能用于功能聯系視角下城市中心體系研究[10-13]。
為了整體地認識軌交線網與上海城市中心體系的匹配程度,以下將使用兩種大數據認識不同類型的功能聯系。使用軌交刷卡數據,研究軌交出行功能聯系視角下的城市中心體系;同時使用手機信令數據表征全方式出行聯系下的城市中心體系;將兩者進行比較,量化分析軌交線網與上海城市中心體系匹配程度,進一步探討兩者匹配程度的影響因素。
1 城市中心體系與軌道交通匹配
1.1 全方式出行功能聯系和軌交出行功能聯系
按照城市中心承擔的主要職能,一般可以將城市中心體系分為就業中心體系和公共活動中心體系兩大部分。在功能聯系視角下,就業中心是由“居住—工作”功能聯系定義,公共活動中心是由“居住—游憩”功能聯系定義。
手機信令數據的用戶軌跡表示了包含所有交通出行方式的全方式出行軌跡,能從信令數據計算出用戶“居住—工作”“居住—游憩”功能聯系,測度出全方式出行功能聯系視角下的中心體系。軌交刷卡數據的用戶軌跡僅表示了軌交出行時空軌跡。從軌交刷卡數據能計算出軌交乘客的“居住—工作”“居住—游憩”功能聯系,并測度出軌交出行功能聯系視角下的中心體系。這也是整個軌交線網承載的功能流動的表現。
因此,可以將全方式出行功能聯系視角下的城市中心體系作為固定比較對象。將軌交出行功能聯系視角下城市中心體系與其對比,依據兩者一致性程度判斷軌交網絡與城市中心體系的匹配程度。軌交網絡與城市中心體系的匹配程度可以表示為軌交出行表征的功能聯系與全方式出行表征的功能聯系之間的匹配程度。
1.2 就業中心和公共活動中心及其范圍界定
本文以上海中心城區內有軌交服務的就業中心、公共活動中心為研究對象。就業中心包括兩類。第一類為有軌交服務的城市主、副中心,及地區級公共活動中心,如南京東路市級商業街、徐家匯市級副中心等。這一類屬于服務業就業中心。第二類是有軌交服務的產業園區,如漕河涇開發區、彭浦工業區等。這一類屬于制造業就業中心,部分已經轉型為生產性服務業就業中心。以上兩類就業中心合計41個。本文中的公共活動中心包括有軌交服務的城市主、副中心,以及地區級公共活動中心共31個。如就業中心、公共活動中心的規劃邊界直線距離400 m以內存在軌交站點,則視為有軌交服務。
1.3 規模等級一致性和來源范圍一致性指標
采用規模等級一致性、來源范圍一致性兩個指標測度軌交網絡與中心體系的匹配程度。規模等級一致性是全方式出行表征中心規模等級、軌交出行表征中心規模等級的相關性。中心規模等級以在該中心工作或游憩的人數總量、密度等表示,通過計算相關性進行量化判斷。相關性越高,說明兩個體系的規模等級一致性越高,軌交線網與就業中心匹配度越高。單個中心的殘差值可用于量化表示該中心自身的等級匹配度。
來源范圍一致性是測度在軌交出行、全方式出行視角下,分別同一個中心聯系范圍的一致性。計算公式為:

其中,中心核心腹地是該中心就業者或游憩者由近及遠的前80%的居住地范圍,由手機信令數據測度得到,表達了該中心全方式出行的主要來源范圍。來源范圍一致性指標測度了軌交對單個中心的支持程度。該指標的數值范圍是0—1,值越大表示來源范圍一致性越好,該中心的軌交匹配程度越好。
2 數據和數據處理
2.1 軌交刷卡數據
本文使用2016年9月的上海軌交刷卡數據,為持有公共交通卡乘客的軌交全樣本數據,不包括單獨購票的單程票、一日票、多日票在內,總刷卡次數為2.679億次,平均每天約893萬人次。2016年9月的上海軌交刷卡數據包括了軌交全網14條線路(不含金山鐵路支線和磁浮線),共348個站點。經過識別用戶完整合理出行記錄,清洗虛擬換乘數據等預處理過程之后,最終得到2016年9月共有129 231 515次軌交出行記錄,平均每天約430萬次。
2.2 手機信令數據
本文使用2015年11月連續10個工作日、6個休息日的上海聯通手機信令數據。選用該數據集是因為其時間與前述軌交刷卡數據的時間較為接近,反映人群活動規律可以相互比較。采用丁亮等[7]486,[8]64使用的方法識別手機用戶居住地、工作地、游憩地。研究共識別出上海中心城區內80.5萬個既有居住地、工作地,并且居住地和工作地位置不同的手機用戶;還識別出休息日588.1萬人次的常住用戶游憩出行。
2.3 軌交通勤識別
根據通勤的一般規律,參考相關研究[13-14],根據上班時間、下班時間進站站點在1個月中的重復率,識別軌交乘客的居住地站點和工作地站點。
工作日6:00—9:00,某乘客首次進站站點在1個月中重復大于等于12次,將其識別為該乘客的居住地站點。

其 中,F為 頻 數,Mode為 眾 數,Mn(n∈(1,2,…,21)為 該 乘 客 在21個 工 作 日6:00—9:00點首次進站站點。
將某乘客在工作日16:00—19:00進站次數重復最多且超過12次的站點識別為其工作地站點。

其 中,F為 頻 數,Mode為 眾 數,Nnn(n∈(1,2,…,21)為該乘客在21個工作日的16:00—19:00進站站點。
在識別乘客的居住地站點時,若乘客在1個月內工作日6:00—9:00的首次進站站點不是唯一的,且進站頻數前2位的站點互為同一線路上的相鄰站點,則將進站頻數最高的那個站點設為其可能居住地站點,其進站頻數等于該2個站點的進站頻數之和。再將更新之后的進站頻數與設定的閾值進行比較,來判定是否能識別出該乘客的居住地站點。工作地識別同樣使用上述規則。
最終識別出1 090 909張軌交卡對應的居住地站點,1 090 401張軌交卡對應的工作地站點,1 081 740張軌交卡同時對應的居住地站點和工作地站點,由此建立起了軌交出行表征的“居住—工作”功能聯系。按軌交站點計算,共58 863對通勤聯系,其中通勤流量大于600人/d的通勤聯系如圖1所示。總體而言,軌交通勤的主流是向心流。強軌交通勤聯系主要有兩種:一類是外環外站點(佘山、泗涇、徐涇東、唐鎮等站)前往中環附近就業中心的通勤聯系;另一類是各個區域前往內環內就業中心的通勤聯系。漕河涇是具有最強軌交通勤聯系的就業中心。每天通勤人數大于1 000人的通勤聯系有12條,其中8條都是前往漕河涇。
2.4 軌交游憩活動識別
游憩活動是指在休息日居住地、工作地以外“第三場所”的“非職、非住”行為,包含狹義的購物等游憩行為在內,也可能包含符合這一規則的其他行為。對于識別出居住地、工作地站點的軌交乘客,在休息日9:00—21:00,在非居住地、非工作地的出站站點識別為游憩地站點。

圖1 軌交的強通勤聯系(單位:人)

其中Mhome和Njob是軌交通勤者的居住地站點和工作地站點,Pn為常規游憩時間的出站站點。
最終從1 081 740個軌交通勤者中識別出了677 529人在休息日發生過游憩行為,共發生了2 026 844人次軌交游憩出行,平均每個休息日發生22.5萬次軌交游憩出行。按軌交站點計算,共72 385對游憩聯系,將流量大于1 000人次的游憩聯系定義為軌交強游憩聯系(見圖2)。其中,游憩人次大于2 000人次的游憩聯系有7條,分別是佘山—泗涇、九亭—七寶、泗涇—七寶、廣蘭路—金科路、佘山—七寶、芳華路—龍陽路、淞虹路—中山公園。總體上看,內環內不存在強軌交游憩聯系,而部分中環之外地區的軌交線網密度雖然相對較低,但是人們更加依賴軌交進行游憩活動。
3 就業中心體系與軌交匹配度測算
3.1 就業中心規模等級一致性
將手機信令數據識別出的就業者按照基站空間位置匯總到對應就業中心,得到每個中心的就業者數量,用就業密度表示全方式通勤視角下就業中心等級。將軌交刷卡數據識別出的就業者按照軌交站點空間位置匯總到其對應的就業中心,得到每個中心軌交通勤就業者數量,并采用“單站就業量”評估各就業中心在軌交通勤視角下的規模等級(見表1)。

圖2 軌交的強游憩聯系(單位:人次)

通過梳理可知,全方式通勤聯系視角下高規模等級就業中心集中在內環內,軌交通勤視角下高等級就業中心分布較為離散。漕河涇開發區、張江科學城均為中環附近、中環之外的高等級就業中心。軌交通勤視角下,就業中心體系“多中心”趨勢更為明顯。
將信令數據測度下的就業密度和軌交刷卡數據測度下的單站就業量標準化后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兩者呈弱的線性正相關關系,R2為0.420,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回歸模型殘差呈正態分布,不存在明顯的空間自相關關系。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規模等級一致性測度下,上海軌交線網與就業中心體系總體匹配較好(見圖3)。
但仍有部分就業中心偏離趨勢線較遠,軌交匹配程度差異較大。例如,張江科學城、人民廣場、陸家嘴是負殘差絕對值的前3,表示這3個就業中心在軌交通勤視角下的等級要遠高于其在全方式通勤視角下的等級。這3個就業中心都以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對就業者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由于具有專業技術就業者的選擇余地較少,形成這3個中心的就業者通勤距離相對較長,更傾向于選擇軌交通勤。長壽地區中心、大寧地區中心、老西門地區中心是正殘差絕對值排前3的就業中心,表示這3個就業中心在軌交通勤視角下的等級要遠低于其在全方式通勤視角下的等級。這3個就業中心都屬于等級較低的就業中心,且產業多為生活性服務業,就業者多為就近就業,使用軌交通勤的就業者相對較少。這說明在規模等級一致性測度下,產業類型也會影響軌交線網與就業中心匹配程度。

表1 兩種視角下的規模等級位序排前10的就業中心

圖3 就業密度和單站就業量的相關性

圖4 就業中心來源范圍一致性
3.2 就業中心來源范圍一致性
采用公式(1)計算各個就業中心來源一致性,采用自然間斷點分類法,按數值高低分為 “高”“較高”“中”“較低”“低”5類(見圖4)。屬于“高”類的就業中心有:南京東路市級商業街、南京西路市級商業街、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屬于“較高”類的就業中心有:淮海中路市級商業街、控江地區中心、吳淞工業基地等;屬于“中”類的就業中心有:張江科學城、金橋工業區、安亭汽車產業基地等;屬于“較低”類的就業中心有:桃浦工業區、江灣—五角場市級副中心等;屬于“低”類的就業中心有:真如市級副中心、康橋工業園區等。從來源范圍一致性的空間分布上可知,浦西各就業中心與軌交的匹配程度優于浦東,內環內各就業中心的匹配程度普遍好于內環外。來源范圍一致性高低與就業中心產業類型無關。
來源一致性與各就業中心核心腹地范圍內軌交線網布局直接相關(見圖5)。以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的就業中心中,南京東路、南京西路與軌交匹配較好,陸家嘴、張江科學城與軌交匹配較差。外環附近單條軌交線路服務的就業中心如外高橋保稅區、吳淞工業基地、莘莊工業區等與軌交匹配情況差異較大。因為這些就業中心的就業者以就近居住為主,其附近的軌交線路主要滿足的不是其通勤需求,而是附近居民前往市中心的其他出行需求。已轉型的就業中心中,漕河涇和彭浦已經形成了依靠軌交的“郊區大型居住區—就業中心”的通勤模式,因此其來源范圍一致性較高。

圖5 典型就業心核心腹地與強軌交通勤聯系(單位:人)

表2 兩種視角下的規模等級位序排前10的公共活動中心
4 公共活動中心與軌交的匹配度測度
4.1 公共活動中心規模等級一致性
手機信令數據測度的游憩活動強度表征了公共活動中心在全方式出行游憩聯系視角下的規模等級。將軌交刷卡數據識別出的游憩者按照軌交站點的空間位置匯總到其對應公共活動中心,得到每個中心軌交游憩者數量,采用“單站游憩量”評估各公共活動中心在軌交游憩視角下的規模等級(見表2)。

與就業中心體系的研究方法類似,將手機信令數據測度下的游憩密度和軌交刷卡數據測度下的單站游憩量標準化后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兩者不相關,回歸模型的R2僅為0.165,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見圖6)。這表明軌交線網與上海公共活動中心體系的匹配程度要低于就業中心體系的匹配程度。
4.2 公共活動中心來源范圍一致性
采用公式(1)計算各個公共活動中心的來源一致性。采用自然間斷點分類法,將各公共活動中心根據來源范圍一致性分為“高”“較高”“中”“較低”“低”5類(見圖7)。“高”類公共活動中心有:南京東路市級商業街、陸家嘴、南京西路市級商業街等;“較高”類公共活動中心有:淮海路市級商業街、淮海中路市級商業街、老西門地區中心等;“中”類公共活動中心有:真北商業中心、金楊地區中心等;“較低”類公共活動中心有:江灣—五角場市級副中心、大寧地區中心、曹家渡商業中心等;“低”類公共活動中心有:長壽地區中心、世博商業中心、四川北路市級商業街等(見圖8)。
同樣,各個活動中心的來源范圍一致性與各中心核心腹地范圍內軌交線網布局直接相關(見圖8)。各公共活動中心的來源范圍一致性數值普遍高于各就業中心。這是由于游憩活動具有一定“彈性”,易于根據出行時間、業態等調整,就近趨勢明顯。相比之下,就業活動更具“剛性”,無法輕易調整。除此之外,公共活動中心本身職能也會影響來源范圍一致性。例如,具有面向全市人群的特殊性服務,又具有面向周邊區域人群的生活服務的復合型公共活動中心(如世博源、四川北路)來源范圍一致性均較低。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在就業中心體系方面,采用規模等級一致性測度可知,軌交線網與上海就業中心體系總體上匹配程度較好。其中,軌交線網與中環附近就業中心較好的匹配度提升了這些就業中心的規模等級。規模等級一致性指標表明軌交線網較好地支持了上海就業中心體系 “多中心化”。此外,就業中心產業類型會影響到規模等級一致性指標的結果。

圖6 游憩活動密度和單站游憩量的相關性

圖7 公共活動中心來源范圍一致性
在來源范圍一致性測度下,軌交線網與浦西各就業中心的匹配程度優于浦東,與內環內各就業中心的匹配程度好于內環外。影響軌交線網與就業中心來源范圍一致性指標的主要因素是線網結構與該中心的空間關系。就業中心的來源范圍一致性與就業中心的產業類型無關。
公共活動中心體系方面,采用規模等級一致性測度,軌交線網與上海公共活動中心體系總體上匹配程度較差。這與軌交承載的游憩功能較少,以及游憩出行具有“彈性”有關。規模等級一致性指標表明軌交線網與內環內公共活動中心的匹配度相對較好,軌交線網支持的游憩功能聯系呈現更加 “單中心化”趨勢。
在來源范圍一致性測度下,軌交線網與公共活動中心的匹配程度普遍好于與就業中心的匹配程度。這也與游憩出行具有“彈性”,容易調整有關。影響軌交線網與公共活動中心來源范圍一致性指標的主要因素也是線網結構與該中心的空間關系。公共活動中心的職能也會影響該中心的來源范圍一致性。
5.2 討論
由于軌交刷卡數據不包括單獨購票的單程票、一日票、多日票數據,本文僅針對使用公交卡軌交出行乘客。一般來講,使用公交卡軌交出行乘客很大概率是上海常住居民。因此,本文實際上針對常住居民軌交出行表征的軌交線網與城市中心體系匹配,還沒有考慮軌交承載的外來訪客出行流動。類似南京東路、豫園等外地訪客較高的公共活動中心研究結論可能會受到影響。當前,隨著區域一體化趨勢加快,城際之間出行聯系日益增強,軌交在承載城市功能流動,特別是游憩功能方面必然要考慮訪客的影響。目前上海城市中心體系規劃主要考慮常住居民,但未來城市中心體系規劃特別是公共活動中心體系規劃有必要將訪客納入考慮范圍[15],包含訪客出行的軌交線網與城市中心體系匹配情況值得進一步研究。
居住、工作出行具有明確的規律性,通過多日活動規律從手機信令數據、軌交刷卡數據識別居住地、工作地已成為常規方法。游憩活動卻不同,每個休息日游憩出行不具有明確的規律性。因此,無論是基于手機信令數據、還是軌交刷卡數據識別的游憩出行更多的是一種有依據的推測。本文在已經識別出居住地和工作地站點用戶的基礎上,以休息日、出站站點非居住地及工作地等條件作為約束,盡可能減少識別結果與真實情況的偏差。結果表明,盡管個體在休息日的游憩活動可能是不規律的,但整體層面上,軌交刷卡數據識別的軌交游憩出行、手機信令數據識別的全方式游憩出行空間分布特征符合一般認知。這表明本文對游憩出行識別的方法是可靠的。
5.3 規劃展望
通過乘客使用軌交的時空規律,本文從軌交出行中分離出軌交通勤出行、軌交游憩出行,用于評估就業中心體系、公共活動中心體系。本文認為軌交規劃要更加重視軌交對就業中心體系的支撐作用,要重視軌交線網與就業中心的匹配程度。除了關注軌交線網結構與中心體系的空間關系,也要關注就業中心的產業類型影響。對于公共活動中心,要關注軌交線網結構與中心體系的空間關系。尤其要改善中環及附近的軌交線網與公共活動中心相匹配。研究同時提供了一種定量化測度軌交線網與城市中心體系匹配程度的方法,規模等級一致性和來源范圍一致性指標可以成為評估軌交線網與城市中心體系一體化耦合水平的監測指標。

圖8 典型公共活動中心核心腹地與強軌交出行游憩聯系(單位: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