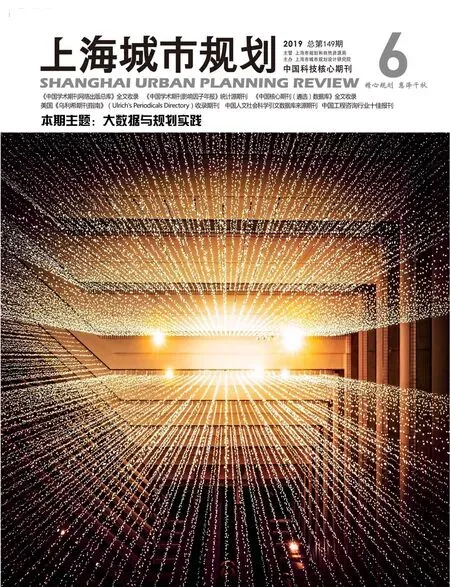城市層面TOD規劃的結構形態解讀
劉 泉 LIU Quan
在城市和片區尺度下,多種典型的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公交導向開發)形態已被規劃領域所熟知,包括美國華盛頓特區阿靈頓縣(Arlington)依托1條地鐵線路形成的廊道開發建設,丹麥哥本哈根由內向外的放射形指狀結構,新加坡連接不同新市鎮的環狀軌道體系及各個新市鎮內部的組團式發展形態,以及我國廣州、上海或日本東京等特大城市中心城區相對均質化布局的網絡模式。但目前國內研究對這些經典案例的分析大多以個案為主,缺少對城市層面整體視角下TOD規劃結構形態的比較。在城市總體層面(或規模較大的城市片區)采用TOD開發模式到底應該呈現什么樣的整體結構?不同的實踐案例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因此,本文對這些規劃實踐的結構形態進行分類,并從空間的整體性、發展的動態性等方面入手,結合建設機制的差異進行對比研究。
1 TOD規劃結構形態的歷史發展
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城市發展受到交通及通信發展的影響[1]251,其中土地利用和交通組織的關系顯得最為重要,特別是在空間形態上,城市的結構布局與主流運輸方式緊密相關[2]。從歷史發展的視角看,TOD規劃與近代鐵路城市規劃建設在空間布局方法上是具有一定的傳承關系的。1990年代,彼得·卡爾索普(Peter Calthorpe)在提出TOD模式時,解釋說他借鑒了城市美化運動、田園城市等近代規劃理論[3]15。也有部分研究提出TOD開發理念和布局方式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日本的郊區鐵路和電車建設時期[4],[5]5,[6],[7]41-42。這說明雖然當代的TOD規劃與近代鐵路城市建設的背景、條件和目標各不相同,但在空間設計層面是具有比較價值的。這種近似性不僅體現在軌道站點周邊地區的規劃布局,以軌道交通為依托對城市整體規劃布局方式的探討也可以追溯到近代時期。
近代城市規劃的一項重要工作即在高速交通時代到來之前探討城市發展建設的新方向[8]137。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1920年代就注意到,自1850年以后,隨著鐵路、汽車、飛機、電話和電報等交通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城市空間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見圖1)[9]134-140。這一時期的規劃師對城市未來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思考,除了柯布西耶以外,在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園城市、索里亞·伊·馬塔(Sori Y Mata)的帶形城市等理想城市模型的研究探索中也均體現相關內容。

圖1 柯布西耶的城市草圖
在汽車交通迅速發展之前,關于理想城市模型的描繪大多與鐵路軌道交通密切相關。在歐洲,隨著鐵路交通的發展,19世紀末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提出以軌道為載體構建城市體系,城市內外的不同組團依靠鐵路實現快速連接[10]107,108。作為現代城市規劃的開端,田園城市模型對后來的理想城市模型的探討產生了極大影響,如1911年亞瑟·庫羅(Arthur Crow)針對倫敦外圍提出的健康城市模型即對田園城市的模型進行了參照[8]135-137。而1917年保羅·沃爾夫(Paul Wolf)的理想城市模型同樣反映出以鐵路為交通載體連接城市中心的類似結構[11]183。日本東京地區基于1915—1935年間軌道網線路建設的良好基礎,于1940年以東京中心為核心的半徑30—40 km區域為對象,提出關東地區大東京規劃模型。這一規劃在對沃爾夫模型的模仿基礎上,綜合綠帶理論、衛星城市理論和阿姆斯特丹會議的精神,對近代規劃理論進行了綜合規劃應用(見圖2)[11]183,[12]41。總體上,無論在歐洲國家還是日本,在鐵路出現以后這一時期的理想城市規劃模型中,依托軌道網絡構建城市空間結構的思路受到普遍重視。

圖2 依托城市軌道和鐵路構建的理想城市模型
在美國,近現代時期的城市發展歷史同樣反映了這種依托鐵路和電車線路進行拓展并形成郊區核心的發展歷程(見圖3)[1]251。加林娜·塔切瓦(Galina Tachieva)重點研究了城市擴張中空間形態演變的方式,將美國郊區發展的歷史分為3個階段,包括從相對集聚的傳統模式到常規郊區開發模式,再到更加分散破碎的蔓延發展模式。其中,在小汽車交通快速發展之前,城市更多的是依靠軌道交通形成的軸帶發展模式[13]。這一時期,城市向郊區的拓展依賴軌道交通支撐的建設,在不同站點地區,市民依靠步行與軌道交通進行銜接,站點地區成為城市拓展的錨點和城市生活的中心[14]。因而這一時期依靠軌道交通進行拓展的發展模式可以被視作TOD發展的萌芽時期[5]5,[15]。
從1920年代開始,特別是在二戰之后,美國公路交通建設超越了鐵路發展,軌道交通的建設受到抑制,小汽車成為城市交通的主宰。1980年代,為了解決城市中心城區的衰敗以及外圍郊區蔓延發展的問題,可持續發展及傳統價值觀開始回歸,土地利用和公共交通相結合以促進城市集約發展的規劃理念逐步得到認同[16]。1990年代,卡爾索普在提出TOD理論時,不僅設計了TOD站點地區的空間模型,也在郊區地區的片區尺度描繪了TOD規劃的總體布局形態(見圖4)[3]162,[17]4,12。新城市主義規劃師將不同時期依托軌道發展的規劃結構歸結為3種基本模式:點軸模式、廊道模式和TOD模式。在形態上,TOD規劃與近代時期基于軌道交通構建的理想城市模型結構近似,其差別在于方式和目的。近代理想城市在規劃初期構建了點軸狀或廊道狀發展形態,而TOD規劃則是在蔓延的條件下,重塑基于軌道站點區位條件的發展節點,依托軌道公交連接成為有序的整體結構(見圖5)[18]15。
在當前階段,低碳生態視角下的城市規劃布局或者公交都市規劃建設中,公交導向的城市結構依然體現了這種整體觀的延續。公交都市或城市層面的TOD規劃被描繪為依托公共交通體系組織土地利用與城市功能,形成連接城市中心區和次級中心的公交廊道,建設高強度開發的組團,外圍則保持低密度發展區和開敞空間,呈現主次分明、疏密相間的多中心、組團化、網絡化、合理緊湊的規劃布局模式[2]43,[19-20],[21]75-84,[22]。

圖3 美國城市交通與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模式

圖4 卡爾索普城市層面的TOD模型與設計
自近代時期理想城市模型到當前的TOD規劃模式,依托軌道發展的城市規劃布局具有共性的結構特征。一是中心城區和外圍組團形成有序的層級關系,二是通過軌道交通對城市中心和組團中心進行連接,三是圍繞軌道站點地區進行綜合開發。其中,單以站點周邊地區的開發來看,其規劃模式也具有一定的近似性[23]。TOD規劃在空間結構上與近代時期理想城市模型結構類似,是基于對小汽車交通和城市蔓延發展問題的反思,是對傳統城市發展模式的回歸與借鑒(見圖6)。
2 TOD規劃結構形態的類型分析
在空間形態上,卡爾索普提出的TOD模式受到田園城市理論的影響,在城市層面的規劃布局上采用了中心城區和衛星新城依托軌道連接和綠帶分隔的結構特點[3]71。在當今的規劃實踐中,TOD規劃結構反映的也是多層次中心網絡與多類型公交模式的結合[24]。城市軌道公交線路的建設與城市整體的中心體系密切相關,由于不同城市空間形態的差異以及軌道公交線路類型的區別,TOD規劃結構形態也是多種多樣。
如美國的CTOD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廊道形態的TOD結構為對象進行了分類研究,按照不同的目的和形態劃分為目的地廊道(Destination connector)、通勤廊道(Commuter)和環狀廊道(District circulator)3種類型,并提出相應的規劃對策建議[25]。部分國內學者對軌道交通線網結構與城市空間形態的對應關系進行研究,提出二者結合的常見形態包括無環放射式、有環放射式和網格式等類型[26-27]。也有學者從動態發展視角對TOD規劃結構形態進行研究,如趙萬民等認為理想化的TOD結構具有從線性結構轉化為TOD走廊,功能逐漸復合,并與城市其他系統結合,形成城市復合中樞的動態發展過程[28]。
總體上,無論是1940年代以前對理想城市模型的探討還是當代的TOD規劃,對基于軌道支撐的規劃結構形態的分類應該基于完整的城市中心體系框架。在以軌道公交為骨架,多中心、層級分布的模式基礎上,結合TOD規劃要素的點(站點地區)、線(軌道線路沿線)、帶(軌道公交廊道影響帶)、面(具有多層級軌道公交系統構成的片區)、網絡(軌道公交覆蓋完善的整體區域)的組合關系,TOD規劃結構形態可以劃分為點軸模式、帶狀模式、放射模式、環狀模式、組團模式和網絡模式6種主要類型(見圖7-圖8)[7]29-33。
點軸模式、帶狀模式是TOD的基本模式,即基于不同軌道站點間距形成的單一線形空間形態。放射模式、環狀模式、組團模式和網絡模式則是基于基本模式形成的4種主要組合模式。這些組合模式可以進一步組合成更加復雜的模型,如前文所述由放射模式和環狀模式相結合的有環放射模式等。其中,組團模式則是指不同空間尺度下TOD模式的嵌套所形成的一種復合關系(見表1)。
2.1 點軸模式
TOD規劃是依托軌道公交體系支撐形成的規劃類型,本身具有線性特征。通過軌道線路連接不同站點形成的線形廊道就是TOD規劃最基本的結構。在特定城市及地區的特定發展階段,如果僅有一條城市軌道作為發展主軸,且軌道線路等級較高,站點之間站距較大,TOD規劃的結構形態就表現為點軸模式。這種模式中,TOD開發主要以站點周邊地區為主,很難影響到軌道沿線距離站點較遠的區域,沿線就會依托各個站點形成相對孤立的點狀開發。
如美國阿靈頓縣著名的R-B走廊①,華盛頓地鐵羅斯林(Rosslyn)站到波爾斯頓(Ballston)站段。[29]83,自1960年代開始進行基于軌道開發帶動的城市復興建設工作,軌道沿線5個不同站點之間的間距在1—1.4 km之間,而TOD開發則以半徑400 m為邊界進行集中建設[5]146-151。因此,廊道上的不同站點地區并不能完全覆蓋軌道沿線區域,而是形成分段獨立開發的節點形態,整體表現為點軸模式。再如深圳地鐵3號線初期平均站間距約1.6 km,而站點地區TOD開發以半徑500 m為邊界,也不能實現對沿線開發用地的全面覆蓋,總體上也可以看作是點軸模式②深圳地鐵3號線初期建設范圍起自紅嶺中路止于龍興街站,全長32.91 km,共21個站,平均站間距1.57 km,最大站間距為3.8 km,最小站間距為0.9 km。按照《深圳地鐵3號線詳細規劃》提出的站點周邊半徑500 m內進行TOD開發的思路,TOD建設范圍也不能實現對沿線開發用地的全面覆蓋,也可以看作是點軸模式。。
2.2 帶狀模式
如果站點之間站間距較小,而TOD站點地區規劃覆蓋范圍較大,不同站點地區TOD開發的影響范圍相互連接甚至重疊,軌道沿線區域就會形成連綿的帶狀模式,如日本東京多摩新城TOD開發[7]38。選擇點軸或是帶狀模式,與軌道站間距有關,也與站點地區TOD開發的半徑范圍有關。不過,模式的差別也并不絕對,TOD形態也并不單一。在同一條軌道沿線站點密集的中心區段,表現為連續的帶狀形態;在站點稀疏的外圍區段,則表現為間隔的點狀分布。
無論是點軸模式還是帶狀模式,將軌道沿線作為整體進行統一考慮,綜合安排沿線土地功能是TOD規劃的重要原則。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5年頒布的《城市軌道沿線地區規劃設計導則》提出“線路層面規劃引導的范圍為軌道站點影響區。……整條線路的站點影響區原則上可作為一個帶型地區統一規劃,宜以線路為單位統一編制”[34]。

圖5 依托軌道發展的城市規劃基本模式

圖6 城市中心體系與軌道公交的結構關系

圖7 TOD規劃的結構形態類型
2.3 放射模式
點軸模式或帶狀模式是指單一軌道線路在小城市、城市外圍的特定地區或軌道建設初期的發展階段。而對于大城市的總體布局而言,隨著城市結構的完善和軌道線路的增多,結合中心地理論下的城市結構模型,軌道與城市的關系更應呈現出層級分明的放射模式。在形態上,放射模式可以劃分為星形和指狀兩種主要形態,形式不同,但內涵一致。
一般來說,在不同方向上均適宜發展的地區,TOD結構多為星形形態,如北美城市夏洛特、埃德蒙頓和丹佛的軌道形態[30]66;而在某些方向上城市的拓展受到限制而只能向特定方向延伸時,如哥本哈根[31]42和二戰以前軌道建設初期的東京[35],城市一側臨海,軌道發展只能沿著廊道向內陸延伸,TOD的結構表現為指狀形態。
2.4 環狀模式

圖8 不同類型TOD規劃的實踐
除了放射模式以外,如果城市內各片區或外圍組團形成封閉的環狀連接,那么就構成環狀模式。這類似于田園城市等近代時期理想城市模型中的描述,將外圍組團與中心城區形成緊密的連接,促進不同組團之間具有交通循環特征的空間聯系。
如在新加坡新市鎮的規劃建設中,55個規劃區中有23個為相對獨立的新市鎮。在主要軌道MRT(Mass rapid transit,大運量快速交通)的布局上,形成了不同發展片區的軌道公交線路。其中西側的13個新市鎮構成了連接中心城區較大尺度的環狀結構。

表1 TOD規劃的結構形態比較
2.5 組團模式
在特定片區內,不同軌道公交線路相互疊加,則會形成以主要軌道為骨架、依托次級軌道公交連接組團內部各節點的組團模式。與點軸模式僅僅促進站點周邊地區開發的模式不同,組團模式對主要軌道線路上站點地區覆蓋較弱的外圍區域通過次級軌道公交連接形成復合結構,對外圍區域產生較強的開發帶動作用,在軌道沿線形成了以站點為中心、連續的組團發展的形態,從更大的范圍尺度形成不是單一節點而是組團或片區整體發展的形態。
組團模式的連接形式可能包括環狀或放射等不同形態。如新加坡榜鵝等地的新市鎮規劃以MRT形成發展軸帶,串聯整個城市的不
同新市鎮,而在新市鎮內部,則依靠次級線路LRT(Light rail transit,輕軌交通)或公交形成環狀連接,形成組團發展特征[32]74,[36]40。溫蒂·莫里斯(Wendy Morris)以澳大利亞金達萊鎮的TOD規劃為例,描繪了放射狀的連接方式[37]59。
2.6 網絡模式
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區,隨著軌道公交網絡密集發展,軌道站點也可能形成網絡化均質布局的空間結構。若軌道線路密集,站點間距較近,TOD開發的影響范圍相互重疊,其間的空隙較少,則基本形成TOD開發建設的全覆蓋,從而形成TOD規劃的網絡模式。
如廣州[33]33、東京等特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核心區域,大多表現為TOD開發基本覆蓋城區的網絡模式。廣州的軌道沿線地區的開發規劃提出:2020年線網密度相比1990年將增加8.5倍,環城高速以內軌道交通站點地區半徑600 m覆蓋率將達到60%,基本覆蓋整個中心城區。
3 綜合視角下TOD規劃結構形態的構建 方法思考
總體上,城市層面TOD規劃的結構形態類型十分多樣。在實踐中可以發現,缺少對宏觀層面TOD結構形態不同空間特質和發展階段的把握,可能導致對不同TOD規劃的作用產生錯誤理解。如過度關注某一站點或某一段線路,以局部空間組織和利益平衡為重,就會導致忽視規劃區與軌道沿線整體的關系;過于關注某一條或某一類軌道線路,忽視多種軌道公交復合發展的結構對城市整體功能及形態帶來的綜合作用,從而影響城市整體和長遠利益。
城市層面TOD規劃結構形態研究的意義是為規劃實踐和管理更準確地認知TOD形態提供參照。使TOD規劃不僅著眼于站點周邊和軌道線路本身,更要從空間結構的復合性、發展時序的動態性以及建設機制的多樣性等方面入手,以更加整體和綜合的視角進行結構形態的構建,以保障TOD開發與城市整體建設的統一協調(見圖9)。

圖9 TOD規劃結構形態構建的3方面
3.1 明確空間結構的復合性
在個案的研究中,對特定區域或線路進行觀察,城市呈現出某種單一的TOD形態模式,但如果從城市整體層面進行觀察,TOD規劃則表現出復雜性。基于軌道形成的城市結構也可能出現多種模式復合存在于不同實踐中的情況。特別是在軌道線網密集的特大城市,城市中心形成網絡化布局,外圍的延伸形成新的點軸、帶狀或組團模式;城市整體層面,TOD規劃形成多種結構形態復合發展的特征。
如在阿靈頓縣,R-B走廊對于阿靈頓地區是廊道,但是對于華盛頓大都市區整體則是放射模式的一部分(見圖8a)。假如未來形成新的發展機遇或者以足夠長的發展時間來預期,這種點軸或帶狀模式也可能在整個華盛頓地區向放射狀、網絡狀的結構演化。再如日本東京多摩地區,單以鐵路軌道為觀察對象,該區域是站點周邊地區半徑750 m范圍形成連續開發的帶狀模式,而如果疊加公交站點地區半徑250 m范圍,則表現為網絡模式(見圖8b)[7]38。因此,在進行城市或線路層面TOD規劃時,不僅要重視沿線地區的開發建設,更要從城市整體視角進行觀察,重視軌道線路與城市結構的整合,使TOD規劃成為優化城市整體結構的空間手段。
3.2 重視發展時序的動態性
規劃形態的研究不能離開時間維度。城市TOD規劃結構形態的形成既需要空間的拓展,也需要時間的沉淀。軌道建設本身具有長期性,而其規劃也并不一定能夠做到一次完成的理想規劃,而存在逐步增加線路分階段建設的情況。因而,軌道建設與城市結構的發展并不完全同步,不同城市的發展水平不一樣,TOD規劃的形態并非一成不變,城市層面TOD規劃結構形態表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征。
雖然城市軌道是以線路為單位進行建設,但無論最終是哪一種結構,應該在軌道線建設之初,從城市動態發展視角介入,以便盡可能使城市整體從軌道建設發展過程中受益。如日本東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在二戰之前與哥本哈根類似,同樣是“指狀結構[31]212”。但隨著軌道建設和城市發展,目前則形成中心城區線路網十分密集的網絡結構與外圍地區的放射發展相結合的復合結構。大野秀敏將2050年的東京設定為依托軌道交通形成的“纖維城市(Fiber city)”[38],東京這種大尺度上的“指狀結構”或“纖維結構”顯然要比丹佛依靠相對較少線路支撐起來的放射模式要復雜得多。
3.3 關注建設機制的多樣性
大城市TOD規劃的復合特征不僅是空間布局本身特征的作用,更受到不同發展建設機制的影響,包括投資模式、規劃管理機制等多個方面。從建設機制的視角,應該將TOD開發作為城市建設協調的平臺與利益博弈的載體,以統籌不同片區、不同部門、不同開發主體的利益關系。在協調和保障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的同時,重視建設機制對城市形態的重要影響,關注相關規劃管理技術規定對TOD地區的管理實效,保障TOD地區開發建設的可行性以及空間形態的合理性。
比如日本東京的私營軌道交通建設長期采用溢價回收的模式[39],城市軌道建設市場化程度很高,但早期開發過程中宏觀統籌不足也造成了線路布局的復雜與混亂。城市軌道建設在中心城區的網絡化和復雜性以及外圍區域指狀拓展的形態正是長達近一百年私人鐵路商業化發展建設機制的真實反映。
與東京不同,新加坡的新市鎮規劃則更多的是基于新加坡整體城市發展規劃下有序的計劃安排,結構十分清晰。主要線路MRT的拓展與次級線路LRT的銜接是城市整體發展需求下的建設統籌,不同等級軌道線路站點與不同層級的新市鎮和社區的空間關系及設施配套是明確對應的[40]。這樣的計劃性使新加坡新市鎮的開發具有更加明晰有序的結構,但是與東京或香港相比,站點地區開發的活力卻相對不足。
此外,在規劃管理上,TOD模式下軌道站點周邊地區能否形成緊湊集聚的開發形態依賴于城市規劃對TOD地區和外圍區域開發強度、建筑高度、用地功能等的控制管理,同時也需要完善步行體系、提供自行車連接、美化外部環境等空間規劃和小汽車出行限制等相關政策的保障。
4 結語
從城市整體層面來看,城市軌道不是單純的“線”,而是有縱深的“帶”,更是城市或地區整體發展網絡的“骨架”,是各個片區組團未來城市開發建設所需要依托的重要空間支柱,起到帶動城市發展和優化城市形態的結構性作用。城市層面TOD規劃結構形態的多樣性來源于軌道建設與城市結構的多種關系。通過對比可以發現,無論采用哪一種結構形態類型,TOD規劃均應從城市層面整體視角出發,充分考慮空間結構的復合性、發展時序的動態性以及建設機制的多樣性可能帶來的發展影響,以通過軌道沿線地區的開發建設達到促進城市整體空間結構的優化與提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