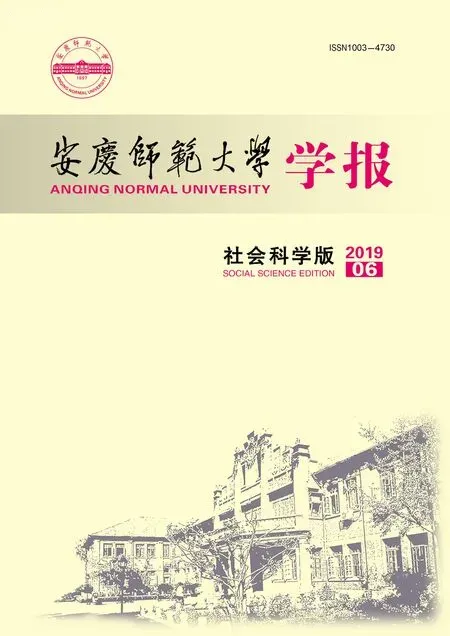網絡文學概念內涵演變
王江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北京102488)
1998年被公認為“網絡文學元年”,實際上,網絡文學及其概念的產生要更早一些。此前,人們曾使用電腦文學、多媒體文學、賽伯(博)文學、數字(位)文學、超文本文學、互聯網(因特網)文學、在線文學、比特文學等,來指代這種不同于傳統龜甲、竹帛、紙張等“原子”形態書寫或傳播介質的新媒介文學[1]。1996 年,《中國時報·資訊周報》推出了“網絡文學爭議”專欄,被認為是“網絡文學”在我國印刷傳媒中首次正式采用[2],此后,網絡文學的稱謂在漢語界逐漸流行。至2019 年,網絡文學已走過二十余年的歷程,從概念的初步確立到成長為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具有特殊價值的“龐然大物”[3],網絡文學概念內涵也在爭議中演變。
一、媒介技術崇拜傾向下的網絡文學
早期,人們對網絡文學概念內涵的劃分多受網絡這一新媒介技術沖擊的影響,帶有或明顯或隱微的技術崇拜傾向。這種崇拜傾向在網絡文學概念界定上有兩類表現:一是“泛化”的媒介崇拜,即將凡是與“網絡”媒介沾邊兒的文學作品都納入網絡文學概念范疇;二是“窄化”的媒介崇拜,即嚴格限定只有利用網絡超文本或超鏈接技術的文學作品才是“真正的”網絡文學。
(一)技術崇拜傾向與網絡文學概念泛化
“兩分法”是早期網絡文學研究中最常見的概念界定,即將網絡文學大致分為傳統印刷文學作品的網絡化形態,和在網絡上創作、傳播的網絡原創文學兩大類。以楊新敏《網絡文學芻議》、歐陽友權《互聯網上的文學風景》兩篇引用率較高的文章為代表,前者認為“網絡文學即與網絡有關的文學”,起碼包括“印刷類文學的網絡化”與“網絡原創文學”兩大類[4];后者指出“網絡文學主要是‘網絡’文學作品和文學信息”,其中,網絡文學作品分為“以電腦為傳播載體的搬上網絡的傳統作品”,及“專為網絡創作、首次在網上發布的網絡原創文學”兩種[5]。兩者雖在具體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其劃分的根本依據都是以“網絡”為核心要素:查看文學作品是否與“網絡”發生某種關聯是判定該作品能否歸于網絡文學范疇的邏輯原則。
將傳統文學作品的網絡化形態、網絡化傳播視為網絡文學概念的一種,雖然在今天看來可能與“新媒介”的內涵大相徑庭,但這本質上是早期新媒介崇拜“泛化”的表現。網絡初興時,上網人數少,網絡普及率低,網上的中文原創資源相對匱乏,一些以搬運傳統文學作品為主的網上書庫或網上書站發展迅速,如“新語絲”“書路”“黃金書屋”“亦凡”“文學城”等早期上網用戶爭相訪問的熱門站點,成為最早連接“網絡”與“文學”的特殊存在,對網絡文學概念的生成產生直接的影響。也正是基于對新傳播方式、新儲存方式中“新媒介(網絡)轉化”這一技術因素的考慮,部分論者強調,“任何一種文學作品一旦上網,都不同程度地具備了網絡的技術特征”[6],即由于網絡的介入,傳統文學作品的傳播方式與閱讀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其網絡形態已不同于紙質形態。如金振邦就曾以《佛山文藝》《山花》《作家》《雨花》《萌芽》《鐘山》等傳統文學雜志的網絡版,以及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經典作品上網后的“電子化形態”為例,說明傳統文學作品“網絡化”后,其接受方式、社會價值、藝術功能等都發生“質的重大變化”,網絡文學的內涵也應含括“傳統文學作品的網絡化形態”[7]。
(二)技術崇拜傾向與網絡文學概念窄化
超文本、超鏈接是網絡技術的核心構成部分,因此,技術崇拜在網絡文學界定中的另一種表現就是對“超文本性”的強調。這一方面與當時國外“超文本”研究在大陸的引介、傳播有關,如美國當代小說家、批評家羅伯特·庫弗認為,基于超文本、超媒介技術發展而成的“超小說”,是“只有在電腦上才可閱讀”的“一種新型的敘述藝術形式”[8];另一方面與中國臺灣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超文本創作、討論有關,如“全方位藝術家聯盟”“歧路花園”“澀柿子的世界”“臺灣網絡詩實驗室”等網站就聚集了一批超文本藝術的愛好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李順興就曾指出,“網絡文學”“指含有‘非平面印刷’成分并以數位方式發表的新型文學,學術上慣稱超文本文學(hypertext literature)。非平面印刷成分的明顯例子包括動態影像或文字、超連結設計(hyperlink)、互動式(interactivity)讀寫功能等”[9]9-10。與之相應,部分研究者在“二分法”基礎上衍生出網絡文學概念“三分法”,將在網絡上創作的作品分為兩種,一種單指利用網絡多媒體與超文本技術創作出來的超文本文學;另一種指那些雖在網絡上發表,但形式上仍采用“傳統”文學創作手法完成的作品。
研究者雖將網絡文學概念內涵分為三個“義項”,但受技術崇拜因素影響,往往把其中體現出網絡超文本或超鏈接技術的創作視為“真正的”網絡文學,強調其在技術上“不可印刷”。如王位慶曾明確指出,Internet 技術是定義網絡文學的“基礎”,無法體現因特網高科技特性的文學不能稱之為網絡文學,網絡文學應是“輔助多種媒體”進行“開放”“互動”創作的“文學式樣”;它可以“觸動不同人類感官感受”,但不可被印刷,只能在網上生存,只能靠網絡技術流傳、顯示,“以全新的不同于傳統文學方式存在”[10]。此觀點為大多數早期網絡文學研究者所默認,如歐陽友權《網絡文學本體論綱》[11]、謝家浩《網絡文學研究》[9]、徐文武《超文本文學及其后現代特性》[6]、王新萍《網絡文學的界定及其特征》[12]、湯愛麗《論網絡文學的交互性》[13]等多與之相似;顧曉鳴[14]、葛紅兵等人還曾以“網話文”“網話文學”命名網絡文學,葛紅兵將充分地利用聲音、圖片、動畫、文字等計算機多媒體技術進行組合創作的“超文本的多媒體語言”藝術視為“網話文學的高級形態”,認為網話文的語言也不同于傳統文學的語言,它“在一個母本中鏈接著不同的子本”,形成一種“多向鏈接語言”,帶給讀者“更為廣闊的欣賞視野”[15]。
出于對網絡新科技的崇拜,一部分論者將這種超媒體的、超文本的網絡文學標榜為與傳統文學完全不同的“新文學樣式”,認為它代表著網絡文學的“前景”,甚至寄予其超越傳統文學而成為“新世紀文學”的希望。如李濤《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之比較》[16]、郭炎武《試論網絡文學的特質及其對傳統文學的超越》[17]等認為,網絡文學的特質在于其融合了“數字化的藝術媒介”及“網絡時代的文化氛圍”,這使它與傳統文學“真正”相“區別”,“完成了對傳統文學一些局限的超越”[17];黃燕妮《論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秩序的新建構》[18]、林春田《網絡文學及其發展前景》[19]、許列星《網絡文學及其文化思考》[20]等認為,隨著網民素質與網絡技術的發展,“超文本文學必然是網絡文學發展的主流形態”[20];葛紅兵、梁寧寧、聶道先、王一儂、滕常偉等在《網絡文學與當代文學發展筆談》中高度評價“網話文”的價值意義,認為“對于文學來說這是一場表現手段和方式的革命性變革”[15],“為文學的新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把作品的寫作和閱讀帶入一個全新的境域”[21],“使得文學的表現方式不單單只有平面的文字構成”[22],從而“開創了繼口頭文學、紙面文學之后的第三個文學時代”[23];黃鳴奮還曾預想,在不遠的未來,讀者可以在網絡文學作品中不僅“體驗到文學趣味”,而且還能“感受到科技意蘊”,“科技標準”和“審美標準”將成為評價網絡文學內容的“雙重影響”,“技術含量高低,早晚將成為評價作品的尺度之一”[24]。
近來,這種帶有明顯媒介崇拜傾向與技術決定論意味的概念界定,雖然隨著大陸網絡原創文學作品的豐盛而有所更改,但一些媒介理論研究者仍堅持以媒介作為第一要素,考察網絡文學的形態與特征。如在首屆網絡文學創作研討會(2014 年)上,有學者認為,“超文本鏈接或多媒體作品,也即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25];單曉曦也指出,“‘網絡原創文學’是只啟動了計算機網絡較初級的傳播性生成功能的結果,它只能體現出網絡文學的一部分特點抑或只具有不充分的‘網絡生成性’,屬于過渡性的、不充分的網絡類型;‘網絡生成文學’是計算機網絡三大基本生成功能都被啟動后的產物,它可以較充分體現網絡文學的審美獨特性亦即‘網絡審美生成性’,屬于充分的網絡文學。”[1]208-209
二、文學審美視角下的網絡文學
1998 年,網絡作者痞子蔡以“傳統手法”在BBS 上創作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風行海峽兩岸的各大網站,被認為是“宣告了網絡文學這一新生事物的誕生”[26],同時也激發了無數文學愛好者在網上進行文學創作的熱情。1999—2000 年間,“網易中國網絡文學大獎賽”、榕樹下“網絡迎千禧,文學新紀元——1999網絡原創文學作品獎”大賽相繼舉行,兩場聲勢浩大的賽事不但促進了網民、媒體、學者、傳統作家等對大陸原創網絡文學作者及作品的關注,而且為網絡文學概念的確立、推廣、討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否認網絡文學概念的獨立性
與新媒介技術崇拜將關注點放在“網絡”相反,秉持文學審美視角的論者將定義網絡文學的重點放在“文學”。有論者質疑網絡超文本文學的審美價值及以網絡媒介重新命名文學的合理性。南帆以“不計其數的意義會不會等于沒有意義?”的追問表達對超文本文學的價值憂慮[27]。王一川、王宏圖等指出,如果缺乏“獨特的精神創造”,那么人們所謂的“超級文本文學”及其“文本多義性”、資源“豐富性”、“閱讀開放性”等特征,就極可能變成一種純粹依靠網絡技術“隨機選擇、提取或組合”而成,或只是類似于“字典辭書式的資料堆積”而成的“文本拼貼”,這種“蒼白無力的”拼貼“也就不大可能產生出偉大的文學了”[28];而且,“這種所謂的‘超級文本’很難被視為真正的藝術創作”,“它只會使網絡文學的面目更為模糊不清,最后導致自身的消解”[29]。陳平原以網絡時代的化學、哲學等學科為例,認為這些學科因其并未體現出“知識體系”的不同,也就未表現出以“網絡化學”“網絡哲學”命名的“企圖”;同理,“文學就是文學,網上/網下的寫作與閱讀,不應該成為或褒或貶的理由”,“強調‘網絡’的獨特性,而忽略‘文學’的普遍性”“并非明智之舉”[30]。
也有論者遵循“文學就是文學”的邏輯,以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傳統)文學范疇和審美為參照,否認網絡文學概念存在的合理性或必要性。持此類觀點的以部分傳統文學作家為代表,如張抗抗在評閱入圍“網易中國網絡文學獎”的三十余篇作品時,感覺到若將這些網絡文學作品打印成紙稿,便“一時難以辨認”“網上”文學和“網下”文學的區別,因而她對網絡文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變文學本身”有所懷疑,認為從“情感、想象、良知、語言等文學要素”考量,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并沒有‘質’的區別”[31]。以2000年《文學報》(4月20日)、《作家》(第5期)組織的有關網絡文學討論專題為例,雖然余華《網絡和文學》[32]、陳村《網絡兩則》[33]、張抗抗《有感網絡文學》[34]、徐坤《網絡是個什么東東》[35]、李潔非《Free與網絡寫作》[36]、李敬澤《“網絡文學”要點和疑問》[37]等文章中對網絡文學的褒貶態度不同,但無一例外都堅持以“文學”為“絕對標準”,不認為網絡的出現改變了文學的本質。比如,同為褒揚網絡文學的價值意義,陳村表示,“對許多的定義或口號沒有興趣”“技術上一定有革命的改良的因素出現,故事的背景和外延會變,但文學指向人心是永恒不變的”“人的‘文學基因’也是一代代相傳的”[33];余華認為,討論傳統出版文學和網絡文學的話題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它們只是網絡與紙質出版兩種傳播方式的不同,而并非“文學本質的不同”[32]。針對部分網絡文學宣揚者的“自說自大”,李敬澤曾指出,“文學產生于心靈,而不是產生于網絡”,“網絡文學”只不過是“網絡在一種驚人的自我陶醉和幻覺中被當做了心靈的內容和形式”[37];李潔非認為,“網絡寫作根本不是為了‘文學’的目的而生的”,“強烈主張撇開‘文學’一詞來談論網絡寫作”,網絡文學的概念是“一種極其機會主義的權宜之計”[36]。
在大陸網絡文學發展早期,這些傳統文學領域內知名作家的言論無形中影響了一些研究者。如鐘友循《網絡寫作的生機與困境》[38]、杜家和《網絡文學三議題》[39]、楊政《文學的困惑與網絡文學》[40]等,盡管使用了“網絡文學”的稱謂,但并不認為它是一個可以獨立的文學概念。鐘友循解釋道,“網絡文學”概念的使用主要是“為了討論問題或提出話題的需要”,僅作為探討的“一種預設、展望、希冀”,如果“清醒地”加以分析,那么“網絡文學”的概念“不但不很嚴謹,甚至還可以說在事實上并不存在”,與傳統文學相比,“網絡文學”“既沒有自己的模樣,也并未構成獨立的品格”,因此它是“一個相當模糊,邊緣既不清晰,內質也尚未真正形成的東西”[38];杜家和認為,相對于傳統媒介載體的文學而言,雖然網絡文學的載體發生了“革命性的”“根本的”轉變,但是其“文學的藝術精神不應該發生裂變”,也“不應該急于追求自己的獨特風格和流派”[39]。
(二)強化網絡文學的概念獨立性
與將網絡文學視為一種“新瓶裝舊酒”[41]的觀念不同,一些論者極力排斥以傳統文學的“舊”標準來衡量或界定“新”興的網絡文學,他們采取反向定義的方法,通過突出或強調網絡文學在創作人群、閱讀受眾、內容題材、語言風格等方面與傳統文學截然不同的審美特征,來實現對網絡文學概念合理性、獨立性的確立。
對活躍在網絡上的大部分作者或讀者而言,他們“不認為傳統對網絡文學的承認就是網絡文學的成功”[42],網絡文學是由他們創作、傳播、閱讀、評判的,也理應由他們自己來界定什么樣的網絡文學是“真正的”、“準確的”網絡文學。王俊秀指出,網絡文學“顯然不能”只是“聯手小說”“多媒體劇本”以及“電子化后”在網上傳播的傳統文學作品,“真正的網絡文學必須是包含網絡文化特質的個人化文字”;網絡文學真正追求的并不是“技術性”,而是“感性”與“人道主義的精神需求”,是“個體生命對于理想網絡的渴望”;相較于從技術上推論概念,從“網絡文化的角度”“人的本體”角度出發去界定“網絡文學”,“往往更接近于事實”[43],進而否定了部分傳統作家與批評家對網絡文學的言論。李尋歡說,網絡文學的“準確定義應該是:網人在網絡上發表的供網人閱讀的文學”,不僅強調網絡文學的創作主體“必須是‘網人’”,而且強調“最重要的是”網絡文學作者的創作動機也“必須是為網上受眾寫作的”[44],這種對網絡文學從“網人”到“網人”的內部范疇、內部循環的強調,有意或無意地剝離了來自“非網人”的評判權與界定權,表達了網民群體以獨特審美需求和審美標準來定義網絡文學的意圖。
早期商業網站、媒體機構與出版圖書出于宣傳或報道的需要,對網絡文學概念獨立的需求、確認、使用及推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海天出版社《一“網”情深:網絡文學薈萃》(1999 年4月)、知識出版社《第一次的親密接觸》(1999 年11月)、三聯出版社《進進出出——在網與絡、情與愛之間》(2000 年1 月)、時代文藝出版社“中國網絡原創作品精選”(200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網絡文叢”(2000 年1 月)、漓江出版社《’99 中國年度最佳網絡文學》(2000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網絡文化叢書”(2000 年1 月)、中國社會出版社“網絡人生系列叢書”(2000 年4 月)、花城出版社“網絡之星叢書”(2000 年4 月、2001 年4 月)、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新銳網絡文學作品選集”(2000 年9 月)、長江文藝出版社“網絡作品精粹”(2000年10月)、海峽文藝出版社“網絡迷情”系列叢書(2000 年11 月)、時代文藝出版社“首屆中國網易網絡文學大賽獲獎書系”(2000年12月)等圖書,都是打著“網絡文學”的旗號,以在網絡上篩選的、由網民創作的文學作品為主要賣點。雖然有人主張不管是“網絡原創作品”,還是傳統作家在紙上創作的、“以網絡為題材”(描寫網民生活或網絡生活)的作品,“都應該稱之為網絡文學”[45],但基于對獨特審美趣味的有意區分,傳統作家以網絡為題材進行創作的作品往往被部分網民排斥在網絡文學范疇之外。如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網絡文學叢書”(2000年1月),選錄了李敬澤、李洱、邱華棟、夏商等在傳統文壇內較有名氣的作家作品,盡管他們中有人在網絡上開辟個人主頁或站點,但由于叢書入選的作品大多不是網絡原創,因此被部分網民認為有“‘掛羊頭賣狗肉’賺吆喝的嫌疑”[46]。
有研究者指出,在網絡文學的多重內涵中,“以傳統的創作手法而只為網絡創作的作品,這類東西最多,也最能成為網絡文學的代表”[47]。為與網絡上的超文本文學相區分,他們更傾向于使用“網絡原創文學”的概念,如鄺煉軍《網絡文學:自由的挑戰》[48]、王永貴《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網絡小說主題初探》[49]、劉熹《論現階段的網絡原創文學》[50]、郭毅《網絡文學存在的意義》[51]等,著重分析“網絡原創文學”除載體新穎之外,因創作人群與題材內容不同而迥異于傳統文學的審美趣味、審美特征,強調網絡文學在情感交流、情感表現、語言表達、敘事結構等方面所獨具的“一些明顯新的特質的文學形態”[52],強調其“獨特的價值觀:不為名,不為利,只為了可以向更多的人表達自己的理念和情緒”(少君)[53],認為正是這些“獨特”之處確立了網絡文學的文學價值,使它成為可以與“傳統文學”并立的概念。
三、生產機制變化下的網絡文學
網絡是一種技術,也是一種生產工具。與媒介崇拜傾向下的網絡文學定義不同,生產機制視角下的網絡文學概念內涵由對網絡所表現的技術特征的強調,轉向對網絡所引起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的強調,即相較于新媒介變革所帶來的單純的文學文本的樣式變化,更側重考察新媒介變革作用于人們的生活和消費方式后所帶來的文學生產機制的變革,據此定義、使用網絡文學概念。
(一)強調自由生產的網絡文學
網絡給文學帶來了什么?技術主導論者傾向于論證由超媒體、超文本、超鏈接技術所帶來的文學表現方式與文本形態的改變,認為“依托互聯網的網絡文學”,具有“多媒體特性”[54];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在“網絡給文學帶來的諸多禮物中”,“自由”“寬 容”“開 放”“公平”等特性,“正在改變 網 絡寫手的寫作習慣、寫作方式以及思維方式”,是網絡給文學帶來的“一次新的契機、新的希望”[55]。
網絡首先帶來的是發表機制的改變。出于對網絡所代表的自由、隨意、平等、共享、無門檻、無功利等文學生產理念的肯定,一些論者將網絡文學視為“全民寫作”“全民文學”的理想狀態。如陳村的“卡拉OK 說”所形容,“Internet 的出現,更給它一個從作者直接抵達最多讀者的路徑,給它走出專業人士的圈子而擴展為‘卡拉OK’式演唱進而領唱的機遇”,等到“上網成了最平常的事情,以后的孩子怎么都看不懂,把文字弄到網上發表,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33];王朔也認為,網絡打破了體制、編輯、評論家、出版商等一切的束縛,使每一個人都有了“自由表達自我的機會”,都可以進行“自由創作任意發表的文字活動”,其中“任意發表”是“無比重要”的,它使網絡文學恢復文學“原初時的天真模樣”,代表著文學的“本來”與“未來”,成為一種“真正的文學”,不僅可以產生出“偉大(傳統)作家”,而且也解放了“全體有書寫能力的人民”[56]。在此意義上,網絡文學概念的內涵近于“網絡時代的文學”,指向在網絡技術普及與網絡理念滲透下,文學生產方式進入網絡時代后的整體面貌。
其次,網絡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讀者-作者”關系。與依靠超鏈接功能進行的網絡接龍小說創作不同,生產機制視角下對網絡交互功能的強調由單純技術上的操作互動轉變為文學生產上的內容共生,使網絡文學成為一種“作者—讀者”合作共構的“集體文學”。王曉華認為,“互生性”是網絡文學的“誕生機制”及“根本特征”,網絡文學的誕生過程其實是網絡“作者/讀者不斷交換身份的過程”,因此,“成功的網絡文本”是由作者與讀者“集體創作”的,“完整的網絡文本”是由作者與讀者的“原創帖和回帖”共同組成的[57];邵燕君曾強調她對網絡文學“有一個非常狹隘的定義”,即事先完成的作品“在網上發表和傳播”都不能稱為網絡文學,網絡文學及其意義“一定是在網絡空間中”由“作者和粉絲的大量互動”而“生產”的[58]。李俊指出,正是因為網絡文學“從根本上讓作者、作品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平等交融起來”,使讀者可以自由地參與、“體驗”“互動”,甚至“決定文學的生死存亡”,所以才使“‘網絡文學’的概念逐漸深入人心”[59]。在這層意義上,網絡文學成為一個動態的、多向的生產關系,而“網絡文學文本”除包括作者創作的主體文本之外,還包括由讀者參與的大量衍生文本或外延文本,因此,如果說超文本文學在技術上是“不可印刷”的,那么在網絡空間中由“作者-讀者”合作共生的網絡文學文本在技術上是“可印刷”的,但在內容上卻是“不可印刷的”,被印刷的部分只是那些“被從互生關系中強行切割出來的部分網絡文本”[57]。
另外,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與進化,尤其是移動網絡終端的廣泛使用,網絡內容的生產與傳播渠道愈加多樣化,網絡文學有時也用于指代在各類網絡平臺上生產的各種文學作品的總稱,囊括了博客文學、微博文學、微信文學等等。如,由梅紅等人編寫的《網絡文學》(2010 年版)教材中羅列了“網絡小說”“網絡詩歌”“網絡散文”“博客文學”等種類[60];其《網絡文學》(2016 年版)則“刪除原博客文學一章,增加社交媒體文學”[61]1,將博客文學、微博文學、微信文學作為“社交媒體文學”的代表形態,強調“我們可以完全拒絕網絡小說,但我們不可能沒有接觸過社交媒體文學,天涯社區、百度貼吧、QQ 空間、博客、人人、微博、豆瓣、知乎……每一個社交媒體的興起都代表著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與數量龐大的用戶群體”[61]205。
(二)強調商業生產的網絡文學
陳村在“榕樹下”網站被售前曾出于對網絡文學商業化的憂慮,感嘆網絡文學的發展“已經過了它最好的時期”,“它的自由,它的隨意,它的不功利,已經被污染了”[62]。且不論這種判斷的對與錯,就實際情況而言,商業化進程的確大大改寫了網絡文學的發展軌跡,尤其是VIP 在線付費閱讀機制的確立與推廣,幾乎重新圈定了中國網絡文學的概念邊界。
網絡文學在持續的商業化生產與運作下已逐漸成長為一個互聯網領域的產業概念。一方面,當前的網絡文學是以商業文學網站創作為主的,眾多標有“網絡文學”的調查報告也大都從商業文學網站為主要調查對象,如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發布的《2017 年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指出,其研究的網絡文學范疇“主要包括文學創作者以互聯網為展示平臺和傳播媒介,以文字為表現手段,創作發表的供網民付費或者是免費閱讀的文學作品”,但其主要的數據來源一為“面向全國20余家主流網絡文學相關企業進行作者、作品、讀者相關數據采集”,一為“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數字出版司基于40余家國內主要網絡文學企業數據統計”[63],可見,由企業生產、運營的網絡文學基本上構成了當前網絡文學的主體。另一方面,影視、動漫、游戲、音頻、話劇、周邊、園區等多種商業開發模式對網絡文學的介入,使網絡文學的“網羅”功能由網上向網下大范圍鋪展,并進一步催生了從產業鏈角度定義網絡文學的“網絡文學IP”、“網絡文學+”概念,成為“政策制定和從業者共謀的時髦和策略”[64]。這在由相關企業、組織或官方機構舉行的一些以網絡文學為主題的活動中十分明顯,如第一屆中國“網絡文學+”大會、第二屆中國“網絡文學+”大會、網絡文學IP 路演、首屆中國網絡文學周等,及“江蘇網絡文學谷”、“重慶市網絡文學創作基地”等,其所使用的網絡文學概念在內涵上更偏向于文學文本之外,由網絡文學與影視、游戲、動漫、音樂、金融、體育、科技、教育等不同領域融合而成的一個產業集合概念。
另外,VIP付費閱讀機制的確立有賴于網絡小說的發展,而該機制的普及又大大刺激了網絡小說的進一步繁榮,使網絡文學在商業化進程中發生了體裁比例上的巨變。目前,未特意標明“網絡詩歌”“網絡散文”等具體含義的網絡文學概念,大都在體裁上默認地指向網絡小說,尤其是在商業文學網站連載的玄幻、武俠、仙俠、都市、軍事、歷史、游戲、科幻、懸疑、體育等長篇類型小說。以漓江出版社策劃的“網絡文學年選”系列圖書為例,《’99中國年度最佳網絡文學》《2000中國年度最佳網絡文學》《2001中國年度最佳網絡文學》《2002中國年度最佳網絡文學》《2003中國年度最佳網絡文學》等選本,囊括詩歌、散文、隨筆、評論、短篇小說、中篇小說等多種網絡創作體裁;而《2015 中國年度網絡文學》(男頻卷、女頻卷)、《2016中國年度網絡文學》(男頻卷、女頻卷)、《2017中國年度網絡文學》(男頻卷、女頻卷)等,雖然仍以“網絡文學”為名,而實際入選篇目與體裁已是清一色的網絡長篇小說。另如閱文“中國原創文學風云榜”、“貓片·胡潤原創文學IP 價值榜”、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優秀網絡文學原創作品推介名單”、“中國網絡文學20 年20 部優秀作品”、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2017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等榜單或報告中的網絡文學概念,實際上也都是等同于網絡(長篇)小說的。因此,在近年來相當一部分的學術研究中,其所談論的網絡文學主要“指首發于網絡、在線連載的超長篇通俗小說”[65],或“主要是指隨著付費閱讀商業模式的建立,在網站發表的類型小說”[66]。
四、小 結
二十余年來,網絡文學在不斷地探索與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作品與經驗。總體上看,在網絡文學概念演變過程中,其初興時因新媒介出世所帶來的技術震撼與沖擊隨著網絡的普及有所減弱,而技術普及后所帶來的審美習慣與生產機制變革等因素在內涵界定中所占的權重逐漸增加。可以說,從口頭歌舞,到龜甲竹帛,到紙張印刷,再到電子網絡,文學一方面會因媒介的載體差異而觸發某種形式上的改變,另一方面又會在人的參與下,在新的媒介形態和生產關系中不斷地尋找、調整到某種適宜其生長的新風格、新機制、新樣貌。網絡文學便是一個在網絡空間或網絡時代中生長著、變化著的文學概念,它生于“網絡”,屬于“文學”,同時也變革著、擴充著“文學”:它將網絡的媒介特征、網民的審美情趣、時代的生產關系等因素經由一系列的創作、發展與篩選過程,積淀成、融合成或內化成某種新的文學藝術手法、題材內容、審美風格及體裁樣式。當前,網絡的技術開發與生產機制仍在進行著新的探索與實踐,網絡環境下的人與文學也在智媒時代發展著、變化著,網絡文學的未來有著許多的可能性與豐富性。因此,無論是總結已有發展歷程、梳理當前發展狀況的需要,還是展望未來發展前景、引導未來發展的需要,網絡文學概念的內涵、演變及其“名”“實”之間的關系等,都有進一步清理、區分、細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