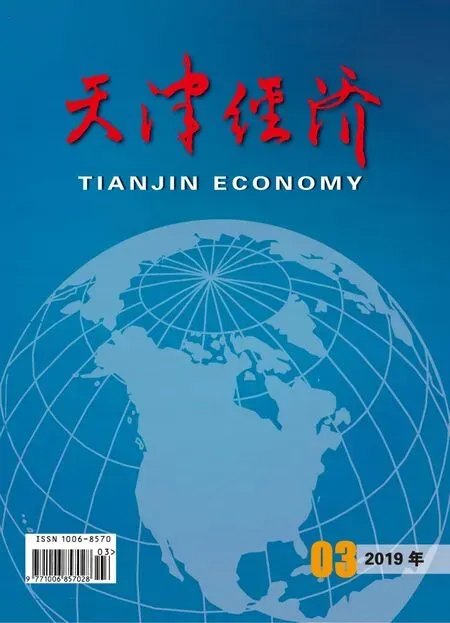兩票制下我國藥品流通市場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
——基于國外藥品流通特點
◎文/馮 謙
“多票制”下傳統藥品流通鏈條主要包含生產企業、藥品流通企業或代理商、醫療機構、藥店等參與主體。藥品從生產企業流向代理商,再經由藥品流通企業配送至醫療機構或藥店進行銷售,層層需要賺取利潤,在這個過程中參與主體會有多次開發票的行為,遂稱為 “多票制”。
為治理“多票制”下存在的流通層級過多、流通過程不合理、藥價虛高等問題,國務院辦公廳分別印發了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要提高醫院藥房藥品采購的集中化程度,推動實行“兩票制”,并提出在2018年內大范圍推行藥品采購和銷售的 “兩票制”。
“兩票制”與多票制的不同是限制發票的開具次數,其中藥品從生產企業到流通企業允許開具一次發票,再者藥品從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允許再開具一次發票。“兩票制”的目的是通過控制藥品在流通過程的環節來降低其流通成本,從而降低虛高的藥價。
在此背景下本文分別從市場中各主體角度出發,以“兩票制”政策作為依據,分析新政實施對藥品流通市場產生的影響,以及市場面臨的新挑戰,并針對性的借鑒國外藥品流通行業相關經驗,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兩票制下流通市場各利益主體的現狀及問題
兩票制新政為整個藥品流通市場帶來了巨大變化,環節中各個主體均面臨一定的轉型,其中各參與主體不僅受到“兩票制”帶來的利益影響,還會面臨不同以往的新問題,接受不同程度的挑戰。
(一)政府
我國藥品生產與流通企業數量龐大,因此政府監管藥品流通環節較為困難。而實施“兩票制”新政有利于加強政府監管,增加醫藥流通環節的透明度,打擊藥品企業“過票洗錢”的暗箱操作行為,凈化市場環境,從而有效控制了從生產到零售終端過程中藥品流通產生的差價。由于“兩票制”下藥品的票、賬和貨物信息必須保持一致,所以藥品來源可追溯性增強,在流通過程中相對保障了藥品質量,增加了藥品生產流通企業的違規成本,最終有利于減少政府監管成本。
然而“兩票制”的實施卻并非易事,其中在地方政府層面就存在一定的阻礙,這是因為“兩票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政府稅收。一方面由于原來地方政府通過稅收提高自己的財政收入,所以要求那些合作的企業在當地設立獨立子公司,這樣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企業內部管理,并且地方政府這些做法不僅不利于提高行業集中度,還造成了藥品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管理上的分散化。另一方面,“兩票制”迫使那些不合規不達標的弱勢流通企業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面臨倒閉和被兼并,從而造成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降低。所以地方政府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利益驅動,在政策的落實上往往會力不從心。
(二)藥品生產企業
首先在符合“兩票制”要求下藥品生產企業除了生產研發之外,還要兼顧原本由代理商負責的銷售與流通環節,這樣流通鏈條的層級被壓縮,銷售渠道變窄,藥品生產企業的成本負擔也將進一步增加。再者,新政策抑制了醫院吃返點的現象,但醫院出于自身財務壓力,需要彌補這些損失,所以其會通過一些手段變相彌補,例如:壓低中標藥品的采購價格,拖延匯款周期等行為,這些都最終轉化為藥品生產企業自身的財務負擔。
“多票制”下生產企業的藥品出廠價高低與其擁有流通層級的多少呈反比關系,層級多的企業藥品出廠價通常較低,這樣方便藥品在流通過程中逐層加價,相反層級少的企業藥品出廠價高以有利于獲得最大利潤。“兩票制”下,原本由代理商負責的流通和銷售業務開始由各生產企業承擔,此時原流通過程中的加價差率如不改變,那些藥品出廠價低的企業就會因為流通環節減少和業務增加導致成本增加,并且如果不改革醫療機構支付制度,醫療機構沒有采購低價藥品的傾向,所以生產企業為了彌補利潤損失,將會在規定的政策范圍內提高藥品出廠價。還有學者提出“兩票制”雖然縮減了流通環節,但流通環節費用卻轉移到了企業內部,并沒有有效減少。從理論上講,直銷可以節省成本,因為其實行從出廠到零售終端一體化配送,減少了物流過程中的環節,但在實際情況中藥品生產企業不擅長藥品流通的環節,因此要自身承擔營銷整個過程,需要付出更大的企業運營成本。
(三)藥品流通行業
資料顯示,發達國家藥品流通價值鏈中的各參與主體收入占比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趨勢,其中藥品生產企業收入占比最高,零售終端次之,而流通行業最少(見圖1),遠低于10%;但在我國藥品流通行業的特點卻恰好與之相反,其占據了至少31%的份額,比生產企業的份額至少多出了11%,這是由于流通企業和醫療機構蠶食了生產企業的利潤,造成了藥品流通的低效率和虛高的藥價。

圖1 國外藥品流通各環節的收入占比
整個藥品流通體系中環節多,銷售渠道分散。由于藥企自身規模無力承擔藥品配送環節,為了自身利益其需要與醫藥流通企業合作,比如配送業務外包。與此同時,市場上還存在一類流通企業,他們不缺少渠道資源但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相關資質,他們通常與有資質的公司進行“合作”即掛靠,雙方之間各取所需。
可以說此次 “兩票制”實施對流通行業影響巨大。首先,因為合規的要求導致藥品流通企業的準入門檻升高,并逼迫中小型企業與經銷商被兼并、重組、轉型或退市,以福建省為例,2012年至2016年期間福建省配送商數量從176家縮減至40家,降幅達77%。其次,大企業通過整合不合規的中小企業,有利于擴大自身規模,降低成本和提高行業集中度。
最后兩票制迫使部分藥企棄標,導致部分藥品出現短缺現象,但這些都是短期現象,從長期來看,兩票制有利于加速中小企業迭代升級,凈化藥品流通市場,有效降低虛高的藥價。
(四)患者
患者主要從兩個方面受“兩票制”新政的影響:一方面體現在新政增強了患者的用藥保障性,并且管理和控制藥品流通環節,規范化運作流程等;另一方面,流通環節利潤攤薄,并且一些偏遠地區對藥品的需求量相對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即使放寬一定票數,由于成本問題,流通企業仍然不會冒險進入這類市場,這也就導致了存在患者無法及時獲得所需藥品的情況。
(五)醫療機構
首先由于取消了藥品加成,正常招標采購的情況下藥品對醫療機構來講已經不能創造任何額外收入,另外“兩票制”對票、賬、貨三者信息嚴格要求一致,這又需要醫療機構自己進行管理,而管理所需的相關人員又會產生一定的成本。并且目前在有政府財政補助和提高醫事服務費政策的支持下,醫院仍不足以彌補因藥品減少的收入。針對這些情況,有部分醫院相繼“試水”采取業務外包的措施,將藥房交給第三方相關公司進行管理,還有部分醫院“另辟蹊徑”,增加一些“治未病”的醫療服務,如設立健康管理中心。然而在藥品供應鏈條中醫療機構始終屬于強勢方。醫療機構為了變相獲得返利,對上游參與企業存在故意延長貨款周期,其中如北上廣江浙等發達地區醫療機構匯款周期平均在3個月左右,欠發達地區甚至長達半年以上;除此之外,醫療機構還有另一種獲取利潤的方式,就是通過采購“二次議價”擴大藥品進貨價與中標價之間的藥價差。議價形成的藥價差看似能夠彌補醫院減少的利潤,實質上不過是藥企變相的通過合法渠道給醫院藥品返利,這樣的“醫藥分離”名不副實。
二、國外藥品流通市場特點
與我國藥品流通現狀相比,發達國家藥品流通的模式更加成熟合理。雖然不同國家流通體制存在差異,但在某些層面上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對我國藥品流通的發展仍具有一定借鑒和幫助之處。
(一)市場高度集中
國外市場中一些企業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下難以獨立維持,紛紛選擇停止經營或者選擇依靠大企業發展,這就促進了國外醫藥市場在集中化方向上的發展。在德國,市場份額的60%~70%由三家醫藥批發商占據;在法國,前三家批發企業占據市場份額的95%;而在美國,這一數字更是達到95%以上。
而這種市場結構進一步穩固了大型醫藥批發企業的主導優勢,有利于其在采購及招標過程中降低成本,保持較強的成本優勢。同時,這些大型醫藥批發企業為市場帶來了高效率、低成本、優質的服務水平以及先進的服務管理理念。
(二)培養專業化中介組織
在醫藥流通領域,發達國家的中介組織非常專業,如美國的集體采購機構(GPO),這類機構主要是根據醫療機構的要求負責與合作商進行業務談判、提高采購效率、降低運營成本。而GPO對于合作的供應廠商來說,相當于一個大型且需求穩定的采購商,貨物需求量大且穩定,并且減少了各種間接成本,因此對于醫療機構和供應商雙方都是有利的。日本制藥協會有藥品電子網,該電子網主要用于提供數據交換服務,其幫助企業實現降低信息化成本并且具有信息共享的功能。
中介組織除了服務于企業、醫療機構,在藥品市場管理方面其還可以為政府提供積極幫助。如,對制造商資料、產品信息等方面的審查工作,歐盟已經交由第三方機構完成,而制造商和第三方機構均要對問題擔責。
(三)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
加快物流領域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以有效降低流通成本。例如:總公司通過網絡對子公司下達網上訂單,而子公司通過網絡及時有效處理訂單。除此之外,子公司可以及時快速給總公司分析上報銷售數據、庫存信息和其他相關信息,以方便總公司進行決策,實現對現金流、信息流、商品流的有效管理。在德國,批發企業與藥店通過網絡實現彈性靈活訂貨,有效降低了倉儲成本。
歐美國家對其全國銷售的藥品在包裝上都有包含基本信息的條碼,這樣客戶對藥品運輸的物流過程就可以了如指掌。另外,一些大型醫藥企業已經擁有了自動化立體倉庫,這些倉庫配備了電子標簽、無線掃描等自動化設備,不僅減少了人員的工作量,降低了勞動力的需求數量,而且能夠保證一定的運作效率。
(四)建立藥品費用控制系統
目前,發達國家在各個環節已形成了一系列相對成熟的控制藥品價格方面的政策。在生產方面,他們鼓勵新藥的研發和生產,并且嚴格審核藥品各項指標。在經營方面,建立大型綜合配送中心,減少流通環節,統購統銷。在價格方面,各國百花齊放,如,法國的嚴格定價管制、愛爾蘭的比較定價、德國的參考定價、英國的藥品利潤控制等。在使用環節方面,分別對病人和醫生兩大主體采取措施,如,規定病患費用報銷范圍,規定醫生接受合理用藥培訓指導等。
(五)零售藥店助力醫藥分離制度
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實行醫藥分開的管理體制,而其制度實施的過程中零售藥店的作用不可忽視。在美國,門診就醫的病人購買藥品需要到零售藥店,因為醫院只針對住院病人設立了住院藥房。在法國,藥品通過零售藥店流向病人所占的比例是84.7%,而藥品通過生產企業銷售給醫院所占的比例是15.3%。在德國,藥店銷售額約占銷售總額的84%。
三、對策與建議
(一)制藥企業借力CSO對接終端
CSO即合同銷售組織(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由原來藥品代理 (銷售+推廣)角色轉為僅負責推廣服務的角色,為服務的醫藥生產企業客戶提供整體營銷的專業服務,然后開具發票,獲取服務傭金。CSO促進了藥品從生產企業流向流通企業最終到達需求終端這一整個流通鏈條的形成,提升了藥品整體流通的效率。另外,CSO還有利于那些擁有資源卻沒有相關資質的自然人通過發揮自身渠道資源等優勢完成轉型,從而達到與藥品生產企業繼續合作的資質要求。
但同時CSO的服務模式存為企業變相洗錢的嫌疑,這也為以后政府的監管帶來隱患。目前,很多CSO機構的業務能力還尚不成熟完善,所以現階段政府部門管理這類機構需要把握好度,不能完全放開同時也不能全面禁止,應盡早制定出臺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來約束引導CSO。
(二)政府科學控制藥品流通差率
在流通過程中藥品每流過一個層級便會產生一層成本,那么藥品加價就成為必然。政府如果要控制好藥品的價格加成,就需要科學控制藥品在流通過程中的加價比例,這個加價比例也就是流通差率。
(三)建立一體化的醫藥流通信息網絡平臺
以往整個流通鏈條中各參與主體間沒有統一的信息網絡體系進行信息交流,藥品流通過程中運作不透明不可控,造成質量保障問題,安全控制問題和價格難題。所以流通鏈條中各參與主體間應建立具備信息交流、收集、流通監控跟蹤等功能的信息網絡平臺。在這個平臺上能夠使藥品信息可視化,方便各主體追蹤查詢藥品的流通情況,方便各方協調利益、共同管控。
(四)加快醫保支付制度改革進程
有部分學者認為,減少流通層級數量對藥品價格的影響收效甚微,要想有效降低虛高的藥價,必須引導和管控醫生在處方行為上做到合規。因為藥品在中標時是明碼標價的。處方權牢牢控制在醫生那里,如果不改革醫保支付制度,“兩票制”在藥品采購環節對醫院就很難起到約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