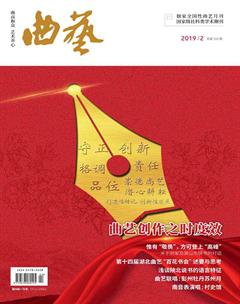第十四屆湖北曲藝“百花書會”述要與思考
歐陽亮

一
2018年11月5日至7日,由湖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湖北省曲藝家協會、中共襄陽市委宣傳部主辦的第十四屆湖北曲藝“百花書會”評獎活動在古城襄陽舉行。該活動是湖北省曲藝界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政府級曲藝獎項,從1981年至今已成功舉辦14屆,推出了一大批深受群眾喜愛的曲藝演員和曲藝作品。湖北曲藝界中,何祚歡、張明智、陸鳴、田克兢等均是從歷屆“百花書會”中嶄露頭角、脫穎而出的。
與河南“馬街書會”、山東“胡集書會”、安徽“苗湖書會”等書會相比,“百花書會”的資歷尚淺。20世紀80年代初,湖北省曲藝界組織重建湖北曲協,并于襄陽開展調研,經徐國華、蔣敬生、郝桂平、董治平等曲藝界人士積極倡議,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由省文化廳、省文聯主辦的“百花書會”于1981年正式落地。該活動旨在保護湖北省特有曲種,檢驗和推選優秀曲藝作品。“百花書會”走過近30年,見證了湖北曲藝由繁盛到迷茫又走向新征程的曲折歷程。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湖北曲藝大發展的時期。1981年至1989年,“百花書會”共舉辦5屆。歷時最長的是1983年在漢口民眾樂園舉行的的第二屆書會,為期9天;參會人數最多的為1985年第三屆,人數超過290余人,共收到170余個曲藝作品文本,其中的25個參加了書會演出①。1987年第四屆書會后還有《湖北省第四屆百花書會優秀作品選集》出版,集中收錄了湖北評書、相聲、快板書、獨腳戲、湖北大鼓、湖北道情等曲種作品,展示了湖北曲藝階段性成果,初步滿足了群眾在文藝寒冬后對精神食糧的迫切需求,也調動了曲藝工作者創演研究的積極性。據不完全統計,1989年至1992年,湖北曲藝的主要陣地之一,漢口民眾樂園共吸引全國40多個戲劇曲藝音樂雜耍團體演出2000余場,觀眾累計達150萬人次,出現了國內少有的演出盛況②。湖北曲藝工作者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湖北卷》編纂準備工作,歷經10年的不懈努力,在整理音樂文字資料500萬字、錄音帶近200盒、相關照片150張的基礎上③,《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湖北卷》于1992年作為原文化部《中國曲藝音樂集成》的首卷出版,為各省曲藝音樂集成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在群眾文化生活日漸豐富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雙重影響下,湖北曲藝專業團體紛紛改制,數量從80年代的22個縮減到僅剩武漢說唱團1個。隨之而來的人才流失使得湖北曲藝步入了低谷。1993年至2003年10年間,“百花書會”舉辦4屆,受經費與大環境的影響,舉辦者的熱情以及節目數量和水平均有一定下降,如2003年舉辦的第九屆書會,僅僅進行了少兒曲藝現場展演評獎。
21世紀以來,借著非遺保護工作的東風,湖北曲藝逐步探索出了新發展路徑。2006年至2018年,“百花書會”共舉辦6屆,不同曲藝藝術類別間的交流與互動日益頻繁,鮮明的流派特色得到進一步肯定與承認。在2008年舉辦的第十一屆書會上,跳三鼓、北路子大鼓、鄖陽四六句等多年未見的曲藝樣式重新出現。而2012、2015年的第十二、十三屆書會,曲種“豐度”進一步增加,湖北小曲、湖北大鼓、沔陽漁鼓、公安說鼓子、漢川善書、宜都梆鼓、宜都楠管、恩施揚琴、襄河道墜子等地方特色曲種與數來寶、相聲、快板等曲種同臺,為湖北觀眾奉獻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2018年第十四屆“百花書會”于2018年2月啟動,得到了湖北省曲協各團體會員、各級群藝館、文化館及相關院團單位積極響應。經過層層選拔,最終有26個作品從89個有效參評作品中脫穎而出,進入終評展演環節。在往屆的基礎上,本屆“百花書會”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參賽隊伍的多元化趨勢
創作上,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參與了部分作品的創作,如湖北大鼓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付群剛創作了漳河大鼓《鄉鎮紀檢員》,利川小曲省級非遺傳承人李源道創作了《決勝新征程》,沔陽漁鼓省級非遺傳承人夏祖勤創作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傳承》,說鼓子省級非遺傳承人徐華創作了《百姓心中有桿秤》,湖北評書省級非遺傳承人付三元創作了《天安門廣場看升旗》等。部分文藝理論家、音樂理論家、作曲家、編導也參與了部分節目的創作,如襄河道墜子《諸葛出山》創作者為曲藝理論家董治平,長陽南曲《歲月靜好人風流》作曲者是湖北省著名音樂家王原平。同時,書會上還涌現了少量集創作表演于一身的曲藝人,如孝感說唱鼓書、東山番邦鼓、湖北大鼓等節目的表演者,也是作品的創作人。
表演上,除武漢說唱團的專業演員外,湖北省各級文聯、曲協、文化館、電視臺、非遺中心等選派的演員占了大部分。而湖北藝術職業學院和湖北省土家族歌舞劇團等專業院校、專業文藝表演團體的加盟,更為湖北曲藝增添了不少專業色彩。另外,武漢市消防支隊和部分業余少兒藝術團隊的參賽也體現了湖北曲藝傳承逐漸普及化和社會化的動向。
創演隊伍規模的不斷擴大是維護傳統不斷代的有力保證,新的表演方式和新作品內容則是推動湖北曲藝緊跟時代的重要推手。
(二)表演形式的創新性探索
在本屆書會中,有11個節目在基本保留傳統表演和伴奏形式的基礎上,適度調整了樂隊和伴舞(唱)的規模,另有5個節目在表演形式上有較大的改變與創新。
在書會上展演的湖北小曲《水調歌頭·游泳》,有別于傳統的四胡或琵琶坐唱,采用了古箏彈唱這一新形式。擊三挑板演唱的利川小曲,在此次展演中演員又使用了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樂器三才板。鄖陽四六句突破了自彈自唱的傳統表演方式,采用了4人扮演固定角色、輔以8人樂隊的形式。長陽南曲、恩施揚琴的兩個作品都采用了較大的演員編制:長陽南曲作品有16人參與演唱表演,在傳統樂器小三弦伴奏的基礎上,增加了蓮廂、板等樂器,采取坐唱、站唱相結合的形式,并在唱腔音樂上融合了當地姊妹藝術長陽山歌、長陽花鼓子的風格;恩施揚琴作品,除一人擊板鼓演唱,另有8人擊打繪有鮮明地域文化標識的白虎圖騰鈴鼓配合演唱。
(三)作品內容的不斷豐富
本屆“百花書會”的展演作品,大部分為近年創作的傳播正能量、謳歌新時代、贊美新生活的作品,主題大體可分為以下5類。
1.諷刺不正之風。湖北大鼓《事關于己》批評了個別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宣傳了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性;78歲的鼓書藝人辛德井創作的洋洋兩萬余言的長篇孝感鼓書《血濺花燭夜》,假托古人故事,表達了老百姓對反貪反暴的訴求。
2.弘揚時代精神。鄖陽四六句《規矩》,將傳統道德規范與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講法律、講紀律、懂規矩等講話精神相結合,宣傳了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監察法》;云夢鼓書《人民公仆湯儉民》歌頌了湖北省優秀共產黨員湯儉民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對農業、農村、農民無限熱愛的先進事跡;漳河大鼓《鄉鎮紀檢員》反映了身邊的先進典型——優秀基層紀檢監察干部劉景貴的故事。
3.聚焦社會熱點。群口快板《大山情》反映了大學生邊遠山區支教的故事;天門說唱《搬豬場》呼吁與倡導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恩施揚琴《再訪吊腳樓》、保康漁鼓《趙家山尋水記》、小品《蹭網》等展現了黨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
4.謳歌全新生活。長陽南曲《歲月靜好人風流》用清雅婉轉、悠揚抒情的曲調歌詠了家鄉的美景與新生活。小品《下棋》呼吁全社會關注關愛新時代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利川小曲《決勝新征程》以農民的視角講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發生的巨變,表達了農民對十九大報告規劃的藍圖充滿希望,齊心協力奔小康的信心。
5.致敬歷史名人。襄河道墜子《諸葛出山》取材于諸葛亮,用曲藝的形式演繹了諸葛亮于襄陽躬耕苦讀,后出山輔佐劉備的歷史故事;著名曲藝藝術家何遠志將毛澤東同志著名詞作《水調歌頭·游泳》譜為同名湖北小曲,表達了一代偉人建設祖國的豪邁氣概。
二
第十四屆“百花書會”是近年來湖北曲藝創演成果的集中檢驗,也是當代湖北曲壇文化生態的生動縮影。通過對本屆書會展演參賽成員、表演形式、題材內容等方面的梳理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本屆書會涵蓋全省各區域的近30個曲種,創下“百花書會”歷史之最,體現了湖北曲藝工作者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自覺。湖北曲藝工作者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強調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統一,不斷推陳出新,發揮了“文藝輕騎兵”的重要功能。但是,通過此次“百花書會”,也可以管窺當下曲藝傳承的困難。
一、區域與曲種發展不均衡
本屆書會上湖北各區域報送作品的數量與獲獎情況,體現出湖北曲藝區域發展分布不平衡的特點。武漢及鄂中南、鄂西南、鄂西北等地區的曲藝發展、活躍程度較高,作品的形式內容較為多樣化。鄂東南、鄂東北地區的傳統鼓書仍有強大的生命力,但舞臺曲藝的發展后勁略顯不足,其他類型曲種發展的積極性未能充分調動。
2007年以來,湖北省已有5批共35項曲藝入選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參加第十四屆“百花書會”的展演作品,僅有湖北評書、湖北大鼓、湖北小曲、長陽南曲、恩施揚琴、說鼓子、沔陽漁鼓、利川小曲、鄖陽四六句、襄河道墜子、武漢相聲等11個省級非遺曲種,數量僅占全省曲藝類非遺名錄的三成。鼓盆歌、漢川善書、三棒鼓、跳三鼓等國家級非遺項目都未有優秀作品入選。結合近年各類曲藝賽事總體來看,全省曲藝品種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均衡的態勢,舞臺上較活躍的仍主要是湖北大鼓、湖北小曲、恩施揚琴、長陽南曲、襄河道墜子等幾個曲種。
這種發展不均衡的狀況,與部分曲種缺少代表性藝術家有密切關系。縱觀中國文藝發展史,代表性傳承人往往對一個曲種、劇種的繼承、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恰恰因為湖北評書有何祚歡,湖北大鼓有張明智、付群剛,湖北小曲有何忠華,襄河道墜子有郝桂平,這些曲種才一直活躍在藝術舞臺上、百姓生活中,并薪火相傳。
二、參與主體有局限
本屆書會有全省近百件作品參與評選,最終進入展演的有26個作品,參演人數170余人,本屆書會的規模可見一斑。而與參演和業內觀摩的人數相比,普通觀眾的身影稍顯單薄。盛大的“百花書會”僅僅成為“局內人”的盛會,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而離開了觀眾的表演就猶如離水之魚,終難煥發鮮活的生命力。可見,在曲藝復興的新征途上,新一代曲藝觀眾的培養需要提上重要議程。
另外,“百花書會”的評獎規則和獎勵機制也從一個側面影響了參與主體的多維度。本屆書會除新人獎外,主要有三大獎項:節目獎(一二三等獎)6個、表演獎(一二三等獎)7個、文學獎3個。獲獎者(單位)由湖北省文聯、曲協聯合頒發榮譽證書。這雖然體現出對曲藝表演人才及文本創作人才的關注,但與20世紀60年代和80、90年代的湖北曲藝評獎辦法相比照,今天的評獎辦法在曲藝人才的培養與激勵政策上仍稍顯不足。
在《湖北省文化事業管理局1963年曲藝創作評獎辦法(草案)》④中,在評選方法上,明確了專業團體與業余團體(辦法中稱為“市”)分別組織、選拔、推薦、評選的規則,兼顧了曲藝發展的專業性與普及性。要求“專、市評選小組,應將準備評選的作品先行組織演出,廣泛聽取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意見。然后將參加評選的作品,連同評選意見及群眾反映,一并報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曲藝工作組轉省評選委員會。”該《辦法》同時凸顯出曲藝作為群眾文藝的本質特點;在獎項設置上,將作品按篇幅分長篇、中篇、短篇分別評獎,同時根據創新程度分“新創作作品”和“新整理改編作品”,分別設置一二三等獎若干。在“新整理改編作品類別”中,又具體分為“從小說、戲劇等新文藝作品改編的曲藝作品”和“整理、改編的優秀傳統曲目”。這一舉措既有效地保護、整理了逐漸消失的長篇書目、傳統書目,又鼓勵了符合時代精神與現代審美的新作品的創作,既保護了曲藝作品的多樣性,又為藝術創作指明了方向。在獎勵辦法上,“評選出的優秀作品,除推薦各地專業及業余曲藝工作者上演和編印出版外,并發給獎金”。獎金標準最低15元/名,最高達到400元/名。此外,“小曲的曲譜也照上面標準另行發給獎金”。這在當時全國農民人均月收入水平5元的標準下,可謂是極大的激勵。而在“百花書會”的歷史上,從第二屆(1983)至第七屆(1996)也曾設立過作曲獎(配曲獎、編曲獎),從第二屆(1983)至第六屆(1993)均設立過“伴奏獎”。這些競賽規則都對相應時期的曲藝創作、編曲、伴奏人才培養發揮過積極作用。
顯然,本屆“百花書會”的關注層面還較為單一,這也是當前全國各類曲藝賽事的普遍現象。中國曲協副主席吳文科認為,“不僅要重視和培養曲藝演員,還要重視和培養曲藝的曲本作家、伴奏弦師、教師編輯、專家學者等”⑤。但目前曲藝界中表演創作俱佳的曲藝人較少;曲藝唱腔音樂作為區分曲種的重要標志,編曲創作的研究成果不足;相較于曲藝創演,曲藝理論研究人才培養明顯滯后;評論宣傳力度不夠,優秀新作品未能得到及時推廣;伴奏弦師老齡化嚴重,伴奏人才的培養尚未引發重視;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通識領域,曲藝師資力量匱乏。
三、繼承與創新關系較模糊
第十四屆“百花書會”展演中,大部分的作品都采用了大編制的樂隊伴奏或創新的表演形式,個別傳統打鼓說書節目遭遇“滑鐵盧”。一位每天在茶館說書的參賽老藝人,言談中流露出失意與不甘:“早知道專業團體來參賽,我們農民曲藝人就不該來的”“民間的,古老的只能靠邊站了”。這雖是個案,但也提示我們今天的曲藝評獎與賽事中,對待曲藝的繼承與創新某種程度上更需要注意分類引導。繼承與創新本就是硬幣兩面,是中國曲藝發展不可分割的整體。僅關注創新,不談繼承,會在一定程度上傷害民間曲藝人的參與熱情。
通過對第十四屆湖北曲藝“百花書會”基本情況的介紹及相關問題的思考,試對新時期曲藝發展提出以下倡議。
第一,各級主管部門要積極引導與支持各類曲藝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傳承與傳播活動,發揮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領頭羊”作用。同時,要進一步完善曲藝競賽評獎細則,加強新一代曲藝觀眾的培養。
第二,文化部門要與高等教育的相關院系、非遺中心聯姻,充分發揮高校在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中的優勢,促進曲藝理論批評、伴奏、編曲、教育人才培養。
第三,新一代曲藝表演者要努力加強理論修養,提高創作能力,處理好藝術實踐與學術研究之間的互動關系。實際上,湖北曲藝老一輩的諸多創作、研究專家如甘發新、張長安、何遠志、陳世鑫等均為弦師或演員出身。扎實的藝術實踐功底為他們后來的創作與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他們創作與理論研究的成果又反過來推動了藝術表演的發展。
第四,在培養新人、關注新作品的同時,民間老藝人肚子里的那些寶貴的傳統書目和表演創作經驗的整理與繼承也需要曲藝界給予重視與關注,且更加急迫。呂驥同志就曾在80年代曲藝音樂“集成”工作中指出:“先要繼承才能發展,才能創新。”⑥習近平同志也談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保護好曲藝多樣性,理清繼承與創新兩者的關系,同時讓創新遵照曲藝的特點與規律有序展開是新時期曲藝復興的當務之急。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祝福湖北曲藝與各區域、各民族曲藝攜手,共筑新時代中華民族的文化百花園!
注釋:
①《湖北省曲藝家協會簡介》,湖北文藝網,2017年8月17日,http://www.hbswl.gov.cn/ doc/2017/08/17/19837.shtml。
②王耀:《民眾樂園的前世今生(三)——最后的輝煌》,載《戲劇之家》2010年08期,第49-51頁。
③湖北省群眾藝術館編印:《湖北說唱音樂集成(第五集)》(內部資料),1992年,第431頁。
④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湖北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湖北卷》,中國ISBN中心2000年出版,第804頁。
⑤張艷:《為了曲藝事業的健康發展與全面繁榮——訪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吳文科先生》,載《戲劇叢刊》2013年01期,第34-38頁。
⑥呂驥:《溫故知新抓緊收集整理曲藝音樂遺產——在〈中國曲藝音樂集成〉第一次編輯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載《中國民族音樂集成文件資料匯編》(內部資料),1986年,第187頁。
[本文為湖北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對接視野下的“戲曲進校園”師資培育路徑與方法研究》(2017GB076)階段性成果]
(作者:湖北第二師范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