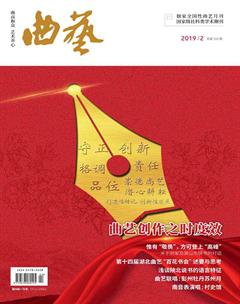廣繼承
關于曲藝的發展,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曲藝要前行,必須有“手段”。這個手段,就是要有繼承傳統、創新驅動曲藝發展的具體辦法。山東琴書的劉士福老師,幾乎是一成不變、一字不改地唱傳統唱段“偷年糕”,但是唱一句大家就鼓掌,為什么?為他唱腔的味道、為他方言的地道、為他的鄉土氣息拿捏得極其準確、為他一點都不做作的那股純真勁兒鼓掌。這方面,他是有其不同于別人的表演方法的;大家為天津曲藝團的“羽扇”鼓掌,為什么?為他們絞盡腦汁地創新、積極地吸收舞美和表現形式的獨特,為他們忠實于曲藝地道的流派韻味鼓掌。我和崔凱同志討論過,認為現有的曲藝理論概念如果針對舊曲藝的生存狀態和表現形式還是比較準確的。但是,如果把這些現有的曲藝概念奉為金科玉律來規范和約束現實中正在發展變化著的曲藝藝術,就會出現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用過時的老概念來否定新生的、改革的、探索的曲藝創作和表演問題就更為嚴重。藝術是流動著的美學,一成不變的美學理論是不存在的,用死概念捆綁活藝術的做法是不符合從實踐到認識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原則的。戴宏森老師生前給我說,保證“大曲藝”戰略的發展,有三個要點:廣繼承、多吸取、勤實踐。下面是他給我的觀點。
——姜昆
“大曲藝”觀念要求曲藝工作者既要有自己從事的局部曲藝的視角,也要努力把握曲藝總體的視角,兩者密切結合,才能打開曲藝改革創新的思路。這還不夠,“大曲藝”視野之“大”,還要求將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所有說唱藝術積累下的寶貴遺產,都看作可資繼承與開發的豐富資源,為我所用。由“大曲藝”引申出“廣繼承”,這是曲藝改革創新題中應有之義。
傳統曲藝的傳承方式主要是一輩輩師徒“口傳心授”,那時的曲藝藝人所處的生存競爭環境,決定了對藝術的傳承一般采取保守主義的態度,“寧贈一錠金,不贈一句春”(春,意即話語,這里指訣竅),“藝不外傳”,是不可能“廣繼承”的。隨著經濟規模、文化市場和傳播技術手段的擴大,繼承的觀念也在由小而大。藝人們不僅要從師父、師爺那里繼承本行藝術,而且要從本行藝術及相關藝術的歷史遺產中溯源淘寶,促進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傳統曲藝中的傳世名作,就可以發現這種“廣繼承”的作用。如傳統對口相聲《鈴鐺譜》(《蛤蟆鼓兒》與《鈴鐺譜》合編)甲乙爭論什么東西叫得最響,為什么?從蛤蟆爭到鈴鐺,以片面性反對片面性,笑話連篇。經考,此段直接繼承了傳為宋代蘇軾編的笑話書《東坡居士艾子雜說》,不知是被哪位前輩引入了相聲。北京曲種太平歌詞傳統代表作《勸人方》傳為相聲奠基人窮不怕所留,流傳最廣。開頭有四句引詞“莊公閑游出趟城西,瞧見了他人騎馬我就騎著驢,扭項回頭瞧見一個推小車的漢,要比上不足也比下有余”,經查《敦煌遺書》,這四句竟是直接繼承了初唐通俗詩人王梵志的一首白話詩《他人騎大馬》:“他人騎大馬,我獨騎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意即較好些)。”(見于《王梵志詩校輯》19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傳統相聲中直接繼承古代笑話、民間故事、正史野史、筆記小說中有用資源的很多,如《扒馬褂》源于《圓謊》,《日遭三險》源于《火燒裳尾》,《吹牛》源于《謎》《且只說嘴》,新編《五官爭功》也是在《嘲人不識羞》《舌鼻爭功》等多篇古代笑話的基礎上編成的。
曲藝的藝術創新離不開兩個源泉:一個是對現實生活的提煉與升華;一個是接收歷代說唱藝術家積淀下來的生活體驗和創作成果。這種繼承不限于一般師徒授受的狹義繼承,而是一種廣義的繼承。舉凡本門本行先人們留下的文本、冊子、藝訣、藝諺、曲譜、絕活、審美觀念、文學類型、結構模式、表演程式、語言技巧、文字游戲等,都應納入我們的搜索范圍,做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溫故知新,古為今用。比如鼓曲唱曲類曲藝,就不能僅僅注意繼承清代形成的大鼓、單弦、彈詞、曲子,繼承的視野還應擴展到唐宋詞曲、元明散曲、俗曲之類,從中獲取創新的營養,啟動創新的靈感。
現在,許多曲藝品種進入了國家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名錄,強調保護要“原汁原味兒”,這不僅是保護工作所需,也對曲藝在廣泛繼承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非遺保護工作本不是要把保護對象束之高閣、偶爾展示,而是要善于調動、利用這些遺產資源,促進今日曲藝改革創新,增強活力,打開廣闊的發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