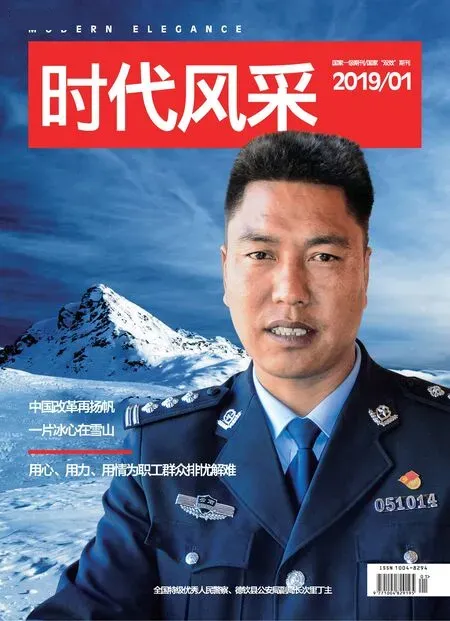走近昆明零工市場
文 何文龍
“打零工”除了要面對收入不穩定因素的困擾,還要面對缺乏必要勞動保障的困境。當發生爭議的時候,打零工很難享受到跟合同工相同的待遇,況且,我國法律在“零工”領域還有空白,給勞動者維權帶來困難。
初冬清晨,時針正走向6點。很多人的鬧鐘還沒響,即使響了也要在被窩里再賴上一刻。因為這時的昆明,正是一天中最冷冽的時候。大街上行人還很少,車輛也不慌張,道路寬敞,不用擔心擁擠。
在普吉路和王家橋路的交叉口,是另一番景象——熙熙攘攘、人頭攢動,七八百號人早早來到這里,準備打零工。
站在人群中,抬頭看遠處的天,一片墨藍。遠處高樓的輪廓猶如被裹在一團棉絮中,模糊不清。
“這地方人最多的時候,有兩千多人。”一名等工的師傅說,“現在天氣冷了,有的人還沒有來,也有人已經等到了今天的活計,干活去了。”
在人群中慢慢走過,耳邊飄過祿勸、尋甸、楚雄、宣威、會澤、紅河、昭通口音。人群中也有來自四川、甘肅、貴州、河南的外省人。
聚在這里的,有20多歲的年輕人,但更多人是四五十歲年紀。其中男工占了大多數,因為在這個站工市場,活計大多是體力活——搬運工、綠化工、建筑工地上的臨時工。
這里的人們,臉上寫著同一種期待:“下一個老板哪哈來?”
一輛面包車靠近人群停下。車窗剛搖下來,車子四周已經圍滿人。大家都想盡可能離“老板”近一點。
“老板,找工嗎?”不同的口音問著同一個問題。
車里坐的大都不是老板,有的是工頭,有的是打工者。但在站工們看來,都是老板。
“工地上做雜活,要4個人。”車里的人簡單說了工地的位置和工種、工期。
在這里,人們等的基本都是雜活。工地上的雜活包括給師傅們打下手、拎水泥、拌沙灰、打掃衛生等。綠化的雜活包括栽花種樹等等。這些雜活的共同點是不需要太多專業技能。
“工錢咋個算?”“130元一天。”
這個價錢在站工們看來還不錯。這里男工的市價每天約120元~150元,女工80元~130元左右。
“時間挺長,地方又遠……”有人希望能再加點錢,討價還價的數目是十多元錢。不過如果活計是多天的,甚至是一周的,站工們不會再議價。
價格商量好,有的人直接上了“老板”的面包車,有的則記下地址后自己過去。前往工作地點的方式主要取決于“老板”怎么來的——有人開面包車,有人開轎車,還有人騎電動車。后兩種沒法帶人,站工們只能自己想辦法前往。
找到活的人一臉輕松,沒找到的轉身繼續回到街邊等待。
清晨6點半到早上8點,是“老板”出現最集中的時刻,也是站工市場最熱鬧的時刻。
很多站工因為起得早,還沒來得及吃早點,他們便會借助在街邊等工的時機來到附近的早點攤前,花幾塊錢買包子或蕎餅,如果買了烤洋芋,他們會熟練地找到早點攤老板插在小車座位旁的水果刀和辣醬缸,把烤洋芋劃成兩瓣,抹上自己喜歡吃的醬。
有著落
早上8點多,天色漸明,行人和車輛逐漸增多,普吉路和王家橋路都迎來早高峰。
站工的人來了走,走了來,面孔雖然不同,但穿著大致相似。男人們都喜歡戴個安全帽或鴨舌帽,腳上穿一雙黑布鞋或解放鞋,衣服和鞋子上大多沾著上一次工作留下的泥巴等痕跡;女人們戴的帽子帽檐更寬更大,也有系著花格子圍裙的。
為了工作方便,站工們穿得都少。男人們在冷風中守候了一兩個小時,感覺冷了,便點上一支煙,默默吸著。他們身旁會帶著工具布包,或者說是超市購物袋,里面裝的是一些磚刀、擦板等工具。這個布包和他們頭頂的帽子一樣,是他們每天干活的必備品。
男人們無聊時就三五結隊打起撲克牌,女人們則一刻不停,納著鞋墊、繡著花。
直到中午,站工們才會慢慢離開,吃完午飯以后,部分人還是繼續回到了這里。
這些人多數租住在附近,每戶十幾平方米,月租300多元。“即便早上沒找到事情做,還是在這里守著會好些,要是運氣好,起碼能等來晚飯錢。”來自會澤的劉樹林(化名)告訴記者,“剛剛那3個工人在這里守了大半天,來了個騎電動車的女人,需要找人幫忙扔裝修垃圾,開價60元,去了3個人,每人能分20元,晚飯也算有著落了。”
為了誰
46歲的劉樹林在這里當站工四五年,他曾去過很多地方打工。1998年,大兒子兩歲,他和妻子決定重新建一間房,盡管手里拮據,但夫妻倆還是咬咬牙,貸款、借錢湊了3萬元,蓋了新房。“房子是蓋好了,一棟磚瓦房,但除了外面的磚瓦框架,家里啥都沒有,就連地都是泥巴的,玻璃窗都沒全安裝。到了冬天,四面透風。”劉樹林說,為了掙錢繼續修房子,他跟著鄰居家的女婿去省外的一個石場打工。
“去的路上差點被騙了。”劉樹林說,半路上有陌生男子來搭訕,稱可以給他們介紹更好的去處。過了一會兒,眾人身邊走過一名挎著皮包的女子,女子的包里掉出一個皮夾,大家都看見了,但沒人敢去撿,陌生男子跑去撿了起來,轉頭告訴大家,里面是錢,很多,打算和大家分。劉樹林回憶說,他瞥見那沓錢里夾著很多報紙,于是趕忙拉著眾人走開了。
后來,眾人來到采石場,干了兩個多月,就遇到了大雪封山,老板給了路費讓先回家,年后再回來干活,干完以后結算工資,從此老板再無音信。
“在家專心種地不出來打工,每天算下來只能掙四五十元。”劉樹林說,按照現在的工價,有時運氣好一天12小時能掙150元甚至200多元。一個月15到20天有活,兩口子加起來能掙六七千元。“主要是時間好調節,家里面孩子、老人有時需要照管,打零工能顧家。而且干一天結一天的工錢,沒多高的風險,如果干一天拿不到錢,大不了第二天不去干了。”
說起孩子,劉樹林很欣慰:“孩子馬上大學畢業,還算聽話懂事。不論如何,我們這一輩子已經這樣辛苦了,不能再讓孩子走我的老路。我就是吃了不識字的虧,一輩子出著苦力,還容易遭騙,我得讓孩子多識字。為了孩子,我們再苦再累也都值得。”
站在記者面前的劉樹林,那雙大腳趾處已經破了洞的黑布鞋里還缺一雙襪子,頭發上的灰塵把他黑色的頭發染黃。但臉上皺巴巴的皮膚在他談到孩子時,卻仿佛有光。
“打零工”除了要面對收入不穩定因素的困擾,還要面對缺乏必要勞動保障的困境。當發生爭議的時候,打零工很難享受到跟合同工相同的待遇。況且,我國法律在“零工”領域還有空白,給勞動者維權帶來困難。
當勞動力市場發生變化,法律、政策勢必要面臨挑戰。對于“零工經濟”這種新型的勞動關系,不少國家都出臺了法律法規,但“打零工”在全世界范圍內還是一種新鮮事物,可借鑒的例證并不多。
業內認為,隨著全球有效勞動力的遞減,“打零工”不再只是個人的選擇,更是國家層面必須納入考慮的問題。當個人在為適應新經濟的新需求不斷提升技能的時候,政策制定者也應該及時出臺相應的法律政策,保障雇傭雙方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