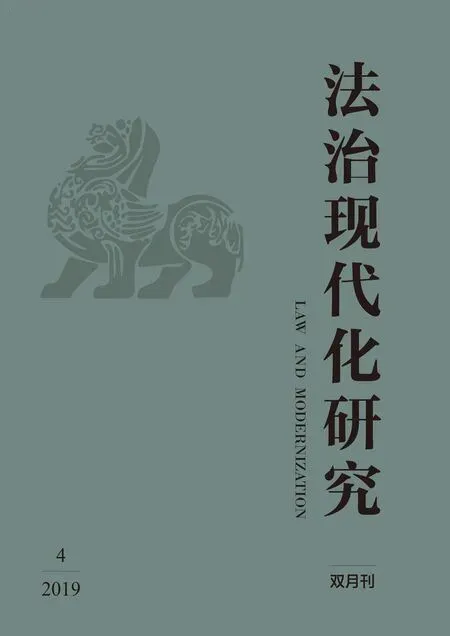《民法總則》中“綠色原則”的憲法依據(jù)及其展開
張 震 張義云
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外國學者已經(jīng)指出,在21世紀由生態(tài)危機所導致的對人類社會的威脅,將會替代核戰(zhàn)爭的威脅。(1)參見Alexandre S. Timoshenko, Ecological Security: Global Change Paradigm, 1 Colo. J. Int’l Envtl. L. & Pol’y 127(1990).環(huán)境問題以及其所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迫使國家在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領域肩負起更多的職責。但是,民事主體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必須將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納入到民事活動中。
“生態(tài)文明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2)習近平:《推動我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載《求是》2019年第3期。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綠色”發(fā)展理念蘊含了豐富的環(huán)保價值,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及十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也多次提及環(huán)境保護與生態(tài)治理;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生態(tài)文明”“新發(fā)展理念”等寫進憲法,標志著對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視,也為法律措施的制定提供了憲法依據(jù),并將從權利、義務角度對公民的個人行為產(chǎn)生影響。(3)參見張震:《中國憲法的環(huán)境觀及其規(guī)范表達》,載《中國法學》2018年第4期。在“綠色原則”產(chǎn)生之前,學界對“綠色民法典”的呼聲不斷。(4)進入21世紀以來,學界對“綠色民法典”的關注度和呼聲不斷。僅就發(fā)表的文章的標題來看,就有一批蘊含著“民法典綠色化”觀點的文章。如呂忠梅:《如何“綠化”民法典》,載《法學》2003年第9期;呂忠梅:《“綠色民法典”制定與環(huán)境法學的創(chuàng)新》,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2期;曹明德、徐以祥:《中國民法法典化與生態(tài)保護》,載《現(xiàn)代法學》2003年第4期。而現(xiàn)行民法總則第9條規(guī)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這不僅是對憲法環(huán)境權的有力回應,也從民事私法的角度主張了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將綠色原則確立為基本原則,規(guī)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這樣規(guī)定,既傳承了我國天地人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理念,又體現(xiàn)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發(fā)展理念,與我國是人口大國、需要長期處理好人與資源生態(tài)的矛盾這樣一個國情相適應。”(5)李建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的說明》,載“新華網(wǎng)”,http://www.xinhuanet.com/2017-03/09/c_129504877.htm,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5月8日。《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的說明》更進一步解答了“綠色原則”的產(chǎn)生背景和實踐價值。為了實現(xiàn)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目標,我們必須從制度以及觀念層面作出相應的回應。現(xiàn)行憲法規(guī)范中的環(huán)境權條款,具有“模糊性與原則性”(6)筆者認為,“環(huán)境權”作為一項新興的基本權利。關于其“模糊性”,從形式上來看,不僅是憲法文本中沒有直接體現(xiàn)“環(huán)境權”三個字;從實質(zhì)上而言,憲法文本中的關于“環(huán)境權”的規(guī)定,都比較原則和宏觀,不能直接運用于實際的情形之中。參見吳衛(wèi)星:《環(huán)境權的中國生成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展開》,載《中國地質(zh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環(huán)境權:法律關系主體享有的各種與環(huán)境相關的法律權益統(tǒng)稱。狹義的環(huán)境權僅指公民個人享有的環(huán)境權益,廣義的環(huán)境權還包括法人、國家的環(huán)境權益。環(huán)境權不是一個單一的法律權利,而是一種綜合的概括性權利,包括與環(huán)境相關的各種權利和利益。……”基于前述對“環(huán)境權”的描述,可見其也是一個兼?zhèn)涠喾N內(nèi)涵與外延的復合型概念。詳情可見王曦主編:《環(huán)境法學》,中國環(huán)境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頁。特點,需要“綠色原則”展現(xiàn)其本質(zhì)并將其具體化,使之更好地發(fā)揮保護環(huán)境、節(jié)約資源以及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作用,更好地實現(xiàn)憲法關系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
一、立足于憲法根據(jù)的“綠色原則”
日益惡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需要不斷強化的環(huán)境保護推動了“綠色原則”的產(chǎn)生。(7)參見王利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詳解》(上冊),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5-46頁。但是從立法依據(jù)的角度而言,“綠色原則”需要從憲法規(guī)范的內(nèi)涵中尋找根據(jù),才能使“綠色原則”符合合憲性審查的結果,才能更準確地把握憲法與民法在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上的關系。筆者認為,以下提及的憲法根據(jù),都可以是“綠色原則”產(chǎn)生的直接或者間接的依據(jù),這些憲法依據(jù)使“綠色原則”的框架更加立體與飽滿。
(一)源自憲法序言中的“綠色”內(nèi)涵
“健全社會主義法治,貫徹新發(fā)展理念……生態(tài)文明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8)現(xiàn)行憲法序言第七段。首先,其中的“新發(fā)展理念”包括了“綠色”的發(fā)展理念,“綠色”發(fā)展理念要求在發(fā)展過程中踐行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方針和策略。也即表明了不論是發(fā)展的過程,抑或發(fā)展的最終結果,都要始終遵循“綠色”理念。對應到民法總則“綠色原則”而言,即民事主體實施的民事行為應當符合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價值目標。其次,“生態(tài)文明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則直接闡述了發(fā)展過程中要明確堅守的底線,即協(xié)調(diào)的生態(tài)文明。“協(xié)調(diào)的生態(tài)文明”不是粗放的、以資源浪費為代價的文明,相反,筆者認為,“協(xié)調(diào)”強調(diào)整體與系統(tǒng),而不是片面與孤立的。從“綠色原則”的層面而言,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任何民事活動都不能以破壞環(huán)境與生態(tài)文明為代價,而是要追求個人利益與環(huán)保利益的有機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再次,“美麗”一次間接地蘊含了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內(nèi)涵,她不僅使人在感官上或是心理上都會感受到由美好環(huán)境帶來的欣慰,也會促使個體對美好生活環(huán)境的追求與向往。對于民事主體的民事行為而言,踐行“綠色原則”也成為應有之義,并自覺地將自身的行為納入“綠色原則”的指導之下。
(二)立足于國家環(huán)境保護義務的展開
“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9)現(xiàn)行憲法第一章第26條第1款。這是對國家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上應該承擔義務的規(guī)定。持反對觀點的學者可能會認為該條不能作為民事私法領域的立法依據(jù),更不能作為“綠色原則”產(chǎn)生之根據(jù)。但是,從人文色彩的角度而言,有觀點認為憲法學的發(fā)展是一個追求人性與人文價值的過程,從人文價值追求的角度來看,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就彰顯了人性關懷的色彩。(10)參見韓大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憲法學的學術貢獻》,載《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5期。因此,這不僅是對我國人民不斷追求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回應,也是“綠色原則”的間接憲法依據(jù)。首先,雖然該條表達的是國家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義務,但是其從憲法規(guī)范的角度明確規(guī)定了“生活環(huán)境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為其他部門法的環(huán)保立法活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jù),民法總則“綠色原則”的出臺也與此息息相關。其次,在法律規(guī)范層面標志著環(huán)境保護的對象即生活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已經(jīng)不再是無法可依的狀態(tài),“綠色原則”追求的“節(jié)約資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正是對該條的有力回應。最后,從規(guī)范意義而言,作為明確的保護“生活環(huán)境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憲法規(guī)范,是憲法作為根本大法在環(huán)境保護領域制度框架上的體現(xiàn),有利于指導民法總則環(huán)境保護功能符合憲法環(huán)境權精神。
(三)尊重與保障人權原則
人權具有具體的社會價值。尤其是在環(huán)境惡化、生態(tài)不平衡的境況下,環(huán)境權體現(xiàn)出來的人權價值就更加明顯。有學者指出,從自然法意義層面而言,環(huán)境權也應當是一項基本人權;從實定法意義層面而言,環(huán)境權作為基本權利或法定權利的屬性也愈加明顯。(11)參見呂忠梅:《環(huán)境權入憲的理路與設想》,載《法學雜志》2018年第1期。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提高而增強的環(huán)保意識與環(huán)境資源稀缺性凸出的特點形成對比,環(huán)境利益成為不可或缺的物質(zhì)與精神追求,由此環(huán)境權就成為一項實際的人權。(12)參見張震:《民法典中環(huán)境權的規(guī)范構造——以憲法、民法以及環(huán)境法的協(xié)同為視角》,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可以明確的是,當生存與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發(fā)生變化,即人們開始追求良好的發(fā)展條件,更需要“良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的時候,環(huán)境權的價值就會逐漸彰顯,因而,人權的價值也會隨著“良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而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此,我們也可以更加清楚地明白環(huán)境權已經(jīng)成為實實在在的人權,并在環(huán)保領域發(fā)揮著巨大作用。“時至今日,良好的環(huán)境是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是體面生活的保障。換句話說,維護人的尊嚴需要良好環(huán)境,人的尊嚴為環(huán)境權提供權利正當性的價值基礎。”(13)張震:《憲法上環(huán)境權的證成與價值——從各國憲法文本中的環(huán)境權條款為分析視角》,載《法學論壇》2008年第6期。因此良好的環(huán)境在人的尊嚴維護層面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對前述觀點的分析中我們又可以明白,良好的環(huán)境、平衡的生態(tài)對于一個人能否體面地生活,能否保證人權不被踐踏并尊嚴地活著的重要性。因而,人的尊嚴的維護需要環(huán)境權,保護環(huán)境與維護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對人權的尊重。就民事私法領域而言,就更需要能夠發(fā)揮指導與評價作用的“綠色原則”。
(四)權利不得濫用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14)現(xiàn)行憲法第二章第51條。此外,基于“綠色原則”與民法總則第132條所規(guī)定的“民事主體不得濫用民事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之緊密配合而產(chǎn)生的確保民事主體正當行使民事權利、維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作用。(15)前引⑦,王利明書,第45頁。筆者認為憲法中規(guī)定的權利不得濫用原則,表明了對個人權利行使界限的限定,應該作為“綠色原則”產(chǎn)生的憲法依據(jù)。首先,從內(nèi)涵上看,權利不得濫用包含了公民行使權利時的限制與界限,民事主體不得濫用自己的權利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而“綠色原則”中也包括了民事主體從事民事行為時“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義務,個人權利的行使應該圍繞以“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為中心展開。其次,從形式上看,權利不得濫用原則中“不得損害”一詞屬于強行性規(guī)定,劃清了個人權利行使的底線。對于“綠色原則”而言,也應然地包含了行使民事權利時不得濫用個人權利,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生態(tài)利益。再次,“綠色原則”不僅是一個原則也應當是一個可行的規(guī)則。“因此通過民法基本原則可以判斷某項制度或權利在民法中的重要性及可行性。”(16)前引,張震文。“綠色原則”發(fā)揮了評價民事主體的民事行為是否有利于保護環(huán)境、節(jié)約資源以及建設生態(tài)文明,通過該原則可以清楚地預見民事活動的過程乃至結果,以及民事主體權利行使得當與否。
二、“綠色原則”的規(guī)范構造
民法總則第9條規(guī)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這一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被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綠色原則,是我國民法典對世界民法發(fā)展作出的獨特貢獻,深刻體現(xiàn)了憲法中的環(huán)境條款,并具有獨特的規(guī)范內(nèi)涵。”(17)前引,張震文。作為未來民法典編撰必須考慮的“綠色化”板塊,“綠色原則”蘊含著豐富的環(huán)保價值,并反映了民法基本原則順應民法“開放性與發(fā)展性”的基本規(guī)律和邏輯。(18)參見王旭光:《環(huán)境權益的民法表達——基于民法典編纂“綠色化”的思考》,載《人民法治》2016年第3期。不僅如此,具有首創(chuàng)性的“綠色原則”也反映了當前我國嚴峻的環(huán)境形勢,并深刻地蘊含了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資源的高效利用等內(nèi)涵。(19)前引⑦,王利明書,第46-47頁。但是有觀點認為,“綠色原則”作為公法或者社會法的原則,不應該納入到民法基本原則的范圍之內(nèi)。(20)參見趙萬一:《民法基本原則:民法總則中如何準確表達?》,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筆者認為,民法總則首創(chuàng)性地規(guī)定了“綠色原則”不僅是對當前我國環(huán)境保護形勢嚴峻性的反映,也進一步闡明了社會活動中的民事主體,不能將自身的行為與環(huán)境保護的理念“背道而馳”。因此,“綠色原則”的制定是真切地期待寬泛的民事活動追求“綠色化”,進而實現(xiàn)保護環(huán)境、節(jié)約資源以及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目標。
(一)“綠色原則”的主體界定
民法總則第9條對“綠色原則”的主體進行了界定。“民事主體”的范圍不止公民,(21)一般認為“公民”概念的政治性較強,通說認為其指代的是具有一國國籍之個人。區(qū)別于民法通則中規(guī)定的“公民”概念,顯然,“民事主體”這一稱謂包含了“公民”,其周延的范圍也廣于“公民”。這樣規(guī)定不僅擴大了主體的外延,也囊括了民事活動中的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包括自然人、(22)筆者認為“自然人”就是存在于一切社會活動中的個體,它突破了國籍、年齡的限制,將社會活動中的個體都包括進來,體現(xiàn)了全民參與的價值取向。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在特定的情形下,國家機關也成為該原則的實施主體。這樣的規(guī)定不僅擴大了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主體范圍,也體現(xiàn)了“全民”參與的價值取向,更進一步體現(xiàn)了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所帶來的利益與應該承擔的責任,以及追求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價值取向。(23)參見[日]黑川哲志:《從環(huán)境法的角度看國家的作用及對后代人的責任》,王樹良、張震譯,載《財經(jīng)法學》2016年第4期。主體范圍的擴大不僅擴大了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參與者的范圍,事實上,在實踐層面上也擴大了參與者的范圍,并將直接影響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效果。可以說,“綠色原則”之所以這樣規(guī)定,就是為了將廣泛的民事活動都印上“綠色”的標簽,通過囊括寬泛的民事活動中的“人”、物、財達到其所追求的“綠色目標”。
(二)“綠色原則”的保護客體
現(xiàn)階段,經(jīng)濟社會快速發(fā)展與資源短缺、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形成鮮明對比。自然資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脆弱性特點,決定了“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成為“綠色原則”的保護客體,二者在“綠色原則”的規(guī)范構造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資源”在民事活動中能夠為民事主體帶來經(jīng)濟利益,為了更好發(fā)揮自然資源經(jīng)濟效益,物權法第119條規(guī)定了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但是高能耗經(jīng)濟活動中資源利用的矛盾與沖突,以及自然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綠色原則”必須將“資源”作為保護對象,并確立其在民事主體經(jīng)濟活動中的重要地位。“生態(tài)環(huán)境”主要強調(diào)自然的因素,自然環(huán)境作為一種重要物質(zhì)條件應該受到應有的重視與保護。(24)參見張震:《憲法環(huán)境條款的規(guī)范構造與實施路徑》,載《當代法學》2017年第3期。作為“綠色原則”的保護對象,說明了人類活動不應該對自然環(huán)境過度干涉,而是應該尊重和主動保護的狀態(tài)。
(三)“綠色原則”的目標追求
“綠色原則”明確規(guī)定了“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表達了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應當堅持的目標追求。“大自然的很多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 提倡節(jié)約利用資源是現(xiàn)代社會人類應該具有的基本價值觀念之一。”(25)前引,張震文。因此,“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理應成為民事主體從事任何民事活動時的目標追求。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尤其是實施可能會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產(chǎn)生負面影響的活動時,應該盡量避免造成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后果。從積極的角度而言,民事主體實施民事行為時,要努力追求節(jié)約資源的效果,達到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目的,將“節(jié)約資源”完全貫徹到民事主體實施的民事行為的整個過程。從消極的角度而言,民事主體應該杜絕個人權利的濫用,克制有可能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產(chǎn)生負面后果的行為。因此,“綠色原則”之中的“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指導民事主體民事活動的“起點、過程、結果”環(huán)節(jié),以促使民事主體達到“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目的。
三、“綠色原則”中蘊含的憲法環(huán)境權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經(jīng)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矛盾高發(fā)期,環(huán)境問題的妥善解決需要完備的環(huán)境法治體系予以應對。對于民事領域的環(huán)境保護而言,則需要民法在寬泛的民事活動領域中發(fā)揮環(huán)保功能。作為基本原則的“綠色原則”發(fā)揮著實際的指導與評價功能,也蘊含著豐富的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以“權利”為核心建構起來的,并具有顯著的開放性與發(fā)展性特點的民法體系,面對生存環(huán)境惡化、資源浪費嚴重、生態(tài)環(huán)境失衡等情況,民法權利體系所要求的權利保護的需求,自然擴展到保障和滿足民事主體的環(huán)境權利領域。而憲法環(huán)境權的抽象性表達與概括性規(guī)范需要民法思維予以解讀,才能架構起基于溝通與整合基礎之上的“憲法—民法”環(huán)保價值體系。
(一)民法表達方式下的憲法環(huán)境權
“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該規(guī)定展示了處于“權力本位”的國家所承擔的環(huán)境防治職責,也強調(diào)了國家應該履行憲法規(guī)定的環(huán)境防治義務。這種基于國家立場的環(huán)保義務,其周延性主要覆蓋了國家的環(huán)境保護職責,但是也需要從國家層面走向民事主體層面,才能更好地實現(xiàn)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目標。如前所述,憲法環(huán)境權是一種帶有“模糊性與原則性”的權利,準確地對其予以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從民法思維的角度解讀“綠色原則”之中的憲法環(huán)境權就限定了解釋的邊界與范圍,減輕了民事主體的理解難度。從民法思維角度詮釋憲法環(huán)境權的價值就是將國家的環(huán)境防治義務與民事主體的環(huán)保權利、義務結合起來理解,并解讀出民法表達方式之下的憲法環(huán)境權。
1. 蘊含溝通職能的憲法環(huán)境權
面對日益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時,詮釋憲法環(huán)境權的價值需要與民法進行良好的溝通,作為基本原則的“綠色原則”所持有的環(huán)保價值,是實現(xiàn)與憲法環(huán)境權溝通的有益路徑。憲法環(huán)境權在民法領域中的合理表達,是“綠色原則”對憲法環(huán)保精神的積極回應。(1)從民法總則的內(nèi)部價值意義來看,“綠色原則”規(guī)定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時,應當有利于節(jié)約資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形式上而言是對民事主體民事行為的引導和規(guī)范,旨在確立民事主體在民事領域中的環(huán)保理念。事實上,國家各項必須履行的義務需要人的參與,憲法環(huán)境權中包含的國家環(huán)保義務與職責的實現(xiàn)最終也需要人的參與。(26)國家是由公民構成的集合,因此整個集合的運轉都需要人的參與,國家職能的實現(xiàn)最終還是需要人的參與。參見[英]馬丁·洛克林:《為國家學辯護》,王鍇譯,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立足于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的“綠色原則”將憲法環(huán)境權所包含的更高一級的環(huán)保價值細化為民事領域內(nèi)民事主體的環(huán)境保護義務。“憲法保持它的效力根本上在于,它預設了一個潛在的實質(zhì)憲法。”(27)前引,馬丁·洛克林文。因此,依據(jù)憲法而產(chǎn)生的“綠色原則”成為在民事領域內(nèi)發(fā)揮環(huán)保功能的“實質(zhì)憲法”,憲法環(huán)境權的價值也通過民事活動的途徑得以實現(xiàn)。(2)從憲法與民法總則規(guī)范體現(xiàn)的外部價值意義來看,“國家”到“民事主體”的概念變化,體現(xiàn)了不同的義務主體之范圍,明示了處于外延范圍包含與被包含關系之下的主體,清晰地表達了依據(jù)憲法環(huán)境權而產(chǎn)生的“綠色原則”的淵源,并直接揭示了憲法環(huán)境權的實現(xiàn)從國家義務層面邁向民事主體層面的轉化過程。因此,既是參與者又是受益者的民事主體,必須嚴格約束自身的行為并符合節(jié)約資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目標。
2. 承載整合功能的憲法環(huán)境權
隨著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內(nèi)容寫入憲法,即標志著生態(tài)文明建設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修憲內(nèi)容中的序言部分關于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目標也需要各個部門法的緊密配合才能實現(xiàn)。作為民事領域基本法的民法總則發(fā)揮了在民事領域內(nèi)指導眾多民事主體將民事行為符合生態(tài)文明建設標準的功能。“隨著生態(tài)文明入憲,憲法上的國家基本制度也從經(jīng)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拓展到生態(tài)制度。”(28)張震:《生態(tài)文明入憲及其體系性憲法功能》,載《當代法學》2018年第6期。毫無疑問,“綠色原則”從民事私法領域?qū)椃ōh(huán)境權的價值予以整合,并確保憲法環(huán)境權所蘊含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目標在民事領域得到實現(xiàn)。一是,“綠色原則”直接表達了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在民事活動領域的價值,即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設立、變更、終止自身民事權利或義務時,必須考慮節(jié)約資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一系列民事活動的效力都必須符合“綠色原則”的評判基準。二是,“綠色原則”作為已經(jīng)生效的民法總則的基本原則,在民法典誕生之前承擔著民事領域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任,并傳遞了“綠色民法典”的立法價值取向,即在未來的民法典編撰歷程中,節(jié)約資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一定會成為民法典編撰必須考慮的內(nèi)容。因此,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的實現(xiàn)通過“綠色原則”的巧妙安排,被納入到即將誕生的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之中,為未來的民法典系統(tǒng)化地表達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經(jīng)驗。
(二)憲法環(huán)境權在民事活動中的實際價值
依據(jù)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而產(chǎn)生的“綠色原則”,對民事主體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與義務影響深遠。環(huán)境權作為公私權利的復合載體,(29)參見前引⑥,王曦書,第70頁。其在特定的背景之下也表現(xiàn)為一種公共利益。“綠色原則”作為民事私法領域中的基本原則,將憲法環(huán)境權所承載的環(huán)保價值貫穿到民事活動的始終,將原則化的憲法環(huán)境權類型化為民事領域中極易接受的“綠色”理念與價值觀。民法通則規(guī)定了“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jīng)濟秩序”。其中“公共利益”的外延極具廣泛性,也并未直接闡明環(huán)境保護的相關內(nèi)容。相比之下,“綠色原則”則直接表達了對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維護,更加清晰和簡潔地表達了民事主體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時的環(huán)保理念。
1. “綠色權利”之行使
民法賦予民事主體以環(huán)保的方式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民事主體行使權利時應該樹立節(jié)約資源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意識,在“綠色原則”范圍內(nèi)的權利行使,法律予以保障。但極具公法權利色彩的憲法環(huán)境權在民事私法領域的實現(xiàn),需要“綠色原則”發(fā)揮媒介作用,筆者認為,“綠色原則”的媒介作用就是將憲法環(huán)境權環(huán)保價值的理念,通過“綠色原則”的規(guī)范表達而形成民事主體易于接受的基本原則,并兼具指導與評價民事活動的作用,從而影響民事權利的行使。一方面,“綠色原則”發(fā)揮著指導作用,引導民事主體將民事權利的行使符合既定“綠色標準”;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具有評價功效的民事原則,“綠色原則”將會對整個權利行使的過程進行評價,否定危害生態(tài)環(huán)境、浪費資源的行為、結果。強調(diào)“綠色權利”的意義在于重視“綠色權利”行使之下的塑造作用,即重視“綠色原則”對民事主體“綠色權利”行使的規(guī)范作用。最后,“綠色原則”強化了民事主體對民法上環(huán)境權利的認知,在實證法秩序上不斷加強對環(huán)境權利的認可,進而增強環(huán)境權利維護意識。
2. “綠色義務”之履行
民事主體履行民事義務應當區(qū)別于破壞環(huán)境、浪費資源等不環(huán)保的義務履行方式。同時,民事義務體現(xiàn)的是義務主體的不利益,即為他方權利實現(xiàn)而約束自身行為。“綠色義務”的重要功能在于,一方面對受到不利益約束的主體而言,尊重他方“綠色權利”的實現(xiàn),應該嚴格約束自身的恣意妄為;另一方面從權利義務相對性的角度而言,二者的相對性決定了民事主體有權行使“綠色權利”,同時也必須履行與之相對應的“綠色義務”,“綠色原則”標準下的民事義務要求民事主體為了他方“綠色權利”的實現(xiàn)必須作出符合“綠色”標準的行為。因此,民事主體必須以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方式履行符合“綠色原則”的“綠色義務”。
3. “綠色權利與義務”之高度協(xié)調(diào)
民法作為權利宣言書,私法制度圍繞“權利體系”而展開,“在某種程度上,我國幾乎所有權利立法皆在此框架下展開,因此,它實際起到‘權利普通法’的作用”。(30)朱慶育:《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頁。實際上,以權利為核心而構建的民事權利體系,對民事主體權利的維護、實現(xiàn)發(fā)揮著重要功能。但是,完善的權利體系的構成,也發(fā)揮著對義務履行的保障作用,即民事權利界限的清晰劃定平衡著民事義務的積極履行或消極尊重的功能。至此,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行使的“綠色權利”隱含地包括了“綠色義務”的相互對應,“綠色權利義務”形成了一組高度協(xié)調(diào)的規(guī)范構造,進一步強化了民事主體對“綠色民事行為”的認知,有助于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自覺增強環(huán)保意識、踐行環(huán)保行為。
四、跳出文本窠臼的體系性“綠色原則”
“綠色原則”制定出來以后需要進入實踐階段,并發(fā)揮規(guī)范現(xiàn)實、理論溝通的作用。在強調(diào)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中國,單純地將“綠色原則”融入到民事私法領域中,顯然不能完成作為部門法的民法與法治體系中其他涉及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職能的部門法之間的溝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環(huán)境保護呼聲居高不下的背景之下,需要厘清“綠色原則”與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理念間的關系,并確保環(huán)境治理法秩序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在筆者看來,出于對環(huán)境治理良好效果的目標追求,以及實現(xiàn)法治大環(huán)境之下的部門法對話,可以從“綠色原則”內(nèi)涵下的憲法實施、環(huán)境權秩序中的“綠色”因素融入以及民法典編撰的理性開展三個層面展開。
(一)“綠色原則”內(nèi)涵下的憲法實施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憲法因素在各個部門法的誕生過程中愈顯突出。“依憲治國”就是要保證憲法得到切實的實施。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diào)“加強憲法實施”,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強調(diào)“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要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jiān)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nèi)法規(guī)體系,用科學有效、系統(tǒng)完備的制度體系保證憲法實施。”(31)習近平:《更加注重發(fā)揮憲法重要作用 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的水平》,載“新華網(wǎng)”,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2/26/c_136999780.htm,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5月8日。在此背景之下,推動憲法實施已成為不可逆轉之潮流,但是,區(qū)別于西方國家的憲法司法化,我國的憲法實施更多的是通過部門法而實現(xiàn)的,部門法秩序的建立都是立足于合憲性基礎。因此,誕生于合憲性背景之下的民法總則,必須為憲法實施提供新的動力。
從縱向法律關系層面而言,“綠色原則”是對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在民事活動領域最好的反映。作為業(yè)已形成較強的體系性的民法,“綠色原則”將此體系中涉及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內(nèi)容,以精煉的語言予以展現(xiàn)。“憲法是最高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據(jù),立法是憲法約束下在法秩序的各個領域的規(guī)范展開。”(32)張翔:《憲法與部門法的三重關系》,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綠色原則”所代表的在民事領域的環(huán)保價值,就是憲法約束下的立法成果,換言之,產(chǎn)生于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之下的“綠色原則”就是“實質(zhì)意義”的憲法環(huán)保規(guī)范在民事領域的展開。此時,作為“實質(zhì)意義”的憲法環(huán)保規(guī)范的“綠色原則”要盡可能將憲法環(huán)保價值實現(xiàn)于寬泛的民事活動之中。
一方面,“綠色原則”要發(fā)揮好基本原則的功能,作為私法領域中節(jié)約資源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基本原則,應該將其所具備的引導與評價功能徹底地發(fā)揮在民事活動之中。即“綠色原則”要基于立法的目的和原意,將承載著“綠色發(fā)展理念”的憲法規(guī)范的精神貫穿到民事私法領域。另一方面,“綠色原則”不是“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簡單復制的結果,更不是刻意的宣示。她還承擔著彰顯憲法根本法地位和治國安邦總章程的重要使命,同時,在民事規(guī)則不足以應對的時候發(fā)揮兜底作用,將自身蘊含的“綠色內(nèi)涵”功能運用到解決民事糾紛、促進社會和諧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之中。因此“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表明民法總則對憲法規(guī)范的尊重,也進一步詮釋了依據(jù)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而產(chǎn)生的“綠色原則”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上所蘊含的重要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綠色原則”內(nèi)涵之下的憲法實施,并非“憲法的民法化”的極端思維,“認為所有的民法問題都需要回歸憲法”,(33)王鍇:《憲法與民法的關系論綱》,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1期。這種只從憲法中找答案的思維極不適當。照此,“綠色原則”內(nèi)涵之下的憲法實施就要求我們主動避免兩個陷阱:一是,過分強調(diào)“綠色原則”的唯憲法化,只按照憲法環(huán)境權的價值發(fā)揮功能,而忽視了其本身的價值與規(guī)律;二是,過度地強調(diào)“綠色原則”在私法領域中的原則性作用而忽略了與憲法環(huán)境權價值的對話,過分矯正“綠色原則”對權利義務的影響,而未考慮到憲法環(huán)境權在維護個體環(huán)境權利時表現(xiàn)出來的共性。那么,“綠色原則”內(nèi)涵之下的憲法實施,就是統(tǒng)一憲法環(huán)境權與“綠色原則”在環(huán)境權益維護上的共性,但是也要區(qū)別二者的個性,并將屬于各自個性的那部分內(nèi)容歸屬到各自的領域中。
(二)環(huán)境權秩序中的“綠色”因素融入
以環(huán)境問題為導向而產(chǎn)生的年輕法律部門——環(huán)境法,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科,產(chǎn)生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門的邊緣地帶。(34)民法中有污染環(huán)境造成他人損害而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guī)定,刑法中有關于危害環(huán)境而構成犯罪的刑事處罰的規(guī)定,行政法中也有關于環(huán)境執(zhí)法的相關規(guī)定,可見環(huán)境法生長于多數(shù)部門法之外的邊緣地帶。事實上,根據(jù)有關學者的研究表明,大量涉及民事、行政、刑事責任的環(huán)保案件的判決,其中引用環(huán)保法的跡象寥寥無幾,環(huán)保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對事實的認定。(35)參見呂忠梅:《環(huán)境法回歸路在何方?——關于環(huán)境法與傳統(tǒng)部門法關系的再思考》,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5期。此外,對于環(huán)境法中環(huán)境權的性質(zhì),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觀點認為,根據(jù)《人類環(huán)境宣言》《東京宣言》《社會進步和發(fā)展宣言》《內(nèi)羅畢宣言》的內(nèi)容,環(huán)境權屬于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應當屬于人權。(36)參見呂忠梅:《論公民環(huán)境權》,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6期。有觀點主張將抽象的環(huán)境權具體化之后納入民事權利體系,因此該觀點傾向于主張環(huán)境權的私權性質(zhì)。(37)參見馬晶:《論環(huán)境權的確立與拓展》,載《長白學刊》2001年第4期。有觀點認為環(huán)境權是一種概括性權利,需要立法加以完善。(38)參見唐澍敏:《論環(huán)境權》,載《求索》2002年第1期。也有觀點認為環(huán)境權具有基本權利的特征,同時也兼具公益性、預防性、有限性等特征。(39)參見蔡守秋:《論環(huán)境權》,載《金陵法律評論》2002年春季卷。可見,學界對環(huán)境權的性質(zhì)并未達成一致的觀點。
與發(fā)展成熟的法律相比,環(huán)境法顯然是一部新興的法律。依照前述,環(huán)境法似乎可以容納其他成熟學科邊緣地帶中的有關環(huán)境法治的相關內(nèi)容。以筆者看來,這種現(xiàn)象是造成環(huán)境權性質(zhì)乃至環(huán)境法定位模糊的原因之一,但是這種局面顯著的優(yōu)點便是:擴展了環(huán)境法體系的開放性,并奠定了環(huán)境權利義務秩序的發(fā)展性。據(jù)此,縱向維度上,環(huán)境法產(chǎn)生于憲法之下,符合合憲性審查之結果。同時,環(huán)境權也符合憲法環(huán)境權之價值,成為“實質(zhì)意義”的憲法環(huán)境權。橫向維度上,環(huán)境法與其他涉及環(huán)境保護的部門法之間的交流也更加符合實際之需求。筆者認為,正是因為作為部門法的環(huán)境法中的環(huán)境權性質(zhì)的多樣性,并且當環(huán)境權被解釋為私權時,作為私法原則的“綠色原則”才有融入環(huán)境權秩序中的可能性。
實現(xiàn)環(huán)境權秩序中“綠色”因素融入的目標,需要民法與環(huán)境法的對話,尤其是當環(huán)境權被認為是私權的時候。二者的融合媾通是“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兩種理論范式之間的對話”。(40)侯佳儒:《環(huán)境法學與民法學的對話》,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頁。兩種不同主義之間的對話是兩種不同立場和視角的交融。誠然,當環(huán)境權利義務秩序表現(xiàn)為私人的權利義務時,“綠色原則”的價值與此時的環(huán)境權就處于同一對話范圍之內(nèi),它們都追求同一價值目標,即“生態(tài)、資源本位”,這也恰當?shù)胤从沉恕懊袷轮黧w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jié)約資源、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尤其是,在生態(tài)和環(huán)境日益惡化的今天,環(huán)境權秩序表達的權利義務規(guī)范與“綠色原則”的豐富內(nèi)涵相互配合,既可以應對實證法意義上的環(huán)境與生態(tài)問題,也可以從自然法層面填補了環(huán)境權的缺失的“綠色”價值。
(三)民法典編撰的理性開展
“民法總則是民法典的開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統(tǒng)領性作用。民法總則規(guī)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一般性規(guī)則,統(tǒng)領民法典各分編;各分編將在總則的基礎上對各項民事制度作出具體規(guī)定。”(41)前引⑤,李建國講話。“綠色原則”作為民事私法領域中具有生態(tài)價值的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必將對民法典分編中涉及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規(guī)定提供依據(jù),并決定其內(nèi)在環(huán)保價值理念。因此,民法典編撰的過程中,“綠色”價值在分編各部分中的占比,對民法典形成體系化的環(huán)保功能有著重要的影響。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后的初始期,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當然包括干凈的空氣、美麗的環(huán)境等,(42)前引②,習近平文。民法典的編撰不得不考慮關乎人民切身利益的環(huán)保與生態(tài)因素。民法典不再單純地考慮民事主體經(jīng)濟利益的得失,而將環(huán)境利益的重要性擺在了民法典中更顯眼的位置,因此民法典的轉型過程中必然包含著朝著“綠色民法典”發(fā)展的可能。“綠色原則”作為在民法典誕生前的重要基本原則,實現(xiàn)了對民事私法領域中民事活動的“綠色”評判,展現(xiàn)了民事基本原則對生態(tài)與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視,同時“綠色原則”的功能發(fā)揮也刺激了民法環(huán)保精神的誕生。因此,民法典轉向的“綠色”之路是民法自我反思和自我揚棄之路,也是民法固有精神與價值的修正,(43)周珂主編:《我國民法典制定中的環(huán)境法律問題》,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頁。作為體系性地表達環(huán)保理念的民法典,必將重視“綠色原則”產(chǎn)生的實際環(huán)保價值與效果。
在傳統(tǒng)的視角下,民法的功能主要是為“個人本位”之上的理性“經(jīng)濟人”服務的,“經(jīng)濟人”符合了追求利益與經(jīng)濟價值最大化的目標。但是,隨著“綠色原則”的誕生,理性“經(jīng)濟人”需要文明“生態(tài)人”的適度修正,至少二者要進行平等的溝通與對話。(44)前引,周珂書,第58-59頁。所以,民法典的編撰更需要更認真地定位“綠色原則”的環(huán)保價值,更嚴謹?shù)匾?guī)定分編各部分中的“民法環(huán)保功能”條款。環(huán)境問題的有效解決是環(huán)境立法的出發(fā)點,但是帶有“綠色”性質(zhì)的民法典也即將發(fā)揮其在民事領域中的環(huán)保功能。筆者認為,這樣規(guī)定正是環(huán)保價值在民法體系中不斷得到重視的表現(xiàn),也是從民法角度對亟待解決的環(huán)境問題的回應。
蘊含“綠色性質(zhì)”的民法典極易被貼上“環(huán)境法化”的標簽,這種簡單且極端的看法并不能正確看待“綠色”民法典的發(fā)展路徑。所以理智的看法是:民法典仍然是民事主體活動領域的基本法,只不過時代賦予了她在民事領域更多的環(huán)境保護職責。
五、余 論
“綠色原則”產(chǎn)生于日益嚴峻的環(huán)境形勢之下,她深刻地詮釋了憲法環(huán)境權在民事領域的時代價值,也標志著憲法生態(tài)文明內(nèi)涵在民事領域得到實現(xiàn)。“綠色原則”不僅承擔著民事領域中的環(huán)保使命,也包含著各種各樣的關于民法是否需要包含環(huán)保價值的立法思想。(45)這里所言的“各種各樣的立法思想”,其實指“綠色原則”是否作為民法總則基本原則的確立過程中的各種觀點與思考。可以說第9條在民法總則中“功成名就”的過程,的的確確是一個“一波三折”的過程,甚至是煎熬。可參見呂忠梅等:《“綠色原則”在民法典中的貫徹論綱》,載《中國法學》2018年第1期;劉益燈、王伊迪:《論〈民法總則〉中的綠色原則》,載《社科縱橫》2018年第10期。即便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環(huán)境權”,但是2018年憲法修改后,憲法序言等部分無處不體現(xiàn)著環(huán)境保護、資源節(jié)約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目標追求,展現(xiàn)了我國憲法文本中豐富的環(huán)保價值。當然,“綠色原則”誕生的意義并不僅限于民法領域,即指導民事主體實現(xiàn)保護環(huán)境、節(jié)約資源以及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目標,以及為即將誕生的民法典分編部分中的環(huán)保價值的確立提供理論與實踐基礎。從廣義的環(huán)境法治體系角度而言,“綠色原則”的確立為整個環(huán)境法治體系注入了活力,并對綜合性的環(huán)境法治體系的形成產(chǎn)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