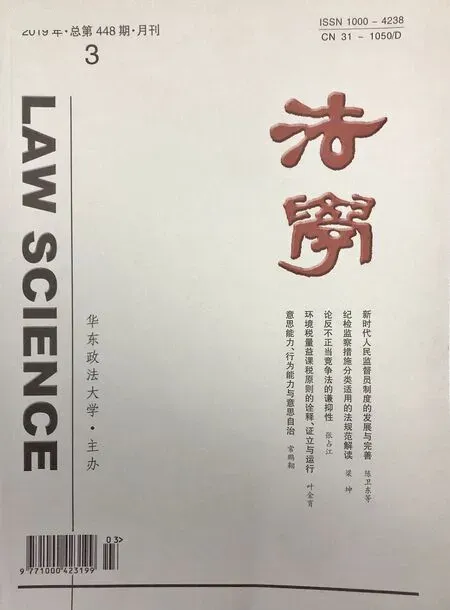論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謙抑性
●張占江
一、問題的提出
“競爭”原則上是私人事務,對其進行干預本屬于市場經濟的例外,但是禁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以下簡稱“反法”)的一般條款在確保規制周延性的同時因適用標準上的模糊,〔1〕依學界通說,《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確定了市場交易行為須遵循之原則,并對“不正當競爭”予以概括界定,稱為一般條款。最高人民法院在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海帶配額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書)中提出,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是一般條款的核心,其中“誠實信用原則主要表現為公認的商業道德”。但究竟該如何解釋“公認的商業道德”,是采取基于競爭效果本身的解釋,還是采取抽象的道德解釋,抑或是側重競爭優勢“權利化”的解釋,理論與實踐的分歧明顯。經常逾越其應有之界限,把正當的競爭行為貼上不正當競爭的“標簽”。
(一)不正當競爭認定中的過度干預
就目前的司法實踐言,依“反法”一般條款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思路主要有如下兩種:(1)一般競爭利益的權利化,以權利保護的方式適用法律。此點在適用一般條款處理涉互聯網的軟件干擾類不正當競爭糾紛中體現得尤為明顯。〔2〕根據法院內部的調研統計數據,從2002~2017年各地法院共審理了大約141件相關案件,自2005年后年均在10件左右。(參見“中國知識產權新年論壇:新反法互聯網專條的司法適用”會議,2018年1月27~28日,于北京粵財JW萬豪酒店)。法院對這類案件裁判皆以競爭優勢受到的損害為論證基礎,明顯帶有權利侵害式侵權認定的痕跡。相關裁判采用權利侵害式的侵權法思維,先確定一種受保護的合法權益,如先論述特定商譽、商業模式(如“免費視頻+廣告”)等受法律保護,再從權益受損推論侵害行為的不正當性;或者以權益是否受到侵害作為論證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對行為本身的正當性僅作擺設性、象征性或套路式的論述,對認定其正當性的相關元素并無實質性考量。〔3〕相關分析,參見孔祥俊:《〈民法總則〉新視域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2期;劉維:《論軟件干擾行為的競爭法規制——基于裁判模式的觀察》,《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周樨平:《競爭法視野中互聯網不當干擾行為的判斷標準——兼評“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法學》2015年第5期。法院甚至還發展出專門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強調除非基于公共利益否則不能損害在先經營者之營業利益,并作為一項重要的裁判規則被廣泛適用。〔4〕“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最初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3年審理“百度與360插標不正當競爭案”中提出,強調非因特定公益(如殺毒)的必要,不得直接干預競爭對手的經營行為。(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2352號民事判決書)該原則在之后的系列案件中得到適用,例如,“獵豹瀏覽器屏蔽優酷網視頻廣告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終字第3283號民事判決書)和“極路由視頻廣告屏蔽不正當競爭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4)京知民終字第79號民事判決書)。就備受矚目的廣告屏蔽類案件而言,筆者在威科先行數據庫中通過對“廣告屏蔽”“屏蔽廣告”分別進行標題與全文精確搜索,又在案由為“不正當競爭糾紛”的案例中通過搜索“廣告”進行補充檢索,共計檢索出20份已結案件的司法文書(檢索截止日期為2018年12月12日)。其中18個案件采用了權利侵害式侵權法思維或者適用“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認定屏蔽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只有2個案件基于競爭本身的效果通過綜合利益衡量認定屏蔽行為不構成不正當競爭。參見“騰訊公司訴世界星輝公司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70786號民事判決書;“快樂陽光公司訴唯思公司案”,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2017)粵0112民初737號民事判決書。這等于是將經營者的競爭優勢所產生的商業利益在事實上上升為權利加以保護。(2)競爭行為評價道德化,將“搭便車”“不勞而獲”作淺層的理解,簡單地將其與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畫等號。〔5〕參見蔣舸:《關于競爭行為正當性評判泛道德化之反思》,《現代法學》2013年第6期。其實,“模仿是競爭的天然血脈”,〔6〕Bonito Boats,Inc.v.Thunder Craft Boats,Inc.,489 US 141(1989).競爭離不開對他人成果之使用,將“搭便車”“不勞而獲”等一般商業倫理觀念當成具體判斷標準,極易不適當地擴張專有權的范圍。而且,注重從行為人的主觀意圖判斷行為的不正當性還可能帶來極高的不確定性。〔7〕同前注〔5〕,蔣舸文。在與技術有關的不正當競爭案件中,原被告雙方都會高舉道德旗幟,〔8〕例如,在廣告屏蔽類案件中,被屏蔽方強調其行為旨在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免費視頻,而屏蔽方則主張其行為使消費者免受不受歡迎的廣告的滋擾。但抽象的道德考量無法給出一個清晰的答案,多數時候,其不過是為公權力偏好干預和管制市場價值的“家長式”情懷提供法律和道義上的支持罷了。〔9〕同前注〔3〕,孔祥俊文。
上述兩種思路的共同指向都是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將競爭利益權利化等于是將競爭靜態化,以保護競爭的名義阻礙競爭,保護了特定競爭者而不適當地限制了不特定市場主體的競爭自由。而以道德名義將行為認定為不正當競爭還可能增加企業市場行為的風險,于是避免類似行為便成為企業降低風險的唯一路徑,最終將會抑制企業的創新激勵,壓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空間。
(二)被忽視的“反法”謙抑屬性
導致產生上述問題的本因在于理論與實踐都嚴重忽視了“反法”內在的謙抑性。謙抑性最初在刑法領域被反復提及。例如,陳興良教授認為,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法(而用其他的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收益——有效的預防或者控制犯罪。”〔10〕陳興良:《刑法的價值構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頁。它主要強調在立法環節的去刑罰化和法律實施環節的輕刑罰化。近些年,謙抑性的概念才被明確引入經濟法的話語體系。例如,有學者提出,作為一種理念的經濟法的謙抑性,“是指在自由主義和市場競爭基本假設下的私法能夠發生作用的范疇內,經濟法應保持必要的謙恭和內斂,讓位于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機制,而不輕易使用國家干預,令經濟法作為一個補充性和最后手段性的機制而存在,杜絕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時‘泛干預主義’傾向的發生。”在其看來,“謙抑干預應當成為統率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思維方式。”〔11〕劉大洪、段宏磊:《謙抑性視野中經濟法理論體系的重構》,《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
在本質上,“反法”是一種對競爭自由的限制,而競爭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是效率和繁榮的基礎,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其必須保持謙抑,避免將正當的市場行為歸入不正當競爭的范疇,故其制度構造源于一種“法無禁止即自由”之理念,圍繞限定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邊界展開,從而為企業在廣泛空間內留有競爭自由。針對“反法”一般條款適用標準的不確定性,謙抑性不僅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認定的分析范式。
理論界與實務界對不正當競爭問題的關注更多地是直接論證“行為為什么是不正當的”,體現的是一種積極干預的思維,而非在優先考慮“為什么不是”(即競爭沖突的市場可調節性)的基礎上再進行判斷的謙抑思維,導致了一種盲目的或“家長式”的干預。鑒于此,本文的研究擬在彌補這一缺憾,在厘清“反法”介入競爭正當性、合法性基礎之前提下,構造一種市場優先的不正當競爭認定理念,以及在比例原則支撐下的不正當競爭認定的技術框架,從而確立“反法”的內在謙抑性。
二、理論基礎:法律何以介入競爭
(一)私法自治的保障與限制的均衡
發揮市場經濟優勢的關鍵在于確保私法自治。〔12〕參見劉凱湘、張云平:《意思自治原則的變遷及其經濟分析》,《中外法學》1997年第4期。私法自治給個人提供一種受法律保護的自由,從而使個人獲得自主決定的可能性。社會發展的歷史證實,保證個人自主決定實現的制度是符合人性的制度,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制度;經濟發展的歷史揭示,自主決定是調節經濟過程的一種高效手段。〔13〕參見熊丙萬:《私法的基礎:從個人主義走向合作主義》,《中國法學》2014年第3期。
競爭自由所強調的競爭不受限制或扭曲,是私法自治所強調的主體“自決性”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延續。不受扭曲的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盡管競爭自由不一定在憲法規范上進行直接表述,但其可從基本權利的指導性效力上推導出。基本權利的功能就包括確保經營者自由營業的空間。〔14〕參見[德]羅爾夫·施托貝爾:《經濟憲法與經濟行政法》,謝立斌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11~116頁;[德]弗里茨·里特納、邁因哈德·德雷埃爾:《歐洲與德國經濟法》,張學哲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頁。作為客觀法的基本權利所確立的價值秩序構成了國家各項制度構造必須遵循之原則,〔15〕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這就使得私法自治不僅是私法上的基本原則,而且統領整體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構。
但是,絕對的私法自治面臨著社會整體正確性之責難,〔16〕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頁。故很難完全得到實現。一方面,競爭天然地蘊含損害競爭(不正當競爭、壟斷)的因素,完全自由必然導致對整體秩序的損害;另一方面,自治觀念應該是指在完全、充分地意識到所有的可得機會,掌握了所有相關信息,或最一般地說,在偏好形成過程中甚至沒有受到任何非法限制的情況下而作出的決定。然而,現實情況卻是,這些因素并不一定完全具備,私人決策在多數情形下其實只是無奈和無知之舉。也就是說,私法不能不借助于公法而獨立存在,〔17〕參見王利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與私法自治》,《中國法學》2014年第5期。表面上不受干預的決策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決策。故此,法律始終在努力尋求一種平衡,以私法自治為出發點的同時又嘗試對其加以限制;而為了避免過分壓縮自由之空間,限制本身同樣受到嚴格之約束。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們的法律顯然有些操之過急,缺少一種控制干預的機制以確保均衡的實現。
(二)競爭自由與競爭秩序的兼容
政府干預的正當性既在于彌補私法自治之局限,消除不正當競爭及壟斷,又在于保障和拓展私法自治。規制法學的旗手桑斯坦(Sunstein)強調,恰當的規制在有助于提高社會整體福利的同時又增強了行動能力,促進私人的選擇。〔18〕參見[美]凱斯·R.桑斯坦:《權利革命之后:重塑規制國》,鐘瑞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通過規制改變可得機會和信息等限制條件,往往可以改變在不合理條件下形成的私人偏好,從而促進偏好形成過程中的自治。規制在此情形下“不是真的要迫使人們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反而是通過強制來使他們能夠做他們想做的事情。”〔19〕同上注,第3頁、第56頁。德國學者同樣也意識到,缺少政府干預因素的支持與補充,私法自治制度就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之作用。〔20〕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納、邁因哈德·德雷埃爾書,第138頁。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怎樣的規制才屬恰當,才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從憲法上言,基本權利所確定的行為自由也要受到限制,但只能基于一種更普遍的自由的實現。〔21〕如羅爾斯所言:“限制自由的理由來自自由原則本身。”[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頁。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本身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基本權利,無論是基于其他基本權利,還是基于公共利益,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最終歸結于基于實現更普遍的自由。這種更普遍的自由就是經濟競爭秩序。因為只有競爭秩序才能賦予所有企業通過與市場兼容的手段獲取競爭優勢的機會,與此同時,消費者的需求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整個社會才能在競爭的推動下不斷取得進步。換言之,競爭秩序是所有市場參與者主權(共同利益)實現之基礎,它與市場參與者的行為自由兼容。是故,規制正當性的邏輯闡釋為:競爭自由是憲法基本權利及其對行為自由保護的必然結果,反之,只有基于構造競爭秩序實現更普遍的競爭自由,才能對個體自由進行限制。
但在事實上,缺少了政府的介入,競爭秩序也不可能存在。競爭既可提供給每個人在市場中勝出的機會,又可能使其面臨被淘汰的風險,導致市場主體對競爭的態度充滿矛盾,當競爭對己有利時舉雙手贊成,對己不利時就設法破壞或規避。一旦將構造、維護或服從競爭秩序的愿望留給私人自由決策只會造成混亂無序,只有通過政府對私人行為的謹慎干預才可能實現競爭秩序。〔22〕參見邱本:《論市場競爭法的基礎》,《中國法學》2003年第4期。
從整體上看,一來無限制的自由本身就不可能實現或不可能很好地實現,二來對自由的限制必須受到嚴格約束,因為離開對自由的確認和保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根本無法實現。這一機制的實現也就是政府只能基于競爭秩序限制私人的行為自由,或者說,確保私法自治以有利于競爭秩序的方式實現,這正是經濟法本身的精髓所在。經濟法的特殊價值是整體經濟的正確性。〔23〕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納、邁因哈德·德雷埃爾書,第28頁。
經濟法基于競爭秩序才能干預市場主體自由的機理與憲法保留原則一致,使其獲得了充分的合法性。民法和經濟法在此點上緊密地銜接在了一起。王軼教授強調,唯有社會公共利益可以成為民法對民事主體的自由進行限制的根據。它們明確民事主體自由的邊界,這個邊界同時也是國家可以發動公權干預私人生活的界限。〔24〕參見[英]邁克·費恩塔克:《規制中的公共利益》,戴昕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6頁。
作為一種典型的干預機制,“反法”對特定主體競爭行為的禁止本質上是為了實現更普遍的競爭自由,而且對特定主體自由的限制只限于保護競爭秩序之需。或者說,只有行為損害了競爭秩序才能納入“反法”的禁止范圍。由此,“反法”的構造一方面是個人以及賦予其權利的私法自治問題,另一方面是作為公共產品的競爭秩序的供給問題。從更一般的角度觀察,立法是保障“法治國之自由的一種形式”。只要立法者本身不進行干涉或者不具有干涉的權限,則存在普遍的行動自由,尤其是從事經濟活動,創造經濟價值以及競爭的自由。〔25〕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納、邁因哈德·德雷埃爾書,第217頁。在經濟法領域,法律保障自由功能的出現遠早于其保護基本權利的功能,該功能在實踐中被充分遵守,立法者必須作自我克制。政府干預相對于個人自由的整體實現而言,必須處于輔助地位,這不僅是一種對政治道德的要求,而且更多地涉及一個憲法國家的結構性原則,它通過“自由優先于國家的理念而獲得正當化”,是“真正的自由”。〔26〕同上注,第218頁。
(三)正當性定位:內嵌謙抑屬性的法律規制
私法自治被視為一種長期的制度,政府干預被限定于彌補私法自治的局限和確保私法自治的實現,或者說,立足于將競爭自由融入競爭秩序的建構。歸根到底,政府干預的正當性建立在將謙抑品格內在地嵌入其適用邏輯之上。
其一,在任何經濟領域都應當優先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只有在市場失靈或者說競爭秩序受到損害而市場自身無法糾正時,國家干預才具正當性。這樣的干預被限定于窮盡市場救濟的情形,屬于市場調節失效后的“二次調整”,〔27〕同前注〔11〕,劉大洪、段宏磊文。即當一人的行為損害了另一人基于競爭(秩序)享有的利益,而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礎上的機制又失靈時,規制才是必要的。〔28〕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納、邁因哈德·德雷埃爾書,第312頁。
其二,即使于市場失靈之場合,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也必須適應市場固有之邏輯,旨在恢復而不是取代或顛覆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29〕或者說,國家的經濟干預不是顛覆私法自治的框架。同上注,第219頁。于此意義上言,規制是輔助市場發揮作用,故被稱為間接干預,以區別于代替市場作出決策的直接管制。沿此邏輯,政府對競爭干預本身只是為競爭創造條件,絕不可厚此薄彼。競爭得以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就是每個市場主體的競爭自由不受扭曲,每個市場主體都必須擁有平等的參與競爭、展開競爭和獲取競爭收益的權利,這也是基本權利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延續。給予在先商業模式權利化的保護而忽略其他不特定經營者的商業創新的權利等于從根本上破壞了競爭。
其三,在既有經驗和理性無法判斷某一領域的市場是否失靈時,應優先假設市場未發生失靈,暫不進行國家干預。競爭本身是復雜和不可預測的,究竟在哪些方面創新、究竟采取怎樣的商業模式、究竟誰會勝出等都無法事先作出準確預判。尤其是在一些高新技術領域,企業的技術與經營上的沖突、對立不可避免,單憑道德直覺難以對其進行評價。在缺乏足夠經驗和共識的前提下,魯莽的競爭干預反而可能惡化市場的競爭狀況。為了扼守謹慎干預的界限,原告需要承擔較高的證明責任,司法者也需要有充分的說理義務。對開放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基本原則的認可導致任何對此原則的偏離都需有足夠充分正當的理由〔30〕同上注,第69頁。來證明市場和私法都無法糾正對競爭秩序的損害。
三、觀念內核:競爭沖突市場調節優先
市場優先是經濟法謙抑性理念在基本原則領域的映射。〔31〕參見劉大洪:《論經濟法上的市場優先原則:內涵與適用》,《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最大程度地發揮私法自治的作用,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目前對“反法”的解釋和適用恰恰因為沒有充分慮及市場的優先性,才導致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過于寬泛。市場經濟的“統治者”是技術和偏好,分別對應供給側經營者之間的技術創新(對抗)和需求側消費者的選擇。而技術上對抗很可能導致商業模式上的沖突、競爭格局的變動,由此引發競爭損害。故此,下文分別從技術對抗、競爭損害和消費者選擇三個維度來說明市場調節的優先性。為了說理更具針對性和細致性,筆者主要借助充分體現技術競爭特性且備受關注的系列廣告屏蔽案的處理展開論證。
(一)技術對抗空間的預留
技術創新、技術對抗是現代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法律對競爭的保護必然意味著對技術使用行為正當性的評價要為技術創新預留空間。換言之,對技術有關的不正當競爭爭議的處理需以承認技術中立性為前提,不能僅因技術功能之間的沖突就加以責難,而應立足于技術所產生的整體社會效果進行評價,從而為經營者開發新技術產品和探索新的經營模式提供機會。〔32〕參見孔祥俊:《論反不正當競爭的基本范式》,《法學家》2018年第1期。由于社會公共利益只具評價意義而不具主體意義,故在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中,對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考量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源于不受扭曲競爭帶來的創新利益。
就廣告屏蔽案件而言,廣告屏蔽技術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廣告屏蔽軟件是內容服務商“免費內容服務(諸如視頻、新聞等)+廣告”商業模式面臨的最主要威脅之一;另一方面,廣告屏蔽軟件很大程度上能夠保護用戶的利益。〔33〕屏蔽軟件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避免了廣告對用戶的損害:(1)降低用戶獲取信息的注意力。對于用戶獲取信息來說,不同形式的網絡廣告存在程度不一的干擾。尤其是大量出現的橫幅廣告對用戶造成了嚴重的干擾。(2)影響用戶的良好體驗。彈窗廣告需要加載或運行第三方程序,占用帶寬和降低網速,并具有一定的安全風險。(3)侵犯用戶的數據隱私。Digital Content Next公司的調查發現,高達68%的用戶擔心廣告定向追蹤能夠跟蹤他們的互聯網行為,泄露個人隱私。(參見韓紅星、覃玲:《廣告攔截的發展及對媒介生態的影響》,《當代傳播》2017年第1期。)事實上,美國移動安全公司Lookout在2012年發布的報告顯示,部分激進網站未經用戶允許便搜集用戶的電子郵件地址或手機號碼,有些網站還會直接安裝跟蹤應用,并向用戶推送廣告,嚴重侵犯了用戶的個人隱私。(參見張小強、黎婷婷:《廣告屏蔽應用對數字傳媒業的沖擊與應對策略》,《傳媒》2017年第20期。)正是因為其對消費者福利有改善之效,所以廣告屏蔽的市場需求是巨大的。〔34〕2016年,有將近7 000萬美國人使用廣告屏蔽軟件,有超過2億的中國人和印度人使用屏蔽廣告的移動瀏覽器。See Max Willens,How Many People Use Ad Blockers? That Depends on Whom You Ask,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http://www.ibtimes.com/how-many-people-use-ad-blockers-depends-whom-you-ask-238 4864 ,last visit on June 21,2016.例如,美國蘋果公司2015年發布的iOS9在Safari中開放了廣告屏蔽應用,多款收費廣告屏蔽軟件在蘋果應用商店瞬間登頂即是一個典型例證。〔35〕參見杰羅姆:《廣告攔截崛起:一個免費互聯網時代的終結?》,https://www.jianshu.com/p /05e452381b03,2018年12月20日訪問。
“免費內容服務+廣告”商業模式面對屏蔽軟件的“劣勢”完全可通過技術上的改進加以扭轉。其一,研發針對屏蔽行為的反制技術。屏蔽軟件對視頻網站廣告的攔截主要是通過改變瀏覽器與視頻網站軟件之間的調用條件,在軟件運行中攔截、修改、增加或屏蔽本地客戶端和遠程服務器之間的數據交換信息,實現改變視頻網站在瀏覽器上展現廣告的能力。但這并未改變視頻網站本身,視頻網站完全可采取技術手段對瀏覽器的內容侵權進行拒絕,或者拒絕瀏覽器瀏覽網站。其二,改進廣告的形式。廣告旨在追求商業利益,但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廣告存在與否,而是廣告的推送是否最大程度地兼顧到用戶的體驗。原生廣告因為與內容、環境高度融合,注重為用戶提供更好的閱讀體驗和有價值的內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有道詞典與寶馬公司合作,推出獨具特色的原生廣告形式,利用既有的“每日英語”欄目進行廣告宣傳,并就寶馬1系列車推出英語在線問題,用戶在學習英語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受到廣告的影響,將廣告信息轉化為對受眾有價值的形式表現出來,獲得了良好的推廣效果。〔36〕參見廖秉宜、何怡:《原生廣告的概念辨析與運作策略》,《廣告大觀》(理論版)2017年第5期。其三,提供用戶需要的廣告。美國互動廣告局發布的《廣告攔截:誰在使用?為什么會被使用?如何再次贏得用戶的心》報告顯示,如果發行商在用戶瀏覽網站時能為用戶提供符合需求并有價值的內容,那么三分之二的美國地區用戶都愿意關閉廣告攔截。〔37〕See IAB Ad Blocking Report: Who Blocks Ads,Why,and How to Win Them Back,https://www.iab.com/wp-content/uploads/2016/07/IAB-Ad-Blocking-2016-Who-Blocks-Ads-Why-and-How-to-Win-Them-Back.pdf,last visit on Dec.12,2018.
可見,應對廣告屏蔽行為的巨大技術創新空間的存在,使得互聯網企業運營商的市場前景依然廣闊。例如,谷歌公司開發的Chrome瀏覽器一直開放廣告攔截插件的使用,其擁有高達56%的桌面瀏覽器市場,但其廣告收入并未因此受到影響,數據顯示,其廣告收入從2004年的31億美元穩步增長至2014年的596億美元。〔38〕See Ankit Oberoi,The History of Online Advertising,https://www.adpushup.com/blog/the-history-of-online-advertising/,last visit on Dec.12,2018.又如,德國網絡廣告市場規模從2015年的715萬歐元增加到2017年的844萬歐元,仍將持續增長之勢頭。〔39〕Vgl.Statista,Nettovolumen in den einzelnen Segmenten des Online-Werbemarktes in Deutschland in den Jahren 2015 bis 2017 und Prognose für 2018 (in Milliarden Euro).轉引自張飛虎:《〈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視角下廣告屏蔽軟件的合法性問題》,《電子知識產權》2018年第7期。
然而,對“免費內容服務+廣告”商業模式的庇護扼殺了上述技術創新的可能,發達市場經濟體早已摒棄了權利侵害式侵權法思維,轉而將技術問題交由技術來解決。在著名的德國“電視精靈案”中,原告是一家以在播放的電視節目中投放廣告為盈利方式的電視臺,被告生產和銷售被稱為“電視精靈”的一種廣告屏蔽裝置。用戶通過在選定的節目廣告播放時間內向安裝該裝置的電視機或錄像機發出指令信號,跳轉到其他節目,并在廣告時間結束時返回原頻道。原告認為被告推廣、銷售“電視精靈”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最終,德國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決,理由主要是,原告自身具有針對屏蔽行為的應對和自救能力。“傳媒企業也必須接受市場的挑戰,而市場的生命力就在于商業活動自由和創新。”“原告完全可以通過與廣告經營者一起努力激發并維持觀眾對廣告節目的興趣,或者主動采取技術革新來解決廣告屏蔽的問題。至于到目前為止是否存在這樣的技術手段以幫助原告避免被告產品對其經營活動造成的生存威脅和影響與本案的法律問題認定無關。”〔40〕BGH,Urteil v.24.06.2004,Az.I ZR 26/02.與這一裁判思路一脈相承,德國法院在“白名單廣告案”中再次強調原告除了加入白名單外,還可以有多種選擇方式,“既可以拒絕屏蔽了廣告的用戶進入網頁;又可以做出技術上的改進以防止廣告被屏蔽。況且,在線廣告只是在線新聞行業多個融資模式中的一個。”〔41〕416HKO 159/14.德國上述經典判決明顯秉持了“市場的歸市場”“技術的歸技術”的理念,依靠市場和技術解決競爭糾紛,以發展的眼光對待競爭問題,重點考量原告是否具有市場的和技術的應對能力,從而避免將技術創新引發的沖突動輒就認定為不正當競爭,此一做法無疑更有利于商業創新和技術進步。〔42〕同前注〔32〕,孔祥俊文;同前注〔39〕,張飛虎文。
反觀在我國備受關注的“騰訊公司訴世界星輝公司案”二審中,法院的裁判(包括所引入的專家分析意見)對屏蔽行為對被屏蔽方影響的分析中一個致命缺陷就在于,未能考慮到上述可能的應對方案,由此得出的視頻網站因為廣告被屏蔽而轉向在視頻服務中收費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結論,或者視頻網站無法維系運營的結論,皆無法令人信服。〔43〕參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8)京73民終558號民事判決書。最終,對屏蔽行為不正當性的認定因抑制技術創新而損害了動態競爭。
(二)市場損害中性原則的厘清
競爭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一方優勢的確立即意味著另一方劣勢的產生。競爭造成的損害是中性的,損害本身并不具有是與非的色彩,不構成評價競爭行為正當與否的傾向性要件,充其量不過是對不正當競爭行為認定的一個考量因素。〔44〕同前注〔32〕,孔祥俊文。
普通法上的一項堅實的侵權法原則就是“競爭損害并非侵權”(competition is not a tort)。〔45〕Shank v.William R.Hague,Inc.,192 F.3d 675,687(7th cir.1999);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law,Business Tor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Handbook,ABA Publishing,2014,p.22.在美國享有巨大影響力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重述(第三版)》第1條規定,除非符合特別規定,“凡是從事商業或者貿易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不需要對該損害承擔責任。”換言之,“競爭自由默示一種可以誘使潛在客戶與其本人而不與其競爭對手從事交易的‘競爭特權’(a‘privilege’to compete)。”英國法官Robin Jacob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奪取他人的市場或者客戶一般不構成侵權。無論是市場還是客戶都不是原告自己的。”〔46〕Hodgkinson Corby Ltd.v.Wards Mobility Services Ltd.[1995]F.S.R.169.See Christopher Wadlow,The Law of Passing-off:Unfair Competition by Misrepresentation,Sweet & Maxwell,2011,pp.5-6.
商業模式的更迭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由此造成的損害不能直接得出行為不正當性的結論。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帶配額案”中就曾指出:“競爭對手之間彼此進行商業機會的爭奪是競爭的常態。對于同一交易機會而言,競爭對手之間一方有所得另一方即有所失。”所以,“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上,一種利益應受保護并不構成該利益的受損方獲得民事救濟的充分條件。”〔47〕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可惜的是,在此點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態度并非一以貫之,在之后的“騰訊訴360案”中,法院強調“正當的商業模式必然產生受法律保護的正當商業利益”,〔48〕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終字第5號民事判決書。明顯是開了倒車。
在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中,對競爭損害的考量以競爭者的生存不受威脅為底線。法律之所以將“損人利己”界限劃在是否導致競爭對手無法生存之上,是基于增強市場競爭的對抗性,提升市場競爭的張力、韌性和強度的考慮,〔49〕同前注〔32〕,孔祥俊文。避免任何與在先商業模式產生沖突的行為動輒得咎。在“電視精靈案”中,德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明確指出:“被告的廣告屏蔽裝置的銷售雖然加重了原告的經營負擔,但并未威脅其生存。”但是,如果禁止被告生產和銷售“電視精靈”,那么“則會使其遭受毀滅性打擊,因為廣告屏蔽是其商業模式的核心。”〔50〕同前注〔40〕。在“白名單案”中,德國法院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原告并未證明正面臨被市場淘汰的情境”,若其“提供的新聞服務不再僅僅通過廣告籌集資金,其經營活動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改觀”。故此,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證明“屏蔽真正地危害了原告生存”。〔51〕同前注〔41〕。
在實證法上,德國曾經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直接以對競爭者自由構成“顯著損害”(Spürbarkeit)作為不正當競爭行為認定的門檻(§3I,UWG,2008)。為了與歐盟《不正當商業行為指令》(UCPD)保持一致,《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UWG,2016)刪除了這樣的表述,但并未放棄這樣的要求,而是將其納入到對“不正當”的解釋之中。〔52〕Vgl.Christian Alexander,UWG 2015-Ende des schwierigen Weges zur Richtlinienkonformit?t?,Betriebs-Berater,BB 5.2016.S.1.按照“電視精靈案”的判決,“顯著損害”就是“導致競爭者任憑自己的努力都無法將自己的業績在市場上合適地展示”,破壞了憑借真本事爭勝的競爭秩序。
法律對競爭損害的態度決定了競爭發揮作用的空間。僅僅因為導致競爭損害就認定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實際上就是打著保護競爭的旗號阻斷競爭的過程;而對競爭損害的寬容,則給予了更多的競爭自由。目前我國采用的權利侵害式侵權法思維(尤其是“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或抽象的道德評價標準天然地有利于主張正當商業模式的一方,任何與之沖突的商業模式都被認定為“干擾”或不正當競爭,這顯然是落入了“競爭者保護”的邏輯,僅僅因為原告受到損害就草率地認定被告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53〕需說明的是,作為不正當競爭認定依據的競爭損害并不只是著眼于行為對競爭者的影響,還包括消費者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在內的競爭相關者利益整體權衡后的結果。能夠作為競爭行為判斷依據的只能是對競爭秩序的損害,而不是對競爭者的損害。“致使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門檻降低,使不正當競爭的范圍易于事實上擴大化。”〔54〕同前注〔32〕,孔祥俊文。
(三)消費者自由決策不受扭曲標準的確立
在技術創新之外,競爭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消費者偏好”。“消費者偏好”決定了競爭的結果。同樣以屏蔽廣告案為例,一方面,“免費內容服務+廣告”盈利模式的好壞由網絡用戶來決定。美國的網頁廣告模式就是依據用戶體驗成功地實現了轉型。這一領域的巨頭YouTube在2010年推出“True View”服務,用戶可以選擇是否跳過廣告以及廣告呈現的方式,甚至可選擇在視頻特定位置觀看某廣告。另一方面,即使屏蔽方與被屏蔽方合作,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用戶。著名的廣告屏蔽應用AdBlock Plus軟件商曾多次與谷歌、亞馬遜、微軟等平臺企業談判,在收取一定的費用后將其廣告納入某“白名單”,使其免受攔截。〔55〕同前注〔33〕,韓紅星、覃玲文。“白名單”的設定本身必須滿足一些旨在確保消費者利益(諸如不追蹤用戶隱私、不發送彈窗)的硬性標準。
“消費者偏好”要在競爭機制中發揮作用,關鍵在于競爭過程中傳遞的信息的真實性以及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即消費者的自由決策機制不受扭曲。〔56〕See Tim W.Dornis,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Conflicts: Historical-Comparative,Doctrinal,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pp.287-295.在司法實踐中,只要消費者自由決策的機制不被扭曲,一般就不會認定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如在“電視精靈案”中,德國最高法院的裁判就再三強調“認定是否構成對競爭者廣告營銷的阻礙關鍵是看該阻礙行為是否剝奪了消費者的自主決定權。”因為電視觀眾完全有權決定是否選擇使用“電視精靈”,所以“被告只是為電視觀眾提供了一個技術幫助讓他們離開其本來就不想看的節目”而已。〔57〕同前注〔40〕。
我國在“反法”修訂過程中,學者對消費者利益能否成為獨立的不正當競爭認定標準一直存在爭議,雖然持肯定意見者不在少數,〔58〕參見李友根:《論消費者在不正當競爭判斷中的作用——基于商標侵權與不正當競爭案的整理與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孔祥俊:《論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新定位》,《中外法學》2017年第3期;吳峻:《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司法適用模式》,《法學研究》2016年第2期;周樨平:《論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消費者保護功能》,《競爭政策研究》2017年第2期。但仍有人拒絕將消費者利益作為不正當認定的獨立標準。〔59〕參見焦海濤:《不正當競爭行為認定中的實用主義批判》,《中國法學》2017年第1期。而法院一直傾向于將消費者利益作為證明經營利益受損的一個工具,不具有獨立評價的地位。此種情況在最新的兩起廣告屏蔽案件的裁判中有了明顯改觀,法官在這兩起案件中因消費者利益改善而拒絕認定被告屏蔽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60〕同前注〔4〕,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需明確的是,競爭過程中的消費者是一個整體形象,對消費者的自由決策的“實質性扭曲”,〔61〕與對競爭者利益的“顯著損害”含義一致,對消費者決策的“實質扭曲”也強調的是消費者基于競爭秩序享有的利益受損的程度,這是一種在正常市場風險之外所遭受的非市場損害。指的是企業因此不合理地獲得了競爭優勢的行為,而不是侵害消費者個體利益的個別行為。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是其納入“反法”而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界限,這也正是“反法”作為經濟法所具有的公共屬性的體現。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考量集中在受害人數的多寡、造成損害的范圍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企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進行的欺詐或顯失公平的行為等因素,但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為限。〔62〕參見楊宏暉:《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令與德國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的新變革——以消費者保護的強化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2010年第2期。
四、法律技術:比例原則對干預邊界的限定
市場調解優先除了意味著優先發揮市場在解決競爭沖突中的作用外,還意味著依據競爭本身的屬性和客觀效果認定行為的不正當性。競爭的過程是動態的利益均衡的過程,作為利益衡量工具的比例原則在限定不正當競爭邊界上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它被視為對不正當競爭規制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種“更好的結構性規范”。〔63〕同前注〔24〕,邁克·費恩塔克書,第286頁。過度規制或規制不足很大程度上源于“未向社會和經濟規制中引入比例原則。”〔64〕Sunsteine,C.R.,After the Rights Revolution: Reconceiving the Regulatory Sta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81.
(一)作為“對規制限制”的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在本質上是一個對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平衡與協調的工具及具有普適性的判斷行為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其通過考察不同方式(行為、手段)對兩個相沖突利益(原則、目的、價值等)的各自影響,選擇能夠最大程度上同時兼容兩種利益的方式。〔65〕參見蘭磊:《比例原則視角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解釋——以視頻網站上廣告攔截和快進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為例》,《東方法學》2015年第3期。該原則最初濫觴于行政法領域的警察法之中,后逐漸上升為一項憲法原則,最終擴展適用于整個法律秩序。〔66〕轉引自鄭曉劍:《比例原則在民法上的適用及展開》,《中國法學》2016年第2期。
在構成上,比例原則一般包括三個子原則:一是妥當性原則,即所采取的措施可實現所追求的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則,即除采取的措施外,無其他給關系人或公眾造成更少損害的適當措施;三是相稱性原則,即采取的必要措施與其追求的結果之間并非不成比例(狹義的比例性)。〔67〕參見[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頁。
妥當性原則關注手段與目的的聯系,比較容易查明,而且即使相關行為只是部分有助于目的之達成,仍可滿足。當然也確實存在某些行為僅僅以追求某個目的為借口,實際上完全無助于該目的的實現。必要性原則實際包含兩層意思:其一,存在多個能夠實現目的的行為方式,否則必要性原則無適用的余地;其二,在能夠同等實現目的的諸方式中,選擇對第一種價值侵害最小的一種。由于技術的復雜性,要求被告在行動時逐一考察各種可選方案并選擇其中侵害最小的方式顯然是一種苛求。實踐中通常會給予被告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只要求不存在侵害性明顯更小的替代方式即可。〔68〕同前注〔65〕,蘭磊文。狹義比例原則強調的是利益平衡的方法,權衡追求目的所要達到的利益(收益)與為實現這一目的而對相沖突利益造成的損害(成本)之間是否成比例,這一平衡過程并不是通過精確地計算兩個變量的數值大小然后加以比較,而是較為粗略地比較兩個變量。〔69〕同上注。只有當損害明顯大于收益時才構成對狹義比例原則的違反;如果造成的損害與所實現的收益相比并不明顯失衡,則認定行為合法,從而給行為人留下足夠的自由裁量空間,避免動輒違法。〔70〕同上注。
在性質上,比例原則是“一種規范”,違反此規范將遭受制裁,也是“一種審查工具或手段”,〔71〕陳淳文:《比例原則》,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8頁。為執法者提供制裁的理由。這兩種性質體現為比例原則的“本體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前者指的是作為公民“自由權利不受公權力不當限制與侵害之準繩”,〔72〕謝世憲:《論公法上之比例原則》,載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三民書局1994年版,第127頁。“任何國家公權力之行為違反了這個原則,會導致違憲的后果。”〔73〕陳新民:《德國公法學基礎理論》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頁。后者指的是其提供一套可供理性操作和論辯的思維工具,為最終的結論提供強有力的支撐理由。〔74〕同前注〔66〕,鄭曉劍文。
(二)在不正當競爭認定中適用的正當性
比例原則最初適用于傳統的公法領域,一方面確認公權力基于公共目的可以限制私權利,另一方面又將其限制在必要限度之內。隨著權利與權利、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沖突的頻現,比例原則從一個處理政府與私人利益沖突的原則轉化為一個處理私人之間利益沖突或者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沖突的原則,逐漸拓展至私法、經濟法領域。
經濟法以私法自治為其構造的邏輯起點,旨在彌補私法自治的局限,保障和拓展私法自治的作用空間。而對私法自治構成威脅的一是國家公權力過度干預,一是私權利的濫用。在國家公權力對私權利施加某種限制的情況下,比例原則可以發揮其所具有的“限制之限制”的功能,即要求此種限制須服務于一個價值更高的正當目的(如實現公共利益);所采取的限制手段須有助于目的的達成;在有多種手段供選擇時,需要采用最為和緩的干預手段進行限制;該最為和緩的干預手段對利害關系所產生的負擔與其所追求的目的之間在效果上要相均衡。如此,既可確保國家職能的充分實現,又可維護私法自治不被過度介入和干預。在一方不當地獲取或維持競爭優勢的情形下,也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則對此種過度的自由進行限制,恢復競爭約束之下的均衡。因為,對私法自治的限制,不僅在于禁止恣意,還在于禁止過度。反對極端“禁止過度”是比例原則之精髓。〔75〕參見鄭曉劍:《比例原則在現代民法體系中的地位》,《法律科學》2017年第6期。
具體到“反法”領域,比例原則適用的正當性包括如下三個層次。
其一,比例原則的適用切合“反法”利益平衡的制度機理。現代意義上的“反法”對不正當競爭的認定“越來越具有利益平衡的意蘊”。〔76〕孔祥俊:《論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現代化》,《比較法研究》2017年第3期。“反法”通常具有保護經營者(競爭者)利益、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三疊加的保護目標。〔77〕相對于舊法而言,2017年11月4日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第2款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界定發生了明顯變化。首先,將“擾亂市場競爭秩序”置于經營者和消費者權益之前,意味著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首先要考量市場競爭秩序,也就是競爭機制和公共利益意義上的損害;其次引入消費者利益,使利益衡量法律結構更加完善。至此,從法益保護的角度看,新修法實現了“公共利益”“經營者利益”“消費者利益”三疊加的保護目標。參見孔祥俊:《論新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時代精神》,《東方法學》2018年第1期。而不同的利益主體基于競爭享有不同的利益,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就必然是對這些相關沖突的利益進行衡量。
利益衡量的方法無非有二,一是參考權利位階,一是訴諸比例原則。〔78〕參見梁迎修:《權利沖突的司法化解》,《法學研究》2014年第2期。如果權利位階存在高低之分,那么位階高的權利通常會被視為具有更高的價值并得到優先保障。但是,經營者的營業利益無時無刻不與自由競爭相沖突,這兩種沖突的利益無所謂誰更“高階”,沒有哪一方必須在沖突中獲勝,〔79〕參見于飛:《權利與利益區分保護的侵權法體系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頁。故此,只能采用比例原則在個案中確定哪種利益更值得保護。
比例原則相對具體的規范構成及判斷方法可以在司法層面進行展開和操作,從而為解決權利之間的沖突或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提供指南。將其作為利益衡量的指導和參考框架,既可妥當地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又能為法官和當事人提供較為明確的預期。〔80〕同前注〔66〕,鄭曉劍文。或者說,既符合競爭有優勢的利益屬性和保護需求,又避免了抽象道德的不確定性。
其二,比例原則的邏輯、適用結果與市場競爭的本質高度契合。競爭是一種爭勝過程,是在不同利益主體相互約束、激勵和反制的互動下不斷推出、改善產品和服務的過程,這種約束、激勵和反制本身就體現為對既有利益的損害和對新型利益的創造。只有允許對既有利益的適當損害才可能為新型利益的發展騰出空間,也才能刺激既有利益的不斷改進。〔81〕同前注〔65〕,蘭磊文。基于比例原則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認定邏輯可以將誠實信用原則與公認的商業道德標準轉換為一個依據競爭效果展開的客觀的利益權衡的框架,排除對某種特定權益的專門保護,最大程度地實現各種利益的協調與兼容。
在“淘寶訴載和、載信案”中,一審法院認為,對一項競爭行為是否予以規制,應綜合考慮經營者、消費者等各方的利益,并對其他經營者因被訴行為遭受的損害與停止被訴行為對行為者利益造成的損害進行衡量。競爭的利益均衡的功能特性決定了無論哪一種利益都不具有抽象意義上的絕對優先地位。該案的二審法院在進行更精細的利益衡量后特別指出,消費者在競爭過程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可以提升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并不能當然被排除在不正當競爭行為之外,仍要就被控行為的正面效果與對被干擾者所造成的損害進行衡量”。〔82〕參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7)滬73民終198號民事判決書。
其三,比例原則的適用是法治框架構建的必然要求。以一種更為連貫的視角來看,基本權利所確定的行為自由要受到合憲性制度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必須滿足比例原則。〔83〕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納、邁因哈德·德雷埃爾書,第145~146頁。比例原則被視為對規制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種“更好的結構性規范”。〔84〕同前注〔24〕,邁克·費恩塔克書,第286頁。作為一種典型規制,“反法”本質上是為了實現更普遍的競爭自由而對特定主體的行為自由進行限制,其劃定企業競爭行為的負面清單,同時也將政府對企業行為的干預限定在這一范圍內。由此,與其說“反法”是對干預的授權,毋寧說是對干預本身的限制。
總之,從本體論意義上言,比例原則在“反法”中的適用切合了“反法”本身的制度機理,與其通過公權力的介入彌補市場局限和為市場發揮作用創造條件的制度邏輯相適應。它實際上筑起了維護私法自治的兩道屏障:對外抵御國家公權力對競爭的過度介入;對內確保私法自治不被競爭者實施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損害。從方法論意義上言,比例原則為涉不正當性的判定提供了一個更具可操作性的框架與思路,使裁判更加具體化與規范化,降低了過度干預的風險。
(三)不正當性判定中的利益考量框架
比例原則的教義學功能就在于其可以使權衡過程合理化和權衡內容具體化,〔85〕Vgl.Val Hans Hanau,Der Grundsatz Verh?ltnism??igkeit als Schranke privater Gestaltungsmacht,Verlag Mohr Siebeck 2004,S.95.從而使諸種相互沖突的法益和諧均衡。〔86〕轉引自前注〔66〕,鄭曉劍文。其適用的最大價值正在于與摒棄權利侵害式的侵權法思維和抽象道德判斷的需求相吻合,最大程度地限定政府干預競爭的邊界。很多依據“反法”一般條款認定的不正當競爭案件引發的爭議在根本上是源于缺乏一個穩定的、完整比例原則的分析框架,導致一些案件在利益考量因素上顧此失彼,或存在結構性缺失,或邏輯混亂。
在現代“反法”體系內,所有市場參與者均受保護。〔87〕Vgl.Emmerich,Unlauterer Wettbewerb,7.Aufl.,2004,C.H.Beck.,S.29.對于競爭者的保護主要是保護其基于自由競爭所享有的利益;對于消費者的保護主要是保護基于自由決策不受扭曲所享有的利益;對于社會公眾的保護主要是保護其基于不受扭曲的競爭所享有的利益。這些利益權衡要素在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中并無固定的價值位階和權重,行為正當性與否則取決于其是否最大程度地實現相關利益的兼容。
權利侵害式的侵權法思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幾乎將在先商業模式作為一項權利加以保護,賦予特定經營者免于競爭的特權;將競爭正當與否的判斷局限于在先經營者的利益是否受到損害,忽視了其他經營者競爭的自由以及消費者利益的獨立判斷價值。被廣泛適用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在本質上就是該思維的延續,雖然將“公益”作為干預的唯一正當化理由,從表面上賦予了公共利益很高的權重,但實際上卻會因阻斷競爭、限制創新而最終損及公共利益。
此前的大多數廣告屏蔽案件將屏蔽行為認定為不正當競爭就是基于此一思維。例如,在“大摩與樂視廣告屏蔽案”中,二審法院的判決雖然向前邁進了一小步,確認“反法”保護的是原告依托“免費內容服務+廣告”商業模式進行經營活動所獲取的合法權益,而非商業模式本身,但其裁判仍未能跳出“勞動成果權利化”的桎梏。法院特別強調:“競爭必須是經營者通過付出自己的勞動而進行的正當的競爭。”“大摩公司利用用戶存在的既不愿支付時間成本也不愿支付金錢成本的消費心理,推銷屏蔽軟件,目的在于依托樂視網公司多年經營所取得的用戶群,為大摩公司增加市場交易機會,取得市場競爭的優勢,屬于不當利用他人市場成果、損害他人合法權益來謀求自身競爭優勢,”〔88〕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滬73民終75號民事判決書。所以判其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并無不當。直至最新的兩起廣告屏蔽案,法院的態度才發生了轉向,認定屏蔽行為并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此際,法院判決的說理才具有了比例原則分析框架的雛形。詳言之,其一,在妥當性層面,法院都注意到了屏蔽行為有助于消費者免受不受歡迎的廣告滋擾。其二,在必要性層面,法院特別強調屏蔽軟件給予了消費者自由選擇的空間。尤其是在“騰訊公司訴世界星輝公司案”中,法院判決在此點上說得非常詳細。首先,世界星輝公司廣告屏蔽軟件并非直接和無選擇屏蔽任何廣告,而是只有用戶選擇勾選“強力攔截頁面廣告”選項時才能實現廣告過濾功能。其次,從屏蔽項的設置看,在所設置的四個選項中,以不屏蔽任何廣告為首選,默認屏蔽項只限于針對色情、賭博等不良廣告,即屏蔽軟件是否使用、如何使用,最終均由用戶決定,最大程度地考慮了對內容提供商的影響。其三,在相稱性層面,法院著重論證了屏蔽對內容提供商并未造成實質性損害。在“騰訊公司訴世界星輝公司案”中,法院指出,會員制與非會員制用戶的存在以及財務報告的分析都可說明廣告收入并非原告唯一的收入來源,屏蔽行為不會對其產生“根本性影響”。雖然判決未能像“電視精靈案”中德國最高法院的判決那樣詳細列舉內容提供商各種應對屏蔽的可能(如在正片情節中融入廣告或者與正片內容進行分屏顯示進行改進等),但是法院還是提到了視頻網站可通過進一步改善自身的經營和服務來謀求發展。〔89〕在“快樂陽光公司訴唯思公司案”中,法院在此方面做得更為出色,該案的判決詳細論證了原告應對屏蔽行為的諸多技術方案。
仍顯遺憾的是,法院判決在說理上將三個層次的內容交織在了一起,缺乏一個清晰的邏輯。在此方面,“大眾點評訴百度公司案”的二審法院的判決有了很大改觀。〔90〕參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滬73民終242號民事判決書。審理該案的法院全面考量了信息爬取行為所有相關者的利益。既考慮到信息獲取者的財產投入、信息使用者自由競爭的權利,還顧及到公眾自由獲取信息的利益,以及信息和互聯網發展所必須的信息共享、互聯互通的特點。〔91〕該案的一審(參見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528號民事判決書)與二審的裁判結果雖然一致,但是在理念和思路上卻有了很大差別。一審法院主要立足于漢濤公司基于收集、整理、加工對大量信息所產生的商業利益的保護,缺乏對整個信息產業的信息傳播、其他經營者合理使用信息、消費者獲取更多信息利益的考量。裁判建立在“未經允許使用他人的勞動成果”的邏輯上,以“不勞而獲”“搭便車”為主要依據,這一方面陷入了道德判斷的泥沼,另一方面事實上創立了一種“勞動成果權”。實質上體現的是一種“保護競爭者”而不是“保護競爭”的思路,是“權利侵害式侵權”而不是比例原則下的“利益衡量”思維。最重要的是,在行為正當性判斷上清晰地體現了比例原則的三個子原則的分析脈絡。其一,就妥當性而言,二審法院確認了百度公司將從大眾點評網上爬取的點評信息用于百度地圖,用戶在搜索到商戶位置的同時,還可了解其他消費者對該商戶的評價,這種商業模式上的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用戶體驗,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具有積極的效果。其二,就必要性而言,由于存在明顯對漢濤公司損害方式更小的方式而未采取,可認定百度公司對大眾點評數據的使用方式已超過必要限度。如法院判決所言,它本可以采取一種對大眾點評網損害更小的少顯示或部分顯示點評信息的方式,在基本保證用戶體驗的情況下降低對大眾點評網的損害。其三,就相稱性而言,百度公司的爬取行為所產生的積極效果與對大眾點評網的損害相比并不相稱,對大眾點評服務產生了實質性替代。更重要的是,這種行為還可能使得其他市場主體不愿再就信息的收集進行投入,破壞了正常的產業生態,對競爭秩序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旦進入這一領域的市場主體減少,消費者未來所能獲知信息的渠道和數量亦將減少。因無法滿足必要性和相稱性的要求,故百度公司的爬取行為才被法院認定為不正當競爭。
五、結論
美國著名競爭法學者霍溫坎普教授曾深感憂慮地指出:“反壟斷政策經常基于對競爭損害的夸大擔憂,發展出一些具有過度保護性的規則,以消費者利益為代價使無效率的企業擺脫競爭的約束。”〔92〕Christina Bohannan,Herbert Hovenkamp,Creation Without Restraint: Promoting Liberty and Rivalry in Inn- ov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XI.同樣地,在“反法”適用過程中發展出的權利侵害式侵權法思維、過于寬泛的道德化判斷,嚴重低估了競爭本身此消彼長的對抗性,將競爭損害等同于不正當競爭,或者將對他人成果的合理使用認定為不正當競爭,過度保護了競爭者。這種對私人競爭關系的不合理介入和過于寬泛的不正當競爭認定方式已經完全失去了其限定企業競爭行為“負面清單”的意義,從根本上動搖了企業自由競爭的基礎。
“反法”的謙抑性源于一種法治化的要求。尊重市場的權威、尊重私法自治的原則是由憲法基本權利條款所決定的,也是民法與經濟法相互銜接、相互支援的體系所決定的。市場競爭具有復雜且不可預測性,若對競爭行為過多地指手畫腳,很可能損害企業的競爭自由。也就是說,在錯綜復雜和具有內生性的市場競爭面前,法官對于不正當競爭的判斷必須保持足夠的謙抑。〔93〕同前注〔32〕,孔祥俊文。極端私法自治無法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哈耶克也不否認政府干預的價值,只是他將公法的邊界限定在為自生自發秩序的作用的發揮提供必需的框架,反對以公法扭曲或替代私法。〔94〕參見[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1卷,鄧正來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頁。從結構上講,“反法”確保私法自治優先發揮作用,對競爭關系的介入以私法自治無法發揮作用為前提,以維護競爭秩序為限;并且這種干預不是取代或扭曲私法自治,而是旨在彌補其不足或者為其更好地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反法”的謙抑性還源于自身的制度邏輯。它是為實現更普遍的競爭自由而介入私人競爭關系,融合了私法和公法,最終體現了經濟法的特性。民法自身無法克服私法自治的局限,需要政府干預,而這種政府干預又必須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圍內以確保真正的私法自治的實現。作為這種對私權與公權的雙重限制,內在嵌入了謹慎的干預思維,而強烈干預的“家長”式情懷本身就是對這種謙抑性的背離。
“反法”的謙抑性強調的是其作為一種干預而建立在市場調節失效之后的后發性、恢復市場作用的輔助性,以及與市場邏輯保持一致的適應性之上。就后者而言,意味著對不正當競爭界定的標準是基于競爭本身。歐肯早就提及,對“不正當”的定義通過“不受扭曲的競爭”獲得。〔95〕參見范長軍:《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頁。“不受扭曲的競爭”是各方利益的均衡,比例原則是利益平衡的工具,故此,對不正當競爭的認定必須在比例原則的分析框架下展開。該框架的客觀性可最大程度地避免因權利侵害式侵權法思維和商業道德判斷所致的過度干預風險,將政府對競爭的干預限定在應有的范圍內。在全球互聯網經濟、數字經濟、分享經濟勃興的今天,對在市場上誕生的創新型經濟模式和商業模式,不應動輒就采取行政干預或動用司法資源,而應更多地留待市場自身來解決。〔96〕參見鄭友德、王活濤:《新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頂層設計與實施中的疑難問題探討》,《知識產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