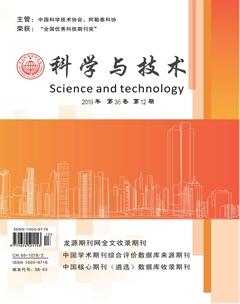羊毛氈藝術創作中的審美邂逅
姚嫻婧
摘要:本文以羊毛材料以及作品表現力為出發點,順應羊毛運動的社會趨勢,論述了羊毛氈在現在藝術領域的發展狀況。通過介紹國外羊毛氈藝術家及其作品在平面、立體、雕塑以及可穿戴藝術等多方面的展現,對不同風格和表現形式下的羊毛氈在藝術中呈現的作品案例進行淺析,闡述了羊毛氈藝術在世界范圍所掀起的創作浪潮。最后談及中國的羊毛氈藝術領域的發展方向,展望羊毛氈藝術創作在未來更大的可能性,以及所呈現更高品質的審美邂逅。
關鍵詞:羊毛氈;羊毛運動;可穿戴藝術;羊毛氈藝術;審美邂逅
一、關于羊毛氈藝術
羊毛是百分之百天然非人造的蛋白質纖維,質地細軟而富有彈性,強韌耐磨,具有縮絨特性,是理想的編織原料。羊毛的表面覆有鱗片層,其作用是保護羊毛不受外界損害,鱗片排列的不同,對羊毛的光澤和滑澀有很大的影響。[1]這種材料在藝術創作中表現出很神奇的特性,不但在簡單層面上可以作為新型產品的面料,而且可以用來進行軟雕塑作品的創作,同時還具備筆觸感和色彩的藝術語言。作品所呈現的方式也多種多樣,根據表現需要可以是平面化的、褶皺的、立體的、輕薄的或是厚重的等多重效果。
羊毛運動(Wool Campaign)是在2010年10月從英國正式開始實行,次年,威爾士親王開設了現代羊毛展,展示羊毛的時尚設計方案。隨后,由羊毛運動發起的羊毛流行趨勢被逐漸引入至包括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日本等國的市場。在2012年,羊毛運動正式在中國啟動。[2]至今,羊毛產品與藝術品在世界范圍內都有著非比尋常的影響力,并且逐漸進入主流的大眾審美之中。
羊毛氈,是羊毛運動下最賦創意的產物,作為羊毛材料的眾多衍生品之一,具有獨特的實用性與藝術性。自人類文明出現以來,羊毛氈就作為保暖的重要手段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早在唐代人們就已經嘗試用羊毛氈進行藝術創作,如印花毛氈地毯、毛氈壁毯等。現如今,手工藝者不斷嘗試尋求羊毛氈在現代生活中的新鮮答案,從服裝、鞋子、衣帽、首飾、包裝、玩具等多個產品方向,到毛氈畫、毛氈雕塑和現今流行的可穿戴藝術等,它給予了創作者無限的可能性。
羊毛氈的制作方式主要分為針氈和濕氈兩種。使用羊毛纖維進行雕琢塑形,受外力的作用下羊毛纖維的鱗片進行相互交叉纏繞進行沾化,利用羊毛纖維的高可塑性,藝術家們遵循羊毛氈的可能性,發揮自身的靈感創意塑造出別具風格的羊毛氈雕塑作品。羊毛氈在沾化的過程中出現不同程度的肌理效果,濕氈進行揉搓時,會不經意間形成褶皺的肌理,添加多量的羊毛時也會呈現出各種突出的肌理效果,這些肌理效果仿佛在模仿著自然界所存在的樸素真實的藝術效果。[3]在平面的羊毛氈創造時藝術家通常模仿油畫水彩的繪畫效果,進行繪畫一樣的創作模仿刺繡的效果進行人像、動植物圖案繪制,效果逼真細膩。打破平面藝術的局限性,使用針氈方式進行戳制出立體的圖案。羊毛氈藝術的表現力大膽自由,為藝術提供著無限的可能性,彰顯著材料的質感美。
二、羊毛氈藝術家及其作品
當我們去思索這些羊毛氈作品通過材質本身、畫面效果、象征、隱喻等傳遞給我們的感受時,我們就在理解作品所呈現出來的藝術家所表達的情緒。從用戶情感需求的角度和感性需求的角度出發,尊重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相結合,借用羊毛的柔軟特性進行合理表達。羊毛氈的設計更多的考慮到了受眾人群,了解受眾偏好,制作出富有情感味道的作品。當藝術作品作用于觀眾,它在訴說著它們自身的特性,并且為更為客觀深刻的反映奠定了基礎,從而帶給觀者一種特殊的審美邂逅。各國藝術家也紛紛選擇羊毛氈作為主要的藝術創作材料,通過不同的手段做出不同的藝術作品,從而呈現出羊毛藝術的視覺盛宴。
1、丹妮·艾弗斯(Dani Ives)
丹妮·艾弗斯(Dani Ives)是一位自學成材的藝術家,也是Good Natured Art的創始人。她的靈感來自對自然和科學的熱愛。她早年對環保教育事業熱愛使她不斷遵循自我的愛好,偶然發現了針氈,滿足她對藝術創作的需要。短短幾年時間,丹妮研發了獨特的針氈風格,她稱之為“用羊毛繪畫”。憑借這種風格,她不再使用油漆和刷子,而是使用羊毛纖維和氈針創造分層顏色的效果,創造出質感和深度。力圖通過創造充滿細節和現實主義的動物肖像和植物作品來推動這種纖維藝術的界限。她的針氈“繪畫”作品呈現出優雅大方,富有現代意義,高超的技法,她在不斷探索纖維藝術領域工作的無限可能性。
2、伊斯帖·堡得(Eszter·Burghardt)
伊斯帖·堡得是一位來自加拿大的毛氈藝術家,作品多以自然為主題進行創作。她的作品既包括可穿戴藝術,還有活靈活現的毛氈動物雕塑,以及用毛氈去模擬自然景觀,比如火山噴發等。
作品《披著羊皮》描繪人穿著氈狀動物毛皮身處在曠野上的場景。人物穿著羊毛氈所做的可穿戴雕塑,就像寓言“披著羊皮的狼”一樣,去代指穿著羊皮的(人類)才是真的惡棍。借此表達了對人類破壞環境的不滿與控訴。她使用的是冰島羊毛,對原羊毛進行加工制成大面積氈片,通過手縫,針氈,然后蒸汽定型等手段最終形成可穿戴雕塑品。這是在用一種當代藝術的方式,去揭露事物的本質。用隱喻的特性來呈現一段奇妙的羊毛氈藝術的邂逅之旅。
作品《羊毛巖漿》獨辟蹊徑,使用毛氈模擬火山噴發的自然景觀,表現了作者對自然觀察之細致以及羊毛氈表現手法之精妙。她采用羊毛氈和其他微小景觀的結合進行模擬自然的拍攝。藝術家創作微小立體場景,然后以一種可以處理建筑模型的方式拍攝它們。隨后呈現出一組華麗的風景,體現出不同的趣味,令人難以置信。
3、卡拉Calar
卡拉是一位來自荷蘭的藝術家,她認為馬是世界上她最喜歡的動物,她認為可以用一個詞去代表荷蘭馬文化—“Friesian”。“Friesian”起源于13世紀的時候羅馬人被用來打仗的馬的品種,現如今這種馬也出出現在馬術表演和馬車游行。她的設計來源于她對馬的熱愛,在日常生活中她積累了許多創作素材,通過與馬進行接觸,認真觀察馬的體姿與神態找尋表現馬的藝術方式。在她的作品《馬面具》的創作中,她選取馬的頭部,并很好地抓住了馬的神態,將馬抽象化為臉部和馬蹄鐵的結合。該作品面部顏色的選取是混合后的灰藍色調的羊毛,鐵蹄是深灰色的鐵制;面部的材質選用的是柔軟的羊毛進行戳制,與馬蹄的剛硬鐵制形成強硬的對比。柔與硬的對抗,把馬的精神表現的極為恰當。這種柔與硬的對抗,賦予這個雕塑一種后現代的特性,即解構后的重組,使雕塑有了新意義。關于馬,她還有許多其他的作品:用羊毛制成的馬頭雕塑,羊毛馬燈具,羊毛氈馬畫等。
通過解讀這些不借助任何黏合劑進行塑造,作品一體成型,顏色鮮明,光澤度十足的作品,我們能感受到平面和立體的藝術作品,在公共藝術創作中所呈現出的獨特的藝術審美情趣;也能感受到在全球性的羊毛運動大趨勢下羊毛氈藝術所呈現的時代機遇和挑戰下,藝術家超越羊毛材料本質所展現的藝術魅力以及對羊毛氈的全心付出;更深刻的認識到羊毛氈藝術家的責任與使命以及該項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近幾年手工羊毛氈紛紛流行開來,手工藝者秉承著不忘初心,簡單認真的生活態度做著DIY設計工作,用羊毛戳制著她們的夢想,帶領高壓生活節奏下的人們開啟造物的神奇之旅,制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幫助人們釋放壓力,治愈心靈,是全民藝術的一個良好開端。羊毛氈藝術還處于萌芽階段,越來越多的藝術專業的畢業生在大膽的嘗試、創新、突破。她們表達著自我,引領著毛氈藝術的發展方向。
三、總結
當技術與工具的創新持續擴散,藝術變得更加輕松便捷,為了打破一成不變的手工觀念,藝術家們要做的是挖掘更深層次的精神話題,將藝術作品的創作內容質量不斷提升。[4]羊毛氈藝術的本質是在高壓社會下改善現狀溫暖人心,并獲取相應的市場回報。在藝術與技術的交融時代下,具有獨特表現力的藝術作品正在悄然興起。當羊毛氈藝術的精神層面的東西逐漸被接受,對特定的問題進行深耕,創作富有精神層面的藝術作品,這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這樣建立在不斷復制批量生產的波普大環境下的特殊表現模式,定會在作品中賦予新的生命力更好的發揮作品的藝術價值。沒有任何一項藝術會一直沉睡,羊毛氈藝術正在打破僵局。藝術家是不會永遠滿足于低層次的簡單的戳戳樂作品,需要不斷的技術創新,藝術革命,有意識的改變著生活的現狀。
羊毛氈藝術作品所呈現的自然氣息的材料質地和工藝制法不斷喚起大家的關注,人們對大自然的向往,漸漸消除著機器大生產下的生活帶給人們的冷漠和無趣,讓藝術變得更加溫暖,更需賦“人情味”。傳承與發展靠的不僅僅是優秀藝術家的藝術作品,還有藝術創作所需要的社會環境和市場空間。我們需要將民族的世界的民族的藝術傳承下去,更好的將中國的傳統工藝在當今藝術創作的大熔爐里更好的發揚下去,給予羊毛藝術事業更深的養分。
參考文獻
[1] 張海東,文紅. 軟裝飾藝術設計與制作[M]. 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2] 賴松. AWI誠邀中國企業登陸倫敦摩登羊毛展[J]. 紡織服裝周刊,2011(22):31-31.
[3] Mackay M. Art in Felt and Stitch[J]. 2012.
[4] 劉遠航. 藝術創作與工匠精神的關系之我見[J]. 中國文藝家,2017(6).
(作者單位:大連工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