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部的努力,完成普通的生活
陳竹沁
十幾年前,我們家族里出了一樁惡性事件。我的一位遠房叔叔撞上醫療事故。一個腸道小手術失敗,醫生在他的腹部開了一個造口,外接口袋排泄。我沒有親眼見過他,只是在家人的敘述里,留有朦朦朧朧的印象:一個溫柔和氣的中年男子,提著“口袋”,在妻子的攙扶下,一同走在馬路上。
他一定過得很難:身上隨時涌現的異味,勞動和社交的逐步喪失,還有農村里的議論和同情的目光……誰也不知道,弦是從哪一刻繃斷的。再次聽到他的消息,是令人震驚的“殺妻慘案”,他本人也自殺身亡,留下一個年幼的孩子。
趕稿的深夜,我突然想起這個叔叔來,被自己的一個念頭驚出冷汗。也許,他不是大家以為的那樣瘋了,而是隱性抑郁癥導致的“擴大性自殺”?我搜了搜期刊資料,據一家寧夏醫院統計,98例直腸癌并行結腸造口術患者,46例量表評分顯示抑郁,還有41例為焦慮;一家河南醫院的肛腸外科對80例造口患者家屬的研究發現,近10%有抑郁癥,57.5%可能有抑郁癥狀。
可我們誰也沒有理解過他,也沒有幫助過他。事實上,共病是抑郁癥的主要特點之一。產后抑郁近年來經過媒體報道,已經有所普及,但還有許多慢性病,包括關節炎、哮喘、心血管疾病、癌癥、糖尿病和肥胖等,都和抑郁癥有關系。許多年過去,中國各級醫院對抑郁癥的識別率仍然只有三成,就醫率不足一成。
出現那個念頭,多少受到陳速的影響。最早是今年春節那會兒,我在“渡過”公眾號上看到他的留言,講到二十多年前他代理一起車禍致抑郁癥的索賠案。這引起了我對抑郁癥選題的強烈興趣。最近我約他見面細聊才知道,他自己后來也查出過季節性抑郁癥,及時用藥康復,就此成了半個抑郁癥專家。
陳速對報章上的離奇自殺、他殺案件分外關注,比如一個教師的后腦被學生打了一拳,沒多久就自殺身亡;他也為一位老友的離世分外惋惜,當年她的北大男友莫名性情大變,是我叔叔夫婦的“翻版”。他還通過一篇心理學碩士論文的后記描述,斷定作者的研究對象和他是“病友”,線索不過是那個姑娘每到冬季就躲在寢室大吃甜食。
至此,我才理解了他最初對我玩笑般的“診斷”,近乎條件反射的職業病。他找到我在周刊的一份年終總結,上面赫然寫著“上半年我用睡眠謀殺焦慮,下半年我用焦慮謀殺睡眠”、“在冬天,不喝酒的我‘酗酒的方式就是大量吃甜食,而且必須在深夜……”他截圖并劃下紅線,“季節性情緒失調的診斷標準有7條,你符合2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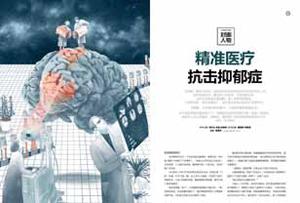
2019年第7期封面報道《 精準醫療抗擊抑郁癥》
我哭笑不得。在選題推進過程中才慢慢意識到,我確實有著典型的抑郁思維模式,如完美主義、低自尊、高度自省等等。在朋友圈發文尋找采訪對象,給了我另一個不算太意外的發現:每個人恐怕都有一個抑郁的朋友,但幾乎沒有人愿意公開談論病情。
七年前的這個春天,我到南京參加南方報業的終面。一個名叫走飯的南京姑娘剛剛因抑郁癥自殺。我在面試時說,選擇做記者,就是希望做電話線另一頭他們一直沒有等來的那個朋友。
七年后,走飯宣布“離開”的那條微博,成了互聯網最大的樹洞,而我第一次來到一個抑郁癥患者的電話線那頭。她剛上大學,和走飯當時的年紀差不多。我久久地聽著她與自己身上的“小惡魔”搏斗繼而和解的故事,腦海中冒出穆旦的那首小詩,或許沒有人比抑郁癥患者更能體會它了:
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我只覺得它來得新鮮,/是濃烈的酒,清新的泡沫/注入我的奔波、勞作、冒險。/仿佛前人從未經臨的園地/就要展現在我的面前。/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從人物故事轉向科學探索,這是《南方人物周刊》七年來的第二個抑郁癥封面。神經科學的進步依舊艱難,但到底還是多了一絲曙光。氯胺酮療法的創始人評價強生新藥,給患者提供了“大寫的‘希望”。克服恐懼,從正視“深淵”開始。作為時代船頭的瞭望者,我們要傳遞的,也正是這份“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