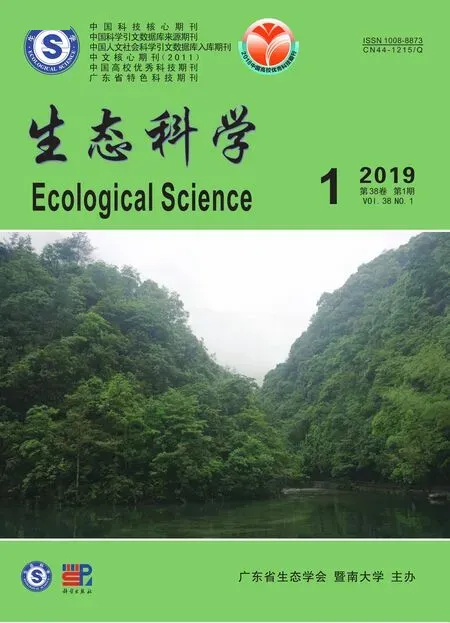小型淺水湖泊沉積物磷的賦存形態及其相關性分析
向速林, 李松貴, 張旭, 付成鋼, 吳蓓
?
小型淺水湖泊沉積物磷的賦存形態及其相關性分析
向速林, 李松貴*, 張旭, 付成鋼, 吳蓓
華東交通大學土木建筑學院, 南昌 330013
以孔目湖沉積物為研究對象, 應用七步連續提取法測定其中的不同形態磷, 探討了該湖泊沉積物中各賦存形態磷的分布特征, 并對其進行了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 該湖泊遭受的磷內源負荷比較大, 磷污染嚴重; 沉積物中TP含量在2338.63-2954.98 mg·kg-1, 平均為2671.37 mg·kg-1; 沉積物中各形態磷含量從高到低依次為: Fe-P>De-P>Ca-P> OP>Al-P>Oc-P>Ex-P, 分別占TP的53.9%、28.7%、8.8%、6.2%、1.2%、0.9%、0.3%; 生物有效磷含量為1583.59 mg·kg-1, 占TP的59.28%; 沉積物中TP與Fe-P極顯著相關, Oc-P與Ca-P和OP與Ca-P均相關, 而TP與Ex-P、Al-P、Ca-P和OP相關性較差, 說明沉積物中TP含量主要來自于Fe-P。這一研究結果為揭示小型湖泊富營養化發生機制提供了數據及理論支撐。
磷形態; 沉積物; 分布特征; 相關性; 孔目湖
1 前言
磷是湖泊的限制性營養元素之一[1], 過剩的磷會導致水生生態系統初級生產力升高, 進而導致水體富營養化, 破壞湖泊水生生態系統平衡。磷通過一定的物化、生物作用積累在湖泊沉積物中, 沉積物逐漸成為營養鹽的重要儲存庫[2-3]。在外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時, 內源磷釋放成為主要的污染因子。當外界環境條件發生變化時, 通過再懸浮、吸附解吸、化學擴散及有機質降解等過程, 沉積物中的營養物質會再次釋放到上覆水中[4-5]。而內源磷負荷主要來自沉積物的釋放, 是淺水湖泊形成藍藻水華的重要因素[6]。其沉積物中不同賦存形態的磷, 呈現不同的地球化學特征, 對磷在沉積物與上覆水界面的遷移轉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7]。因此, 研究沉積物中磷的不同賦存形態及其分布特征不僅可以反映不同區域沉積物的釋磷潛力, 還有助于認識湖泊沉積物磷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機制, 對湖泊富營養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當前, 國內外針對湖泊沉積物磷形態或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大型深水湖泊[8-15], 但針對城市小型淺水湖泊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城市小型淺水湖泊相對于深水湖泊來說沉積物磷的吸附、釋放等地球化學特征更為復雜, 主要體現在水位淺、淤泥厚、相對封閉、易受人類活動影響等。其風浪作用干擾明顯, 表層沉積物氧化更為充分, 單位體積水體與沉積物的接觸機會更大, 沉積物與上覆水界面磷的交換也更為頻繁[16]。因此, 對城市小型淺水湖泊的研究則更具有現實意義和研究價值。本文主要研究孔目湖沉積物磷的賦存形態、含量的變化規律, 并對沉積物不同賦存形態磷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相關性進行了分析, 以期了解近年來人為干擾活動對湖泊沉積物磷的累積效應和分布特征的影響, 進而為深入研究城市小型淺水湖泊富營養化內源磷釋放機制及水環境修復提供參考依據和理論支撐。
2 材料與方法
2.1 樣品采集
孔目湖(115°88′13.6″—115°88′54.9″E, 28°73′69.8″—28°74′41.7″N)是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華東交通大學南區的一個校內湖, 湖泊呈爪形, 其水面總面積約0.27 km2, 平均水深約1.2 m, 最深處達2 m, 是集景觀、養殖于一體的封閉式城市小型淺水湖泊。由于大量的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排、上游水葫蘆和魚類等動植物殘骸及常年的雨水徑流等經過物化、生物作用后含有相當水平的磷元素進入湖中, 導致水體富營養化程度加劇, 雖然進行了清淤、修復等工程, 但水質依然沒有得到改善, 湖內每年仍發生大量魚類死亡現象, 水體顏色可見度高、有臭味, 嚴重影響人們的生活環境且加劇水環境的污染。
結合該湖泊地理位置、排污口具體位置信息及水生植物分布等, 并盡量避開水草茂盛、表層沉積物易受擾動的區域, 確定了9個采樣點(如圖1), 于2017年9月19日, 利用自制的柱狀采樣器采集厚度約為10—15 cm的9個沉積物柱狀樣品, 采樣點特征如表1所示, 現場裝入聚乙烯塑料袋后冷藏保存, 帶回實驗室保存在冰箱中冷凍干燥后備用。其中, 取表層0—2 cm沉積物樣品進行磷賦存形態及其水平分布的研究。同時, 將L4、L5、L6三個點的沉積物柱狀樣品以2 cm為單位間隔分層, 用于磷賦存形態垂直分布的研究。

表1 采樣點具體特征匯總

圖1 沉積物采樣點分布圖
Figure 1 Sketch map of studied area and sampling points
2.2 研究方法
沉積物TP的測定采用高氯酸-硫酸酸溶-鉬銻抗比色法[17]; 沉積物各磷形態采取七步連續提取法[18]測定, 即: 易交換態磷(Ex-P)、鐵磷(Fe-P)、鋁磷(Al- P)、閉蓄態磷(Oc-P)、自生磷(De-P)、碎屑磷(Ca-P) 和有機磷(OP); 生物有效磷(BAP)的含量估算公式[19], 即: BAP=Ex-P+Fe-P+Al-P+0.6′OP。本研究采用SPSS20.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用Origin8.6軟件繪制圖形。
3 結果與分析
3.1 沉積物中磷賦存形態的水平分布
3.1.1 總磷及不同形態磷的水平分布
各采樣點表層沉積物總磷及不同賦存形態磷的含量, 見圖2。由圖2可知, 各采樣點TP的含量的高低排序為: L8>L2>L1>L5>L7>L3>L4>L6> L9。表層沉積物(0—2 cm)總磷含量范圍為2338.63—2954.98 mg·kg-1, 平均含量為2671.37 mg·kg-1, 顯著高于國內其他湖泊[20-22]。其中, 總磷含量最大值出現在L8監測點, 最小值出現在L9監測點, 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水力沖刷的作用下, 大量的外源磷涌入周邊, 有的被湖中懸浮物吸附直接沉淀下來, 有的未能被水生植物來得及所吸收的磷吸附在沉積物表層, 導致L8監測點表層沉積物總磷的含量異常偏高, 與其他監測點總磷含量有所差異; 另一方面可能是該湖泊兼水產養殖功能, 因大量的投餌養殖, 使得餌料殘渣和魚類糞便直接或間接沉降到沉積物表層, 不同賦存形態的磷酸鹽與碳酸鈣形成共沉淀或被氧化鐵膠體吸附[23], 導致湖泊水體磷污染嚴重, 進而使得該湖泊整體總磷含量較高。
從圖2可以看出, 同一監測點不同形態磷Fe-P、De-P、Ca-P及OP的含量變化具有相同變化規律, 其含量大小均為Fe-P>De-P>Ca-P>OP; 不同監測點同一形態磷的含量變化存在一定差異性, Ex-P、Al-P、OP含量的最小值分別出現在L4和L9監測點, 而De-P、Ca-P含量的最大值出現在L7監測點, 這可能是由于沉積物中不同形態磷的釋放能力不同, 在一定物理化學條件下, 不同形態磷之間可以相互轉化, 導致各形態磷之間含量也有所差異。
同時, 由圖2可知, 沉積物的各形態磷含量由高到低的排序為: Fe-P>De-P>Ca-P>OP>Al-P>Oc- P>Ex-P。通常, 生物有效性磷(BAP)是指能被藻類可直接利用的潛在活性磷, 包括沉積物直接或間接向上覆水水體釋放的并參與上覆水水體中磷在循環的可直接吸收態的磷[19], 其中Ex-P、Al-P、Fe-P和部分OP都可以通過生物礦化作用間接轉化為可供生物利用的無機形態磷。因此, 可利用公式估算生物有效磷(BAP)的含量: BAP=Ex-P+Fe-P+Al-P+0.6′OP。BAP的含量能真正反映沉積物污染狀況及其內源釋放能力的大小[24], 可通過生物或化學作用轉化成活性磷被生物所利用或進入上覆水水體, 從而導致水體富營養化。分析可知, 該湖泊BAP含量范圍為1188.16—1899.84 mg·kg-1, 平均含量為1583.59 mg·kg-1, 平均比重占TP的59.28%, 與廣州流花湖(58.57%)[25]生物有效磷占TP比重相似, 比湖北喻家湖(32.42%)[22]、南京玄武湖(36.2%)[26]略高。由此可知, 該湖泊過高的生物有效磷含量, 反映了沉積物污染較為嚴重, 其釋放風險也較大, 不但加劇了水體富營養化, 同時也加大了該湖泊富營養化控制的難度。
Ex-P易通過解吸作用被水生植物直接吸收利用, 是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重要形態磷。溫度、pH、溶解氧(DO)及擾動等環境因子改變都可能導致Ex-P向上覆水體擴散, 從而影響湖泊水體的營養狀況[27]。總體上, 9個采樣點Ex-P含量都相對較少, 其含量占TP比重不到0.5%, 但在沉積物內源磷的釋放時, 該部分磷會首先得到釋放, 因而不容忽視。沉積物中Al-P含量一般處于較低水平, 其分布與酸堿度、沉積物粒度、黏度和形成時間等有關[28]。在過酸或過堿的條件下, 都會加速其溶解。其含量最高點出現在L4監測點, 最低點出現在L1監測點, 平均含量為32.11 mg·kg-1, 所占TP的比為1%—1.4%, 表明該湖泊沉積物中Al-P含量整體水平較低。Fe-P同Al-P一樣, 通常被認為是生物可利用性磷, 其含量與外源磷輸入有關, 主要來源于生活污水、工業廢水和部分農業面源流失的磷[29]。Fe-P的含量范圍在1012.15—1753.27 mg·kg-1之間, 所占TP的比為43.3%—58.5%, 其主要磷形態為Fe-P, 遠高于其他形態磷的含量, 與宋鵬鵬等[30]的研究結果相反, 這可能與沉積物特性、環境條件等有關, 反映了不同區域、不同水生態系統其沉積物Fe-P含量的差異性較為明顯。

圖2 各采樣點表層沉積物中不同磷形態的含量
Figure 2 Concentrations of different phosphorus forms for different sampling points in surface sediments
Oc-P主要來自鐵鋁氧化物覆蓋的結合態磷及自然巖石狀態磷[31], 具有穩定、不易釋放等特點。Oc-P的形成與沉積物的物理化學風化強度有關, 其地質意義明顯, 但很難被生物所利用[32]。該湖泊沉積物中Oc-P含量范圍為18.38—30.22 mg·kg-1, 平均含量為24.56 mg·kg-1, 其含量高于Ex-P含量, 僅次于Al-P含量。同樣, De-P和Ca-P也較難被分解, 屬于較穩定態磷。De-P是一種生物作用而沉積的顆粒態磷, 主要來源于沉積物中動植物死亡殘體引入的鈣磷, 一般難以被生物所利用[32]。De-P含量具體表現為689.41—878.50 mg·kg-1, 平均含量為764.18 mg·kg-1,其含量僅次于Fe-P。這可能與該湖泊長期養魚有關, 由于水質惡化, 水中溶解氧降低, 死魚事件頻發, 大量死魚殘體留在湖中, 從而導致湖泊De-P的含量偏高。Ca-P主要包含于沉積物中的原生礦物顆粒中的部分鈣磷, 其來源于各種難溶性的磷酸鈣礦物, 穩定性高, 在非強烈的還原條件下很難釋放, 難以被生物利用。其含量與溫度、水動力條件、微生物活性及酸堿性等因素密切相關[33]。研究表明, 人為排放的生活污水會導致上覆水水體較高濃度的Ca2+和溶解性磷酸鹽形成難溶性的鈣磷酸鹽沉淀, 在該湖泊的Ca-P平均含量為233.97 mg·kg-1, 比De-P含量較低, 表明生活污水是導致該湖泊水體富營養化的重要來源之一[34]。
OP的含量與沉積物沉積特性、外源輸入、早期成巖過程、生物作用及有機質等因素有關[16]。從圖2中可以看出, 該城市淺水湖泊沉積物OP的含量相對較低, 其范圍為109.81—224.30 mg·kg-1, 平均含量為162.67 mg·kg-1, 由于浮游動植物、微生物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產生的磷酸酶的生物作用, 在其催化水解下, OP可以轉化其他可被生物所利用的形態磷, 具體表現為沉積物中OP的含量偏低, 向上覆水釋放的磷含量偏高, 從而導致湖泊富營養化的歷程加快。
3.1.2 各形態磷平均值所占TP的百分比
由圖3可知, 無機磷中易交換態磷(Ex-P)平均含量為8.21 mg·kg-1, 占TP的0.3%。鐵結合態磷(Fe-P)含量最高, 范圍在1012.15—1753.27 mg·kg-1, 且L8采樣點含量最高, 平均含量為1445.46 mg·kg-1, 占TP的53.9%。鋁結合態磷(Al-P)含量很低, 平均值為32.11 mg·kg-1, 占TP的1.2%。閉蓄態磷(Oc-P)含量較低, 平均含量為24.56 mg·kg-1, 占TP的0.9%。自生鈣磷(Ca-P)含量平均值為233.97 mg·kg-1, 占TP的8.8%。碎屑態磷(De-P)含量較高, 僅次于Fe-P, 平均值為764.18 mg·kg-1, 占TP的28.7%。有機磷(OP)平均含量為162.67 mg·kg-1, 占TP的6.2%, 較Ex- P、Oc-P及Al-P平均含量所占TP的比重多。

圖3 各監測點不同形態磷平均值所占TP的百分比
Figure 3 The percentage of TP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orus in different monitoring sites
該淺水湖泊各采樣點不同形態磷含量差異性較大, 說明外源磷輸入對湖泊不同區域的影響程度不同。由圖3可知, 各形態磷所占TP比的高低排序為:Fe-P>De-P>Ca-P>OP>Al-P>Oc-P>Ex-P。沉積物不同賦存形態磷的含量反映了沉積物磷的釋放潛能和湖泊受污染程度, 其中Fe-P的占比在50%以上, 說明該湖泊受生活源的影響明顯, 其污染較為嚴重。由于Fe-P的遷移轉化可以在短時間內使上覆水水體磷的形成快速循環[35], 其含量表明該湖泊沉積物Fe-P的釋放潛能很大, 對水體富營養化作用貢獻也較大。
3.2 沉積物中磷賦存形態的垂直分布
3.2.1 總磷及不同形態磷的垂向分布
因篇幅及工作量限制, 以下選三個點分析垂直分布, 如圖4。三個監測點的柱狀沉積物TP平均濃度分別為2738.18 mg·kg-1、2596.24 mg·kg-1和2519.08 mg·kg-1(L4>L5>L6)。L4、L5、L6 三個監測點柱狀沉積物總磷的含量從下到上變化范圍分別為2564.19—3210.69 mg·kg-1、2337.24—3016.71 mg·kg-1及2333.81—2657.28 mg·kg-1。由圖4可知, L4、L5、L6三個監測點沉積物TP都隨深度的增加而減少。在7 cm以下的TP濃度變化不大, 其TP平均含量下降緩慢。表層含量明顯高于底部含量, 具體表現為“表層富積現象”, 這種分布特征說明近年來該湖泊沉積物的TP含量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可能是大量的外源含磷物質輸入并轉移到沉積物表層[36]; 也可能是沉積物中磷的地球生物化學作用而向表層遷移所導致的[37]。
由圖4可以看出, 該湖泊柱狀沉積物各形態磷中Ex-P在TP中所占比例最小, 在垂直分布上變化相對較穩定, 整體呈現下降趨勢, 這可能與表層沉積物中有機質礦化作用和微生物分解作用等有關[36], 表層沉積物向上覆水中釋放較多的正磷酸鹽, 而為了維持沉積物與上覆水間的磷平衡狀態, 較多的溶解性磷酸鹽會被沉積物吸附成為顆粒態磷酸鹽, 因此表層沉積物Ex-P的含量較高。隨著深度的增加, 環境條件處于相對還原狀態, 更有助于解吸磷, 因此隨著深度的增加, Ex-P的含量呈現逐級遞減趨勢。
Fe-P相對含量是最多的, 所占比例也是最大的, 同時也是被認為可被生物所利用的一種形態磷, 在一定的條件下易釋放到水體中。由圖4可以看出, L4、L5監測點沉積物Fe-P含量在垂直方向表現為隨著深度的增加先減少后增加而后再減少, L6監測點沉積物Fe-P含量在垂直方向則表現為隨著深度的增加而一直減少, L4、L5、L6三個監測點沉積物Fe-P總體上呈現隨著深度的增加而減少趨勢。可能是隨著深度的增加, 溶解氧不斷降低, 環境條件變得相對還原, 沉積物Fe-P易被釋放進入上覆水中, 但在氧化還原電位相對較高的環境條件下, 溶解性正磷酸鹽重新被Fe3+捕獲再次形成鐵磷礦物而沉淀下來, 表層氧化層的存在抑制了磷酸鹽的遷移, 導致沉積物表層的Fe-P的富集[38]; 也可能是隨著深度的增加, 非礦物晶型逐漸變得有序化, 鐵氧化物礦物和氫氧化物礦物與磷酸鹽的結合能力也相對變弱[39]。Al-P垂直分布規律呈現與Fe-P相類似的規律, 但其含量相對來說較低, 所以對該湖泊富營養化的貢獻不大。

圖4 L4、L5、L6三點沉積物中總磷及不同賦存形態磷的垂直分布
Figure 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phosphorus and different species of phosphorus in three sediments of L4, L5 and L6
Oc-P相對Ex-P含量較多, 但L5、L6監測點Oc-P含量其垂直分布是隨著深度的增加先減少后增加, L4監測點Oc-P含量其垂直分布是隨著深度的增加先增加后減少, 由于Oc-P主要來自鐵鋁氧化物覆蓋的結合態磷及自然巖石狀態磷[31], 屬于比較穩定態的磷, 在強還原條件下很難釋放出來, 說明L5、L6監測點沉積物中氧化物隨著深度的增加而減少, L4監測點沉積物中氧化物隨著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同樣, De-P和Ca-P也屬于相對穩定態磷, 但其垂直分布規律與Oc-P不同, L4、L5監測點沉積物De-P含量的垂直分布隨著深度的增加先減少后增加, L6監測點沉積物De-P含量的垂直分布隨著深度的增加變化規律不明顯, 這主要是因為De-P是一種生物作用而沉積的顆粒態磷, L4、L5監測點位于該湖泊主體部分和排污口周邊, 其水產養殖中魚類、螺類和上游種植大量的水葫蘆等動植物殘骸通過物化作用沉淀在沉積物中并不斷積累所導致的。而三個采樣點Ca-P含量隨著深度的增加變化規律不明顯, 這可能與微生物活性及酸堿性的不同有關[33]。L4、L5、L6監測點沉積物OP含量都表現為隨著深度的增加而減少, 可能與微生物的活性及沉積物沉積特性等有關[16]。
3.2.2 不同形態磷的垂向分布平均值所占TP的百分比
從圖5中可以看出, 在L4監測點7種不同形態磷占TP的比例為: Fe-P>De-P>Ca-P>OP>Oc-P>Al- P>Ex-P,其中Fe-P平均值所占比例為55.1%, 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逐漸減小, 在7 cm以下變化不大; 其次De-P平均值所占比例為26.65%, 并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也是逐漸減小, Oc-P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是先減小后增大, 其Oc-P平均值所占比例為1.24%; Ex-P、Ca-P、OP及Al-P平均值所占比例不超過10%。
由圖5可知, L5監測點沉積物在不同深度不同形態磷所占TP的百分比為: Fe-P>De-P>Ca-P>OP> Al-P>Oc-P>Ex-P, 其中Ca-P和OP比例相當, 所占比例分別為8.99%和8.19%, 都是隨著深度的增加而減小的趨勢; Fe-P所占比例為55.69%, 且隨著深度的增加變化不大, 其次是Oc-P, 其所占比例為0.91%, 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是先減小后增加, 在9 cm后達到最大; 之后是De-P, 所占比例為25%, 整體趨勢是隨著深度的增加而先增大后減小; Al-P所占比例為1.02%, 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逐級遞減; Ex-P所占比例最小, 僅有0.21%。
L6監測點不同形態磷所占TP的比例為: Fe-P>De-P>OP>Ca-P>Oc-P>Al-P>Ex-P, 相比L4、L5監測點, 相同深度下L6所占比例變化最大。Fe-P所占比例最高, 其所占比例為47%, 且所占比例隨著深度的增加逐級遞減; De-P所占比例為27.93%, 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逐漸減小; OP所占比例為13.57%, 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變化不明顯; Ca-P所占比例為8.81%, 隨著深度的增加所占比例變化不大, 7 cm之后比較穩定; Oc-P和Al-P所占比例相當, 分別為1.24%和1.15%, 都是隨著深度的增加而減小; Ex-P所占比例為0.3%。
通過以上沉積物不同賦存形態磷的垂直分布狀況分析可以得出, 其一方面受人工干擾的影響較大, 其主要因素為大量外源磷的輸入; 另一方面可能與沉積物的特性也有關, 沉積物顆粒越細, 對上覆水磷的吸附能力越強, 表層沉積物磷的含量也越高[40]。
3.3 表層沉積物總磷及不同賦存形態磷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通過表2表層沉積物總磷及不同賦存形態磷之間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可得, 沉積物中的TP含量與Fe-P含量間呈顯著正相關(R=0.939,<0.01), Ex-P含量與Fe-P含量間呈明顯正相關(R=0.486,<0.05), Ca-P含量與Oc-P含量間呈顯著正相關(R= 0.627,<0.05), Ca-P含量與Fe-P含量間呈顯著負相關(R= –0.507,<0.05), 而TP含量與Ex-P含量、Al-P含量、Ca-P含量及OP含量間的相關性不大, 表明沉積物中TP的富集主要來自于Fe-P含量的增長, Ex-P、Al-P、Ca-P及OP在遷移轉化過程中對TP的影響不明顯, Ex-P與Fe-P、Ca-P與Oc-P呈良好的趨同性, 而Ca-P與Fe-P可能不同源或彼此具有拮抗性。同時也可得出, 沉積物中OP含量與Ca-P含量間呈顯著正相關(R=0.599,<0.05), OP含量與Oc-P含量間呈明顯負相關(R=-0.527,<0.05), 由于OP是部分生物可利用磷, 主要來源于農業面源污染[41], 而Ca-P主要來源于各種難溶性的磷酸鈣礦物, 難以被生物所利用, 表明該湖泊沉積物中OP的來源有一定的差異性。

圖5 L4、L5、L6三點不同形態磷的垂向分布所占TP的百分比
Figure 5 Three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orus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ercentage of TP at L4, L5, L6

表2 表層沉積物總磷及不同賦存形態磷之間的Pearson相關性(n=9)
注: *表示<0.05; **表示<0.01。
4 結論
(1)孔目湖沉積物中TP含量為2338.63—2954.98 mg·kg-1, 各采樣點TP的含量的高低排序為: L8>L2>L1>L5>L7>L3>L4>L6>L9。
(2)孔目湖沉積物磷的賦存形態的水平分布特征表明, 同一監測點不同形態磷Fe-P、De-P、Ca-P及OP的含量變化具有相同變化規律, 其含量大小均為Fe-P>De-P>Ca-P>OP; 不同監測點同一形態磷的含量變化存在一定差異性。
(3)孔目湖沉積物磷的賦存形態的垂直分布特征表明, 沉積物磷呈現的表層富集現象揭示了內源污染較嚴重, 其一方面受人工干擾的影響較大, 其主要因素為大量外源磷的輸入; 另一方面可能與沉積物的特性也有關。
(4)通過相關性分析得知, 沉積物中的TP含量與Fe-P含量間呈顯著正相關, 表明沉積物中TP的富集主要來自于Fe-P含量的增長。
[1] WANG Zhen, GAO Wei, CAI Yunlong, et al. Joint optimization of population pattern and end-of-pipe control under uncertainty for Lake Dianchi water-quality management[J].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2012, 21(12): 3693–3704.
[2] 龔瑩, 王寧, 李玉成, 等. 巢湖水體-沉積物磷形態與有效性[J]. 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 2015(3): 359-365.
[3] WANG Lingqing, LIANG Tao, ZHONG Buqing, et al. Study on Nitrogen Dynamics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of Dongting Lake, China[J]. Aquatic Geochemistry, 2014, 20(5): 501–517.
[4] 李大鵬, 黃勇, 李偉光. 底泥再懸浮狀態下生物有效磷形成機制研究[J]. 環境科學, 2008, 29(7): 1824–1830.
[5] 肖文娟, 曹秀云, 宋春雷, 等. 太湖不同營養類型湖區沉積物磷的形態與吸附行為的比較[J]. 環境工程學報, 2015, 9(7): 3525–3530.
[6] 黃清輝, 王東紅, 王春霞, 等. 太湖梅梁灣和五里湖沉積物磷形態的垂向變化[J]. 中國環境科學, 2004, 24(2): 147–150.
[7] 楊柳, 唐振, 郝原芳. 化學連續提取法對太湖沉積物中磷的各種形態測定[J]. 世界地質, 2013, 32(3): 634–639.
[8] 李樂, 王圣瑞, 焦立新, 等. 滇池柱狀沉積物磷形態垂向變化及對釋放的貢獻[J]. 環境科學, 2016, 37(9): 3384– 3393.
[9] 王忠威, 王圣瑞, 戴建軍, 等. 洱海沉積物中磷的賦存形態[J]. 環境科學研究, 2012, 25(6): 47–53.
[10] 王敬富, 陳敬安, 曾艷, 等. 貴州紅楓湖沉積物磷賦存形態的空間變化特征[J]. 湖泊科學, 2012, 24(5): 789–796.
[11] DING Wei, ZHU Renbin, HOU Lijun, et al. Matrix-bound phosphine, phosphorus fractions and phosphatase activity through sediment profiles in Lake Chaohu, China[J]. Environ Sci Process Impacts, 2014, 16(5): 1135–1144.
[12] YUAN Hezhong, AN Shuqing, SHEN Ji,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cords of phosphorus species in different trophic regions of Taihu Lake, China[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4, 71(2): 783–792.
[13] LIU Kai, NI Zhaokui, WANG Shengrui, et 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hosphorus in sediment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of Poyang Lake[J]. Zhongguo Huanjing Kexue/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5, 35(3): 856–861.
[14] GKELIS S, PAPADIMITRIOU T, ZAOUTSOS N, et al. Anthropogenic and climate-induced change favors toxic cyanobacteria blooms: Evidence from monitoring a highly eutrophic, urban Mediterranean lake[J]. Harmful Algae, 2014, (39): 322–333.
[15] RYDIN E. Potentially mobile phosphorus in Lake Erken sediment[J]. Water Research, 2000, 34(7): 2037–2042.
[16] 李大鵬, 黃勇. 風浪與底棲生物擾動對底泥內源磷釋放的協同作用[J]. 中國給水排水, 2013, 29(4): 17–20.
[17] 鄭習健, 陳瑞珍. 酸溶──磷銻鉬光度法測定污泥中的磷[J]. 環境科學與技術, 1996, (3): 15–17.
[18] 朱廣偉, 秦伯強. 沉積物中磷形態的化學連續提取法應用研究[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03, 22(3): 349–352.
[19] BOSTRM B, PERSSON G, BROBERG B. Bioavailability of different phosphorus forms in freshwater systems[J]. Hydrobiologia, 1988, 170(1): 133–155.
[20] 岳宗愷, 馬啟敏, 張亞楠, 等. 東昌湖表層沉積物的磷賦存形態[J]. 環境化學, 2013, (2): 219–224.
[21] 邵雪琳, 魏權, 高麗, 等. 天鵝湖瀉湖表層沉積物中各形態磷的空間分布特征[J]. 土壤通報, 2015, 46(1): 127– 132.
[22] 魯群, 李秀, 李湘梅. 湖泊底泥中磷形態及分布特征研究[J]. 環境工程, 2014, 32(4): 135–139.
[23] 范成新, 張路, 包先明, 等. 太湖沉積物-水界面生源要素遷移機制及定量化——2.磷釋放的熱力學機制及源-匯轉換[J]. 湖泊科學, 2006, 18(3): 207–217.
[24] KANG Xuming, SONG Jinming, YUAN Huamao, et al. Phosphorus speciation and its bioavailability in sediments of the Jiaozhou Bay[J]. Estuarine Coastal & Shelf Science, 2017, (188): 127–136.
[25] 俞林偉, 譚鎮, 鐘萍, 等. 廣州流花湖底泥磷的垂直變化特征[J]. 生態環境學報, 2007, 16(5): 1358–1363.
[26] 彭杜, 劉凌, 胡進寶. 玄武湖沉積物磷形態的垂向變化和生物有效性[J]. 水資源保護, 2009, 25(1): 31–35.
[27] 許春雪, 袁建, 王亞平, 等. 沉積物中磷的賦存形態及磷形態順序提取分析方法[J]. 巖礦測試, 2011, 30(6): 785– 794.
[28] 蘇玉萍, 鄭達賢, 莊一廷, 等. 南方內陸富營養化湖泊沉積物磷形態特征研究[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05, 24(2): 362–365.
[29] RUBAN V, LóPEZ-SáNCHEZ JF, PARDO P, et al. Harmonized protocol and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extractable contents of phosphorus in freshwater sediments--a synthesis of recent works[J]. Fresenius’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1, 370(2-3): 224–228.
[30] 宋鵬鵬, 侯金枝, 高麗,等. 榮成天鵝湖沉積物磷的賦存形態和時空分布特征[J]. 水土保持學報, 2011, 25(3): 98–102.
[31] S?NDERGAARD M, JENSEN J P, JEPPESEN E. Role of sediment and internal loading of phosphorus in shallow lakes[J]. Hydrobiologia, 2003, 506-509(1-3): 135–145.
[32] 吳峰煒, 汪福順, 吳明紅, 等. 滇池、紅楓湖沉積物中總磷、分態磷及生物硅形態與分布特征[J]. 生態學雜志, 2009, 28(1): 88–94.
[33] 徐康, 劉付程, 安宗勝, 等. 巢湖表層沉積物中磷賦存形態的時空變化[J]. 環境科學, 2011, 32(11): 3255–3263.
[34] 王琦, 姜霞, 金相燦, 等. 太湖不同營養水平湖區沉積物磷形態與生物可利用磷的分布及相互關系[J]. 湖泊科學, 2006, 18(2): 120–126.
[35] 章婷曦, 王曉蓉, 金相燦. 太湖不同營養水平湖區沉積物中磷形態的分布特征[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07, 26(4): 1207–1213.
[36] WANG Shengrui, JIN Xiangcan, ZHAO Haichao, et al. Phosphorus fractions and its release in the sediments from the shallow lak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rea in China[J]. Colloids & Surfaces A Physicochemical & Engineering Aspects, 2006, 273(1–3): 109–116.
[37] 周慶紅, 姚素平, 高良敏, 等. 楊莊采煤塌陷水域沉積物中氮磷形態垂向分布特征[J]. 江蘇農業科學, 2015, 43(4): 321–323.
[38] 王雨春, 馬梅, 萬國江, 等. 貴州紅楓湖沉積物磷賦存形態及沉積歷史[J]. 湖泊科學, 2004, 16(1): 21–27.
[39] 潘成榮, 汪家權, 鄭志俠, 等. 巢湖沉積物中氮與磷賦存形態研究[J]. 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 2007, 23(1): 43–47.
[40] 高敏, 張生, 羅強, 等. 烏粱素海不同粒徑沉積物吸附磷實驗研究[J]. 環境工程, 2011, 29(6): 107–109.
[41] XU Delan, LEI Zexiang, WANG Hongjun, et al. Distribution of Phosphorus in Sediments of Onshore Reed Areas of Lake Taihu[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17(4): 557–561.
Fraction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osphorus in sediments of a small shallow lake
XIANG Sulin, LI Songgui*, ZHANG Xu, FU Chenggang, WU Be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 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Taking the sediment in Kongmu Lak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even-step continuous extra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forms of phosphorus in the sediment. The distributions of all phosphorus form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phosphorus loading accounted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in this lake, resulting in a serious phosphorus pollution. The contents of total phosphorus (TP) in the sediments ranged from 2338.63 to 2954.98 mg·kg-1with an average of 2671.37 mg·kg-1. The order of different form phosphorus contents in the sediments was Fe-P>De-P>Ca-P>OP>Al-P>Oc-P>Ex-P. Their proportions were 53.9%, 28.7%, 8.8%, 6.2%, 1.2%, 0.9% and 0.3% of TP, respectively. The content of bio-available phosphorus was 1583.59 mg·kg-1, which accounted for 59.28% of TP. There was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P and Fe-P. Also, both Oc-P and OP demonstrated a correlation with Ca-P. In addition, a weak correlation could be inferred between the TP and Ex-P, Al-P, Ca-P and OP.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P content in sediments is mainly from Fe-P. This study provides data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lake- eutrophication in this city.
phosphorus forms; sediment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correlation; Kongmu Lake
10.14108/j.cnki.1008-8873.2019.01.005
X703.1
A
1008-8873(2019)01-033-09
2017-12-27;
2018-03-04
江西省教育廳科技項目(GJJ150540); 江西省自然科學基金(20114BAB213020)聯合資助
向速林(1978—), 男, 江西撫州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從事水資源與環境研究, E-mail: slxiang2001@163.com
李松貴(1991—), 男,碩士生, 主要從事水資源與環境研究, Email: 120759839@qq.com
向速林, 李松貴, 張旭,等. 小型淺水湖泊沉積物磷的賦存形態及其相關性分析[J]. 生態科學, 2019, 38(1): 33-41.
XIANG Sulin, LI Songgui, ZHANG Xu, et al. Fraction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osphorusin sediments of a small shallow lake[J]. Ecological Science, 2019, 38(1): 3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