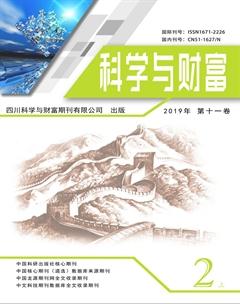李漁編劇藝術“三美說”之我見
李洋
摘 要:本文將李漁的編劇藝術“三美說”置放于新時代語境下,在中西方戲劇創作理論的互證中對其加以重新梳理和闡釋,以期為我國當前的戲劇創作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李漁;三美說;編劇藝術;之我見
一、故事:非奇不傳
(一)奇與新
李漁說,“新即奇之別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共見,萬人共見,絕無奇矣,焉用傳之?”對于戲劇創作來說,故事若不“新”,效果則不“奇”。為此,他批評了當時劇壇上的不良現象,“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也,皆老僧碎補之鈉衣,醫士合成之湯藥。取眾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種‘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時光流轉,幾百年過去了,李漁批評的這種現象,依然存在于當前的戲劇領域。
李莎在《戲曲“同質化”現象之思考》一文中說,“時至今日,……我們見到了太多大化之、扁平膚淺的應景之作。此類作品停留在對社會表象的觀察上,慣常以通用的概念出發,以集體的感悟替代個體的感悟,因因相襲,人云亦云,了無新意。”瑏瑠了無新意的作品,肯定贏得不了觀眾的注意。
而貝克(Baker,G.P.)認為,“所有戲劇家的共同目的是什么?有兩個。第一,盡快贏得觀眾的注意。第二,保持觀眾興趣的穩定,最好是使之有加無已,直到劇終。”瑏瑡那么,如何才能盡快贏得觀眾注意,并使觀眾的興趣有增無減呢?李漁給出的答案是,“且戲場關目,全在出奇變相,令人不能懸擬。若人人如是,事事皆然,則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憂者不覺其可優,苦者不覺其為苦,即能令人發笑,亦笑其雷同他劇,不出范圍,非有新奇莫測之可喜也。”瑏瑢這已經將道理說得相當透徹了:欲求“奇”,必先“新”。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新”,并非僅指題材之新,還應包括故事的立意之新、講述故事的視角之新,以及改編劇本時的“變舊成新”。李漁認為,“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至于傳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
(二)奇與真
尚“奇”求“新”,不等于荒唐怪誕。黑格爾說,“藝術家之所以為藝術家,全在于他認識到真實,而且把真實放到正確的形式里,使我們觀照,打動我們的情感。”赫爾德強調,“真是一切美的基礎”。戲劇之“美”同樣要建立在“真”的基礎上,否則就會成為空中樓閣、無本之木。李漁的下述觀點與此類同:“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于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人情物理”作為“荒唐怪異”對立面存在,顯然是表“真實”之意。這個背景下,就形成了“理真”和“情真”兩種不同的建構取向。
1.理真
李漁提出,藝術創作“雖貴新奇,亦須新而妥,奇而確。妥與確,總不越過一理字,欲望句之驚人,先求理之服眾。”那么,何謂“理”呢?鄭燮認為,“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能發生,則事也”。這就進一步指出了“理”和“事”的關系,即“事”是“理”的感性顯現。這個意義上而言,強調“理真”,便是強調“事真”。而具體到戲劇創作,“事真,故奇”瑏瑠則是呂天成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從而明確地指出了“奇”需以“事(理)真”為基礎。
2.情真
李漁提出,“文乎生情,情不真則文不至耳。……情真則文至矣。”又道,“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為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即前人已見之事,盡有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隱攻微,被泉下之人,自能效靈于我。”這兩段話都突出強調了“情真”在戲劇創作中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情真”應做兩個層面上的理解,一是劇作者的情感之真,即劇作者對所述之事以及事中之人要報以“溫情和敬意”“了解之同情”;二是劇中人物的情感之真,即劇作者設身處地,深入到劇中人物內心,發掘其豐富而真實的情感世界,并給予生動呈現,從而折射出世間冷暖,人生百態。
二、文詞:警策拔俗
李漁“三美說”中提出的第二個觀點是,“文詞不警拔,不傳”。那么,我們需要回答的是“文詞”何以“警拔”呢?答案至少包括以下幾點。
(一)“說一人,肖一人”
貝克在論述戲劇何以打動觀眾時指出刻畫好人物性格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戲劇中,動作無疑是最直接地感染著一般觀眾的。可是如果劇作家要和觀眾暢所欲言地溝通思想,那么寫好臺詞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一個劇本的永久價值終究在于其中的性格描寫。性格描寫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它是在觀眾中使劇本的主題或人物產生同情的主要手段。”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更是口氣堅決地強調:“一切與性格無關的東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顧。對于作家來說,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強性格,鮮明地表現性格,是作家在表現人物特征的過程中最當著力用筆之處。”如果說上述文字表明貝克、萊辛認識到了“性格描寫”對于戲劇創作的重要性的話,那么,與二人相比,李漁的不同凡響之處則在于他回答了“如何性格描寫”這一更具實踐性的創作難題:“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
(二)重機趣
李漁說,“‘機趣二字,填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陳賡平對此的解讀是,“‘機就是說全部戲曲應有生氣,前后貫串,不得補綴成篇。‘趣就是要戒除傳奇中的腐板道學氣,造語應有風趣。”這里指出了“機趣”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一是有效推進劇情,二是生動活潑,富有情趣。下面老舍的兩段話則是這兩個層面的最好證明,他說:“我要求自己用字造句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不單純地、孤立地去用一個字、造一句,而是力求前呼后應,血脈流通,字與字,句與句全掛上鉤,如下棋之布子。”又言:“喜劇的語言必須有味道,令人越咂摸越有意思,越有趣。
三、功能:有裨“風教”
李漁認為戲劇作品除了“情事要奇”“文詞警拔”之外,還應“有裨風教”。“風教”一詞出自《毛詩序》,“意為《風》乃至《詩》的性質和功能,兼具‘風與‘教,是為‘風教”。陳立群在論述“風教”的當代價值時提出,“風教”作為文化治理的先聲,為現代文化治理觀念的醞釀、技術的準備等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即使不再是我們時代的主旋律,其根基與內容也與當代有很大的歧異,但作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持存良久的文化治理技術和實踐,它們仍然可以為我們當下的文化治理提供借鑒”。具體到戲劇領域,王夢佳認為,隨著時代思潮、社會風氣,統治政策及文人審美理想等多方面因素的變化,“風教”理論也發生著不斷變化,但“對其作為戲劇審美標桿之一而存在的合理性,卻是一直被普遍而廣泛地認同著”。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我們不拘泥于李漁“有裨風教”的歷史背景和具體內容,而是從文藝作品要“勸惡揚善”“文以載道”這一古今相通的精神層面對其進行重新闡釋的話,就會發現李漁的這一觀點為我們構建新時代的戲劇觀、提升戲劇的社會文化功能,指導當前的戲劇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正如賀拉斯所言:“詩人的愿望應該是給益處的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幫助……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換句話說,“文藝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是緊密地聯系著的,不能彼此分割的,文藝術的審美作用不能離開一定的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而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必須通過審美作用才能實現。”顯然,這段論述與李漁所提倡的“事”“文”“有裨風教”的“三美說”可以互為支撐。
參考文獻:
[1]張春麗. 李漁的藝術管理與經營[J].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 40(5):138-140.
[2]駱兵. 論李漁觀眾本位的戲曲接受觀[J]. 廣西教育學院學報, 2002(2):102-107.
[3]吳喜梅. 由《閑情偶寄》看李漁尚俗的戲劇觀[J]. 理論界, 2007(6):2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