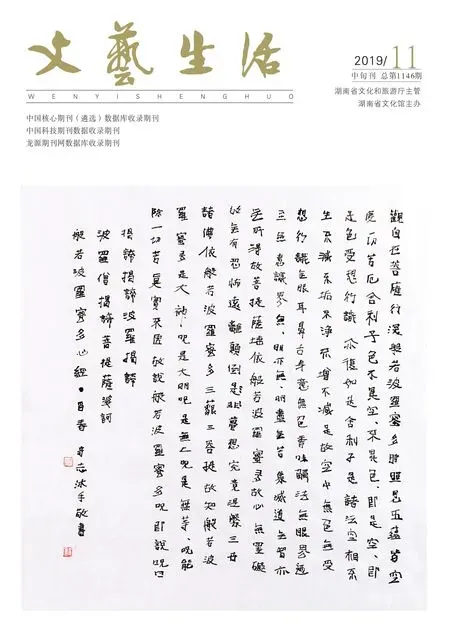試論軸線關系中越軸美學的價值
師 儀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 福州 350000)
一、軸線關系規則的形成及定義
1915年,美國導演大衛·格里菲斯導演了一部在美國電影史乃至世界電影史上都極具影響力和爭議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在這部影片中,導演開創了一種人物對話的鏡頭剪輯法則,即由一個中景雙人鏡頭加一組正反拍鏡頭構成,這種手法被后人稱為“好萊塢”三鏡頭法。“好萊塢三鏡頭法”能夠自然流暢地處理人物對話與空間的關系,在確保時空統一的同時,既不能讓觀眾感受到創作者的存在,也不能讓觀眾明顯地意識到自己旁觀者的地位,從而順利地在影像營造的封閉空間內進入“夢境”。因此,作為好萊塢電影核心敘事語言的“三鏡頭法”一度被視為電影創作的金科玉律,且這種剪輯方式至今仍被廣泛地運用于當下的影視作品中。而在“好萊塢三鏡頭法”中所遵循的一條基本調度規律便是“軸線規則”,即180度規則。
所謂軸線,是指被攝對象的視線方向、運動方向以及和其他交流對象之間所形成的一條虛擬的直線。在實際拍攝有軸線存在的場景時,只有將機位置于180度區域內,才能保證各個鏡頭畫面的方向感與空間感的一致性,否則就是越軸。
在電影中,軸線一般分為三種,即方向軸線、動作軸線和關系軸線。方向軸線是指處于相對靜止狀態的人物視線與能看到的物體之間構成的軸線。動作軸線也叫做運動軸線,一般運用于被攝主體運動的方向、路線或是軌跡中,在表現運動時,剪輯需要考慮到運動軸線的存在,避免產生跳躍感,關系軸線是指被攝對象關系和視線所形成的軸線,也是軸線規則的核心部分。
二、軸線關系規則的相關性思考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影理論學者將拉康的鏡像理論引入到電影研究當中,他們認為電影銀幕和鏡像階段具有相似性。如果把銀幕看作是一面鏡子,那么觀眾在最初觀看電影時,便會像嬰兒照鏡子一樣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并進入到想象界,將自己與銀幕中的形象產生認同,進而感到愉悅。然而,很快他就會意識到自己與銀幕中形象的差別,覺察到“母親”形象的缺失,從而來到象征界①。在意識到匱乏的象征界中,觀眾渴求重新達成統一。這種被性欲化的欲望需要遵從“父之法”,即作為象征秩序的語言,達成與作為認同客體的“母親”的決裂,在確認其自身的主體性并看到自己與“母親”相分離的身份后,視覺的快感由此獲得。因此在每次觀看電影的過程中,都是一次從想象界到象征界的滑動,都是一次對鏡像階段和俄狄浦斯階段的重復。而為了使觀看感受更加真實,便形成了相關的制作規律,之后近乎變成制作流程中的標準手段,其中三鏡頭法是好萊塢電影敘事語言的核心,也是世界范圍內電影語言中最常用的剪輯手法和敘事技巧。由于正反打本身即是主觀鏡頭和半主觀鏡頭,因此能夠自然而然、不留痕跡地把觀眾帶入到劇情中,消除了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對影像表現形式的有意注意。
對于好萊塢夢幻電影來說,重要的是,既不能讓觀眾感受到創作者的存在,也不能讓觀眾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的旁觀者地位。當然,與之而來的即是千篇一律的影像風格,也就是沒有風格的風格,因此追求風格化的法國人將好萊塢三鏡頭法戲稱為“零度剪輯”,通常我們將其稱為連續性剪輯②。
三、越軸的美學效果
(一)立場轉變
記得大學時期的第一節剪輯課上,老師曾向大家講解了軸線規則,在肯定這一規則對于正反拍鏡頭重要性的同時,也提到了越軸鏡頭在呈現特殊效果的同時可能造成的空間混亂。由于當時認知有限,筆者曾一度把軸線規則奉為垚臬,在此后完成的幾項拍攝作業中,嚴格地遵照軸線規則完成了影片的拍攝與剪輯,產生的效果無疑是流暢和規范的,但總是覺得在某些鏡頭的表現上缺乏張力。于是筆者不禁提出疑問,軸線規則是不是必須遵照的法則,越軸是不是一定會影響觀影效果?直到筆者觀看了小津安二郎導演的一系列作品,這種疑惑得到了解答。以家庭劇著稱的小津導演在其早期和中期的作品中大量運用越軸鏡頭,這種特殊的處理手法非但沒有帶來明顯的違和感,反而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在小津導演的《晚春》中,曾宮紀子一直未婚照顧著年老的父親,由于她已年歲不小,因此父親和姑姑都有意讓她早日成家。紀子的好友北川綾離婚后成為一名速記員,兩人經常到彼此家中串門,在閑聊中總是涉及到感情與婚姻問題。其中有兩場戲都發生在北川綾家中的會客室,在這兩場調度不多的對話場景中,小津導演并沒有遵循軸線規則,而是選取了四個固定機位進行拍攝。雖然在兩場戲中鏡頭不斷地越過軸線,但仔細看來,并不是沒有任何規律,而是沒一個機位都代表著不同的立場,每一次越軸都意味著立場的轉變。
(二)情節反轉
通常情況下,依照軸線規則拍攝的正反打鏡頭鏡頭能夠清除地交代人物關系與故事情節,但是在特別情況下,比如某些情節轉折點或要制造一種緊張情緒時,越軸能夠帶來產生視覺和心理上的改變。
在《羅生門》多囊丸所回憶的一場戲中,大盜多囊丸突然從樹叢里竄出來,圍著武士和妻子真砂看。在第一個鏡頭中,多囊丸跑到一塊空地上拔出手中的劍朝武士揮舞,為了表現出武士的警覺,這個鏡頭需要從武士的角度拍攝,從畫面上來看,此時機位的設置位于武士的右后方和多囊丸的左前方。忽然多囊丸大笑道“你不要懷疑我”,當然這種情況下不論劇中人還是劇外人都絲毫無法放松。這突如其來的轉變,讓我們以為即將發生的打斗得到了反轉,從而機位之間形成一條對角線,加上視角的轉換也伴隨著情節的反轉,因此這種處理方法并不突兀。
(三)構圖需要
有時越軸的目的是為了構圖,而有些時候為了構圖也需要越軸。
在巖井俊二的《情書》中,渡邊搏子在已故未婚夫藤井樹的房間發現一本中學同學錄,渡邊搏子萌生了給天國的藤井樹寄一封情書的想法,于是把藤井樹曾經在小樽市讀書時的住址抄寫在手臂上。此時,端著茶店的藤井樹的母親走進房間,問坐在沙發上的搏子“那是什么秘密?我是指秋葉先生他們。”正在低頭寫地址的渡邊搏子馬上起身,告訴藤井樹的母親他們今晚準備夜襲。此時她們之間構成一條關系軸線,按照常規的正反打鏡頭拍攝的話,兩個機位應該設置在軸線的同一側即渡邊搏子的左側和藤井樹母親的右側。但接下來卻是一個過渡邊搏子右肩拍攝的外反拍鏡頭,從背景來看,搏子的臉應該朝向右側,但在畫面中母親的臉卻向著左側,顯然這是一個越軸鏡頭。從大體上看,此時越軸似乎并不是很有必要,有學者甚至認為這可能是由于拍攝時先用替身完成了外反拍鏡頭,而在拍攝反向鏡頭時場記忘記了之前的機位,從而產生了錯誤。但仔細分析便能看出,這一越軸鏡頭與構圖是息息相關的,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攝影機過渡邊搏子左肩拍攝的話,那么遠景將是貼著圖紙的墻,書柜必然也會被取景框卡掉一截,看上去比較凌亂;此外,如果此處不越軸,那么藤井樹母親的視線就與渡邊搏子的視線正好相對,這樣她說話時也不必轉過身子,而談到兒子的事對一位母親來說也顯得比較傷感,面對面溝通這樣直接的交流顯然與此時的心境不相稱。
(四)越軸創作再思考
在許多時候,越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認為,一部作品的形式和結構越不可見,那么觀眾就越會被愚弄,進而相信幻覺。被愚弄得越多,就越會被利用。形式和結構越可見,觀眾就越能明白形式和意識形態是如何運作且事實上是不可分離的。形式和結構可見的藝術作品,變成了一種了解文化中更宏大的權力結構的工具③。按照布萊希特的觀點,像常規的正反打鏡頭,很容易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產生幻覺,但如果在必要時打破這種規則,那么觀眾也會在鏡頭切換的一瞬間從前一個鏡頭中所產生的幻覺中跳脫出來,并站在一個全新的角度審視眼前的人物和事件。這時,畫面中人物的視線是否與上一個鏡頭中的人物視線相交已不重要了,因為這非但不影響觀眾對劇情的理解,反而產生了一種類似于戲劇理論中“間離”的效果,從而使觀眾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人物的情感與命運。
如果說好萊塢電影是以觀眾的觀影體驗作為創作主旨,那么越軸就是以個人的藝術風格作為創作主旨。觀眾是否能馬上融入影片,是否會迅速產生移情,或許并不是我們最期待的結果。我們以越軸的方式把觀眾從既定的環境中解放,常態化演變為陌生化,陌生化就是歷史化,亦即說,把這些事件和人物作為歷史的、暫時的去表現。同樣地,這種方法也可用來對當代的人,他們的立場也可表現為與時代相聯系,是歷史的、暫時的。
四、結語
軸線規則所具有的規范化和高效率毋庸置疑,但這并不是說,軸線規則就是電影創作的規則,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這些規則并不是死板的戒律,而是一個手法選擇的體系,電影是沒有絕對的文法的。當然我們討論這一問題的目的并不是要批判軸線規則從而拔高與之相對的越軸方式,畢竟越軸在多數情況下仍然被視為一種特例。盡管在表面上看來,軸線規則和越軸是相互矛盾的個體,但本質上它們圍繞的都是鏡頭與敘事,都是為了達到理想的視覺效果。
軸線不是神話,越軸也不是為了打破神話。方法無關新舊,只關乎恰當,在保持必要規則的同時敢于不斷嘗試與創新,這大概就是電影的魅力所在吧。
注釋:
①雷晶晶.論“縫合”:一個電影概念的梳理[J].當代電影,2015(04):68-70.
②周傳基.打破“軸線”,一個中國神話[J].當代電影,1996(06):42-44.
③羅伯特·考爾特.電影、形式與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