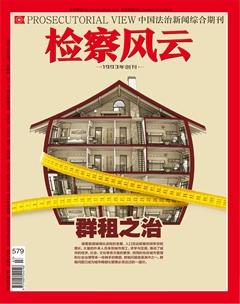朔風吹干了蒼天的淚
魏小燕
羅布泊,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灘:沒有一棵草、一條溪,就連天空中也不見一只鳥兒飛過,夏季氣溫高達70℃。因為我國地質學家彭加木在這里失蹤,上海探險家余純順在那里遇難,于是憑添了羅布泊神秘的色彩,激發了我骨子里的野性,于是有了新疆哈密羅布泊戈壁大漠探險之行。
哈密,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下轄地級市,位于新疆東部,是新疆通向中國內地的要道,自古就是絲綢之路的咽喉,有“西域襟喉,中華拱衛”和“新疆門戶”之稱。《漢書·西域傳》記載了當年張騫率眾人開出了著名的絲綢之路,現在羅布泊地區的大海道、大南湖、小南湖就是這古絲綢之路中的一段。之所以稱之為大海道,大、小南湖是因為當年的羅布泊也是像仙湖一樣的美,水草豐茂,牛羊成群。然而經過千百年的地殼變化,原來的海,水漸漸退去,直至20世紀70年代完全消失。大漠,一片孤寂、空曠,羅布泊從此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朔風沙蝕成就了現在壯觀的雅丹地貌,這里匯集了古城堡、海盜船、烽燧、驛站、化石山以及眾多罕見的地理地貌,各種被風沙雕刻了數千年的砂巖帶給人們不同凡響的視覺沖擊,令人欣喜若狂、忘卻自我。
一早,我們跟隨大漠飛虎戶外旅游車隊的越野車,沿哈羅(哈密—羅布泊)公路一路顛簸,駛向羅布泊腹地大海道的扎營地。到達扎營地時,大漠上起了風,師傅剛搭好的二人帳篷,風就這么輕輕一掠,帳篷竟然滾了好遠好遠。眼看小帳篷不行,領隊趕緊支上新買的充氣大帳篷。這個帳篷,可以住10人左右,最高的頂部有3米多。誰知,這么大的帳篷,這么多四角壓好的大石頭,在大漠風的眼里,就像一塊小手絹,它一揮手,帳篷就飛上天了!我們第一次領教了戈壁灘大風的恐怖,怪不得這里從來沒有任何生命可以生存,就連蚊蟲也沒有,空中也沒有任何飛禽敢于穿越。
好在領隊生存經驗豐富,馬上命兩部越野車分別緊貼帳篷兩側,用繩索把帳篷緊緊地拴在越野車的車輪上,背面拴上許多大石頭,帳篷總算固定住了;領隊命我們女生八人去車里搬下行李,壓在帳篷里,我們攝影人的相機又重又沉,為搭好帳篷立了汗馬功勞。攝影隊里的男同胞們膽子都是極小的,嚇得全部鉆到了我們的帳篷里。怎么辦?外面的風發了瘋似的咆哮著,帳篷被吹得呼啦啦的抖動,好像隨時可以飛上天空。面對此情此景,大家也就不拘小節了,擠一擠,湊合湊合吧。這一夜,帳篷里睡了十九個人,這一夜男女混雜,這一夜狂風肆虐,沙塵滿天;這一夜我迷迷糊糊不敢睡實,分分秒秒擔心那帳篷的頂會被大漠的風掀掉,帳篷的門窗會被戈壁的狂風撕開!
天漸漸亮了,咆哮了一夜的風突然停了。我走出帳篷,發現四周是那么的寧靜,在這曠野里,只要你不發出聲音,那么四周就回應你一個字:靜!這里沒有任何污染,空氣通透新鮮,戈壁廣袤而空曠,遍布的礫石、碎石和流沙狂野而古樸,壯觀的雅丹地貌雄偉地矗立在沙漠之中,沒有任何人工雕飾的痕跡,完完全全原生態的自然美和滄桑美。
擼一把滿臉的黃沙,用礦泉水漱漱口,結個伴,找個避風沙的地方休息,然后,背起相機跟著領隊開始創作。
我在哈密待了十天,三進羅布泊腹地,大海道扎營兩夜,大南湖扎營兩夜,小南湖扎營一夜。第一天扎營大海道突遇沙塵暴,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大南湖扎營巧遇千載難逢的雨,要知道,戈壁之所以稱之為戈壁,就因干旱無雨。向導說,羅布泊一年不雨是常態,幾年無雨也是有的,我們卻偏偏在十天內就嘗遍了它的狂虐和恩賜:太陽出來時,干燥酷熱,大漠無遮無攔,無處避陽,帳篷里雖可遮陽但悶熱無比待不上兩分鐘;下雨時和落日后,寒風吹骨透心的涼,每天都是襯衫與滑雪衫交替著裝;大漠是無人區,進去后只能吃些自備的馕和簡單的菜湯、粥,生活無比艱苦;在烈日、大風、沙陷、沙塵飛揚的茫茫戈壁荒漠,背著沉重的相機、三腳架,一步一陷的爬上沙包,走過礫石沙灘,尋找著荒漠帶給我的震撼和滄桑的美。不能不說,這是一種生命的歷練。
離開羅布泊,回到魔都上海,竟仍然對那荒無人煙的大漠難以忘懷。都市的繁華無法與那孤寂、蒼涼的荒漠相比;大漠以其千萬年練就的睿智承載著風化與演變,詮釋著恒久的守望,表達著頑強的生命之光。
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卑微和渺小的,所以,我敬畏大自然,敬畏生命!
編輯: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