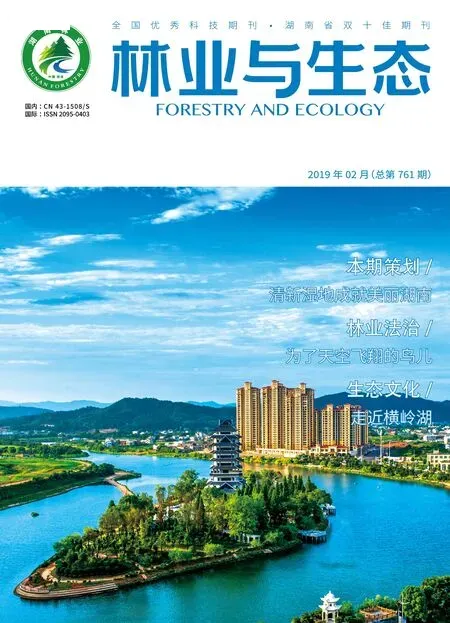走近橫嶺湖
文 /杜 華
這是一個秋陽艷麗的下午。幾位愛好文史研究的友人,在縣城某一處茶坊,聊起了橫嶺湖濕地,均提議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文人多隨性,總有悲春傷秋,張揚恣意之舉。那么,說走就走。
驅車過湘江大橋,沿江北上,約莫十七八公里后,到達湘臨村。湘資兩水經湘臨匯入洞庭,兩水匯合處泥沙淤積,乃船舶航行險要之地。經年江水沖積以及地殼運動,湘臨村沿岸形成許多曼妙河洲,豐水季節時,與南洞庭湖連成一片。河洲內側靠近堤岸處,鷺鳥翔集,云低水清。近年來聲名鵲起的景點—斗米咀,便在此地。在春天里油菜花綻放的季節,兩江一湖把這方沃野滋養,湖洲遍地金燦燦,綠油油,水汪汪。從省內外慕名前來攝影、踏青、享受自然風光的游客接踵而至。誰能想到,就在距斗米咀不遠處的橫嶺湖省級自然保護區,亦是如此的豐富廣袤,尤甚一籌呢。
至湘臨22塊碑處,從嵌滿麻石的防洪大堤拾階而下,穿過一片秋天里灰綠的楊柳林,到河邊去乘坐機船。對岸便是橫嶺湖。初春時,我曾和攝影愛好者到這里來拍照。其時河水尚瘦,兩岸淺褐色的河坡上,性急的草籽花已開了,像鋪著一塊綠底繡花的絨布,一眼瞧去,軟綿綿的。河床裸露處,泥土濕潤皸裂。我們在河床上走,深深地呼吸,把初春時攜了花粉的甜甜的空氣吸進肺里,感知將要迎來的一場醞釀已久的蓬勃與萌發。現在呢,在我們來之前幾天,下過幾場透雨,扁瘦的江面浮起了許多。泥土疏朗的裂紋在吸飽雨水后消失不見。浪花起伏,輕拍河岸,似是河水奔流輕聲的喘息。深秋金色的陽光,灑滿河流和村莊,照在河畔靜靜的機船上。駕船的老頭坐在船尾,臉堂黝黑,堆滿皺紋。一支香煙架在過于蒼老的指間,煙霧寂寂升起來,我仿佛看見了時光隨煙霧消散,生命點滴逝去的樣子。一切都是那樣自然而然。
“我們去看橫嶺湖。”
“對面就是。”老頭眼神一亮,爽朗地回答。
機船突突突開起來。河面很窄,我們蕩漾在一圈清波之中,不到十分鐘便過了河。
爬上河坡,是一片開闊的草地。春天時,粉色和紫色的草籽花隨地勢起伏,一直鋪展到遠處,和風拂過,朵朵花兒仰臉致意,令你不知從何下足。踩在哪里都不忍心。秋天里,草籽花和百蟲蟄伏,牛筋草與蒼耳卻依然蒼翠,密密匝匝卷入眼簾。秋陽溫暖,在如洗的天幕下,曠古的藍與遼闊的綠將你挾裹。你是否愛極了這綠呢,來不及細品,便往上走。“橫嶺湖省級自然保護區”石碑就矗在這汪汪的綠中間。橫嶺湖東起湘江,南抵洞庭圍,西臨益陽、沅江,北接東洞庭湖磊石山,總面積達4.3萬公頃,由24個常年性湖泊和三大片季節性洲土連綴而成。豐水季節里,草甸、湖洲和蘆葦地被水淹沒,與洞庭湖連成一片。慕名而來的游人便在秋后和春天到來,賞花、踏青、攝影、野炊……在水中蟄伏已久的神秘陸島,打開花枝招展的羽翼。那些白色鳥與嘰嘰淺唱的蟲蟲是何時來,又是何時走的呢,誰也不知道。
曾聽父親說過,原來的橫嶺湖濕地除了水域和草甸,間或的幾顆楊柳樹外,全都是蘆柴。怎么望都望不到邊際,怎么砍都砍不盡。父輩們把蘆葦稱為“蘆柴”。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砍回來的“蘆柴”可燒火煮飯,可在漲大水的時候捆起來吊在堤岸邊做“浪把”,更大的用途是用來造紙。當時,橫嶺湖的“蘆柴”是縣里一項重要財政收入。湖洲上駐扎著十幾個蘆葦收割站,砍伐大軍浩浩蕩蕩的進入,運輸船載滿了一船一船運出去。
穿越這片水陸洲,如果有船的話,可以深入橫嶺湖濕地。小徑隱在矮小的植被叢中,逶迤遠去,泥地忽干忽濕,間或的小水凼也因為人跡少至而澄亮若鏡。一行人一直往前走,都想走到叢林的盡頭,看看究竟到了洞庭湖的哪一處,卻差點把身旁的獨特風物忽視。我們驚奇地發現,深秋的橫嶺湖,不僅只有柳樹、蒼耳、艾蒿和野薔薇,隱隱若若的,我們還在艾蒿茂盛的溝渠旁發現了龍珠、紅蓼、鳳眼草……這肥沃的綠野,匯聚了我們所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植物幾百余種。早聞橫嶺湖是一座天然的生物博物館,有很多瀕臨滅絕的、在全球都具有重要意義的物種生活于此。今日得見,果然沒有虛傳。那么,春天的時候,你是否囿于海洋般的草籽花油菜花而忽略了可愛的黑天鵝和江豚呢。頓悟。那么,從容地走吧。灰綠色的叢林在秋陽的斑駁中呼吸吐納,那遍野的綠,隱藏了太多的蓬勃奧秘。這樣的一天,只是人生眾多日子里偶然的一天,也是橫嶺湖濕地千古日歷中普通的一頁,我為這樣的遇見和交織而欣喜。
從踏上橫嶺湖界地,一直到湖洲邊境,自始至終只有這條狹窄的小道。路的左邊有一道高坎,坎下的湖溝名叫九條溝,連通洞庭湖和湘江。據說,九條溝有很多野生魚類。我們快要走到盡頭時,遠遠的走過來一個背魚簍的中年男子,手里握著一根釣竿,靜靜地與我們擦肩而過。目光交集,男子露出一抹歉意的微笑。后來聽駕船的老頭兒說,那正是來九條溝休閑野釣的沅江人,這里離沅江近,交通也很便利,還時常有文藝家過來采風和寫生。意想不到的是,在九條溝邊上的水凼里,同行的女友竟然發現了許多黑色的小蝌蚪。瑟瑟深秋,竟然有蝌蚪!趕緊用手機百度搜索:橫嶺湖區域生活著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虎皮蛙。這是否就是虎皮蛙呢?驚喜之余,我們不由得對這塊土地生出一種敬畏。
原路返回來,已是黃昏。橫嶺湖界碑下的坡坎上,依然有湖土堆疊的印記。走進橫嶺湖,心便被橫嶺湖的往事填滿,沉甸甸的。船緩緩離開湖岸時,我們回眸凝望,憧憬著下一個更美好的春天。駕船老頭坐在黃昏的船頭,那一縷亙古的煙霧飄散在夕陽的金色余暉中,只等渡完我們這班客人,他也該回家吃晚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