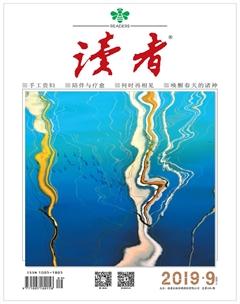陪伴與療愈
黃子懿
青春暫停鍵
張進曾是媒體人,2011年患抑郁癥后,生活重心發生轉變。在一年治療康復后,他寫了本有關抑郁癥診治的書——《渡過》,并開辦公眾號進行科普,幾年下來,聚集了一批讀者和患者。
社群會定期聚集康復者、醫生和咨詢師,舉辦線上家長學堂。張進逐漸發現,很多實際問題還需要面對面解決,尤其是當親子關系需修復、社交恐懼待克服時。青少年抗抑郁的背后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
2018年12月30日,第二期親子營在蘇州開營。本打算招22個家庭,但報名者太多,最后擴大至36個家庭。
李玥在營里既是參與者,又是志愿者。她與張進相識于2017年4月,兒子抑郁癥最嚴重時。
張進說,近年來,抑郁癥有明顯的低齡化趨勢。有研究顯示,中國10歲至24歲的青少年、青年抑郁障礙患病率自2005年至2015年間顯著增加,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高于男,并且隨年齡增加而增高。
那次見面,張進看到李玥的兒子楊玉明,立刻明白他正承受著煎熬。男孩臉色蒼白,雙目無神。他曾翻過天臺,也拿過菜刀,狠狠劃手腕,血流成河。家人需24小時看守。在開營式上,楊玉明說:“你們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
36組家庭中,年齡最小的患者僅9歲半,最大的29歲。營內處處有“雷區”,哪怕是在室內課堂,都時有爭吵、哭泣,或是摔門而去。一天,一行人參觀蘇州絲綢廠,一位女孩突然對媽媽吼叫——廠里養的蠶勾起她不好的回憶:她童年養的蠶都被媽媽扔了。另一位媽媽則在報到時眼淚汪汪地說,在來時的車上,女兒將一杯水潑在她的臉上。
張進說,抑郁癥和壓力有關。壓力下大腦產生應激反應,身體高度警覺,會調動生命潛能應對危機。危機緩解后,大腦會關閉反應,休養生息。一旦壓力持續,應激反應長啟不關,慢性壓力就會讓身體機能耗損,引發抑郁。抑郁癥也有易感群體:敏感、自省、自我要求高、完美主義者等。

“得抑郁癥的孩子,往往都是好孩子。”一位父親感慨道。這里的孩子,大多來自重點中學,原本成績優異。營內帶病幫忙的志愿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學生。然而,這些孩子美好的人生旅途,都被按下了暫停鍵。
最后一根稻草
開營首日是新年跨年夜,一群人參加篝火晚會。楊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獻唱,但左調右調,聲音狀態都無法令他滿意,表演一度中止。“他還是完美主義者,不能接受一絲缺陷。”心理咨詢師鄒峰說。
楊玉明今年22歲,本該念大三的年紀,學籍卻卡在高三。他會吉他彈唱,還能和留學海外的志愿者用日語對話。在重慶那所著名中學,他被錄取到清北班。更早時,他初中就拿了當地數學競賽的獎牌。鄒峰說:“他是個天才。”
母親李玥至今記得兒子高中教室的標語:“從優秀中來,到優秀中去。”那幾乎是重慶最好的班,學習是第一要務,期末考試有末位淘汰。老師說:“要管理好時間,走路要快,上廁所要快,做任何事都要快。”在壓力下,60個學生有的連晚飯都省了,就在教室吃面包。“只有學習,爭分奪秒地學習。”入學后楊玉明對李玥說,同學之間競爭激烈,自己有點吃不消。
首次月考,年級1200多人,楊玉明排100多名,半學期后進步到50多名。按照學校歷年的標準,這已摸到清華、北大的錄取線了。而當他發力備戰期末考試時,肚子開始脹痛。李玥帶他在市區看病,幾番折騰,他落到年級300多名,從清北班降至普通班,頭也時常脹痛起來。
“當時已有癥狀,如果診治對了,或許能躲過這災難。”李玥仍在后悔,未意識到孩子抑郁癥的前兆。“我做生意不差錢,就差信息。”李玥說,高壓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沒抑郁,是因為“人家孩子沒有前面的鋪墊”。
鋪墊,是指楊玉明的初中往事。初一時,楊玉明喜歡班上的一個女生,被傳出后全班起哄。他自尊心強,覺得丟面子,女生亦刻意疏遠,卻與另一名男生走得很近,這讓楊玉明緊張。他當時恰逢青春期臉上長痘,體檢時又被診斷出青光眼,醫生叮囑不要過度用眼,盡量不去黑的地方。“這些都加劇了他的焦慮。”李玥說,兒子中考成績不錯,但似乎命中注定,三人一起考進高中,同在一班。“孩子特別怕他們,有意保持距離,內心很煎熬。”李玥說,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證明給他們看。
楊玉明高二下學期病發崩潰,休學至今。他不會告訴任何外人這些往事。營內上課很少見到他,不多的露面里,他裹著圍巾和手套,戴著黑口罩、套頭帽,像是要將自己保護起來,在室內角落打坐或睡覺。五天里,這樣將自己隔絕起來的孩子不是少數。
生病的家
親子營特設孩子專屬的吐槽大會,家長不能參與。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們之所以被壓垮,與長年累月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在第一期親子營中,一個孩子分享說,有次考試他沒考好,回家后父母看了卷子,就讓他滾,“永遠不要回來”。另一個孩子聽到這兒,說:“你這算好的,我爸媽不僅讓我滾,還扔給我一個枕頭。”
在第二期親子營中,孩子專場相對冷場,他們或低頭緘默,或戴著耳機玩手機,待了一會兒就提前離場。而與孩子們的沉默相比,家長專場則成了一場懺悔。年過不惑的父母,一開口便淚如雨下。一位身材高大的父親說,在女兒成長階段,他做了很多錯事。女兒初中時,他因看不慣她留長發,就抓著女兒的頭發,強行剪斷,“她是那么喜歡長發啊”;還有一次在外旅游,女兒常看手機,他抬手就打了一巴掌,女兒耳穿孔,當夜就送了急診。“這是禽獸干的事,我道歉過多次。”父親哭著說,希望再次公開道歉。
每一個家庭都是一本書。按照一位博士后媽媽的觀察,營內部分家庭呈現出一些共性:父母雙方,有一方過于強勢,另一方相對弱勢甚至缺位。這體現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存于夫妻關系中,導致后者只剩索取、指責和抱怨,“生病的孩子,首先有個生病的家庭”。
開營首日,原生家庭的影響就被提出來討論。
抑郁癥跟后天環境與教育息息相關,也受先天遺傳基因的影響。鄒峰借一個案例提出:代際傳遞的不僅是基因,也有親子恩怨,很多父母將自我成長中的陰影,帶給了下一代。
原生家庭是李玥的痛,傷痕猶在。童年時父母離異,母親帶著她和弟弟經受生活的磨礪,一個人要拉電線、換燈泡、貼壁紙等。母親也這樣要求10歲的李玥。
李玥記恨父母的自私,帶著怨氣結婚。丈夫有過漂亮的女友,但認定李玥更適合做老婆。李玥自卑,從小形成討好型人格。“那時覺得,他從沒愛過我。不離婚就是最低要求。家里一直沒有歡聲笑語,更別說愛的流動。”李玥說,孩子在缺愛的家庭長大,她由此深深自責。
躁郁雙相
營內孩子中,超過一半患雙相障礙。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專家曾指出,近年來中國雙相障礙發病有一個明顯特點:以前高發人群年齡在25歲至40歲,現在至少提前10歲,且整體發病率在迅速上升。與單向抑郁長期的動力缺失相比,雙相有躁期與郁期之分,情緒像是周期性的波動曲線。躁期,患者易出現情緒失調難止、精力高亢、思維奔逸、沖動性的人際交往及購物,以及與現實脫節的妄想乃至幻覺等,這些都被認作是躁狂的表征。抑郁癥的復雜特質性強,雙相尤甚。
發病后,李玥帶著兒子四處求醫。2017年,他在北京被診斷為雙相,但治療藥物產生巨大的副作用,楊玉明頻繁想自殺。最嚴重時,他喪失所有感官知覺。
“狗屁雙相,我從未躁狂過。”楊玉明覺得自己不是雙相。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說清他所患何病。與單向抑郁相比,雙相的確診更為復雜。據2007年一項統計,在歐美國家,雙相患者從首次發病到確診,平均需5年至10年。
“近年來有雙相擴大化的趨勢。”張進說,幾年前很少聽說雙相,但這兩年他遇到的患者,動輒被診斷為雙相,青少年尤甚。雙相又分I型與II型等,更重者則有各種復雜共病交織,診斷用藥都因人而異。為此,一位醫生在營內給出的最多建議是:“好好吃飯、好好睡覺。”
陪 伴
一個有藥學背景的老師指出,抑郁癥成因復雜,有其特定的生理因素,將責任全推給父母并不妥當。他女兒曾是抑郁癥患者,經他陪伴治療后康復。“所有的療愈,都離不開愛。”另一位老師說。
張進也引入了多位康復者分享經驗,強調自救。他說,過去不懂心理學,更強調藥物治療,最近才對抑郁癥的認知形成邏輯閉環:生物、心理和社會。抑郁癥的患病和康復都與這三方面相關。而青少年在社會層面獲得的支持極少,包括家庭。“很多孩子發病,但家長不知道那就是抑郁癥。”
楊玉明休學前,曾服藥好轉過,但為了高考,李玥擅自給兒子停了藥——這是大忌,即使是營內已經康復的講師,大多仍在服藥。此后楊玉明病情加重,近兩年做了24次電休克。
由此,張進想要做“陪伴者計劃”,用社群里的康復者和咨詢師等力量,做有償的一對一長期陪伴式咨詢,以應對抑郁癥診治無標準流程,需更長時間、更多試錯和調整的需求。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支持。開營式上,楊玉明送了張進一句詩:“自以為渡,何以渡人。”被“誤診”為雙相后的生不如死,讓他再也不信任何權威。近一年,他花費約10萬元走訪各地,學習各類自救法。但李玥還是擔心,找人與兒子談。兒子說,電擊“相當于受刑”,他丟了半條命。當年復學為參加高考,他曾遵母囑,用成功學自我激勵,直至全面潰敗。他說,關系好時,他能憶起母愛,但他受不了母親的多次干預。
李玥并非全無收獲,疾病面前,零星的幸福也能讓她感到療愈。這些年,丈夫開始擔起責任,陪兒子去外地治療,在家主動做家務。剛進入2019年,蘇州異常濕冷,李玥忙碌間,丈夫主動送來圍巾。
一天,鄒峰給他們做咨詢,見李玥與丈夫背對而坐,鄒峰說:“你們應該學會牽起彼此的手。”次日,攝影師來拍照,結婚20多年來,李玥的丈夫第一次主動牽起她的手。二人隨后牽手穿行在樹林里,仿佛在一起穿越一座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