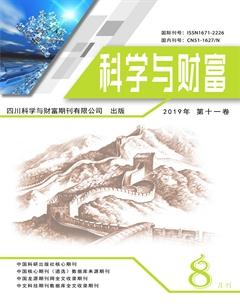公關視域下司法審判中的輿論應對策略
陳文
摘 要: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公民法治意識的不斷提高,輿論監督在網絡中的作用愈發明顯,對司法審判的影響也愈加強大。本文以輿論中最具代表性的網絡輿論為切入點,淺析司法審判與輿論的辯證關系,從而提出近乎合理的在司法審判中的輿論應對策略,以此發揮輿論的積極作用,促進我國司法審判的良性持續發展。
關鍵詞:輿論監督;司法審判;司法獨立
一、輿論分析
讓“于歡案”首次成為公眾的輿論焦點的是《南方周末》
刊登的《刺死辱母者》一文,隨后南方周末微信公眾號推送此篇報道。兩天后,相關話題的信息由5萬條陡然上升超過20萬條。各輿論平臺全面爆發。其中微博約11000條,微信公眾號約26000篇,新聞網站約2700篇,紙媒156篇,其他平臺1390篇。新媒體平臺的介入,使案件博得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據鳳凰網輿情數據監測調查顯示,輿論一邊倒情況明顯,有79.7%的公眾譴責法院審判不公,20.3%的公眾保持中立。[1]
本案輿論爭議的焦點在于法律與人倫道德的沖突,案件的判決結果背離了公眾樸素的道德評價而引發了廣泛熱議。基于道德觀念和倫理觀念,很多公眾認為于歡的做法是情理之中,而將一切歸咎于司法腐敗、警方嚴重失職和司法審判不尊重民意。審判機關在堅守司法中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下,二審法院深入剖析輿論,考慮民意,最終對于歡從輕處罰。而分析近年來的15起典型案件,網絡輿論影響司法的形式呈現多樣化圖景,司法審判對網絡輿論的應對也呈現出司法堅守型、鴕鳥應對型和司法讓步型三種樣態,由此足見輿論對司法審判的影響。[2]
二、司法審判中的輿論應對策略
(一)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堅定獨立行使審判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且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普通民眾往往僅依靠樸素道德觀和基本法律常識就提出自己的輿論態度,其與具有較高法學知識素養和司法實踐經驗的司法裁判者,在思考問題方式、評判案件標準以及認定依據上不同。這就導致了司法審判結果和輿情民意之間的差距,但是這種差距絕不是要挾司法審判甚至凌駕法律之上的利器。面對不同的輿論聲音,司法人員需要理智應對,自覺抵制輿論影響,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空間和環境,理性的看待案件,按照法律,獨立判決,做到所判有法依。
“司法的獨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條件,離開了獨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無從談起”。于歡案二審的改判,究其原因,有輿論監督的作用,本質更是是司法機關自身的糾錯改正。于歡案二審庭審中,檢方提交23份新證據,認為一審判決認定的“于歡捅刺被害人行為不具有正當防衛意義的不法侵害前提,不認為是防衛性質”結果,屬于事實認定不全面,適用法律錯誤。于歡的行為應屬于“具有正當防衛性質,但明顯超出必要性質”的情況,這也是法院改判于歡有期徒刑五年的重要理由。輿論監督更多的落腳在結果,而司法審判重視過程和結果的公正有序,在輿論的監督下,司法審判人員更要提高自身素質,堅守司法獨立。
(二)司法公開,積極應對輿論監督,并創新司法溝通機制。
審判公開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司法同社會公眾開展溝通的前提,更是司法審判自信心的重要表現形式。審判公開首先是信息公開,司法人員將審判情況實事求是的向外界公示,使公眾了解案件及其進展情況,對于案件中不能披露的信息予以說明,避免誤會的發生,表現司法人員的專業性和司法正義,從而提高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于歡案二審庭審過程中,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通過官方微博發布了四十多條圖文并茂、內容詳實的微博,全程直播庭審過程,并在二審判決書中極其詳細地還原案件事實,回應輿論關注的焦點,促成案件的順利結案和司法審判的進一步發展。[4]
此外,應加大對輿論監督的輿情監測,建立輿情檢測研判機制、工作信息發布機制、社會輿論引導機制以及危機輿論應急機制,主動應對輿論信息,積極引導其正確發展。于歡案中,在《南方周末》刊登《刺死辱母者》一文,詳細介紹于歡案前因后果引發熱議后,公檢法系統迅速做出回應,各級人民檢察院派專人調查案件事實真相、搜集證據,對人民群眾存在異議的行為進行調查。傳統媒體和新式媒體也發文回應此案,并以官方說明回應社會爭議焦點,真正做到“答社會所疑,解百姓所惑”。
最后是創新司法溝通機制。思維水平和學識能力的差異導致了公眾對部分案件審判結果的異議,由此引發輿論大潮。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應從容有序的采取有效措施展開溝通,積極引導公眾輿論。例如,法院通過建立網頁、微信公眾號等方法同群眾開展互動,及時解答群眾疑惑、有效疏導群眾情緒,用漫畫等形式將專業術語轉化為通俗易懂的語言等,都是司法機關開展“輿論公關”、讓審判和輿論良性互動的有效方法。
(三)構建司法審判與輿論的良性協商型司法正義。
哈貝馬斯提出“協商型正義”,他認為,法律的核心和關鍵是在公共領域中所形成的對話和協商的過程。實現“協商型正義”就是司法機關與案件利害關系人、公眾輿論與審判結果之間對案件的處理達成一致。基于目前國情,探討協商型司法正義具備一定的風險,但是“協商正義”可以作為一種創新理念,針對特殊的司法審判案件,在條件成熟時適當地引用。因此,在現實司法審判中,司法審判人員在堅持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基礎上,吸收和引進“協商型司法正義”理念的合理因素,從而有利于公正司法的健康發展。[5]
三、結語
綜上所述,信息傳播速度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輿論監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司法機關的工作效率,促進審判結果的公正,但也帶來了影響公信力、干預司法獨立等一系列弊端。探索司法審判與輿論的辯證關系,實質上市探究司法民主、司法公正與社會監督的深層關系。法律無情,司法有情。因此,在司法審判中司法人員應充分考慮社會輿情,合理吸納民意,以法律適用手段為依托,做出公正而合理的判決。
參考文獻:
[1] 康志雄,張宇浩[D].網絡輿論監督與司法審判獨立的沖突權衡研究———以“于歡案”為例.現代商貿工業,2019(13)
[2] 付黎明.司法審判與網絡輿論的博弈——基于15起典型案件的實證分析[N]. 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16)
[3]周華長.淺議網絡時代下輿論監督對司法審判的影響——以于歡案為例[J].法治與社會(司法天地),2018-3(上)
[4] 郭彥軍.司法審判與網絡輿論良性互動探析[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1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