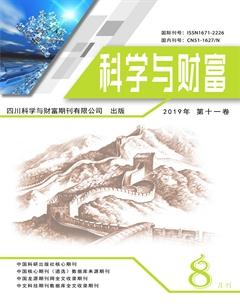論侵害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認定標準
摘 要:信息網絡傳播權控制著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在認定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訴訟中,對被訴行為性質的認定是進行侵權認定的前提條件。縱觀學術界的和司法實務中的各種不同意見,確定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認定標準還是首要問題。本文在厘清何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基礎上,簡要分析了學術界和司法實務中討論較多的幾種認定標準,最后得出了“服務器”標準應為目前認定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中合理選擇、現實選擇的結論。
關鍵詞:信息網絡傳播權;侵害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服務器”標準;
一、問題的提出——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構成要件之解構
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指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傳統的傳播行為只是一種由傳播者“單向”提供作品內容,作為接收者的公眾被動觀看、聆聽的行為方式。其最顯著的特征是非交互性,公眾只能在作品傳播者指定的時間或者在傳播者指定的地點欣賞作品。
構成著作權權利內容的一系列專有權利是著作權法中的核心概念,每一項專有權利都控制著一類行為,換言之,“專有權利”劃定了一個只有著作權人或經其授權的人才能享有的特定領域。那么,受信息網絡傳播權這一專有權利控制的行為就是我們所說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
(一)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是一種交互式傳播行為
不同于傳統的傳播作品行為,一項有效的網絡傳播行為實際上是傳播者和用戶的互動過程,是一種雙向作用的“交互式傳播”。從空間和時間的角度說,作為受眾的用戶掌握著傳播過程的主動權,就是在自己選定的時間、自己選定的地點主動選擇接受這種傳播,簡單地說,就是任何用戶可在任何一臺連接互聯網的智能設備上、在任一時刻點擊下載該作品文件或在線收聽、觀看。以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件共享p2p平臺“百度網盤”為例,首先,作為傳播者的用戶將作品文件上傳到處于聯網狀態的自己的網盤文件夾(實際上為運營平臺統一提供的加密服務器)中;其次,作為傳播者的用戶通過向其他作為使用者用戶分享外部鏈接的方式讓用戶了解該作品文件在百度網盤服務器中的地址。再次,作為使用者的用戶利用網絡瀏覽器登陸自己的賬號或客戶端軟件利用該網絡地址對該作品文件發出訪問請求以獲取其基本信息。最后,百度網盤的服務器響應該訪問請求并提供文件信息,允許作為使用者的用戶將該作品文件儲存到自己的網盤賬戶中,并允許其通過網絡瀏覽器或客戶端軟件進行在線瀏覽查看或者下載瀏覽。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用戶發出掌握著這種傳播的主動權是受限的。也就是說,用戶可以依據自主的意志作出選擇是關鍵,但這種“選擇”也要當然地受到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時間和內容的限制。
(二)以網絡為傳播媒介向用戶提供作品
這里的關鍵詞是“提供”。我國《著作權法》對信息網絡傳播權中“提供”一詞翻譯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中的“making available of”,其強調一種使他人獲得作品的“可能性”,而非他人已經獲得作品的狀態。也就是說這種可能性不要求實際將作品發送至公眾手中,只要將作品“上傳”至或放置于網絡服務器中供網絡用戶下載或瀏覽就構成了對作品的提供,不論是否有用戶實際進行過下載或瀏覽。這也被稱為認定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服務器標準”。目前司法實務中的主流觀點為“服務器標準”,但學術界也對此有很多不同觀點。
具體來說,目前網絡環境中最為典型的交互式網絡傳播行為有三種:
其一、網站經營者直接將數字化作品置于開放的網絡服務器上供用戶在線欣賞或下載。
其二、用戶將數字化作品上傳到開放的網絡服務器上供用戶在線欣賞或下載
其三、用戶將數字化的作品置于P2P文件共享軟件劃定的“共享目錄”或“共享區”之中,使其他網絡用戶能夠搜索并下載被“共享”的作品文件。前文提到的“百度網盤“就是這種情況,每個用戶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共享目錄或對外分享自己共享目錄網頁鏈接,使得其他百度網盤用戶可以將該作品文件儲存到自己的網盤賬戶中進行下載或在線瀏覽。
二、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之認定標準的深層探析
(一)認定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標準之意義
著作權法中專有權利的意義和目的在于控制特定行為。無論該“專有權利”的內容如何,對受該權利控制行為的界定都是法院正確適用該權利的關鍵。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法院對于一種行為是否構成“直接侵權”的判斷,若一種行為根本不在某種專有權利的控制范圍內,則他人實施這一行為不可能對其構成直接侵權,此時只能考察行為人是否在構成間接侵權。具體到信息網絡傳播權這一專有權利,若一行為不在其控制范圍內,那么這一行為不屬于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也就是說界定“網絡傳播行為”是界定相關侵權行為的前提。
(二)認定構成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主要標準之淺析
服務器標準和用戶感知標準在司法實務中爭議較多,前者是指作品信息是否存儲于行為人的“服務器”中,不論該行為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否使得用戶認為作品系由該行為人提供。后者則強調應考慮網絡用戶的感知,如果該行為使得用戶認為被訴內容系由上訴人提供,即應認定上訴人實施了信息網絡傳播行為。該標準通常考慮的是被訴行為的外在表現形式,至于被訴內容是否存儲于上訴人服務器中則在所不論。
服務器標準是一種適用時沒有任何彈性的客觀標準,是純粹從技術角度出發的一種技術性標準。服務器標準之所以能成為主流適用的裁判觀點,主要在于其客觀性特點帶來的實操層面的可操作性。可以說,“服務器標準”與“用戶感知標準”是兩個極端,前者完全依靠技術因素和客觀事實,將服務器標準惟一化和絕對化,后者以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用戶感知標準”作為判斷標準,使行為定性缺乏基本的確定性和穩定性,過于主觀化。
“服務器標準”的優勢包括較高的確定性以及易于舉證,原告只需提供證據證明被告將其作品上傳于對公眾開放的網絡服務器使作品有被公眾獲取的可能性即可。但“服務器標準”在應對手機視頻聚合平臺等隨著IT技術發展而出現的新型平臺時,常常顯得僵化而無力。“用戶感知標準”的實施需要以用戶感知作為判斷基礎,不同用戶的注意程度也不盡相同,如何確保能夠尋找到一個這樣有著一般注意程度的“理性人”來做出公平公正的決斷呢?這樣的認定標準如果離開對個案的裁判,作為普遍性的適用標準似乎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屬于法律性質意義上的標準,從而很難具有說服力。但用戶感知標準對網絡技術的發展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不論行為人利用怎樣繁瑣復雜的網絡傳播技術,只要能夠讓網絡用戶感知到作品的著作權歸屬,我們就可以認定其行為可能構成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服務器標準與用戶感知標準是認定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中的兩個“經典”標準,總體來說,“服務器標準”更有利于網絡服務提供者,而“用戶感知標準”更有利于著作權人。
此外還有實質性替代標準、實質呈現標準、新公眾標準和非商業不明知標準在學術界也有著廣泛討論。
三、“服務器標準”作為現實選擇的合理性
從“服務器標準”出發,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定義是指將作品置于向公眾開放的服務器中的行為。具體來說,著作權法中有關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制決定了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必然是一種對作品的傳輸行為,且該傳輸行為足以使用戶獲得該作品。互聯網環境中,作品以數字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其本質是信息,數字化條件下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典型模式是數字化作品的“上傳—下載—復制—傳播”模式。
(一)服務器標準從客觀層面揭示了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本質特征
1.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是對作品的傳輸行為且該行為足以使用戶獲得作品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十二)項和其來源即WCT第8條中均將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指向對作品的提供行為,且要求該行為足以使用戶獲得作品。在網絡環境下,該傳輸的對象是作品的數據形式,只有對其進行傳輸的行為才有可能使得用戶真正獲得作品。
2.網絡傳輸行為的復雜性:對作品的傳輸行為系指初始上傳作品的行為
互聯網中傳輸信息的技術特性決定了作品信息在網絡中的傳播往往存在著多個獨立的傳播過程,每個獨立的傳播過程均可能包括一系列行為(如傳輸通道的提供、內容的存儲及上傳、緩存、鏈接等),而每一個傳播過程均可以使用戶獲得作品,但各行為之間相互配合共同形成一個單獨的完整的傳播過程。從本質上講,在每一個獨立的信息傳播過程中,必然且僅僅需要存在唯一一個對作品的傳輸行為,該行為將作品的數據形式置于向公眾開放的網絡中,正是因為這一行為的存在才使得公眾可以最終獲得作品,該行為便為初始上傳行為。除初始上傳行為之外的其他行為均非對作品數據形式的直接傳輸行為。
3.任何對作品的初始上傳行為均需以存儲行為為前提
任何初始上傳行為均是對作品的傳輸,而被傳輸的作品必然首先存儲于有形的“存儲介質”中。此處的“服務器”系廣義概念,泛指一切可存儲信息的硬件介質,既包括通常意義上的網站服務器,亦包括個人電腦、手機等現有以及將來可能出現的任何儲存介質。對于“服務器”這一名詞的理解要進行擴大解釋,盡可能寬泛。
綜上所述,根據現有技術,只有將作品上傳到開放的網絡服務器中,才能夠使公眾在網絡中獲取作品。既然“提供作品”是一種客觀行為,那么以高度依賴主觀感受的“用戶感知標準”去認定現實中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并沒有抓住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本質屬性。因此,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應指向的是初始上傳行為,并且任何上傳行為均需以作品的存儲為前提,未被存儲的作品不可能在網絡中傳播,而該存儲介質即為服務器標準中所稱“服務器”,因此,從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定義上講“服務器標準”作為其行為的認定標準最具合理性。
(二)服務器標準符合著作權法中的利益平衡
知識產權法從立法到司法實踐,都面臨著知識產權人合法壟斷與公眾合理需求的矛盾調和問題。一方面,它需要給著作權人以附期限的專有權,以調動著作權人乃至整個社會參與創造性工作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它承載著新知識、新技術傳播的使命,需要為社會公眾保留合理運用的空間。如何構建平衡機制,處理好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對于著作權法是尤其重要的。根據“用戶感知標準”,即使被鏈網站的作品沒有侵犯著作權,深度鏈接行為仍然構成直接侵權,這會使得深度連接這一技術的推廣和使用受到極大的阻礙,進而影響信息流轉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而反觀“服務器標準”,一方面通過明確設鏈者的間接侵權責任,維護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通過適當縮小對深度鏈接的打擊范圍,避免了因過度保護造成的信息獲取障礙,從而平衡了著作權人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
參考文獻:
[1]崔國斌.得形忘意的服務器標準.知識產權[J].2016:8.
[2]王艷芳.論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認定標準.中外法學[J].2017:2.
[3]王遷.論“網絡傳播行為”的界定及其侵權認定.法學[J].2006:5.
作者簡介:
王天昱,1994年12月28日出生,男,漢族,籍貫陜西省漢臺區,現就讀于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2018級經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經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