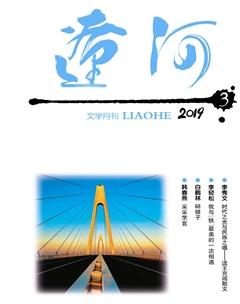黑黢黢的地瓜干兒
楊德君
逛大菜市,我被那些地瓜勾住了眼睛。這沙土地上種出來的地瓜,個頭勻稱,紅艷鮮嫩,干瓤兒,好吃,趕緊掏錢買了一大紙箱,“呼哧呼哧”扛上樓。地瓜,學名紅薯,也叫番薯,在我家鄉遼南,大家都叫它地瓜,而管土豆(馬鈴薯)叫地蛋,在貧窮饑餓的年月,它們可是好東西,鄉民們有順口溜道:“地瓜地蛋,又頂菜又頂飯。丫頭吃成一枝花,小子吃成男子漢。”我自己說是“狐死首丘”情結,是鄉愁使然,妻子說我“土”,是“農民意識”,反正直至現在,我仍然喜歡吃土豆地瓜。
天漸漸冷了,陽臺里溫度太低,妻子打開紙箱,發現有的地瓜長出了黑斑,甚至開始腐爛了,便埋怨我道:“明知道這東西不好放還買這么多!拿屋里來吧,溫度高,幾天就爛了,留在陽臺里還不得像往年一樣凍壞了。
看著妻子無計可施,一臉的嗔怒埋怨,我笑了:“不會的,我來處理。”
我將紙箱搬進來,端來幾大盆清水,把地瓜一股腦地倒進盆里泡上。妻子見狀,不解,追問我要如何處理,我故意賣關子不告訴她,任她在旁邊急得如獼猴抓耳撓腮。我把地瓜洗干凈,上火蒸煮,不一會兒,幾大盆地瓜冒著騰騰熱氣出鍋了。妻子更急了,問我:“你把它們都弄熟了往哪兒放啊?”
我仍然不回答,一邊做出吃的動作,一邊拿出砧板、菜刀,將煮熟的地瓜切成薄片,然后擺放到屜簾上,送進陽臺。妻子嘴一撇,揶揄我說:“我還當有啥高招呢,原來是曬地瓜干兒呀!”
對,就是曬地瓜干兒。記得小時候,秋天收獲完地瓜,奶奶總要把那些被鍬鎬傷了的,被蠐螬、蚯蚓啃咬的,還有那些沒長成的“地瓜毛兒”挑出來,洗干凈煮熟,然后切成片放到窗前的大秫秸簾子上攤曬。秋高氣燥,幾天工夫,地瓜干兒就曬好了,裝進一個大筐里掛到屋檐下,一來那地方避雨通風,地瓜干兒不能返潮變軟,更不能發霉長毛。二來那地方高,又在大人們的眼皮底下,我和弟弟這樣的饞貓絕不敢公然跳到窗臺上去偷吃。
年景好時,地瓜豐收,儲存不過來,有時候也把地瓜生切成片,拿出去曬成生地瓜干兒。這種生曬的地瓜干兒可以磨成面,和玉米面、高粱米面、豆面、小米面摻在一起貼餅子、蒸窩頭、蒸發糕、烙餅,或者搟面條,雖然看上去有些發黑,但味道很好,甜甜的,好吃。
聽奶奶講,當年日本占領東北,成立偽滿洲國,鄉親們沒少偷著給東北抗聯送過地瓜干兒。抗聯也不挑剔,生的熟的都行。不少人還因為這兒進過日本人的大牢,甚至丟掉了性命呢。沒想到這不起眼的地瓜干兒還為抗戰出過力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家仍然過著朝齏暮鹽、啜菽飲水的日子。到了寒冬,生活更加清貧寡淡,糧食不足以讓大人孩子果腹充饑,只好每天喝兩頓稀粥。零食,對于那時的孩子們來說實在是奢侈品。就連處于哺乳期的弟弟妹妹們也沒有面包、餅干等輔助食品,每當他們餓得啼哭不止時,奶奶便塞給他們一塊稍微軟乎一點的地瓜干兒,地瓜干兒被唾液一泡,就有了滋味,弟弟妹妹只顧咂滋味忘記了啼哭。我們這些半大孩子餓得像老鼠上躥下跳、登高上樹,四處尋摸食物,奶奶看著可憐,也會給我們分幾塊。盡管奶奶辭世已經幾十年了,但至今奶奶那充滿憐愛的幽幽目光還在我腦海里清晰可見。
堅硬如石的地瓜干兒,丑陋,黢黑,但卻是好東西,一小塊可以嚼上半天,香甜可口還頂餓。我們小心翼翼地裝進口袋,出去找伙伴們瘋玩去了。有了食物,便有了朋友,地瓜干兒竟然能叫平日里不愿意和我們一起玩的孩子主動親近過來。只要肯施舍一兩塊,那他們就會成為忠實的跟班,和你形影不離,隨你差遣。至于有過牴牾,鬧過別扭的也會因為一兩塊地瓜干而冰釋前嫌,一笑泯恩仇。
那時候稱得上好吃的,只有我們自己栽種和收獲的幾棵向日葵的種籽,媽媽哪天高興了給炒熟了,分撥開,或是犧牲玩耍時間從收割后的豆子地里撿拾來的黃豆粒,在冬夜里可以放到爐蓋上烘熟,再就是冒著挨打的危險鉆進倉房里偷偷敲下來的一小塊兒喂豬的豆粕和花生粕了。至于水果,生產隊分的幾十斤蘋果要留到過年時招待賓客。產于南方的水果只是聽說過,連看都看不到,何況一飽口福了。說來好笑,我十八歲進城讀書,還不認識香蕉、菠蘿呢,柑橘還是因為當兵的姑父來省親才吃過。所以,地瓜干兒就成了彌足珍貴的好東西。
有一次,弟弟和一群半大孩子每人口袋里裝了幾塊地瓜干兒站在避風的墻根下曬太陽,大家擠來擠去,不知誰先發現地上有兩塊地瓜干兒,弟弟說是他掉的,可滿林卻說是他掉的,兩人因此爭執起來,互不相讓,又有幾個孩子摻進來,都聲稱地瓜干兒是自己的,最后動了拳腳,打得一塌糊涂,有的拳頭打到眼眶上,成了烏眼青,有的挨了嘴巴子,腮幫子腫得老高,有的被抓撓成花臉貓,有的頭發被薅掉一大撮,像疤瘌頭。最后好幾家大人都參與了毆斗,要不是大隊民兵趕來平息事態,還不知會鬧到啥地步呢。為此,好幾個家長被村上開了批判會。
我每天放學后,要拿起耙子和草包去田野里摟柴草,為的是晚上能有一個熱炕可以安放我們瘋了一天精疲力竭的身體,驅趕數九隆冬難耐的夜寒。一天下半晌摟柴草回來,早晨灌進肚子里的兩碗稀粥早就隨著幾泡尿撒出去了,加上朔風怒吼,寒氣逼人,更讓人感到饑寒交迫。一大包柴草扛在肩背上猶如一座山,越走越沉重。剛走到村頭的蘋果林,我竟然一頭栽倒在積雪的溝里,把伙伴們嚇壞了,大家圍了過來,有人拉扯我的衣服和胳膊使勁搖晃著,有人大聲地呼喊著我的名字,有人趕忙按壓我的人中穴。大家見我臉色蒼白,滿頭大汗,猜想是餓的,但荒郊野外冰天雪地,到哪找吃的,都急得直搓手,突然,不知道誰從口袋里翻出一塊地瓜干兒來,可把大家樂壞了,七手八腳地把我抬出雪溝,扒開我的嘴巴,將地瓜干兒喂給我。說也怪,不一會兒,我竟慢慢地蘇醒了過來。后來許久,大家一提起來都嘲笑我是饞的。
唉,這不起眼的地瓜干兒,不僅是弟弟妹妹們的“奶片”,是我們交朋結友的“禮物”,是我們消磨時光、消弭饑餓的“寶物”,有時候還是神奇無比的“救命神丹”呢。后來進了城,可以買到的小食品多起來,但土里土氣的地瓜干兒卻讓我難以忘懷,回鄉看望年邁的父母,母親知道我好這一口兒,總會在秋天里曬好,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等我回家時,拿出來給我吃。超市里也有賣地瓜干兒的,顏色、形狀都比我記憶中和母親曬制的好看許多,而且包裝精美華麗,但一放進嘴里,便會知道味道不夠地道,或者說不是記憶中的味道,也不是老母親親手為我曬制的味道。
我放進陽臺里曬的地瓜干兒,與記憶中兒時的地瓜干兒不大一樣,呈現出好看的琥珀色,晶瑩透亮,像一塊塊松香,脫水后糖分得到沉淀和濃縮,咬一口,艮艮的,韌性十足,加上紅薯特有的香味充盈在齒頰之間,十分誘人,我和妻子沒事的時候就吃幾塊,沒多久,屜簾上的地瓜干兒便少了許多。
星期天女兒回家來,妻子抓了一把地瓜干兒神神秘秘地對女兒說:“想不想品嘗一下你爸爸制作的‘楊記特色小食品?”女兒沒反應上來,直愣愣地看著我,問道:“我爸還會制作特色小食品,什么特色?”看女兒不相信,妻子趕緊將一大塊黃澄澄的地瓜干兒塞進她的嘴里。女兒嚇了一跳,扯出來,看了看,才一邊笑著說:“哦,原來是地瓜干兒呀”,一邊放心地重又送進嘴里。然后問我怎么想起做這個了。妻子搶著說道:“你爸爸說了,那是最值得他懷念的兒時美味,帶著故鄉的味道,帶著你太奶奶和你奶奶的乳香。”妻子滿是嘲弄的神色,連說話時還故意拿腔作調。我沒在意她說什么,只是直盯著女兒,本以為吃膩了各式點心和小食品的女兒會對這我所謂的美味流露出不屑,卻不想她滿是艷羨地說:“老爸,你們小時候可真有福氣啊,能夠吃到這么美味好吃的東東,還是綠色食品呢,沒有化肥和農藥殘留,沒有重金屬污染。你曬了多少,一會兒我走時多帶上些。”我愕然不已,嘴巴張得和撲食昆蟲時的蛤蟆差不多一樣大,不知說什么是好。
是啊,沒想到這些土得掉渣的地瓜干兒,在女兒那里卻成了最時髦、最受青睞的環保食品。小時候假如也有餅干、麻花、大白兔奶糖、巧克力、奶油面包,有火腿腸和食品店里琳瑯滿目、色香味俱佳的誘人零食,有水果攤上五光十色的各種水果、干果,我和我的伙伴們誰還會稀罕這灰頭土臉的地瓜干兒呢,誰還會為掉到地上沾滿泥土甚至牛糞的一塊地瓜干兒而不惜和伙伴們打得頭破血流呢?女兒之所以羨慕我們,盛贊地瓜干兒一類的食物,或許是因為她們這一代被蜜罐浸泡得太膩、太久了,正如酒店盛宴上的人們開始青睞野菜、粗糧一樣,無非是尋求調劑口味、刺激味神經罷了。抑或是當下的食品安全形勢太過嚴峻,讓人提及便心生恐慌甚至恐懼,轉而對原生態的、綠色的、環保東西一律懷有敬意。我惟愿是前者。
不管女兒如何,反正我喜歡這家里自制的地瓜干兒,它帶著故鄉泥土味道,帶著祖母和母親的乳香,我迷戀那淡淡的甜,淡淡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