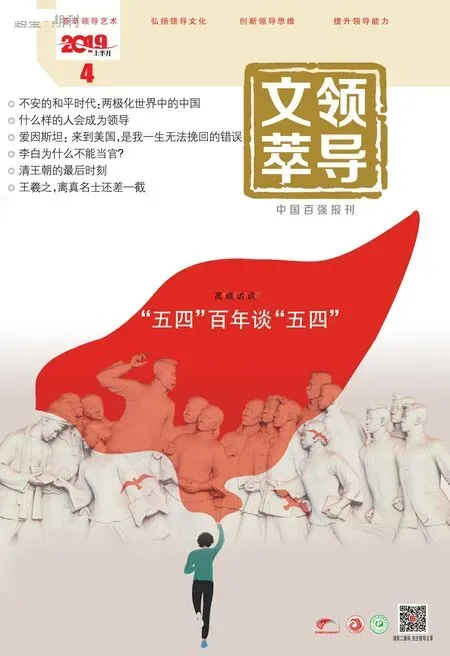懶螞蟻效應
馬薇薇
你是不是經常覺得,付出同樣的辛苦,別人掙得卻比你多?甚至有人真能“躺著”把錢掙了,讓人很不服氣。關于這點,著名幽默作家周腓力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他經過街邊一家服裝店,看到有位老先生靠在店門口的躺椅上優哉游哉地曬太陽。一問才知道,原來這個大大咧咧的“閑人”,就是服裝店老板,而店里忙進忙出的,則是他的老婆跟兩個女兒。作家很羨慕,說:“老先生,您可真有福氣,老婆、孩子都這么能干,您啥都不用做,就可以在這兒曬著太陽享清福。”誰知,老先生聽完,不以為然地搖搖頭,神秘地說:“你覺得我什么都沒做?不對。其實我正在做一件最重要的工作。”作家驚訝地問:“什么工作?”老先生嚴肅地回答:“我在承擔風險。”
這個回答乍看只是玩笑,但是仔細想想,其實也有幾分道理。別看只是一家小小的服裝店,開在哪里,怎樣裝修,進什么貨品,如何擺放,雇什么樣的人,如何管理……稍微一想,就有無數讓人頭疼的細節。所有這些都是選擇,而只要做選擇,就一定要承擔相應的風險。所以,在常見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外,還存在著一種“風險勞動”。
很多領導為了表示自己知人善用,常常會說“用人不疑”。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人總是會變的,人總是有弱點的,哪有真的沒有疑點、值得完全信任的人?既然如此,為什么領導還是經常標榜這句話?道理很簡單,因為領導的職責之一,就是要承擔起察人和用人的責任,認準了一個人,就要充分放權使其得以發揮最大效能。如果半信半疑,想用又不敢擔責,徒增組織人事成本。所以,如果沒有愿賭服輸的魄力,就不適合殺伐決斷的崗位。所謂成大事者不糾結,不能“好謀而無斷”。在不確定的世界做確定的決策,在壓力和焦慮面前保持冷靜,這就是風險勞動者的基本素質。不過,如果你以為風險勞動只是決策者或管理者的事,那就又錯了。有一些看似純體力勞動的職業,其實也有一大部分收入來自風險勞動。比如說,同樣在煤礦工作,下井和不下井的工人,待遇相差極大;同樣是保潔工作,在室內擦玻璃和在室外進行高空作業,收入也大不一樣。這明顯不是由體力勞動的強度決定的,而是由風險勞動的強度決定的。
在企業管理上,對“風險勞動”這個概念還有一個延伸性的應用。如果你整天忙忙碌碌、日程排滿,那反而說明有問題。要讓自己有時間閑下來,要讓一部分人經常能閑下來,去做些看似沒意義卻更具挑戰性的事,才能產生更大的效益。這個現象,叫作“懶螞蟻效應”。螞蟻一直都被看成勤勞的代表,但是北海道大學生物學教授長谷川英佑有不同的看法。他在2002年做了個實驗,將90只螞蟻分成3組,然后觀察它們的日常行為。結果發現,每個小組都有20%的螞蟻其實是不做事的,要么躺著不動,要么就是在巢穴周圍四處閑逛,教授叫它們“懶螞蟻”。這就奇怪了,這么勤勞的生物,怎能容忍一群白吃白喝不干活的廢物?其實,它們的作用只有非常時期才能體現出來。當研究者斷絕了這群螞蟻的食物來源時,那些平常工作起來很勤快的螞蟻立刻陷入混亂,急得團團轉,反倒是那20%的懶螞蟻站了出來,帶領蟻群找到新的食物來源。原來,它們平時的四處游蕩、玩耍,其實是為了偵察和研究。也就是說,螞蟻在億萬年的進化中形成了這樣一個群體智慧:種群要保持一部分“閑逛”的自由,在遇到危機時,才更有可能找到新的出路。
按照現代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的說法,大部分管理者都是“機構的囚徒”。因為公司的每個人都可以隨時來找你,而你也必須應對所有人的需求。這樣一來,你就很容易陷入事務性的繁忙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你變成了“近視眼”,只看到眼前的具體事務,沒時間思考團隊的前進方向。
可是,作為管理者,你要想想,螞蟻的世界那么簡單,尚且需要20%的“懶螞蟻”時刻留意外界變化,人類社會這么復雜,又怎能只考慮眼前的工作?所以德魯克就很直接地說:“一個管理者整天加班還嫌時間不夠用,并非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反而是極大的浪費。”因為管理者最稀缺的資源不是人力,也不是預算,而是時間。不管日常工作多忙,總要給自己留出反省總結和提升的時間,讓自己“閑”下來。這個“閑”不是放空腦子,沉迷于刷劇、玩游戲,而是不帶任何具體目標地琢磨自己手頭上的事。
現代企業管理中也非常重視“懶螞蟻”的貢獻。有些企業會建立完備的戰略規劃和市場分析部門,它們不負責帶來經濟效益,只負責分析市場動向,為企業提供靈敏的嗅覺。還有一些企業,甚至會逼著員工不要太忙,比如谷歌,公司允許員工將自己20%的工作時間用于本職工作之外的項目。就是說,除了公司要你干的活兒,你自己也得去琢磨還能再干點兒啥。而事實證明,這個政策,是谷歌產品創新最重要的來源之一。
總之,掙錢這件事,真的不一定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忙不一定高效,閑也不一定浪費。你覺得別人是在躺著掙錢,其實很有可能只是因為別人選擇了正確的勞動方式。
(摘自《智慧》)